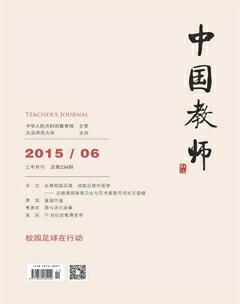21世紀的教育變革
袁麗 李新奇
艾倫?麥克法蘭(Alan Macfarlane) ,英國歷史學家、人類學家,劍橋大學國王學院終身院士,英國皇家歷史學會院士,皇家人類學會院士,英國科學院、歐洲科學院院士。1941年出生于印度,在英國接受教育,先后在牛津大學、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倫敦大學東方和非洲研究學院學習歷史與人類學,獲博士學位。此外,他還是著名的電視節目制作人,在“第四頻道”“世界起飛的那一天”系列節目中擔任專家顧問。其著述頗豐,如《英國個人主義的起源》《現代世界的誕生》等頗具影響力。麥克法蘭教授基于自己的研究經驗,對不同國家的教育問題,包括教育體制、教育價值取向、教育目標等有獨到的觀察與見解。
2014年,受凱風公益基金會的邀請,參加同麥克法蘭教授對話的沙龍活動,在活動期間就教育與教育變革的問題同他展開談話與交流,以訪談錄形式呈現。
中國教師:您對中西方教育體制有一定的觀察和思考,基于這些經驗,您認為當前中西方教育在面對未來時應做出哪些思考?
麥克法蘭:教育應是一個關于猜想的事情,是一個關于我們是否可以為未來世界培育優質青年的實驗。然而,絕大多數的教育制度就像教導士兵如何打贏上一場戰爭的一樣,往往是教師們在自己的舊世界里來培養年輕人,即使那個世界即將“過氣”。但現在,伴隨科技、社會和政治的前所未有的巨大變化,為一個新世界而培育年輕人似乎變得可能。這個新世界需要他們用20年的光景去適應,與我們現在適應的這個時代大相徑庭。我們只能基于近期的趨勢及經驗,才能滿懷憧憬地去想象。這可能影響到我們為青年學生建造學校的趨勢和傾向。在這里,我有幾個初步的想法,關于我在上學期間積累的中西方教育體制的差異,這些想法可能是未來需要的。
首先,從個體競爭力與知識水平到小組團隊合作技能的培養。我的一個工程師和科學家朋友強調在科學領域有一種飛躍——從19世紀早期的個體天才、發明家以及其他人,能夠掌握在他們各自領域,如化學、工程等中取得重大進展所需的基礎知識和技能,到當今獲得進展需要更加復雜和更多的跨領域知識,以至于只有團隊合作才能取得成功。當然,團隊合作已在許多領域和職業中得到體現。例如,陸軍、海軍、工廠以及大學。我日益發覺團隊合作在我的項目中也十分適用。這些項目均需要小組間的密切配合,以實現個人所不能完成的目標。很多對小團隊來說是可行的事情,而對于官員、苦行僧或藝術家來說卻是無法實現的。所以我們極其需要教育年輕人與他人團隊合作,以團隊為單位來開展游戲、運動、音樂和藝術,以及進行探索和問題破解活動。此外,還有小組討論和頭腦風暴、辯論賽和戲劇表演,等等。這些當前在高等教育領域中得以強調的技能,也應在未來的基礎教育中得到發展。
其次,從本地和國內到國際和全球的視野培養。19、20世紀,中國年輕人和其他國家的公民所接受的教育,是基于當地的技能、關系以及知識。英國上層社會由于帝國狀況而有所不同,其有國際化教育,但仍強調本土概念。這個世界正日趨全球化和國際化,大多數的成功人士在進行跨文化工作。他們需要植根于一種文化傳統,需要準備身體和心靈的異途旅行。這是在教育中應傳遞給學生的。這種國際視野和全球視野的培養有三種可能實現的途徑。第一,學校教授一門與人類學相關的學科。人類學致力于通過系統分析和其他國家的文化滲透,從而專注于跨文化理解的技能。這與文化解讀有關,教導我們要尊重他人,還能提供一些幫助我們克服文化差異的方法。第二,通過任何能引起文化沖擊或引發我們重新審視世界觀的活動來獲得系統的文化間的交流。例如,有計劃的海外考察或參觀本國文化中的亞文化。與有國外文化背景的學生、班級或學校結對,采用個人層面如在Facebook上交友和正規結對的方式,例如將各個班級和其他國家學校的班級結對。第三,系統化地進行閱讀、電影賞析、音樂等課程的學習,這些課程的內容來自本土文化之外的文化。
最后,從以書本為依托到視覺媒體學習能力的培養。直到20世紀50年代,最主要的智能通信技術仍書寫文字(或數學符號)。在學校,幾乎所有的教學圍繞閱讀與寫作的學習展開。如今的一切滄海桑田,我們所獲取的關于這個世界的信息,有四分之三源于視覺媒體。電視也好,網絡也罷,抑或是電影,數不勝數。然而,現在幾乎沒有關于如何“讀懂電影”或者制作電影(理解電影的最好方法)的教學提供給孩子。這應得以糾正。因此,應設置解釋視覺影像相關課程,無論是電影、電視或網絡,如優酷等。創作電影的方法,不僅是如何編輯拍攝與把電影放到網絡,更要明白網頁制作方法等。視覺方面的人類學家所需掌握的技能均應得以發展,如制作電影的興趣、攝影、美術、繪畫、設計以及視覺領域的其他溝通技能,包括美術與傳媒基礎歷史等,均應受到鼓勵。
中國教師:您提到教育將經歷變革,那您認為教育變革會體現在哪些方面,有怎樣的特點?
麥克法蘭:就我的觀察和理解,當前的教育變革有這樣的一些特點。
首先,從自上而下的教育到自下而上的教育變革。大多數的教育制度,是加強統治階級的權威以及使可接受的知識代代相傳的產物。傳承智慧或至少傳承一些實用的技能是教育的目的。這種自上而下的模式在當今已不再適用。越來越多的人通過網絡了解天下事,因此,現在所需要的是教授查找、評估和使用信息的技能,不僅是要從書中、文章中學習知識,更重要的是通過聯機數據庫獲得相關內容。在中國山東省可以看到以孩子為中心的用以解決問題的教學方式,那里的教師更像助力者、向導或導師,而不像一個“知識庫”。師范大學大四學生或博士生導師那樣的“知識庫”,我認為就像艦船上的飛行員一樣,派不上用場。
其次,信息技術與其他科學技術的新時代引發教育變革。當前時代和過去相比,其根本變化在于技術移動的迅速,且擁有巨大的影響力。如果我們不能在理解它的基礎上給予控制,我們就會變成它的“奴隸”。因此,我們應教會孩子科技是如何運行的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應用科技。例如,應設置關于社會媒體、電子信函、網絡電話、手機應用、電腦以及其他科技的全方位課程,教會孩子電腦運算、網絡運行的知識,以及科技發展、科技運作和科技控制生活的途徑。此外,也應告訴孩子科技進步的影響。我在《給莉莉的信——關于世界之道》 中所寫的“我們如何來到這個數據時代的”,闡述關于這些內容的全部想法,特別闡述出我們需要維持安靜、完整、平和以及集中注意的時刻,不應因受到科技影響而被席卷一空,使生活支離破碎,而應欣然地去閱讀和散步,擁有遠離機器的一些興趣愛好,有自律,能控制自我對科技的沉迷。
最后,是達成平等的世界的教育變革。世界上的最大變化之一是在不平等的前提下展開的,無論性別、年齡、社會地位或階級,還是高社會流動或消除與生俱來的不平等,其皆為教育核心。年輕人需要學習如何尊重和同情他人,不僅是為了減少差異,更是為了接受其他人可能會比我們懂得更多,但不要奴隸般地跟隨領導或過于敬畏權力。我們需要學著去質疑和挑戰,以一種建設性的和諧方式進行。特別是對性別、年齡、社會階級以及家庭差異的掌控,需要進一步的討論和解決。在這一越來越趨向相對的世界中,沒有絕對理論和真理。這就需要我們探索如何在后現代社會中,理解與掌控已有典范的急速轉變和連珠炮式地涌現出的各種觀念。
中國教師:在這些教育發展與變革中,您認為有沒有特別值得保留與反思的地方?
麥克法蘭:這可能要涉及一些之前的教育內容,主要是指那些基礎技能排序問題。之前有用的教育原理值得一提,如記憶工作(語言、數學、詞匯等)、讀寫技能、語言、歷史和文學、地理、基礎科學等,沒有一樣是要被摒棄的。這花費我們90%的精力去學習的記憶工作,或許應僅占50%。另外的50%應花費在以上所列舉的生活技能,如戲劇、游戲、藝術、音樂、電影、團隊合作等。因此,我認為這個世界使教育愈發富饒,更具趣味,更加實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