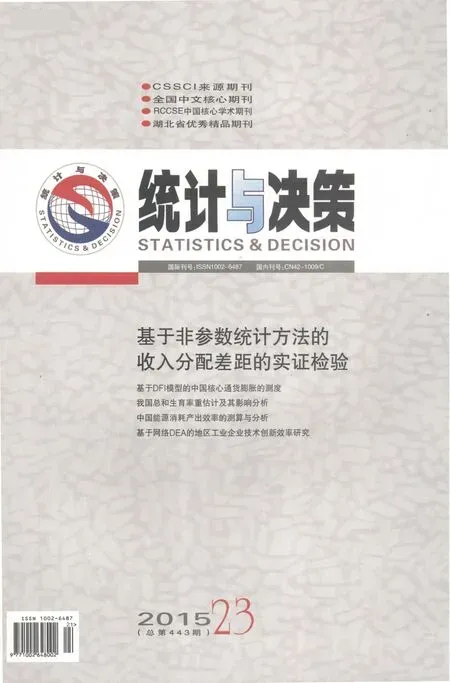產業轉移視角下的教育發展與區域城鎮化差異分析
張曉楠
(西安歐亞學院 高職學院,西安710065)
0 引言
長期以來,教育一直被認為是推動產業發展和城鎮化建設的重要途徑,教育發展所積累的人力資本不僅是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必要條件,更是實現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的基本保證。根據侯冠平、王資博(2013)的研究,以人均受教育年限衡量的教育發展每提高一個百分點,我國的城鎮化水平就提高2個百分點[1]。而產業發展與城鎮化之間的關系更是受到了諸多學者的關注。Krugman(1991)就指出城鎮化特別是城市群和城鎮體系的發展,會有效的凝聚和提升市場的需求,從而為產業升級和產業擴展提供更加廣闊的空間,同時也有利于產業的梯度轉移和經濟中心擴散效應的有效發揮[2],此外,區域產業轉移引發的產業和要素資源的重新布局也成為影響城鎮化的重要因素,蔡昉,王德文(1999)產業的凝聚和擴散可以提高產業內收入和擴大產業間收入的差距,從而吸引更多的要素進入城鎮,使得城鎮的規模不斷擴大,城鎮的體系和功能不斷完善[3]。
但是在城鎮化水平不斷提高的背后,我國不同區域城鎮化的水平和規模卻差距較大,2014年,我國東部、東北、中部和西部四大區域的城鎮化率分別為61.86%、59.60%、47.19%和44.74%,區域城鎮化水平和規模自東向西總體上呈梯度遞減之勢,且區域間差距并未表現出逐漸縮小的趨勢,2005年,東部地區城鎮化率比西部地區高17.34%,到了2014年,兩地區之間仍有17.12%的差距。這就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全新的問題,為什么教育發展在促進城鎮化水平不斷提高的同時卻并沒有縮小區域之間的城鎮化差距。本文就將基于產業轉移的視角分析這一問題產生的根源并提出相應的對策。
1 理論分析與假說提出
區域之間產業發展的不均衡是造成教育發展不能縮小區域城鎮化差異的重要機制,我們可以預期產業在區域之間的轉移將會縮小區域之間的城鎮化差異。首先,伴隨著產業轉移,之前教育發展所培育的遷出人力資本會重新遷回到遷出地,從而彌補產業發展不均衡造成的當地城鎮化損失,我們將其稱為產業轉移的回流效應;其次,產業轉移實現之后,本地教育發展所培育的新增人力資本就會直接選擇在本地就業,這樣就可以直接提高本地的城鎮化水平,我們將其稱為產業轉移的直接增長效應;最后,產業轉移特別是制造業的轉移還會帶動當地第三產業特別是服務業的發展,從而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這就可以吸引更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城鎮,從而提高本地的城鎮化水平,我們將其稱為產業轉移的間接增長效應。正是通過這三種效應,我們可以預期產業轉移可以幫助教育發展在提高總體城鎮化水平的同時不斷縮小地區之間的城鎮化差異。
由此我們提出本文的理論假說:區域之間的產業發展的差距是造成教育不能縮小區域之間城鎮化差距的重要原因,而產業轉移則可以通過回流效應、直接增長效應和間接增長效應來幫助教育發展在提高總體城鎮化水平的同時,縮小各區域之間的城鎮化差異。
2 數據和變量測度
區域之間產業發展水平的差異我們主要從三個角度來探討:產業層次、產業創新能力和產業集聚能力。陳立俊,王克強(2010)指出第三產業尤其是服務業對于城鎮化的促進作用最為明顯,因此我們可以預期,各區域之間的產業層次將存在明顯區別[4]。表1給出了我國四大區域三大產業的結構狀況,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東部地區第一產業比重已經下降到10%以下,第三產業比重不斷上升,而東北、中部、西部地區第一產業比重仍然較大,第二產業比重超過50%,第三產業比重還較小,產業結構升級仍有較大的空間。產業結構升級的差異也影響了產業的創新能力(見表2)。從表2中可以看出,東部地區的創新投入和創新產出在四大區域中占據絕對優勢的地位,新產品開發的效率也較高,其他區域的創新力還有待進一步提升。

表1 我國四大區域產業結構變動情況

表2 2013年我國四大區域創新投入與產出
此外,城鎮化是人口集聚的過程,而人口集聚又以產業的空間集聚為依托,因此產業集聚能力也是影響城鎮化區域差異的重要因素。當前我國東部地區的這些條件相對較為成熟,成為產業集群最為活躍的區域,并通過產業集群帶動了一大批城市的興起和擴張,如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通過產業集聚的帶動成為全國經濟的增長極。其他區域的產業集聚力度相對較弱,從表3中可以看出,我國各產業增加值排名前10位的省份大部分都位于東部地區,表明這些產業發展都呈現向東部地區集聚的趨勢,中部地區第一產業、工業以及住宿和餐飲業有一定的集聚規模,東北地區和西部地區的產業集聚力極弱。

表3 2013年我國四大區域各產業增加值排名前10位的省份個數
上述數據基本驗證了產業發展水平差異是造成教育發展無法縮小區域城鎮化差距的重要因素,因此我們下面主要驗證產業轉移是否能夠縮小教育發展所帶來的區域城鎮化差距。首先,我們需要確定衡量區域產業轉移的指標,根據陳甬軍(2004)和陳浩,郭力(2012)[5,6],我們采用如下公式:

此外,城鎮化指標采用把城鎮人口比重來衡量。同時,由于教育發展也是影響城鎮化差距的重要變量,所以我們在估計模型中將控制教育發展的水平,在具體估計中,本文主要使用每萬人的在校大學生數來衡量該地區教育發展的水平。而對于區位條件、基礎設施建設、政府政策支持等難以量化的因素我們將其作為作為未觀測到的因素μ納入模型。
3 實證結果分析
為了驗證本文的假說,我們以我國四大區域為考察對象,以2003年以來至2013年這11年為考察期,為了確保分析結果的客觀可靠,數據全部依據歷年《中國統計年鑒》的相關數據進行計算。為了使模型的估計結果更加穩健,我們同時使用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為城鎮化水平的代理變量,這是因為正是由于收入在區域上的差別才使得教育發展所培育的人力資本有動力進行跨區域流動。其具體的模型為:
(1)URit=ci+βEDit+αi+μit
(2)URit=ci+β1(IRit)+β2EDit+αi+μit
(3)DPIit=ci+β1(IRit)+β1'(URit)+β2EDit+αi+μit
其中,i=1,2,3,4,分別代表東部、東北、中部、西部四大區域,t=1,2,…,11表示時間,URit表示i地區在t時期的城鎮化率,IRit為區域產業轉移量,DPIit表示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而EDit代表教育發展水平,β是相關變量的估計參數,c是截距項,α為不可觀測的個體固定效應,μit表示隨機誤差項。由于主要考察的是各區域之間差異,不考慮時間對模型的影響,運用eviews6.0對面板數據進行固定效應的回歸分析,可以得到表4的分析結果。

表4 我國產業轉移對區域城鎮化影響的回歸結果
從表4中可以看出,總體回歸結果較好,調整后的可決系數達到了0.9以上,各變量的回歸系數都在5%顯著水平下通過了t檢驗,還得到了各個區域的固定效應截距。對照模型1和模型2,我們可以發現,首先,在不包括產業轉移的情況下,東部地區的截距項為大,而中西部地區的截距項為負,但是在包括產業轉移的情況下,東部地區的截距項變為負,但是中西部地區的截距項變為正,而且前者教育發展的系數估計值更大,這就充分說明了產業轉移能夠扭轉教育發展對于區域城鎮化差距的擴大作用,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我國的區域產業轉移總體上呈現出從東部發達地區向中西部落后地區轉移的態勢,能直接地促進落后地區的產業發展,帶動城鎮化進程。而產業轉移對發達地區的效應主要是為新產業發展提供空間,其對發達地區的城鎮化影響要通過發展新產業來間接實現,發達地區正處于產業結構的轉換期,其經濟效應還有待進一步發揮。二是我國中西部地區的城鎮化水平與東部地區存在著較大的差距,產業轉移帶來的各類要素的注入、人口回流、城市群發展等可以為教育發展促進城鎮化水平的提高提供更為廣闊的空間,據測算,到2020年中西部地區大學生就業比重占總就業的比重將提高10~15個百分點,就業總量將增長3200萬人左右,從而可以大量吸收教育發展所培養的人力資本,更重要的是,相對于具有較高知識水平的高等教育勞動力,具有良好職業技能的熟練勞動力和具有優秀身體素質的農業勞動力在此輪產業轉移中會獲得更多的就業機會和就業崗位,產業轉移帶來的勞動力回流是一個必然趨勢,而由此帶來的城鎮化發展空間也是不可估量的,在此背景下,相對于東部地區發展較為落后的中西部地區城鎮化也必將迎來快速發展的黃金期,而在相關的政策設計方面,我們也可以發現中央政府對于中西部地區推進城鎮化的重視,在新近規劃的21個城市化主體功能區中,就有超過15個位于我國中西部地區,再加上東部地區城市發展規劃中“騰籠換鳥”的產業升級計劃,使得我國中西部地區一方面成為“舊鳥”的新棲息地,另一方面也成為未來城鎮化的主要增長點,這一切都意味著我國中西部地區的城鎮化在未來還有至少20%的提升空間,而其前提則是傳統產業的區域轉移以及由此帶來的資本、勞動力和其他各類生產要素的回流與積累[7];其次,結合模型2和模型3,我們可以發現,無論是對城鎮化還是對城鎮居民收入,中部地區的截距項都大于西部地區,這就說明產業轉移對于中部地區的促進作用要大于西部地區,結合本文的邏輯,我們認為這主要是因為西部地區的教育水平較為落后,使得產業轉移的效果難以充分發揮;最后,對照模型1、2和模型3,我們可以發現教育發展與產業轉移對于城鎮居民收入的促進作用要大于對城鎮化的促進作用,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我國目前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現象,教育發展和產業轉移對城鎮居民收入的促進作用要大于其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吸收作用,因此不利于城鄉收入差距的縮小。此外,對表4的估計結果而言,產業轉移量(IR)的回歸系數都是正的,城鎮化率對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回歸系數也是正的,表明產業轉移對提高我國城鎮居民收入水平和區域城鎮化率有積極的促進作用,也驗證了產業轉移和區域城鎮化互動機制效應在我國近年來的區域產業結構調整和城鎮化進程中得到了較好的發揮,產業轉移確實可以通過增加就業引導勞動力向城鎮集聚,提高城鎮化率。
4 結論與建議
本文基于產業轉移的視角系統分析了教育發展影響區域城鎮化差異的機制和對策。研究發現,由于各區域之間產業發展水平的差異導致了教育發展在提高總體城鎮化水平的同時未能縮小區域之間城鎮化發展的差距。而產業轉移則可以通過回流效應、直接增長效應和間接增長效應來幫助教育發展縮小區域之間的城鎮化發展差距。進一步的研究發現,各區域之間在產業層次、產業創新能力和產業集聚能力上均存在顯著差異,而且產業轉移對于東部地區城鎮化的效應為負,但是卻能顯著促進中西部地區城鎮化水平的提高,因此我們可以通過產業轉移能扭轉教育發展與區域城鎮化差距之間的關系,從而有效縮小區域經濟發展的差距。根據本文的分析,我們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1)積極推進產城人融合發展,構建新型城鎮化體系。
(2)重視制度創新,深化產業分工與合作。
(3)突出產業發展的重點和特色,因地制宜地推進區域城鎮化發展。
(4)重視教育資源的分配均衡,更好發揮產業轉移對區域城鎮化的促進作用。
[1]侯冠平,王資博.經濟增長、教育發展、城鎮化與城鄉收入差距關系研究[J],商業時代,2013(2).
[2]Krugman.Increasing Return and Economic Geography[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1,(2).
[3]蔡昉,王德文.中國經濟增長可持續性與勞動貢獻[J].經濟研究,1999,(10).
[4]陳立俊,王克強.中國城市化發展與產業結構關系的實證分析[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0,(s1).
[5]陳甬軍,陳愛貞.城鎮化與產業區域轉移[J].當代經濟研究,2004,(12).
[6]陳浩,郭力,“雙轉移”趨勢與城鎮化模式轉型[J].城市問題,2012,(2).
[7]張倪,未來中西部地區將是加快城鎮化建設的主戰場[N].中國經濟時報,2014-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