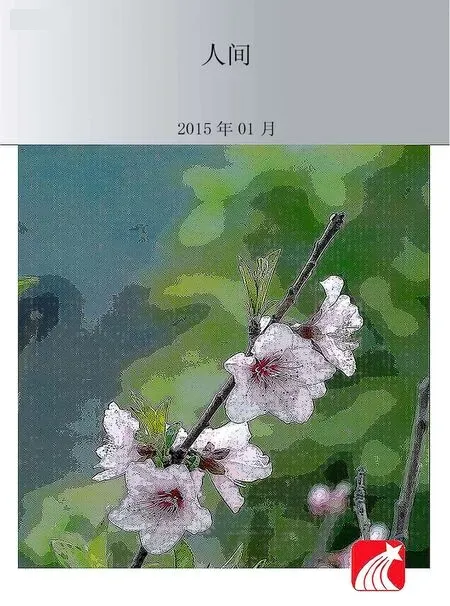漫談文學創作的基本源泉
宜春職業技術學院 潘睿琦
漫談文學創作的基本源泉
宜春職業技術學院 潘睿琦

生活、情感、信仰是每個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三大要素,也必然與社會生活的形象反映-文學創作息息相關。它們在文學創作中扮演著“水之源,木之本”的重要角色,深刻影響著文學創作的產生發展。
文學創作;源泉;社會生活;情感;信仰
一、社會生活是文學創作的基礎源頭
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人民生活中本來存在著文學藝術原料的礦藏,這是自然形態的東西,是粗糙的東西,但也是最生動、最豐富、最基本的東西;在這點上說,它們使一切文學藝術相形見細,它們是一切文學藝術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
小至口頭言語,廣至詩詞歌賦,故事佳作……文學“上得了廳堂,下得了廚房”,活躍在眾人日常生活的各個角落,如影隨形著。三言兩語便可達意,信筆涂鴉便可傳情。文學創作似乎高于生活,卻本是源于生活。生活的酸甜苦辣,跌宕起伏給予了其創作空間,卻也正是因為文學創作讓人們對世間的事事物物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為人們提供了表達與宣泄的處所,希望與幻想巢窩。哲學上有所言:“意識是客觀事物在人腦中的反映。”然而運用與此,客觀事物便是指日常生活,意識則是形成文學創作的中流砥柱……
人各式各樣的行為脫離不開一個重要的因素,便是滿足生活需求,無論是物質需求還是精神需求。文學創作同樣如此。文學是有根的,起源于以勞動為中心的人類生存活動。古往今來,從協調勞動、傳遞信息、記載歷史到教化民眾、思想啟迪、愉悅身心……文學創作的產生無一不是伴隨著歷史和生活的大河應運而生。文學創作本就是社會生活的一分子,他們生活的大環境——經濟、政治、文化、生態等各個方面都是創作來源的要素之一,而無論是素材、題材,還是語言、情節、風土人情、民俗風俗,無一不是社會生活所提供的。體驗生活、參與生活、再現生活是作家的職業使然。他們在文學創作中的敘述、描寫、抒情都是基于對生活的觀察、體驗與感受。或是描畫民情,或是情感流露,或是總結歷史,或是針砭現實,即便是勾畫未來,天馬行空的也離不開對社會生活的積淀與人生感悟。沒有蕭紅在東北沃土上的童年生活,就沒有《呼蘭河傳》中對那片土地上的人民、風情、民俗的細膩描畫;沒有余華對待生活苦難的態度也就沒有《活著》中福貴在大起大落大喜大悲中的從容與堅強;沒有美國二戰之后的“墮落的一代”也就不會出現塞林格在《麥田里的守望者》中傾注的希望……古今中外一切優秀的文學作品,都是作家所處的社會生活成功的藝術再現。
二、情感是文學創作的源動力
文學的創作過程其實是一個情感表現的過程,是作家對其既往情感的再度體驗。所以說情感是文學創作的魂,是文學創作的動力。中國古代人很早就意識到情感在文學創作中的作用,《毛詩序》:“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文賦》:“詩緣情而綺靡。”《文心雕龍》中也多次談到情感在創作中的重要作用,如“情以物遷,辭以情發”等。唐代偉大詩人白居易說“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在他看來,詩歌諸要素莫不先乎“情”。無論是詩歌、散文、小說,抑或是戲劇,作者的情感活動始終貫穿于藝術形象塑造的整個過程之中。所以說情感是文學創作的源動力。
文學創作來源于社會生活,更準確的說是來源于作家置身于社會生活中所產生的情感體驗。文學創作是生活的一面鏡子,更是表達、宣泄、傳遞情感的出口。它是作者在人生軌跡中喜怒哀樂的文字載體,是作者剖析內心世界表達所思所想所感所悟的重要通道,它將作者對于萬事萬物的體味感受以文字的形式表現出來,在傳遞情感時同時傳遞著情感的力量。
沒有真情實感的文學是死的,被賦予了情感的文學才是鮮活的,是值得人們去品味去感悟去欣賞的。不同的作家在生活中的波瀾曲折,百轉千回造成了他們對事事物物或喜或悲或平淡或激昂或從容或激進的各種情感,而正是有所情感,才有了表達的需要與創作的動力。
如同正因有屈原對國家楚王的熱愛,對遭受打壓的憤懣,對奸臣小人的痛恨才有了《離騷》這一傳唱世代的佳作;又如因有舒婷對愛情的堅貞執著的態度,才有了《致橡樹》中“根緊握在地下,葉相觸在云里”的情感表達;而奧威爾的人生體味,對極權主義的痛恨,對自由的向往與追求,才應運而生了《1984》這本讓我們習得了自由精神的著作……所有的文學創作莫不是初始于一種情感的累積及沖動,就像列夫.托爾斯泰曾說:“在自己心中喚起曾經一度體驗過的感情,用動作、線條、色彩、聲音以及言辭所表達的形象來傳達出這種感情,使別人也能同樣體驗到這同樣的感情。這就是藝術活動。”而用言辭所表達的藝術活動便是文學創作。
三、信仰是文學創作的重要來源
與動物相比,人最大的不同在于擁有智慧,會使用工具。而作為精神性極強的人,當我們散落在世界各個角落的時候,我們則更需要有一個共同的東西來作為我們的源頭,作為我們所謂的故土。而這一故土,回頭看是傳統,仰頭望則是信仰。因此,西方有了上帝,有了伊甸園,有了亞當與夏娃,有了許許多多的神話傳說來開天辟地;而東方也一樣,盤古劃開了天與地的界限,女媧造出了世間眾生……而這一切神話故事的誕生,這些關于世界起源、人類出現、國家形成……的說法都便離不開人類在精神世界中歸屬的需要,依靠的需要。落葉歸根,事事物物都牽連著一個“故土概念”,也就是我們所謂的信仰。
眾所周知,脫離了精神世界,便只是行尸走肉。而精神世界的需要,正給予了文學創作誕生的一大理由。如同西漢時期,“君權神授,天人合一”主張的提出,以及董仲舒對于儒家思想的鼓吹、宣揚乃至文學創作,莫不是來源于當時對儒家思想的極力推崇,對這一封建傳統思想的高度崇拜。而在西方,《圣經》、《古蘭經》等諸多著作的產生,也莫不是因為人類心靈世界的需要,對一種普世性,權威性,甚至是超自然性力量的追崇。即便是如同“文化大革命”的文學悲劇時期,文學依然是 “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輔佐者,是樹立高度集中共產主義信仰之下的最佳輔佐人。
文學對精神世界的描述及渲染作用是極強的,它透視人們的心靈世界,抒發人們的思想感情,并力圖通過文學的力量感染眾生,啟迪眾生,與他人達到思想上的共鳴與融合。因而,文學在表情達意的基礎上,便承載了更深的內涵——引導價值取向。一個社會所推崇的精神方向,價值取向或多或少影響著文學創作的思想與內涵。而在信仰的層面,一個地域一個國度的信仰更是其相關文學需要推崇及弘揚的對象。如果說宗教為信仰提供了皈依的處所,那么,文學便是支撐起信仰的頂梁柱。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伊斯蘭教……東方的佛教、印度教……在這些宗教殿堂的光輝照耀下,文學就是那一顆顆相對于宗教世界更加理性更加真實的璀璨明珠,為許許多多人找到了前進的方向,光明的所在。即便是中國社會無神主義的“共產主義信仰”,文學依舊是跑在前頭,喊著,叫著,在社會價值取向的山頭上插上信仰的大旗……
文學為人們勾畫著理想世界,填補人們精神的空虛,滿足人們對于信仰的追求,引導人們向曙光進發,為那單薄的信仰點綴上點點星光。
I04
A
:1671-864X(2015)01-0010-01
潘睿琦(1992.12-),女,宜春職業技術學院教師,研究方向:漢語言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