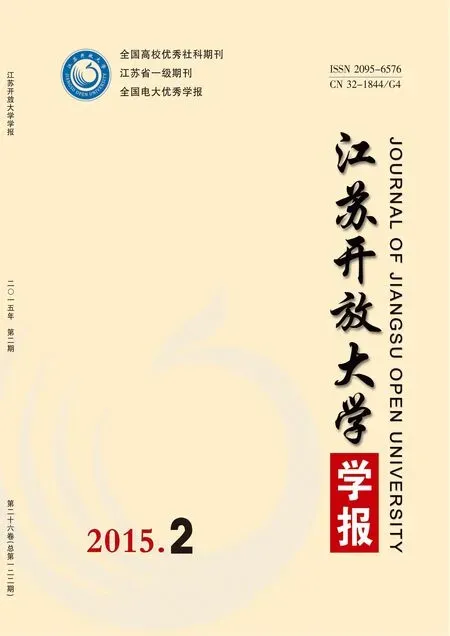反諷敘事、德里達與《雪》之論爭
張 虎
反諷敘事、德里達與《雪》之論爭
張 虎
奧爾罕·帕慕克的《雪》是一部備受爭議的小說,曾引起本土民族主義者的集體焚燒。這其中是否摻雜著一些誤讀的部分?實際上,《雪》的內容可以分成前景、背景兩部分,前景是一元論敘事,背景是互文性敘事,兩者構成一種文本反諷效果。這種反諷在土耳其本土、東西方文化沖突、形而上哲學三個層面展開。最終,通過反思人與雪花的生命構成,帕慕克表征了一種德里達式的延異詩學——“每個人都有一片代表自己生命的雪花”。
帕慕克;《雪》;反諷;延異
《雪》是帕慕克小說中頗富爭議的一部。庫利說,它表現的是土耳其的文化沖突,是亨廷頓之“無所適從”國家的圖解[1];凱茲曼、瑪舍爾·伯曼等人說,《雪》和帕慕克的其他小說一樣,寄托著帕慕克一以貫之的文化雜合理想*Mary Jo Kietzman,"Speaking 'to All Hunmanity': Renaissance Drama in Orhan Pamuk's Snow." Texas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3(2010): 324-353; Marshall Berman,"Orhan Pamuk and Modernist Liberalism." Dissent 1(2009): 113-118.。2005年,這部小說被一些本土極端民族主義者、伊斯蘭分子在街上集體焚燒,據說它涉及了伊斯蘭主義者的濫交、對軍隊和“土耳其之父”的侮辱。那么,這部小說到底追尋探索了什么?帕慕克說,它是“對幸福的一種呼喚”[2]156,“帶上你的女孩,遠走高飛”[2]156。但是,小說的主人公卡并沒有帶走心上人伊佩珂,反而于四年后在德國被槍殺。本文認為,這些問題都與帕慕克在小說中所使用的反諷藝術手法有關,這種手法表現在:在前景中,人物表達出一種一元論思想,呈二元對立趨勢;在背景中,人物、建筑、文本材料具有一種互文性,圖解了德里達的“延異”概念;二者相互映照,展現為一種反諷效果,而且這種效果在三個維度上展開,即土耳其本土、東西方文化沖突、形而上哲學層面。這三個維度通過“同”與“異”的辯證關系相互平行,最終使《雪》成為帕慕克系列小說中反諷效果最突出的一部。庫利的沖突論、文化雜合詮釋分別屬于這種反諷手法的前景與背景部分,對伊斯蘭主義者與軍隊的“侮辱”則是對含蓄性反諷手段的一種過激反應。
一、反諷:土耳其的“同”與“異”
世俗與宗教的矛盾是帕慕克一以貫之的一個創作主題。從《杰夫代特先生和他的兒子們》《寂靜的房子》開始,土耳其世俗化進程與伊斯蘭文化之根的交鋒就存在著。在《白色城堡》中,是霍加與威尼斯學者的博弈;在《新人生》中,是妙醫師與“大陰謀”的對抗;在《我的名字叫紅》中,是細密畫與透視畫的沖突;在《伊斯坦布爾——記憶與城市》中,是清真寺、禮拜堂與金融大廈、現代別墅的角斗。在《雪》中,這種沖突表現為伊斯蘭主義領袖神藍與阿塔圖爾克的扮演者蘇納伊的武力斗爭,導致一場軍事政變和幾十人死亡、上百人受傷。之所以沖突,正如帕慕克所說,是因為雙方兼持一種二元對立的一元論思想。[3]369神藍說:“我就是這么認為的。只有一個西方,只有一種西方的觀點。我們代表另一種觀點”[4]228,“歐洲不是我的未來,我這輩子到現在為止,從沒想過要模仿他們……”[4]271蘇納伊則認為,西方是土耳其唯一的未來,他把宗教分子稱作“反動派們、鮮廉寡恥之徒”[4]155和“伸向共和國、自由和光明的黑手”[4]155,他對卡說:“安拉問題不是一個思想與信仰問題,而要把它當作一個完完全全的生活問題才對”。[4]200也就是說,伊斯蘭不是穆斯林的精神信仰,而是政治伊斯蘭、極端宗教分子的一個代碼。這是一種非此即彼的邏輯。
在文本中,具有這種思維習慣的人有很多,包括宗教學校的學生、軍人、商販、教師以及眾多卡爾斯人。例如,奈吉普給卡講過一個無神論者的故事:一個宗教學校的校長,原是一個虔誠穆斯林,一天,在一個伊斯坦布爾摩天大廈的電梯中,被一個陌生人手中的一本書引誘為無神論者,于是,他開始“猥褻學校里的可愛小學生,想方設法與他們的母親獨處在一起,偷他所嫉妒的一位老師的錢”[4]82,咒罵先知,宣稱真主是不存在的,講話時夾雜大量法蘭克詞語,穿上歐洲品牌西服,蔑視起了所有的人……最后,整個學校都混亂不堪了。面對這一幕,校長痛苦萬分。所以,他再次回到了電梯中,又一次見到了陌生人,結果被對方一刀刺死——這即是無神論者的下場。奈吉普的朋友法澤爾也問卡:“您是無神論者嗎?如果您是無神論者的話,您會想要自殺嗎?”[4]85卡迪菲的同學韓黛說:“就算摘掉頭巾,我相信我也不會成為那種讓男人們爭風吃醋的女人,不會成為那種沉溺于淫欲的女人。”[4]123言下之意是,無神論者時時刻刻想要自殺,不戴頭巾的女人是騷貨、妓女。
與此相對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相似,或曰同一性。這與小說中的一元論前景構成一組反諷關系,即人人聲稱自己是穆斯林或現代文明者,認為自己與別人是不同的,卻對眾人之間的相似性熟視無睹。例如,卡認為奈吉普與他相通,是他童年時期的一個投影。奈吉普說:“我理解你,你就是我的未來。現在,從你的眼神與目光中我看到:你在我身上看到自己年輕時的影子,所以你很喜歡我。”[4]135卡答道:“那么你現在就是20年前的我嗎?”[4]135而且奈吉普同詩人卡一樣,也想成為一位作家,并寫了半部科幻小說。奈吉普同法澤爾也一樣,他們“非常相愛”[4]107,“比小說中寫得還要親近”[4]108,不管相隔多遠,“都知道彼此在做什么”[4]108。如此一來,卡、奈吉普、法澤爾三人是三位一體的,只不過奈吉普與法澤爾是在“同一時間想著同一件事情”[4]135,和卡則有一段“時間間隔”[4]135。這一點更體現在帕慕克對這三人的命名上,Ka、Necip、Fazil實是一個人的名字,即20世紀土耳其著名戲劇家、詩人奈吉普·法茲爾·凱薩庫勒克(Necip Fazil KisaKürek),他主辦的雜志《大東方》文中也提到過。
再如伊佩珂、卡迪菲與美琳達。伊佩珂在準備隨卡離開卡爾斯時,帶了一件黑色天鵝絨禮服、絲綢披肩和一件藍色毛衣。卡迪菲(Kadife)在土語中意為天鵝絨,是頭巾(黑色)女孩的代表,伊佩珂(I·pek)意為絲綢,兩人都曾與神藍(Blue)有過曖昧關系。卡發現,卡迪菲和她姐姐伊佩珂一樣有一雙棕色的眼睛。卡迪菲回憶起小時候的她,一直以美麗、善良的姐姐為榜樣,一天,生物老師對卡迪菲訓斥道:“‘你那聰明的姐姐’也遲到了嗎……因為喜歡你姐姐我才讓你進的教室。”[4]223美琳達是情色片的女主角,卡在德國時經常看她主演的電影,帕慕克(隱含作者)說,“她的一雙大眼睛、結實的身體和舉止都很像伊佩珂。”[4]260而且卡實際上同時愛上了美琳達與伊佩珂,一個在影像中,一個在現實生活中。
其實,即使神藍與蘇納伊也不是完全對立的,他們的一個巨大共同點就是,二人都是瘸子,每天晚上,他們和卡爾斯的每一個人一樣,喜歡端一杯濃茶,在電視上觀看肥皂劇《瑪麗安娜》。由此看來,異中有同,同中亦有異。這種辯證關系更為鮮明地體現在另一種背景敘事中,即同一個人在不同的人生階段是不同的人。如伊佩珂前夫穆赫塔爾曾是一個心高氣傲的詩人,之后放棄創作,經營起了父親的店鋪,這是他曾不屑一顧的生活,他先是信仰馬克思主義,后又希望自己的孩子是一個西化的人,最后又回歸了宗教,成了繁榮黨的主席;卡大學時的同學曾一同抵抗世俗政府,后來有的成了恐怖分子,有的成了政府職員,有的流亡他鄉、杳無音訊;卡迪菲曾是一位西化、現代的伊斯坦布爾女郎,如今成了頭巾女孩的領袖;神藍曾是一位“無神論的左派”[4]321,之后成了一位電子工程師,最后成了一名伊斯蘭恐怖分子的頭目;蘇納伊的確扮演過阿塔圖爾克,發動過政變,但他只是一個演員,他之前甚至還要飾演先知穆罕默德。在《黑書》中,帕慕克寫道:“沒有人永遠是自己,一個人存在就是做別人。”[5]413這或許是對《雪》之背景詩學的一個精準概括與詮釋。
當然,帕慕克諷刺的對象是土耳其的現實政治,而不僅僅是小說中的人物。19世紀以來,在這片橫跨歐亞的土地上,西方似乎一直是西方,與伊斯蘭、東方毫無瓜葛,基督徒是“哈爾比”“卡菲爾”,歐洲是戰爭園地,在阿塔圖爾克的世俗化改革中,伊斯蘭文化是最大的敵人,清真寺、頭巾與阿拉伯字母是恥辱與野蠻的象征,而對現代伊斯蘭主義者來說,西方是索多瑪與蛾摩拉,本土世俗精英是非法執政者,是歐洲的奴隸、穆斯林的叛徒。這種二元對立的世界觀導致土耳其一百多年來在東西方問題上猶豫不決、沖突不斷:梅內門事件、少數族裔叛亂、伊斯蘭百科全書事件、1960年至1980年的三次軍事政變、2010年的“大錘”政變計劃、數不清的游行示威與起義,正如帕慕克所說:“我要指出他們的做法要么屬于東方,要么屬于西方,要么就是民族主義。我在批評一元論的世界觀。”[3]369然而,這些一元論者為什么和神藍、蘇納伊一樣對于異與同的辯證法淡然、漠視呢?他們何時才能發現一個人的存在就是“做別人”呢?
二、文化沖突與互文詩學
在《雪》中,帕慕克所書寫的不僅是土耳其境內的沖突問題,也是全球性的東、西文化沖突問題,如9·11、塔利班武裝、海灣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巴以沖突等,將這兩者連接在一起的是卡的旅居身份和卡爾斯亞細亞旅館的一次秘密會議。
卡的故鄉是伊斯坦布爾,13年前因一篇文章被迫流亡德國法蘭克福,多年后,他又回到了卡爾斯調查頭巾自殺事件,尋找大學時的同學伊佩珂。小說《雪》的第29節“我的遺憾——在法蘭克福”和第41節“每個人都有一片雪花——遺失的綠色筆記本”從隱含作者帕慕克的角度細致描寫了卡在法蘭克福的生活。通過卡的腳步,土耳其的問題與全球性文化沖突問題聯系在了一起,而且卡在法蘭克福始終處于邊緣地位。另一個更緊密地將全球與土耳其連在一起的是亞細亞旅館會議。蘇納伊發動軍事政變后,神藍發起了一次秘密會議,地點在亞細亞旅館,與會者有伊斯蘭分子、世俗主義者、庫爾德族裔、穆斯林婦女、民主人士等卡爾斯各界人士,他們共同聲討政變事件,號稱要在一家德國報紙《法蘭克福評論報》上發表一份聲明,其中一人甚至說這份聲明就應叫作《關于卡爾斯發生的事情致全人類的聲明》。 在會議中,人們展開熱烈爭辯,頻繁提及、論述東西方文化的關系:“一個西方人,當他遇到一個窮國的人,他的心里本能地就會產生歧視……西方人還會認為,這個人也許滿腦子都是那些害得他們國家貧窮的胡思亂想”[4]276;“我們永遠不要成為歐洲人”[4]277;“他們代表全人類,而我們代表穆斯林”[4]279;“你呀,不知道我們都見過什么樣的歐洲女人……”[4]280這次會議形象地展示了伊斯蘭人在西方面前的獨特文化心理,也含蓄述及了東方主義問題,是對該問題的一次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復調探索。
面對這種范圍更廣的文化沖突,帕慕克設置了一層更為含蓄秘密的反諷敘事,即在人物、情節與文本材料上不斷向外延伸,在互文之路上實現東西文化的跨越。卡的孤獨與邊緣身份讓人想起K——卡夫卡《城堡》中的主人公,在土語中,Ka與K發音相同,《城堡》與《雪》一樣下著一場沒完沒了、掩蓋埋葬一切的雪,卡和K一樣沉默寡言,一樣來到一個陌生之地,一樣肩負著一種似是而非的任務,一樣被本地人拒千里之外,一樣經歷過一段動人又奇怪的愛情,一樣不理解這里所發生的一切,一樣無辜地死于異鄉。因此,格林姆說:“《雪》與《城堡》之間存在一種沉默的伴侶關系”[6]1,并在《帕慕克的非東方——在〈雪〉中重現卡夫卡的〈城堡〉》一文中對二者進行了周詳比較與分析。這是人物角色上的互文。再如,戲中戲是小說《雪》的中心內容與情節,一部戲名為《祖國還是頭巾?》,一部戲名為《卡爾斯的悲劇》。第一部戲劇講述的是:一個穆斯林女子脫掉黑袍與頭巾,在舞臺中央一把火燒之,之后被野蠻笨拙的宗教狂抓住、折磨,最后,凱末爾總統出現,拯救了女子,懲罰了宗教狂。這是劇內情節,同時這也是一次軍事政變。劇外的情節是舞臺上站滿一排士兵,他們舉起步槍,向觀眾席中放槍,隨后就是持續三天的革命。《卡爾斯的悲劇》講的是:頭巾女孩卡迪菲在觀眾面前勇敢痛苦地扔掉了頭巾,之后一槍打死了扮演阿塔圖爾克的蘇納伊,實現了個人的復仇。
這兩部戲劇,包括小說《雪》在內,大致取材于不同時代、文化背景中的三個劇本。首先,《雪》的情節內容大致取自貝斯卡特(Cevat Fehmi Bakut)的戲劇《冰雪消融之前》(Buzlar??zülmeden),在《雪》的第22節,帕慕克提及了這一戲劇。它講述了這樣一件奇聞:一群瘋子從一家精神病院逃出來,來到了一個小鎮上,此時,大雪來襲,道路封堵,瘋子利用這次機會,在三天內占領了這座小鎮,之后,他們通過各種舉措解決了小鎮上的全部問題,如把地主的土地分給窮人,向有錢人征稅,以修建鐵路與公共設施,慢慢地,窮人們開始擁護、尊敬富人。所謂“冰雪消融之前”指的是瘋子們必須在雪化前完成一切改革、解決小鎮上的所有問題。最后,雪化了,小鎮居民獲得了幸福的生活,瘋子們被重新抓回瘋人院。這則戲劇首演于20世紀五六十年代,諷刺的是當時土耳其當局與政府的無能。
《祖國還是頭巾?》應源自于納米克·凱末爾的愛國劇《祖國還是斯里斯特》。該劇首演于1873年,講述的是一個名為喆克伊的女子,為了報效祖國,女扮男裝參加了保衛斯里斯特的戰斗,最終與戀人伊斯萊姆·貝結合的故事。這部戲劇在當時受到觀眾的熱烈歡迎,也首次在帝國時代對“祖國”(Vatan)這一概念作了精彩詮釋與演繹。可惜,不久后,納米克·凱末爾就被蘇丹放逐,1888年病逝塞浦路斯。但在帕慕克的《祖國還是頭巾?》中,女子不是穿上男兵的盔甲,而是脫掉了黑色的長袍,一把火燒掉了這個代表著“中世紀黑暗的破布”[4]108,她追求的是個人的自由,國家與人民成了她的敵人,而非為之犧牲的對象。
《卡爾斯的悲劇》模仿自托馬斯·基德的《西班牙悲劇》或莎士比亞的《哈姆萊特》,皆采用了一種打破藝術與現實的復仇戲劇形式,并且在《雪》的第36、37節,帕慕克兩次提及了《西班牙悲劇》。《西班牙悲劇》的故事梗概是:西班牙國王的侄子巴爾薩澤因情仇殺死了波琳比莉亞的戀人安德烈亞,之后又與葡萄牙王子殺死了與波琳比莉亞相戀的霍拉旭。為了替子復仇,霍拉旭的父親赫羅尼莫與波琳比莉亞設計了一出戲中戲。這出戲講述的是一個土耳其皇帝看上了一位騎士的妻子潘西達,為了滿足個人情欲,他派人殺死了騎士,潘西達為替夫報仇,殺死了皇帝,最后自盡。在這出“戲中戲”中,赫羅尼莫教唆波琳比莉亞、巴爾薩澤與洛倫佐分別扮演這三個角色,最后,在巴爾薩澤與波琳比莉亞舉行婚禮的前一天,殺死了謀害霍拉旭的兩個兇手。在《哈姆萊特》中,以戲復仇的雙方變成了哈姆萊特與叔父克勞迪斯。在《雪》中,不論是蘇納伊的政變還是卡迪菲的復仇,采用的都是這樣一種假戲真做的藝術手法。美國學者凱茲門曾細致深入地比較、闡釋過這一問題,將《雪》稱之為“卡爾斯版的《西班牙悲劇》”[7]325。帕慕克雜合東、西文化的創作無疑是對亞細亞旅館會議中之激烈爭辯的一種巨大嘲諷與顛覆。
三、帕慕克的“延異”詩學
既然帕慕克在《雪》的背景敘事中利用了各種手法反諷其前景部分,那么,他是否在該文本中提出了什么思想或哲學主張?在第24節“我,卡——六角形的雪花”中,帕慕克寫到了卡讀過的一本百科全書,在該書的第4冊封底上有一幅圖像:一位母親和躺在她鼓起來的肚子里就像睡在一只雞蛋里一樣的嬰兒。旁邊的注解是,從嬰兒到長大成人,每增長一歲、一個月,嬰兒的體質、骨骼與心理都會發生較大的變化,每一歲的“他”、每一個月的嬰兒幾乎都是不同的人,但是,從他漫長的一生來看,他又有著太多的共同點,是同一個人。后來,卡再次讀到這一頁時,它被人撕掉竊走了。這一頁是讀者們潛入《雪》深層主題的一個缺口。
德里達的“延異”(differance)概念與百科全書中的這幅圖像是相通的。所謂“延異”是指理解一個事物或符號,不僅需要理解該物的過去,也需預測它的未來,每一個物或符號都存在于一個更大、更永恒的物之鏈條或系統中。因此,過去還有過去,未來還有未來,對當下之物的理解與把握成為一種永恒性的延遲:“延異是指,在釋義過程中,每一個元素必須是‘在場’的,在當下存在。然而,每一個元素不僅與自己關聯,亦與他者關聯。過去是一種元素,目前它仍對當下影響,保持著一些痕跡。可實際上,它已被自己的未來,也即未來的印跡所解構。因此,這一釋義的追溯與過去、未來皆相關。我們所謂的存在,以它不是什么、絕對不是什么來完成,但過去與未來也是一種不斷被修正的存在。”[8]142-143這是德里達在《演講與現象》中對延異做出的詳細解釋。在延異這一概念中,物的同與異具有一種辯證關系,即所有的事物都是一種當下的存在,存在于一種特定的時空中,在這一層面上,物與物可以是相異的,但如果將過去、未來,也即其他時空納入進來,不同的物只是一個范圍更廣、更大的物之鏈條或體系的一個部分、一個點,不同的物實際上屬于同一個更大的“物”。這即是帕慕克在《雪》甚至所有小說的背景敘事中所傳達的一種形而上哲理。
那么,這一哲理在《雪》中表現在哪些地方呢?《雪》的氣候背景是雪,漫天飄灑的雪花,這一片片雪花幾乎是一模一樣的,白色的,呈六角星狀結構,但“每一片雪花都具有其特有的六角形結構”[4]214。它們是同,也是異。在文本中,帕慕克有時也逆向表述這一哲理。例如,在第32節,帕慕克呈現了一種好萊塢式的聚焦:先看到“慢慢轉動的地球”[4]284,鏡頭慢慢拉近,看到一個國家——土耳其,再拉近一些,是馬爾馬拉海、黑海,然后是伊斯坦布爾……“掛著的衣服、塔麥克罐頭廣告”[4]284……卡之房間的窗戶……在桌邊寫東西的卡,最后縮焦到卡筆下的文字:“憑著我所作的詩,我將被載入世界史冊: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尼尚坦石,詩人尼嘠爾大街16/8號,詩人卡。”[4]284在這一聚焦的每一個層面,都有人與卡相似、相同。另外,《雪》中對建筑的描繪也彌漫著這樣一種延異意味,即同一幢建筑里曾住著不同的人,被用作不同的場所或地點:卡住的卡爾帕拉斯旅館曾住過被沙皇流放的大學教授、做水牛生意的亞美尼亞商人、希臘的孤兒們;卡爾斯的警察局曾是一個亞美尼亞富人的別墅,后來又成了一家俄國人的醫院;蘇納伊關押宗教學生的牢房有上百年歷史,它曾是亞美尼亞基金會籌建的一座醫院,20世紀40年代時,這里又成了國立高中,60年代時,“許多卡爾斯年輕人成為馬克思主義者,與西方為敵,他們童年時就是在這兒喝下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送來的強力酸奶”。[4]180
在人物上,卡是將這一詩學貫徹到底的一個角色。卡是將《雪》之前景與背景連接在一起的樞紐,他置身于一元論的對立與沖突中,不斷受到迫害與排擠;同時,他也是第一個發現并向讀者一一展示雪花、建筑與空間中之延異特征的人物形象。首先,卡自己在言與行中是一個糅合容納一切異質的人,他與世俗精英蘇納伊交心,也與伊斯蘭主義分子神藍合作,他是一個世俗的布爾喬亞,后來又漸漸開始信奉安拉,他說自己“想成為一個西方人,也想成為一個安拉的信仰者”[4]142。因此,蘇納伊說他是一個“思想在歐洲、心系宗教狂、腦子一片混亂的詩人”[4]206。其實,卡所擁有的不是“混亂”的腦子,而是一顆同情每一個人的心,這種能力被帕慕克視作“人類最偉大的力量”[3]236。詩人這一身份更足見卡不是一個無知者,而是一個孤獨者甚至是先知。因為在土耳其文化中,詩人是一種極為神圣的職業,安德烈在《奧斯曼詩歌》中說:“詩歌,尤其是抒情詩,在奧斯曼文化中極為流行、十分重要,具有豐富的蘊義,這一切不可能被當代的西方人所理解……多少年來,奧斯曼詩人寫下成千上萬首詩歌,而且幾乎每一個人都夢想著成為一位詩人,不論是統治者還是農夫,宗教學者、浪子抑或酒鬼。”[9]4帕慕克也曾一針見血地指出過《雪》中卡的神圣身份:“在本國,成為一位詩人意味著成為一個知識分子,一個啟蒙者,一個文化修養較高的人,一個富于力量的人。”[2]161如果從這一角度出發,帕慕克所要表達的哲理與詩學就鮮明亮麗了。
同時,這種詩學甚至體現在與卡相關的所有地理空間中。卡的故鄉在伊斯坦布爾——一座東西方文明雜陳、交匯的古都,如今,他來到卡爾斯。卡爾斯的歷史脈絡是這樣的:奧斯曼帝國時期,這里是一個多民族聚居地,生活在這里的有亞美尼亞人、波斯人、庫爾德人、希臘人、格魯吉亞人、切爾卡西亞人,1878年,這里被俄羅斯人占領,沙皇亞歷山大三世與他的情人在這里幽會、一起狩獵,后來,這里一度落入英國人的手中,甚至一度成了一個獨立的國家。1920年,土耳其軍隊再度進駐這里,他們接受了城市的俄羅斯風格,定居于此。卡也曾流亡法蘭克福,他在那里的居住地也是一個文化雜交地域,那里有土耳其的果蔬店、烤肉店、法蘭克福圖書館、意大利咖啡館、坐滿了南斯拉夫工人的冷飲店和庫爾德人開的糖果店……至此,帕慕克在《雪》中所埋藏的延異地圖已經躍然紙上。
回到小說一開始漸漸從天上降下的大片雪花,讓人不禁想到:“一片小小的雪花其實圖解了每一個人一生的精神歷程。”[4]376卡說:“雪花從結晶到落地化為水,平均需要8至10分鐘時間,除了風、嚴寒和云的高度外,還有太多的因素影響到雪花的成形”[4]375-376,人又何嘗不是如此呢?所以,帕慕克在《雪》中詩意地寫道:“每個人都有一片代表自己生命的雪花。”[4]376
然而,四年后的一個午夜,卡卻在法蘭克福的大街上被一個伊斯蘭恐怖分子槍殺。這是藝術對現實的又一次尖銳抨擊與聲討。
帕慕克自稱為東西方文化的橋梁,在《雪》的反諷敘事中,人的身份、地理空間、文化、物的本質體現為“同”和延異,而東方主義、文明沖突論、凱末爾世俗主義、原教旨主義等邏各斯中心主義思維定式則被解構,最終被還原成卡爾斯那場紛紛揚揚的雪。也即,這反諷夾雜著深深的哀傷與呼愁。這哀傷其實也是土耳其文化的一部分,作為奧斯曼帝國——人類歷史上最輝煌、龐大的伊斯蘭帝國——的后裔,它如今沒落、“無所適從”,又不甘處于世界的邊緣。而在橫跨歐亞的博斯普魯斯大橋邊寫作的帕慕克卻獲得了一種俯視東西方的世界性眼光,這目光、視力最終也成為他一生的寫作理想和主題:“每個人都有時是東方人,有時是西方人,實際上,永遠是兩者的結合。”[3]370
[1] David N. Coury."Torn Country": Turkey and the West in Orhan Pamuk's Snow[J]. Critique,2009(4): 340-349.
[2] Michael Mcgaha. Autobiographies of Orhan Pamuk: The Writer in His Novels[M]. Salt Lake City: The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2008.
[3] Orhan Pamuk. Other Colors:Essays and a Story[M]. Trans. Maureen Freely. New York: Alfred A.Knopf,2007.
[4] Orhan Pamuk. Snow[M]. Trans.Maureen Freely.New York: Alfred A. Knopf,2005.
[5] Orhan Pamuk. The Black Book[M]. Trans. Maureen Freely,New York: Vintage Books,2006.
[6] David J. Gramling. Pamuk's Dis-orient: Reassembling Kafka's Castle in Snow[J]. Transit,2007 (1): 1-20.
[7] Mary Jo Kietzman. Speaking "to All Hunmanity": Renaissance Drama in Orhan Pamuk's Snow[J]. Texas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2010 (3): 324-353.
[8] Jacques Derrida. Speech and Phenomena and Other Essays on Husserl's Theory of Signs[M]. Trans. David B. Allison.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73.
[9] Walter G. Andrew ed. Ottoman Lyric Poetry: An Anthology[M].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97.
責任編輯 虞曉駿
The Narrative of Irony,Derrida and the Debate aboutSnow
ZHANGHu/JiangsuNormalUniversity
Snowby Orhan Pamuk is a controversial novel and had once been collectively burned by Turkish nationalists. Does it mix with any misreading? Actually,Snow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arts of foreground and background. The narrative of the foreground is monism,while the background is intertextuality. These two aspects form a textual effect of irony,which spreads on three aspects as Turkey,the cultural clash between East and West,and metaphysics. Finally,Pamuk represents a differance poetics of Derrida by reflecting the life compositions of human and snowflake- "everyone has his own snowflake".
Pamuk;Snow; irony; differance
I106.4
A
2095-6576(2015)02-0059-06
2014-07-12
張虎,江蘇師范大學文學院講師,文學博士,主要從事土耳其文學研究。(frodo2006@163.com)
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帕慕克與蘇菲神秘主義思想研究”(13CWW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