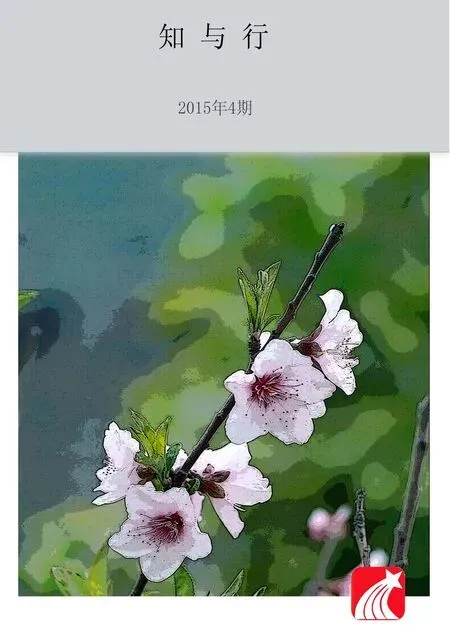論馬克思政治自由觀的“共同體-個體”互構范式
施曉花,王 萍
(1.金陵科技學院 思想政治理論教學部,南京 210000; 2.空軍工程大學 理學院社會科學部,西安 710000)
?

論馬克思政治自由觀的“共同體-個體”互構范式
施曉花1,王萍2
(1.金陵科技學院 思想政治理論教學部,南京 210000; 2.空軍工程大學 理學院社會科學部,西安 710000)
[摘要]在馬克思政治哲學的語境中,“共同體”“個體”“社會”“個人”是一系列相互對應并且及其重要的范疇。馬克思從語義學與政治學的雙重角度出發,揭示了“共同體”與“社會”“個體”與“個人”的差異,同時形成了以“共同體-個體”互構范式為基礎的馬克思政治哲學體系。“共同體-個體”互構范式體現了主體尺度和客體內容、個人發展與社會發展的辯證統一。馬克思的政治自由觀以“共同體-個體”互構范式為平臺,呼喚人的主體性,闡明人的“共同體”屬性和共同體的有機性。“共同體-個體”互構范式既使得馬克思的政治自由觀呈現出一種獨特性,又充分體現了馬克思政治自由觀鮮明的政治立場和價值訴求;既是深刻理解和總體把握馬克思主義精要的一個嶄新視角,也對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具有重要意義:尤其是改進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彰顯公民和黨員的主體地位;健全公民政治參與制度;強化公民社會的建設,使政治民主化由上而下的推進轉為上下的雙向建構和良性互動,為中國特色政治發展提供新的路徑導向。
[關鍵詞]馬克思;政治自由;共同體;個體;社會;個人;互構
在馬克思政治哲學的語境中,“共同體”與“個體”是一對相互對應并且及其重要的范疇。馬克思從語義學與政治學的雙重角度出發,揭示了“共同體”(或者稱之為聯合體、共同存在物)與“社會”“個體”與“個人”的差異,形成了以“共同體-個體”互構范式為基礎的馬克思政治哲學體系。馬克思的政治自由觀以“共同體-個體”互構范式為基礎,充分展現了政治自由思想的有機性和生命力。“共同體-個體”互構范式既使得馬克思的政治自由觀呈現出一種獨特性,又充分體現了馬克思政治自由觀的鮮明立場和價值訴求;既是深刻理解和總體把握馬克思政治思想精要的一個嶄新視角,也對突破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瓶頸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 “共同體”“社會”“個體”“個人”在馬克思政治哲學語境中的差異性解讀
馬克思對諸多概念的甄別和分疏不僅體現了他治學態度的嚴謹,而且還體現了他對以往一切舊哲學范疇下的歷史觀的揚棄,這種“有意”的分離和當時德國社會充斥著思辨哲學與偽哲學的氛圍密不可分。馬克思說:“他們在幻想、觀念、教條和想象的存在物的枷鎖下日漸萎靡消沉,我們要把他們從中解放出來。”[1]3
馬克思的“共同體”有三個方面值得關注:其一,馬克思的“共同體”并非過去的“共同體”。因此,馬克思指出:過去的共同體“對于被統治階級來說,它不僅是完全虛幻的共同體,而且是新的桎梏”[1]63。其二,馬克思強調共同體與共產主義緊密相連,這既說明了共同體存在的條件性,同時也說明了共同體的政治理想和價值訴求。“在真正的共同體條件下,各個人在自己的聯合中并通過這種聯合獲得自己的自由。”[2]共同體是共產主義的共同體,共產主義意味著國家和階級的消亡,因此,共同體超越了私有制條件下虛假共同體的階級性,具有普遍性和無階級性特征。其三,馬克思的共同體關注“普遍”的人的生存和發展,探究“一般”的人的基本生存方式,回答在何種程度上,什么樣的共同體才能夠使人從一種生存狀態轉向本體上的存在狀態(自由的生活),以實現人的自由和全面的發展。
那么,在馬克思的政治哲學語境中,“共同體”是否就是“社會”?顯然不是[1]3。馬克思熟知國民經濟學家們對于“社會”概念的理解和用法,因此,馬克思強調:“在國民經濟學家看來,社會是市民社會,在這里任何個人都是各種需要的整體,并且就人人互為手段而言,個人只為別人而存在,別人也為他而存在。”[3]134因此,在馬克思看來,“社會”只有在社會學語境中強調“社會形態”這一范疇時,才具有普遍意義。在政治學語境中,社會被賦予了和真實共同體相對立的貶義色彩。一言以蔽之,在馬克思看來,“真實共同體”又聯又合,而“社會”和“虛假共同體”以利益為紐帶,要么聯而不合,要么合而不聯。
馬克思對“個體”與“個人”概念的區分,在思維方法上和其對“共同體”與“社會”概念的甄別大同小異。馬克思對于“個體”(或者說單個人)這一概念的使用是與“類”或者與“共同體”抑或與普遍意義上的“社會”、總體等概念相對應,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馬克思使用“個體”這個概念是不僅要強調個體的社會性——“個體是社會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現,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現這種直接形式,也是社會生活的表現和確證”[3]85。更重要的是強調個體聯合的重要性——“以一種全面的方式,作為一個總體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質”[3]85。
同樣地,馬克思揚棄了德國古典哲學的遺產,指出了“有個性的個人”和“偶然的個人”之間的差別,“不是概念上的差別,而是歷史事實”[1]67。在德國古典哲學中,“個人”這一概念已被用來明晰地指具有“自我意識”的個人。在馬克思政治哲學的語境中,“個人”既是指在市民社會中感性的、個體的、直接存在的人,也是指在政治國家中“抽象的人”“人為的人”“法人”。同時,市民社會中存在的個人比在政治國家中存在的個人更為具體、現實,并且構成后者賴以存在的基礎。而不論是市民社會中的“個人”,還是政治國家中的“個人”,實質上都不過是一種“階級個體”——“他們不是作為個人而是作為階級的成員處于這種共同關系中”[1]66。
如此,馬克思通過對一系列概念的分離與揚棄,逐步形成了其“共同體-個體”互構范式的雛形,這個范式既體現了馬克思和包括德國古典哲學在內的一切舊哲學劃清界限、批判舊世界、建設新世界的巨大決心,也成為其呼喚無產階級革命主動性、構筑無產階級自身解放的強大的思想武器。
二、“共同體—個體”互構范式的理論品質
為了進一步批判德國哲學從“天國降到人間”的思維范式,以及德國的“哲學英雄們”令人啼笑皆非的思想兜售,馬克思的“共同體—個體”互構范式以 “人間升到天國”的考察方法、追求主體尺度與客體內容、個體發展與共同體發展的辯證統一展示其科學性以及強大的生命力。
(一) 追求主體尺度與客體內容的辯證統一
主體是自然性與社會性的統一,是內容和形式的統一。政治主體以自身的內在尺度作為衡量標準對主客體間的關系進行理性反思、現實創造與理想追求。客體內容,是指作為政治主體在社會實踐中的對象化存在物,政治客體不能離開合乎政治主體內在尺度的客觀標準產生、形成、發展的必備內容。政治客體的發展若合乎政治主體的內在尺度,則具備對政治主體的正價值,反之,政治客體若背離政治主體的內在尺度,則必將成為政治主體所揚棄的對象。馬克思的“共同體”力圖擺脫異化的政治共同體的制約,實現個體的真正自由——也就是對人的本質的全面占有。馬克思用“魚”和“被污染了的水”的關系比喻人與“本質”的分離:魚的“本質”是它的“存在”,即水。河魚的本質是河水。但是,一旦這條河歸工業支配,一旦它被染料和其他廢料污染,河里有輪船行駛,一旦河水被引入只要簡單把水排出去就能使魚失去生存環境的水渠,這條河的水就不再是魚的“本質”,對魚來說它將不再是適合生存的環境了[1]42。可見,只有當對象對人來說成為人的對象或者說成為對象性的人的時候,人才能實現對自身本質的占有。因此,追求主體尺度和客體內容的辯證統一無疑成為馬克思構建真實共同體的應有范式。
馬克思的“共同體”既飽含著對個體的生命、自由、財產、尊嚴等政治價值的維護,也蘊含著對共同體的民主、平等、法治、正義等政治價值的追求。馬克思維護的“個體”主要是指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被資本主義經濟、政治體制排斥的廣大勞動人民。對弱勢群體利益的維護以及對人之本真狀態的追求成為馬克思揚棄作為資產階級利益工具存在的“虛假共同體”的最有力的武器。同時,“互構”一詞充分體現共同體與個體的同生共存,相互作用。共同體是人的本質全面展開的平臺,個體對自身權利的合理訴求和合法擴張必將不斷推進共同體的發展,使得人以“人的形式”成為“人的本質”。
(二)追求個體發展與共同體發展的辯證統一
任何個體,同樣也是“類”存在物,“類主體”一方面追求“類利益”和“類價值”, 類主體間存在著一定的趨同性;另一方面,不同主體的異質性決定了利益和價值之間具有沖突性,這種沖突如果得不到有效協約,可能會導致個體間的分化,加速個體的原子化和共同體的碎片化。
事實上,在馬克思看來,共同體的“虛假”與“真實”的本質區別在于這些共同體是否將生活于其中的個人的自由發展作為價值訴求,組成這個共同體的個人是否能自由地發揮主體性。從這個層面看,馬克思指出私有制條件下共同體的虛偽性在于他維護的是統治階級的利益,廣大勞動者則只有在“自由被埋葬的那一天,在牧羊人的帶領下,才能與自由為伍”[4]3。在“虛假共同體”中,利己主義縱橫天下,獨領風騷。正如德國古典哲學家費爾巴哈指出:“沒有這種利己主義,人簡直不能夠生活,因為我要生活,我就必須不斷吸取有利于我的東西,而把有害于我的東西排出身體以外。”[5]551因此,必然導致“每個人不是把他人看作自己自由的實現,而是看作自己自由的限制”。“計算”和“算計”成為個體發展的本能,個體發展與共同體發展無論如何都存在著不可協調的矛盾。
馬克思建立共同體的最終目標是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自由發展”是指每個人的發展不屈從于外在目的,不屈從于強加給他的任何活動和條件;人的發展能為個人所駕馭,個人可以根據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從事多方面的活動和發展多方面的能力[6]369。“全面發展”主要是指人的勞動活動和能力的全面發展、人的社會關系的全面發展,也就是人的本質的全面豐富和展開,是對人的本質的全面占有。[7]29-30馬克思認為,共產主義社會是“個人的獨創的和自由的發展不再是一句空話的唯一社會”,“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通過社會生產,不僅可能保證一切社會成員有富足的物質生活,還能保證他們的體力和智力獲得充分的自由的發展和運用。這是人類最美好的理想,也是科學共產主義的真諦。可見,“真實共同體”成為現實個體的“詩意棲居”。人只有生活在這種真實共同體中,才能實現“雙腳站立”,成為合乎人性的人。
三、馬克思政治自由觀的“共同體—個體”互構意蘊
馬克思的政治自由觀以其 “共同體”—“個體”互構范式為平臺,強調人的“共同體”屬性,呼喚人的“主體性”,闡明共同體的有機性,并由此指出實現政治自由歸根到底取決于處于共同體中的能動的人,共同體以“人對人本質的全面占有”形成共同體的器官,創造著具有豐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覺的人。
(一)強調個體的“共同性”屬性。在馬克思的政治思想中,反復強調人的“共同體屬性”。筆者認為,“共同體屬性”和“社會屬性”在馬克思的政治范疇中是有區分的。這種區分不同于“共同體”與“社會”的區分。馬克思強調“共同體屬性”,一方面強調階級斗爭中個體聯合的重要性,為后來風起云涌的工人運動作理論準備;另一方面,強調共同體的正能量——“只有在共同體中才能有個人自由”[1]63。這說明了共同體對于個體的重要性,沒有共同體,就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個體,當然也不可能有屬于個體的政治自由。個體只有在共同體中,才能煥發出生機與活力,才能實現政治自由。馬克思強調“社會屬性”,則主要用以和德國古典哲學中“孤立的、抽象的人”決裂。
(二)呼喚個體的“主體性”。個體主體性是推進政治自由最基礎、最革命、最能動的因素。馬克思將對個體主體性的呼喚投射到對德國社會現實的無情批判中,馬克思指出:“應當讓受現實壓迫的人意識到壓迫,從而使現實的壓迫更加沉重;應當公開恥辱,從而使恥辱更加恥辱”,“為了激起人民的勇氣,必須使他們對自己大吃一驚。”[4]5因此,馬克思大聲疾呼:“向德國制度開火,一定要開火!”“批判不是頭腦的激情,而是激情的頭腦。它不是解剖刀,而是武器。”[4]4
(三)闡明共同體的有機性。“共同體”的有機性在于它的整體性。這種整體性賦予了共同體新的屬性,擯棄了資本主義社會逐漸形成的原子化個人以及由此造成的社會的分層和斷裂。
共同體在“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的社會理想的旗幟下,自覺形成了與之相符的政治使命感和責任感,同時共同體賦予了個體諸如自由、平等、幸福、尊嚴等符合人性需求的正價值。在馬克思看來,政治自由通過政治主體的政治活動得以實現,主體性不僅為個體在政治活動中確立自己的政治角色、評判現實政治、開展政治活動、追求政治抱負、實現政治理想設定了價值標準,而且為現實政治生活的合法性及有效運作賦予了人權內涵與文明屬性。自主的個體擺脫群體依附,迸發出活力、激情和創造力,造就欣欣向榮的政治生態環境;自主的個體在規范的社會環境中對自己的政治態度、政治行為、政治信仰做出選擇,從而積極投身政治實踐,推動政治發展。
從本質上看,馬克思政治自由觀的理論主線是圍繞實現人類解放這一主題而層層展開。馬克思對政治自由的闡釋顯示出了鮮明的“共同體-個體”互構意蘊:以現實的處在社會關系中的個體為起點,在追求全人類解放的旗幟下,個體和共同體均被賦予了倫理和道德的正價值,互動、互助、互構。這無疑是對以往所有剝削階級政治思想的顛覆性重構。基于“共同體-個體”互構方法的政治自由范式,既強調個體主體性,又強調共同體與個體的平等性和互動性,這是對輕視個體利益的傳統共同體主義和對輕視整體利益的自由主義理論均是有效的補充,也是對于馬克思共同體思想的繼承發展。“共同體-個體”互構既能使個體的權益與自由選擇得到充分尊重,又能使共同體與個體和諧而均衡發展,從而為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提供更加基礎有效的政治理論路徑。
四、馬克思政治自由觀“共同體—個體”互構范式的當代價值
馬克思政治自由觀的“共同體—個體”范式為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深化政治體制改革指明了方向。政治自由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但是,如果沒有與之匹配的“共同體-個體”互構平臺,作為手段的政治自由與作為目的的政治自由必將分離,不利于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可持續發展。
從主體方面看,要彰顯公民和黨員的主體地位。政治自由以公民主體意識的回歸、主體精神的弘揚為途徑,以黨員權利的保障、責任的到位,能動性的發揮為切入點。由此,務必要改進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從傳統的執政實踐看,執政理念先于執政實踐,社會意識相對獨立性體現得較為明顯。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公民的主體性存在著一定的缺位,相應的,公民權利、公民責任、公民意識等方面表現比較薄弱。共同體的強大與個體的孱弱使得公民在現實政治中消極與被動,政治認知膚淺,政治情感冷漠,政治意識薄弱。與此同時,在執政黨的建設過程中,黨內民主、基層民主的作用并沒有充分發揮,黨員被服從的現象并不少見,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黨員積極主動地參與黨內生活及管理的權利削弱,主體性缺失,黨組織整體功能得不到積極發揮,部分導致了十八大報告所指出的“基層黨組織渙散,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突出,一些領域消極腐敗現象易發多發”。
從“互構”渠道看,要健全公民政治參與制度。“政治參與”體現公民參與政治的“合法性”,“有序”的政治參與既體現公民的政治素質,也是實踐政治自由的方式方法。正如排隊上公交一樣,如果雜亂無章,你爭我奪,既不能保證乘客順利上車,也不能保證司機順利開車。公民的主體性因為“無序”會被削弱,政治參與因為“無序”會流于形式,并且成為叢林法則的溫床。當前,要健全公民政治參與的制度建設,保障公民常態化常規化地參與現實政治,有序有效地行使公民權利和履行公民義務,激發政治系統的生機和活力,促進政治生態的新陳代謝。同時,要充分發揮網絡作為公民政治參與的渠道作用。在對待網絡政治參與方面,要做到一方面充分發揮網絡優勢,另一方面要充分看到網絡帶來的“負效應”,防止“成也蕭何,敗也蕭何”,要提升網民的道德感、責任感。讓網絡參與進入法治化的軌道。
從對象方面看,要強化公民社會的建設。政治自由要改造的對象是現實政治中由于政府與個體間力量的不平衡性而導致的政府“合法壓制”,具體表現為政治權利得不到保障、政治訴求得不到伸張。公民社會作為獨立于個體和政府之外的第三方,可以緩解個體和政府間的張力。從公民社會的物質形態來看,它不以營利為目標,因此,不具備市場性,獨立于市場系統之外;從公民社會的精神實質來看,公民社會的運轉需要組織系統的自發自愿,也就是說,公民社會內在蘊含著一種責任意識和奉獻精神,因為它的服務對象不會對他直接產生效用。因此,這樣的組織具有自發性,非營利性,非政府性。加強社會主義公民社會的建設,給當代中國的政治轉型、協商民主的有效治理開辟新的路徑,也為政治自由的發展提供新的路徑導向。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2]馬俊峰.馬克思政治哲學視野下的共同體[J].廣西社會科學,2011,(4).
[3]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德]路德維希·費爾巴哈.費爾巴哈哲學著作選集(下)[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
[6]陳小鴻.論人的自由全面發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7]王平.對人的全面發展問題的理論思考[J].哈爾濱市委黨校學報,2006.
〔責任編輯:張毫焉涵〕
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
[中圖分類號]B0-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0-8284(2015)04-0009-04
[作者簡介]施曉花(1976-),女,江蘇啟東人,博士,講師,從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研究。
[基金項目]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理論與實踐”;金陵科技學院科研啟動基金項目“生態思維視域下的政治參與模式研究”
[收稿日期]2015-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