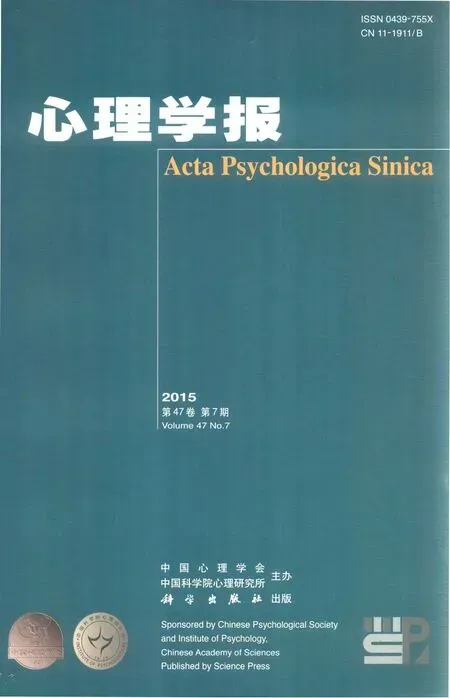基于名人面孔視覺特征和語義信息的視覺統計學習*
唐溢張智君曾玫媚黃可劉煒趙亞軍
(1浙江大學心理與行為科學系,杭州310028)(2云南民族大學教育學院,昆明650504)(3西南民族大學社會學與心理學學院,成都610041)
1 前言
在日常生活中,人類除了加工事物的視覺特征(如顏色和形狀等)和語義信息(如名稱)外,還對事物間的時空規律(如時間順序或空間位置信息)特別敏感。例如,當我們對一個新環境(如陌生的超市或城市)進行短期的熟悉后,就能自動習得場景中事物間的時空關系。有研究者認為,人們之所以能夠自動加工場景中的規律信息,是因為統計學習(statistical learning)能力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Turk-Browne,Scholl,Chun,&Johnson,2009)。
統計學習就是個體自覺地運算刺激間的轉接概率(transitional probabilities,TP)掌握統計規律的過程(Fiser&Aslin,2001)。該概念最初由Saffran,Aslin和Newport(1996)在研究嬰兒的語言習得時提出,他們給嬰兒呈現由無意義音節組成的刺激序列。這些音節每三個構成一個三聯體(triplet),三聯體內每個音節的時間順序固定不變,而各個三聯體之間的時間順序變化(如pa-bi-ku/go-la-tu/da-ro-pi/pabi-ku/da-ro-pi…)。更具體地說,在整個序列中,每個音節出現的頻次相同,而刺激之間的轉接概率不同。轉接概率的運算方式為TP=P(XY)/P(X),其中X和Y為刺激元素,P(XY)為整個刺激序列中XY組合出現的頻率,P(X)為X出現的頻率(Miller&Selfridge,1950),即三聯體內部元素間的轉接概率為1,而三聯體之間元素的轉接概率小于1。結果發現,在兩分多鐘的學習(聽覺呈現)后,嬰兒能明顯地分辨出呈現過的三聯體(如pa-bi-ku)與未呈現過的三聯體(如pa-la-pi)或偶爾呈現的三聯體(如bi-ku-da)。他們認為,嬰兒是通過“統計運算”(statistical computation)音節間的轉接概率而習得語言規律的(Saffran et al.,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