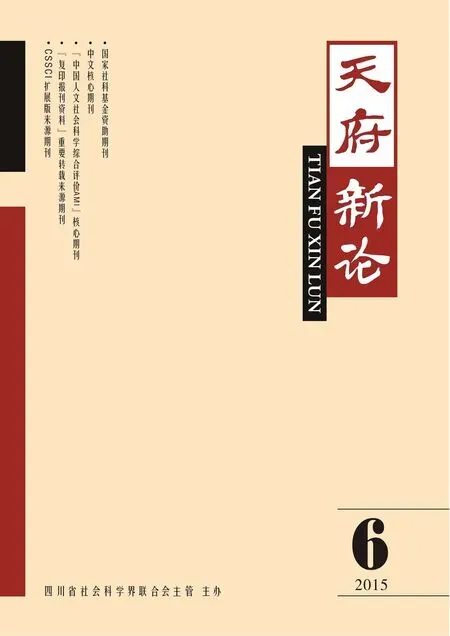以勝利者的名義:新的抗戰記憶與抗戰影視劇的書寫策略
張慧瑜
以勝利者的名義:新的抗戰記憶與抗戰影視劇的書寫策略
張慧瑜
作為20世紀中國歷史中的重大事件,抗日戰爭深刻地改變著中國的國家形態和中華民族的品格。如果說在毛澤東時代抗日戰爭是反抗日本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的戰爭;那么,20世紀80年代抗日戰爭則變成“落后就要挨打”的悲情動員;而新世紀以來,在中國經濟崛起的大背景下,抗日戰爭又被書寫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組成部分。與此相應,20世紀80年代以來影視劇中的抗戰敘述也經歷了三次大的轉型。
抗日戰爭;抗戰記憶;影視劇;創作類型
今年,中國舉行了盛大的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大閱兵,抗日戰爭再次成為熱門話題。作為20世紀中國歷史中的重大事件,抗日戰爭深刻地改變著中國的國家形態和中華民族的品格。如果說在毛澤東時代抗日戰爭是反抗日本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的戰爭,那么,20世紀80年代抗日戰爭則變成“落后就要挨打”的悲情動員,而新世紀以來,在中國經濟崛起的大背景下,抗日戰爭又被書寫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組成部分。近些年,抗戰影視劇的流行也是大眾文化領域中引人注目的現象,既有電視劇《亮劍》、《我的團長我的團》等經典之作,也有《抗日奇俠》、《一起打鬼子》等抗戰雷劇。本文主要分析四個問題,一是為何要重新紀念抗日戰爭,二是抗日戰爭的性質和兩種史觀的轉變,三是近代以來中國對日本的雙重態度,四是近些年抗戰影視劇的創作類型。
一、以“勝利者”的名義
以前,中國只有國慶大閱兵,今年是首次以紀念抗戰勝利的名義舉辦閱兵,而且,這還是一場帶有國際色彩的大閱兵,邀請了一些國外政要和外國儀仗隊參加。這種“勝利日”的紀念對于當代中國人來說很新鮮,也是比較陌生的歷史經驗,盡管抗日戰爭已經過去了70年,但中國第一次如此大規模地紀念抗戰“勝利”。與血淚斑駁的中國近現代歷史悲情敘述不同,中國是以抗戰勝利者、二戰勝利國的身份來舉辦這次盛會,抗日戰爭也被重新指認為一次偉大的勝利,是一百多年來中國人民反對外敵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可以說,這次找回歷史的“勝利”不像是歷史的緬懷,更像是一次歷史的重新追認。
9月3日作為抗戰勝利紀念日,是1946年中國國民黨中常會決議確定的,新中國成立之后,1949年12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把“八一五”作為抗戰勝利紀念日。1951年8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發布通告,將抗戰勝利紀念日改定為9月3日,直到1999年9月18日,國務院對《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進行修訂,延續了9月3日為抗戰勝利紀念日的規定。①參見“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百度百科。在當代,中國與抗戰相關的紀念日是“九一八”、“七七事變”和“八一五”,前兩個是日本侵略東北和發動全面戰爭的日期,被作為中國遭遇恥辱、動員全民族抗戰的特殊象征,“八一五”則是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八年全面抗戰結束的日期,9月3日沒有特別作為重大紀念日。其主要原因是在革命歷史敘述中,抗日戰爭只是中國人民反抗外來侵略者的一個歷史階段,抗戰之后的解放戰爭才是最終的勝利,也是新中國的勝利。再加上9月3日作為勝利紀念日帶有國民政府的色彩,實際上也是當時作為中國政府合法代表的國民政府接受了日本政府的投降書。
重新把9月3日作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是2014年2月27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以國家立法的形式通過的決議,今年是第二次紀念抗戰勝利日。在這次人大會議中,還確定把12月13日設立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從這樣兩個紀念日可以看出一種新的對于國家和人民的理解。這兩次紀念日的主體都是國家,一個是國家的勝利,一個是國家的恥辱,此處的國家是一種相對抽象的“中國”,一個模糊了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界限的國家。在這種國家的論述中,人民是被屠殺、被砍頭、被殺害的死難者,而不再是因反抗而壯烈犧牲的人民,也就是說,只要在戰爭、災難中無辜受難的中國人,國家都有責任紀念。這種被動的受害者同樣是一個抽象的人民,這也是南京大屠殺故事在抗戰圖景中被反復講述的原因。這樣兩個國家紀念日成為抗戰故事中最重要的節點,一個是受害者的恥辱,一個是勝利者的驕傲,至于如何從受害者變成勝利者,卻有些語焉不詳。從近些年每次遇到地震等自然災難造成重大人員傷亡時設立國家哀悼日,也能看出這種新的國家與人民的關系。
這種模糊中華民國與新中國界限的敘述所完成的是現代中國與當代中國一體化的任務,從兩個影視作品中也能看到這種趨勢。一是2009年的《建國大業》,這部電影論述1949年的合法性是放在1945年抗戰勝利組建聯合政府的背景中展開的,仿佛說內戰之后1949年的政治協商會議是對1945年抗戰勝利的接續,也就是說,1949年的新中國建立在1945年抗戰建國的基礎之上。二是2011年的《建黨大業》講述共產黨誕生的故事。在原來的革命史敘述中,共產黨誕生是從1919年五四新文化運動講起,從一戰結束、蘇聯建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開始。而在《建黨大業》中,歷史往前延伸了,其把建黨放在1911年辛亥革命的背景下展開,也就是說,1921年共產黨成立一直到1949年新中國建立,是對1911年中華民國的接續,在這個意義上,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接續在一起,變成了同一個現代中國。所以說,南京大屠殺是國民政府的恥辱,也是當下中國的恥辱;抗戰勝利是國民政府的勝利,也是當下中國可以分享的勝利。這種從歷史中找回了曾經擁有或不曾擁有的“勝利”,是一種新的歷史記憶的重塑。
二、抗日戰爭的性質與兩種史觀的轉變
現在大規模紀念抗戰,著眼點往往放在戰爭與和平的永恒主題上,而很少討論抗日戰爭的性質問題,這個問題恰好是需要特別強調的。20世紀80年代以來,抗日戰爭只被作為民族國家之間的常規戰爭,反而弱化抗戰作為反法西斯戰爭的面向。
先從三個概念說起,一是“抗戰”,二是“反法西斯戰爭”,三是“二戰”。這三個概念有重疊的地方,但強調的側重點不同。“抗戰”主要是指中國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戰爭,這一概念一般是中國使用。“反法西斯戰爭”是冷戰年代社會主義國家指稱“二戰”的說法,也是對二戰性質的定位。上世紀30年代德國、日本走向法西斯化是其發動對外侵略戰爭的根本動因,反對德國、日本的侵略就是反對法西斯主義,而反法西斯主義戰爭包括著反資本主義、反帝國主義的含義,因此,其帶有左翼或共產主義的色彩。“二戰”是英美國家經常使用的概念,把第二次世界大戰放置在“一戰”的序列中,這種說法其實模糊了“二戰”的性質。過去在“二戰”的敘述中是沒有中日戰爭的位置的,因為只有發生在歐洲的戰爭才具有“世界性”,中日戰爭只是附屬的、區域性的戰爭。我們現在更多地使用“二戰”的說法,實際上采用的是英美等西方國家對這場戰爭的定位,抗日戰爭也被作為“二戰”的“東方主戰場”,這其實消弱了抗戰反法西斯主義的意義。
這次抗戰勝利紀念日的全稱依然是“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指出了抗日戰爭的雙重性質,一是中華民族反抗外來侵略者的國家戰爭,二是抗戰也是落后國家的人民反抗帝國主義法西斯的國際戰爭。因此,抗戰不僅是中日之間的戰爭,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有機組成部分。之所以強調抗戰反法西斯的一面,與探討抗日戰爭為什么會發生有關,也就是追問日本為什么要侵略中國?難道中國落后就應該被“侵略”嗎?這和日本在上世紀30年代國際經濟危機和大蕭條的背景下走向法西斯化、軍國主義化有關。近代以來,日本面臨西方列強的侵略,主動進行明治維新改革,走向“脫亞入歐”的道路。只是,日本在追求工業化、現代化的過程中始終伴隨著對外侵略戰爭,如1894年的甲午戰爭、1905年的日俄戰爭、1931年的侵華戰爭、1942年的太平洋戰爭等,這和西方原發資本主義國家先工業化后進行海外殖民的道路是一致的。通過對外戰爭,它一方面掠奪殖民地的資源,另一方面開辟海外市場,這些都與服務國家的工業化有密切關系。抗日戰爭的背景還與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危機有關,一些國家通過戰爭轉移、轉嫁國內社會矛盾。可以說,德國、日本走向法西斯化,這本身是資本主義無法克服自身危機的產物。在這個意義上,反法西斯主義不只是抵抗外來侵略,也是反思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的發展道路。與“一戰”的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爭霸戰不同,“二戰”的反法西斯主義具有“世界性”,這不僅體現在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與蘇聯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大聯合”,而且,20世紀30年代的國際主義精神也參與到反法西斯主義的實踐中。就像白求恩的故事是典型的國際主義和反法西斯主義的結合,還有西班牙內戰中來自各個國家的“國際縱隊”。二戰結束之后在冷戰的背景下,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用“二戰”來掩飾法西斯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必然淵源,而社會主義陣營則用反法西斯主義來批判資本主義必然法西斯化。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的抗戰論述開始從反法西斯主義戰爭轉變為一種中日之間的國家戰爭,這是在“告別革命”、去冷戰的背景下從革命史觀向現代化史觀轉變的結果。與社會主義革命、階級斗爭、人民作為歷史的主體等革命史觀不同,現代化史觀以民族國家為敘述主體、以現代化的發展主義為任務,于是,包括抗日戰爭在內的中國近現代歷史重新從革命史改寫為現代化史觀。在毛澤東時代,抗日戰爭是中國近代以來革命史的組成部分,是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重要環節,抗戰之后的解放戰爭則是反帝、反封建的繼續,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新民主主義革命完成,抗戰史鑲嵌在百余年來中國反抗外來侵略走向社會主義革命的大敘述之中。新時期以來,在現代化史觀中,抗日戰爭占據著重要的位置,抗日戰爭被作為中國貧窮、落后而遭受外敵侵略的屈辱歷史,尤其是南京大屠殺的故事,成為苦難深重的中國人遭遇凌辱的象征。中國人民反抗外來侵略者的革命史、抵抗史變成了中國遭受屈辱和創傷的受害史、悲情史,也就是用“落后就要挨打”來作為新一輪現代化的悲情動員。與此相關的是,關于中國的自我想象重新變成了前現代的、沒有經歷現代的鄉土中國。20世紀90年代,隨著市場化改革、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愛國主義、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疊加”成為新的主流意識形態,抗日戰爭也成為傳達這種主旋律的影視劇題材。新世紀以來,伴隨中國經濟崛起,主流意識形態進一步升級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因此,20世紀80年代的民族悲情史又被組織到民族復興的論述中,抗日戰爭開始從民族屈辱和悲情轉變為一種抗戰勝利的故事。抗戰勝利被指認為中華民族復興的起點,這恐怕與當下中國的經濟實力和大國崛起的心態有關。
三、抗戰勝利的曖昧性與被遮蔽的歷史敘述
抗戰“勝利”本身在中國現代史中是比較曖昧的,這種曖昧性與二戰后的冷戰歷史格局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一次深刻影響當下世界秩序的戰爭,這場戰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讓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站在了一起,結成了世界反法西斯主義的“同盟國”。二戰一結束,冷戰鐵幕隨之降臨,世界分隔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像中國的內戰、朝鮮戰爭、越南戰爭都是發生在兩大陣營之間的“中間地帶”的戰爭。
內戰爆發以及國民黨的敗北,使得國民政府作為抗戰勝利者的身份非常可疑。一方面,抗戰的最終勝利并非完全來自于國軍將士的勇敢作戰,反而有賴于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日根據地和包括美國、蘇聯等同盟國的大力支持,尤其是1942年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后把美國拖入太平洋戰爭以及蘇聯紅軍出兵東北,按照日本的說法,日本被美國打敗,而不是當時積弱積貧的中國;另一方面,抗戰之后的國共內戰,國民政府很快一潰千里,從抗戰勝利者變成了偏居一隅的流亡政府。因此,對于抗戰的勝利,國民政府更像是勝利的失敗者。另外,冷戰之后,美國占領日本,至今依然在日本駐軍。由于冷戰的需要,日本作為法西斯國家的戰爭責任被英美世界極大地赦免,這也造成德國法西斯是人類的公敵,而日本則不是“世界”的敵人,反而日本國民的普遍感受是從侵略者變成了二戰的受害者。①在這個意義上,廣島、長崎作為對日本走向軍國主義道路的懲罰,給日本人民也帶來的慘痛災難,只是廣島、長崎作為一種“亞洲的傷口”又糾纏于亞洲/西方的話語之中。日本的侵略戰爭是在抵抗西方列強的旗幟下展開的,而日本作為失敗者/原子彈受害者的身份又被作為亞洲的失敗,“亞洲”成了日本成功與失敗的雙重“借口”。在“亞洲”的遮羞布之下,那個已然晉身為西方列強之一的日本以及成功走向帝國主義侵略之路的日本就消失不見了。
近代以來,日本確實是對中國產生過特殊影響的國家。我們評價日本經常會出現兩種情緒,一種就是仇恨、憎惡,把日本叫做“小日本”、“日本鬼子”,另一種情緒則是羨慕和崇拜,認為日本更文明、更現代。這樣既愛又恨的情緒從甲午戰爭以后就出現了。甲午戰爭的失敗讓晚清知識分子倍感恥辱的同時,也發現東洋的富國強兵之路是值得貧窮落后的中國學習的榜樣,因此,留學日本成為晚清民初很多知識分子的選擇,如魯迅、蔣介石等。到1905年日本在日俄戰爭中取得勝利,也被認為是“亞洲的勝利”,②如1924年,孫中山逝世前夕在日本神戶發表了名為《大亞洲主義》的演講,號召其他弱小的亞洲國家向日本學習,因為日本打敗了傳統的西方國家俄國,暫且不討論俄國作為西方內部的他者,這種亞洲主義的問題在于,日本的勝利究竟是亞洲的勝利,還是西方的勝利呢?因為正是憑著日俄戰爭日本加入了西方的列強俱樂部。是亞洲國家“脫亞入歐”最為成功的典范。日本確實也是少有的落后國家能夠避免被西方列強殖民的案例,其所選擇的道路是把自己也變成西方列強,加入“八國聯軍”俱樂部。直到二戰結束,日本被美軍打敗、占領,這種明治維新以來的日本現代化之路才被認為是有問題的,因為它最終走向了法西斯主義。與之相反,中國經歷近代受侵略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變成主權獨立的社會主義國家,被認為是落后國家擺脫殖民、獲得民族獨立的成功范例,中國也改變了對日本既愛又恨的情緒,在社會主義革命的視野中體認到日本人民也是法西斯主義的受害者,并把二戰后日本國內的反美斗爭作為受壓迫人民反抗帝國主義的組成部分。
冷戰時期,日本在美國的大力扶持下迅速實現經濟起飛,成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員。這與日本處于冷戰的前沿陣地的位置有關,也是續日本之后亞洲四小龍經濟崛起的地緣政治原因。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國文革結束、改革開放開始。1978年底中國領導人鄧小平訪問日本,他乘坐日本高速列車新干線的新聞報道,讓中國人看到一個高度發達的、現代化的日本,日本的形象從法西斯主義的受害者再度轉變為現代化的優等生。這種“震驚”體驗又一次改變中國人眼中的兩國近代史,中國從鴉片戰爭到文革結束的歷史被認為是現代化的失敗,而日本從明治維新到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才是現代化的“正途”。與此同時,在以民族國家為主體的現代化論述中,日本繼續扮演著給中國帶來巨大創傷的外敵形象,這種對日本既愛又恨的情緒再次“復活”。③這一點在《南京!南京!》(包括《拉貝日記》)中呈現得更為清楚,正如導演在回應為什么要選取日本人的角色時有意無意地說:“70年前日本真的很強盛,一個步兵單兵一年可以有1800發子彈的實彈射擊訓練,我們能有10發就不錯了。1943年以前我們拼刺刀拼不過日本人,必須是二對一。日本人在日記本上對自己參加的每一場戰役都畫有戰略圖,我們的軍隊文盲占百分之九十九”。陸川對于年輕日本演員的敬業精神也贊許有加,正如他們的前輩配備著優良的裝備和素質,這些年輕的日本演員也是如此充滿良知地不敢演強奸戲,直到導演說如果不演這些女大學生就會一直裸下去,這些日本演員才勉強同意,演完后馬上就把衣服給女演員蓋上,如同影片中那些充滿內疚和悔恨的日本士兵,及時槍斃了遭到奸污的中國女人,因為“這樣活著還不如死掉”。《陸川全面回應<南京!南京!>觀眾質疑》,載南方日報,2009年04月24日。這份愛恨交織的情感是一種典型的殖民地、落后國家對西方現代性的雙重經驗,既渴望現代化(變成西方),又深受現代化所害(被西方侵略)。在這種現代化的視野中,只有進步與落后、變成西方或被西方所侵略的兩種選擇,那種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所導致的法西斯化以及落后國家尋求民族獨立與現代化并重的革命之路都不可見了。④當然,能否在現代性之外對現代性進行批判依然是一個問題,從某種程度來說,現代性的全球擴散恰好是以對現代性的抵抗的方式完成的。18世紀北美反抗英國殖民地建立了美利堅合眾國,20世紀俄國在無產階級革命的意義下反抗資本主義全球秩序,顯然,馬克思對于現代性的批判也是在現代性內部展開的,而日本所謂的“脫亞入歐”也是以打敗俄國這樣的西方國家才得以晉級為西方列強之一,并進一步打著反抗西方的旗號,吞并、殖民東亞各國,對現代性的反抗和質疑卻使得現代性的邏輯播散到更多的區域。
這種以現代化為基調的民族國家史觀也帶來一些歷史敘述的困境,特別體現在兩個領域,一是如何講述內戰的故事,二是如何處理抗戰與中國革命的關系。如果把抗日戰爭講述為國共聯合抗日的民族國家之戰,那么,隨后發生的國共內戰就變得非常曖昧和難以講述。新世紀以來最熱播的革命歷史劇《亮劍》主要講述李云龍打鬼子以及與國民黨將領楚云飛聯合抗日的故事。《亮劍》中有一句臺詞是“國家利益高于意識形態,民族利益高于一切”,這句臺詞被李云龍、楚云飛和日本特種兵將領山本一木都說過,他們都是為了各自的國家利益來打仗,也是忠實于自己國家、民族利益的職業軍人,如果沒有戰爭,他們三個彼此惺惺相惜的男人應該是好朋友。用國家主義來理解抗戰,使得抗日戰爭的性質變得模糊了,戰爭沒有正義與非正義的區別,只是兩個國家為了各自的利益來打仗。這部電視劇的魅力是把李云龍這樣的紅色將領塑造為民族國家的英雄,從而使得以階級革命為內核的紅色經典實現華麗轉身。為了避免內戰中兩個好兄弟李云龍與楚云飛兵戎相見,電視劇采取了內戰一開始李云龍就負傷住院、談戀愛的情節,解放后借民主黨派之口質問李云龍“中國人為何要打中國人”。確實,從中華民族的角度很難處理內戰作為階級戰爭的事實,這導致抗戰劇流行、內戰劇很少的現象。如果非要講述內戰的故事,新世紀以來的影視劇發現了一種恰當的好辦法,把國共內戰呈現為暗戰和諜戰故事,像《暗算》(2006年)、《潛伏》(2009年)一樣勾心斗角的辦公室化的職場政治。比如《人間正道是滄桑》(2009年)中大哥國民黨楊立仁、小弟共產黨楊立青是親兄弟,他們抗日戰爭時期聯合抗日,內戰開始就通過諜戰來智斗。所以,國慶獻禮劇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就不再講述“三大戰役”的故事,只講述北京和平解放的故事,如《戰北平》(2009年)、《北平戰與和》(2009年)、《北平無戰事》(2014年)等。
另外一種被國族抗戰史所遮蔽的歷史,就是中國革命與抗日戰爭的內在關系。如果說在毛澤東時代主要講述共產黨領導下的敵后游擊隊率領人民群眾打擊、騷擾小股日軍的故事,如《平原游擊隊》(1955年)、《鐵道游擊隊》(1956年)、《地雷戰》(1962年)、《野火春風斗古城》(1963年)、《地道戰》(1965年)等,那么,在恢復國共聯合抗戰以及國民黨正面抗戰的“撥亂反正”中,正規戰、國軍抗戰的故事則成為新的主流,尤其是以《我的團長我的團》(2009年)、《中國遠征軍》(2011年)等為代表的赴緬抗戰的國軍故事,這就使得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戰的故事變得斑駁游離。抗日戰爭是中國共產黨從工人階級的先鋒黨轉變為中華民族的政黨的關鍵時期,實現了階級論述與民族論述的辯證統一,也進一步完善和明確了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的任務。這從毛澤東抗戰期間發表的《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一系列重要文章中可以看出。另外,抗日戰爭對于共產黨來說,一方面是反對日本法西斯主義的對外戰爭,另一方面,也是發動、組織和動員群眾進行人民戰爭的過程。與那些把敵后游擊戰表現為《抗日奇俠》(2010年)、《一起打鬼子》(2015年)等抗戰雷劇不同,游擊戰爭恰好是與人民戰爭密切結合在一起的,而不只是像好萊塢超級英雄那樣打擊僵尸化的敵人。
四、抗戰影視劇的三重轉型與五種創作類型
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抗戰敘述經歷了三次大的轉型:第一次是把抗戰故事變成悲情史、受難史,這主要體現在南京大屠殺的歷史故事上。第二次是把抗戰敘述的民國化和國家化,體現在以革命者及其領導的革命群眾為敘述主體的敵后抗戰故事轉變國共聯合抗日的故事,或者突顯國軍將領在正面戰場上的意義。這種抗戰敘述的“民國化”也始終伴隨著國家化,也就是把反日本法西斯的戰爭敘述為兩個現代民族國家之間的戰爭,抗戰英雄被塑造為國家英雄、民族英雄,這種抗戰影視劇服務于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家主義和愛國主義的主流意識形態的需要。第三次是把國家化的抗戰敘述進一步國際化和二戰化,也就是把中國的抗戰故事升級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有機組成部分,中國變成與美國、英國“同一個戰壕”的同盟國,突顯抗戰的國際面向,這與新世紀以來中國作為大國的自我想象以及中國的新國際視野有關。在這種背景下,出現了五種抗戰劇的創作類型。
第一種是南京大屠殺的故事。南京大屠殺作為歷史事件在20世紀50到70年代的革命敘述中,不僅僅被作為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血淚斑斑的近代史中最為慘烈的一幕,而且作為日本走向法西斯、軍國主義的明證,是中國遭受帝國主義侵略最為具象化的呈現,但是,在那個時代并沒有出現以南京大屠殺為背景的抗戰影片。因為“南京”這一國民政府“消極抗日”而丟失的“首都”無法放置在共產黨領導下全國人民抗戰的革命敘述里,再說,只有人民被屠殺而沒有人民奮起反抗的情節,很難完成“人民作為歷史主體”的論述。20世紀80年代之后,南京大屠殺才開始被不斷地拍攝為電影,如《南京大屠殺》(1982年,紀錄片)、《屠城血證》(1987年)、《南京大屠殺》(1995年)、《黑太陽南京大屠殺》(1995年)、《棲霞寺1937》(2005年)、《南京夢魘》(2005年,朗恩·喬瑟夫導演紀錄片)、《南京浩劫》(2007年,好萊塢拍攝)、《南京!南京!》(2009年)、《拉貝日記》(2009年,中德合資拍攝)、《金陵十三釵》(2011年)等。這些講述“南京大屠殺”故事的影片都以呈現日軍的殘暴和中國人的被屠殺為情節主部,這種中國人民的創傷體驗沒有轉化為抵抗侵略者的革命動員,反而被組織到一種民族悲情中。這也成為導演陸川認為中國關于“南京大屠殺”只有控訴式的書寫,沒有中國人的抵抗的緣由。①對于電影《南京!南京!》的解讀,可以參見筆者發表在《電影藝術》上的文章《后冷戰時代的抗戰書寫與角川視角》,2009年第4期。
第二種是國共聯合抗日的故事。新時期以來,關于抗日戰爭的敘述再次成為國軍與共軍“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敘述空間。在面對日本作為一種外在的民族敵人的意義上,國軍不僅被恢復了正面抗戰的“歷史地位”,而且國共之間的意識形態沖突也在中國人民族身份的同一的意義上獲得整合,這使得抗日戰爭變成一種中國人抵抗外辱的國族之戰。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抗戰影片中,國民黨、國軍形象開始呈現一種正面的積極抗戰的形象,比如《西安事變》(1981年)、《血戰臺兒莊》(1986年)、《鐵血昆侖關》(1994年)、《七七事變》(1995年)等。直到《南京!南京!》(2009年)、《金陵十三釵》(2011年)等國產大片中,直接把抵抗日軍的國民黨士兵書寫為中國軍人的代表。近些年,在大眾文化領域,除了發掘那些被冷戰歷史所遺忘的抗戰老兵外,更有名的民國軍人是1942年作為英美同盟軍的中國遠征軍,這些承擔國際責任的抗戰老兵被命名為國家英雄。正如在一本“獻給為中華民族抗擊日本侵略者而戰的中國軍人和盟軍軍人”的書《國家記憶》中,作者從美國國家檔案館中找尋到當時美國隨軍攝影師拍攝的赴緬作戰的中國遠征軍的身影。在序言中作者深情地寫道,以前抗戰歷史都是“認賊作父”,“直到此前多少年,做夢都想不到,有那么多父輩的影像,如此清晰,宛如眼前”〔1〕。這是一次借助美國攝影師的目光把曾經的敵人、國軍重新指認為“父親”的故事,而同名作者的另一本書直接命名為《父親的戰場:中國遠征軍滇西抗戰田野調查筆記》,這種尋父之旅所實現的是把當代中國與現代中國“合并”為抽象的民族國家的過程。這種文化的民族國家化,也是當下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秩序民族國家化的曲折反映。
第三種是土匪、農民抗日的故事。隨著20世紀80年代革命敘述的瓦解和現代化敘述的顯影,曾經被革命動員和賦予歷史主體位置的農民又變成了前現代的自我表征,這導致在抗戰敘述中,曾經作為抵抗者的人民又變成了被砍頭者和愚昧的庸眾。如20世紀80年代的第五代電影《一個和八個》(1984年)和《紅高粱》(1987年),前者講述了一個被懷疑為叛徒的革命者在遭遇日軍的過程中把一群土匪改造為抵抗的中國人的故事,被懷疑的革命者與土匪在“有良心的中國人在打鬼子”、“不打鬼子算什么中國人”的國族身份的意義上獲得整合。而后者講述了一段看不出具體時空秩序的“我爺爺”與“我奶奶”的遙遠傳奇。沒有共產黨的引領,伏擊日本人成為一種在民間邏輯中的英雄復仇。也正是在這種革命者缺席的狀態下,出現了一種沒有經過革命動員和啟蒙的農民成為抗戰主體的策略,這可以從姜文的《鬼子來了》(1999年)和馮小寧的《紫日》(2001年)中看出。《鬼子來了》一開始,“我”作為游擊隊長半夜交給馬大三兩個麻袋,從而就消失不見了。對于掛甲屯的村民來說,他們不是啟蒙視野下的庸眾,也不是革命敘述中的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主體,他們是生活在殖民地的“良民”。從這個角度來說,影片恰好處理了左翼敘述的困境,即在外在的革命者缺席的情況下,以馬大三為代表的“人民”能否自發自覺地占據某種歷史的主體位置。《鬼子來了》在把“日本人”還原為“鬼子”的過程中,也是馬大三從前現代主體變成獨自拿起斧頭向日本鬼子砍去的抵抗的、革命的主體過程。與《鬼子來了》相似,馮小寧的《紫日》(2001年)以一個被俘的北方農民楊玉福的視角來講述二戰末期的故事。
第四種是外來視角下的抗戰故事。20世紀90年代中期,出現了一種借西方人的視角來講述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敘述策略,如馮小寧執導的《紅河谷》(1996年)、《黃河絕戀》(1999年)和葉大鷹導演的《紅色戀人》(1998年)等。在這些影片中,占據主體位置的是一個“客觀的”西方男人,中國則被呈現為一個女人、女八路軍的形象。《紅河谷》講述的是1904年西藏人民抵抗英軍侵略的故事,但是,這種抵抗的故事卻放置在一個英國年輕探險家瓊斯的目光中來呈現。這種西方視點的故事在《黃河絕戀》中更為明顯,這部影片完全以美國飛行員的內在敘述為主。在日本這個殘暴的敵人面前,影片中的“中國人”放棄了家族仇恨而成為一種抵抗的主體,只是這種土匪和八路軍聯合阻擊日軍的故事被改寫為“拯救大兵瑞恩”的故事,為了把美國飛行員歐文安全送到根據地,所有的中國人都“心甘情愿地”犧牲了。《紅色戀人》也以一個美國醫生的回憶為視點,呈現了一段都市革命情侶的生死之戀。通過把自我的歷史敘述為他者眼中的故事,革命故事獲得一種言說和講述的可能。2009年上映的《南京!南京!》則把這種外國視角轉化攻占南京的日本士兵角川。與那種落后者、弱者、被砍頭者的主體位置不同,中國導演可以想象性地占據一個西方化的現代主體,這也許與中國走向“大國崛起”和“復興之路”的歷史進程有關。
第五種是把抗戰講述為二戰故事。如果說20世紀80年代是把抗日戰爭從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降級”為中日兩個民族國家之間的戰爭,那么,新世紀以來的抗戰敘述則“升級”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國際”戰爭。需要指出的是,在以歐洲為中心的二戰敘述中,抗日戰爭一直被西方所忽視,這不只與當時國民政府的弱國地位有關,更重要的是與日本在冷戰后被美國赦免、成為對抗東方社會主義陣營的“自由世界”的合法成員有關。這體現為戰后日本沒有像德國那樣被徹底清算戰爭責任(如沒有追究天皇的戰爭責任),就連南京大屠殺等人間慘劇也幾乎不被西方社會知曉。直到冷戰結束后,1997年華裔女作家張純如出版《南京大屠殺:被遺忘的大屠殺》,才使得這次慘絕人寰的大屠殺進入西方主流視野,也使得德國納粹黨人約翰·拉貝所留下的記錄南京大屠殺的日記得以出版。1997年首先出版中文版《拉貝日記》,被作為南京大屠殺確實發生過的“權威”證詞。〔2〕2014年英國歷史學家拉納·米特出版《中國,被遺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戰爭全史》,首次向西方世界呈現抗日戰爭的全景。從這里也可以看出,長期以來,在二戰的“世界”視角中沒有中國抗戰的位置,之所以這些“被遺忘的”故事又被重新提起,與冷戰終結和當下中國的崛起有關。這種西方世界有限度地對南京大屠殺、抗日戰爭的認識,都會引起國內社會的極大關注,因為這些來自西方的目光正好呼應著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走向世界、加入英美主導的西方秩序的內在渴望。近些年,抗日戰爭越來越被放置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背景下來呈現,不僅恢復國軍正面抗戰的形象,而且恢復國民政府作為同盟國、與英美并肩作戰的位置。近年出現多部關于國軍赴緬作戰的中國遠征軍題材的圖書、電視劇和電視專題片,比如在電影《一九四二》(2012年)、《開羅宣言》(2015年)中把蔣介石表現為二戰時期的國際領袖,參與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有趣的是,這種把抗戰“國際化”的趨勢并沒有凸顯抗日戰爭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國際性”,不會講述蘇聯援助中國抗戰的故事,也難以呈現白求恩式的國際主義戰士的身影。
總之,從20世紀80年代中國被書寫為落后者、弱者的悲情敘述,到當下中國高調紀念抗日戰爭的勝利,都反映了改革開放時代的中國不同的自我想象和對未來的期許。對日本的理解,不應該陷入近代以來形成的惡魔與榜樣的魔鏡效應,而應該直面現代性所帶來的創傷,尋找克服現代性的新路。
〔1〕章東磐.國家記憶:美國國家檔案館收藏中緬印戰場影像〔M〕.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
〔2〕戴錦華見證之維〔A〕.印痕〔C〕.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責任編輯:謝蓮碧)
J9
A
1004-0633(2015)06-019-7
2015-09-06
張慧瑜,博士,中國藝術研究院電影電視藝術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方向:中國電影史、當代大眾文化。北京100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