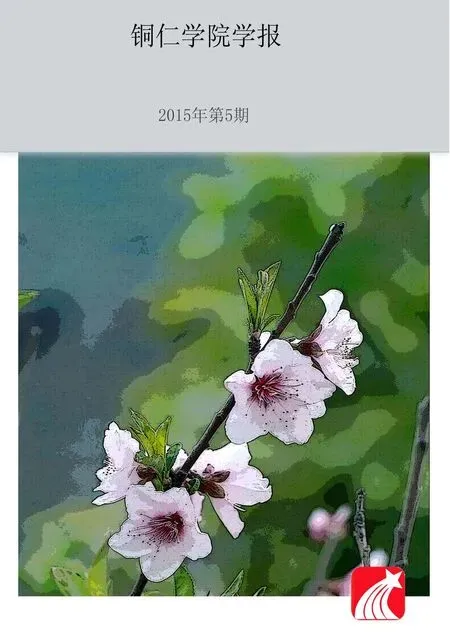熟讀《文選》理
——主持人語
【梵凈國學研究】
熟讀《文選》理
——主持人語
范子燁(1964-),黑龍江省嫩江縣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文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文選》學會理事、中國孟浩然研究會理事、中華文學史料學會理事、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理事和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古文學與文化。主要著作有《〈世說新語〉研究》、《中古文人生活研究》、《悠然望南山——文化視域中的陶淵明》、《中古文學的文化闡釋》、《春蠶與止酒——互文性視域下的陶淵明詩》和《竹林軒學術隨筆》,發表學術論文近二百篇。
某一年的正月初一,兒子宗武十五歲的生日,杜甫先生高興地寫了一首《宗武生日》詩:
小子何時見?高秋此日生。自從都邑語,已伴老夫名。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
熟讀《文選》理,休覓彩衣輕。凋瘵筵初秩,欹斜坐不成。流霞飛片片,涓滴就徐傾。
或許是受到孔子“吾十有五而志于學”(《論語·為政》)的自我表述的影響,老杜對兒子在文學藝業上期望甚殷,至于世俗所推許的老萊子式的孝道,他并不掛懷,正所謂望之深而責之切,一位慈父的襟懷躍然紙上。清浦起龍《讀杜心解》卷五之三評此詩:“前四提筆。中四,勖子正文。后四,以己之老憊,儆惕后生。”“‘何時見’,期以學成名立也。中四句,字字家常語。質而有味。由祖而來,詩學紹述。此事直是家業。人言傳說有子,特是世上俗情耳。須得學問淵源,本于漢魏,熟精《選》理,乃稱克家。豈必戲彩娛親,方為孝子。面命之語,如聞其聲。”杜甫出身于北方世族京兆杜氏,祖父杜審言是初唐著名詩人,而晉代大將軍杜預則是其遠祖。如此顯赫的家世自然使杜甫感到自豪,因而在詩中勸勵兒子要秉承家學,發揚光大,而要做到這一點,則必須以“熟讀《文選》理”為第一要務。唐人素來重視《文選》自不必言,但何為“《文選》理”?廣義而言,《文選》中的一切問題,都屬于“《文選》理”;狹義而言,“《文選》理”則是專指《文選》所包含的文章妙道。我想,老杜的本意當指后者。然而,以今人的文化眼光和學術視域來觀照這部中古時代的文學圣典,則我們不妨以前者為“《文選》理”。
本期梵凈國學研究的五篇論文正是“熟讀《文選》理”的結晶。
鐘仕倫教授的《〈永樂大典〉所錄〈文選〉考釋》以《永樂大典》殘卷所錄 47則《文選》為核心,對其所依據的《文選》原始版本進行考證,謹慎地推斷贛州學刊本為其版本淵源,屬于六臣注本中的“李善—五臣注”系統。文章指出,《大典》所錄《文選》不僅為《文選》版本學提供了一個可資研究的對象,而且有用于唐鈔《文選》集注本、敦煌寫本、胡刻本、明州本和景宋本的校勘,具有一定的文獻價值。研究中古時代的文學典籍,今存《永樂大典》殘卷確實值得重視。實際上,在傳統的選學研究史上,版本研究一直處于核心位置,但目前此方面的研究幾乎處于飽和狀態,很難有所突破,故仕倫教授的這篇宏文是一個絕大的貢獻。文章詳細比勘蕭《選》諸本,其功力之深,讀者一望即知。做這樣的學問是非常辛苦的。讓我們向他致敬。
胡旭教授的《〈文選·奏彈曹景宗〉發覆》重點闡發任昉《奏彈曹景宗》一文產生以及進入蕭《選》的歷史背景。基于對其不同的文學意義與歷史意義的深刻認知,文章深入開掘了這篇作品背后的隱情。作者指出,此文之所以能入選《文選》,有三方面的因素:一是因為曹景宗家族在梁大通年間的徹底敗落,二是因為南朝上層社會流行尚文黜武的社會風氣,三是此文在文章分類方面具有一定的典范意義。同時,作者發現,《梁典》、《梁書》中關于“曹景宗被彈”一事的記載和感情傾向,受到了《奏彈曹景宗》一文的影響,而北朝的《魏書》由于受此文影響較小,因而相關的記載比較客觀。通過對這三部歷史典籍關于曹景宗以及司州之戰、鐘離之戰有關記載的比較,作者還原了當時的歷史真相以及曹景宗其人的原貌。但文章的建樹尚不止此。胡旭教授指出,梁武帝是一個工于心計的君主,他成功地利用任昉的正直,以徇情的方式,使曹景宗對其感恩戴德,達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換言之,蕭衍正是巧妙地利用了當時文臣武將之間的矛盾,取得了制約滿朝文武的雙贏雙效。學者固然不是政治家,但是,不懂政治的人,或者沒有政治眼光的人,也絕不會成為優秀的學者,因為政治素養的欠缺必然使其看不到時時影響文學創作的非文學因素。這是胡旭教授這篇文章給我們的重要啟示。這位《選》學屆的“旭哥”一向給我瀟灑美少年的印象,文章寫得如此老道,實在值得贊許。受他的啟發,我想在這里對一些相關問題略作申說。我對《文選》卷四十的奏彈之文一向很好奇,如果說沈約的《奏彈王源》屬于契合蕭《選》選錄標準的典范之作的話,那么,任彥昇的兩篇奏彈文字就都有問題,《奏彈曹景宗》是典雅不足,《奏彈劉整》則純粹是大白話,至今還被語言學家們奉為研究中古口語的秘庫。由于《奏彈劉整》的風格完全不符合蕭《選》的擇錄標準,我甚至認為,這篇文章是在蕭統不知情的情況下被劉孝綽等人胡亂塞進來的,或者如曹道衡先生所說,《文選》本來就是一部未定稿未完成的書。《奏彈劉整》的背后是否另有隱情?期待著“旭哥”為我們再作發覆。歷史上的曹景宗,其縱欲豪奢固然屬于惡習,但其為人風格也值得欣賞。《梁書》卷九《曹景宗傳》載:
性躁動,不能沉默,出行常欲褰車帷幔,左右輒諫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宗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獐,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饑食其肉,甜如甘露漿。覺耳后風生,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遭此邑邑,使人無氣。”
這一代名將的豪氣確實令人感動。傳世所謂岳飛《滿江紅》的“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正源自曹景宗的豪言,辛稼軒《破陣子·為陳同甫賦壯詞以寄》的“弓如霹靂弦驚”也源自曹景宗的壯語。《奏彈曹景宗》說:“竊尋獯獫侵軼,暫擾疆陲,王師薄伐,所向風靡。……故司州刺史蔡道恭,率厲義勇,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徂秋,猶有轉戰無窮,亟摧丑虜。方之居延,則陵降而恭守;比之疏勒,則耿存而蔡亡。若使郢部救兵,微接聲援,則單于之首,久懸北闕,豈直受降可筑,涉安啟土而已哉!”這是以漢代的匈奴比擬北魏之鮮卑。其實作為儒將,岳武穆與曹景宗的為人風格完全不同,他與當朝皇帝的關系也不同于曹景宗與梁武帝的關系,所以《滿江紅》用曹景宗的典故實在不倫不類,正可證明其為偽作,但無論《滿江紅》的作者是誰,他都肯定是一個“熟讀《文選》理”的人。
宋人對《文選》的尊崇熱度遠不及唐人。張明華教授的《陸游“國初尚〈文選〉”的歷史考察》和李昇博士的《南宋理學家編選〈左傳〉風尚的形成及其文化成因》這兩篇論文就探討了這方面的問題。明華教授以大膽的質疑精神和科學的求證態度對陸放翁“國初尚《文選》”之說進行了歷史性的考察,確認了宋初出現的文選學著作并不多,士人學習《文選》的情況也不多見的事實,同時,他從宋初詩文出發,對所謂“當時文人專意此書”的情況進行了印證,發現這種情況僅在宋庠、宋祁兄弟的文集中有較多體現。這些觀點一經明華道出,即可確證無疑,因為他是根據現存的文獻來立論的。但是,他并不以為放翁糾偏為滿足,通過考察,他證明在慶歷時期以后,《文選》的影響仍然較大,主要表現在集選詩的出現。由此,宋代《文選》流布和影響情況就基本清楚了。李昇的研究正可與明華互補。他首先根據《文選》的體例說明蕭《選》不選經書的事實(當然,《文選》所收子夏《毛詩序》和杜預《春秋左傳序》屬于經部著作),隨后表明這一事實乃是北宋以前人所共尊的慣例,這一慣例在南宋時代被打破,《左傳》作為經部著作被編入了詩文選本之中,且主要是南宋理學家所為,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文學景觀。隨后,他深入揭示了這種文學景觀賴以生成的文化動因,如北宋的“疑經棄傳”思潮,南宋理學家對《左傳》文理文風的推崇,南宋進士科的現實需求以及宋代“《文選》學”的衰落等等,都對編選《左傳》風尚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如此透過文學的表象,深挖其思想史以及現實需求的本質,確實表現了不俗的學術功力。
張一南博士的《晚唐齊梁詩風的詩體結構》一文雖然研究的主體對象是晚唐詩人群及其詩風,但是,由于其論題關涉齊梁,故可視為對《選》學的拓展性研究,對于我們認識南朝文學的特質是有幫助的。她指出,晚唐齊梁詩風的詩體結構可通過聚類分析的方法,具體給出每一位詩人在詩體結構系統圖中的位置。這些詩人可分為舊式詩人與新式詩人兩大類。前者以關隴集團后裔為主,創作結構完整而忠實于齊梁舊體;后者以士族和寒素為主,創作結構殘破而傾向于新體。在論文中,一南采取了數理統計的方法,得出了可靠的結論。這篇文章是其關于齊梁、晚唐詩歌的系列研究成果之一,讀者如果和她即將在《文藝理論研究》、《云南大學學報》等刊物上發表的論文一同觀賞,則對其所言所論能夠獲得更為具體的感受。這篇文章沒有涉及具體的文獻材料,甚至所研究的詩人名字也并未完全呈現在我們面前,但由于作者成竹在胸,且與即將發表或已經發表的成果互相配合,必然能夠取得很好的研究效果。
《文選》的魅力是無窮的,《選》學的話題也總是說不盡的。
2015年7月5日夜記于京城嘯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