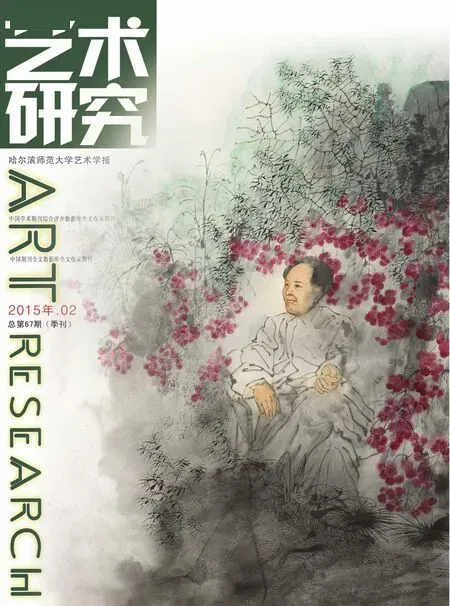默斯·坎寧漢先鋒派藝術的創新之處
曹圣迪 冮 毅
默斯·坎寧漢先鋒派藝術的創新之處
曹圣迪 冮 毅
藝術要與時代同步,現代舞奠基一代的舞蹈家,接受了社會動蕩以及戰爭的洗禮,舞蹈不再僅僅具有浪漫主義色彩,而是更多地體現出對人性的關懷。20世紀50、60年代,以坎寧漢為代表的新一代的現代舞蹈家通過不斷反叛前人的藝術,進而形成更為獨特的舞蹈思想和形式。他們的藝術既與傳統藝術有聯系又區別于傳統。
機遇 變革 東方哲學思想
20世紀50年代,西方現代舞進入了一個開放與自由的時期。藝術家或通過自我實踐,或是經過大師培養起來的年輕一代的現代舞家,他們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兼備傳統與變革,逐漸形成具有個人風格的藝術流派和訓練體系。處于在傳統現代舞和后現代舞兩個時代之間的默斯·坎寧漢,對現代舞的發展起到了承上啟下的巨大作用。他吸取眾家之所長,不斷完善形成了“坎寧漢體系”,并將東方的哲學思想與西方的現代舞相結合創造出了“機遇編舞法”。坎寧漢一生都在追求著永恒的“變”化,不僅是舞蹈,還涉及音樂和舞美等方面。他的“變”化將現代舞推向更高的領域。
一、默斯·坎寧漢訓練體系的創新之處
默斯·坎寧漢訓練體系的創新之處就在于他借鑒了各家訓練體系的優勢,將現代舞與芭蕾與相融合。一方面,他吸取了老師瑪莎·格雷姆以呼吸為原動力的“收縮—伸展”訓練體系中的精髓,格雷姆認為,“舞蹈需要技術,舞蹈家需要接受訓練。只有身體具有一定的可塑性之后,進而才能對自我的本質進行開發”。她的訓練體系以呼吸為基礎,以脊椎為軸,身體進行扭轉或收縮與伸展,她的作品常以這種緊張的收腹之后,脊椎強有力的伸展,來傳達出人性的沖突。坎寧漢訓練體系中十分重視脊椎下部的中央平衡點,他認為只有把握這個中央平衡點,身體就像彈簧一樣,可屈可伸。
另一方面,默斯·坎寧漢訓練體系的另一個創新之處就在于他吸收了芭蕾舞訓練的精髓,從先驅一代到奠基一代現代舞家,芭蕾和現代舞一直處于“對立”的狀態,先驅一代舞蹈家伊莎多拉·鄧肯,她認為,“芭蕾舞的美學是對女性人體的束縛與摧殘,只有身體自由才能達到心靈上的自由和精神上的自由”。在自然狀態下舞動是鄧肯所向往的。所以,她所追求和渴望的舞蹈藝術就與當時的芭蕾藝術是背道而馳的。而奠基一代舞蹈家處于一個社會動蕩的時期,她們經歷了戰爭,所以她們的藝術就放棄的浪漫主義色彩、芭蕾舞的輕盈和在空間中優雅的身體線條。瑪莎·格雷姆認為只有赤足踏地,強硬的身體線條和人體能量的釋放,才能表達出她的內心狀態。她認為傳統芭蕾藝術是外在化的,也就是形式美。在現代舞和芭蕾舞這樣一個對立的局面下,坎寧漢對芭蕾藝術沒有進行全盤否定,而是吸取了芭蕾舞中快速靈活的腿部訓練技巧。因此,形成了“坎寧漢體系”中的背部與軀干粗獷有力且表現自由和腿部的快速靈活。比如《空間點》中,從舞者腳下的動作,從走到跑再到跳,都可以看出他對芭蕾腿部技巧的運用,但又不拘于芭蕾藝術的形式,而上半身的弓身動作也體現出他對格雷姆訓練體系的繼承。坎寧漢借鑒各家之長,形成了獨特的現代舞訓練體系,直到現在,坎寧漢訓練體系仍是美國現代舞五大訓練體系的重要流派之一。
二、默斯·坎寧漢舞蹈創作的創新之處
任何一位具有創造性的舞蹈家,他的創造精神都來自于對生活的理解、人生閱歷和文化底蘊。坎寧漢的創造靈感來源于影響了中國數千年的哲學著作《易經》,從音樂家凱奇那得到了本英譯的《易經》,并參悟其道,可見坎寧漢是一位具有深厚文化修為的藝術大師。《易經》揭示出世間萬事萬物皆“變”的發展規律,“無極生有極,有極生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演八卦,八八六十四卦”,在偶然之中蘊藏著必然。坎寧漢深受《易經》哲學思想的影響,創造了“機遇編舞法”。在舞蹈編創過程中,以擲骰子、抽簽的方式來安排演員的動作、空間、時間和方式。如坎寧漢在《偶然組舞》中,就運用了八卦的概念,將空間分為了六十四塊。再用“機遇”的方法決定節奏和動作在空間中的連接順序。
格雷姆認為,現代舞是“某種觀念的顯示”,是“內心圖畫和視覺化”的展現。“機遇編舞法”的創造使坎寧漢擺脫了格雷姆藝術中緊張沉重的肢體語言和對戲劇性的強烈追求,建立了屬于他自己的“純舞蹈風格”。他認為,“舞蹈就是舞蹈,動作本身就有含義”。他說:“動作之外的東西與舞蹈毫不相干,某個特定的舞蹈并不源于我對某個故事、某種心情或某種表達方式的構思,這個舞蹈的容量源于運動本身。”這就致使他的純舞蹈風格具有以下幾方面的特點:沒有故事和情節;舞蹈注重時間結構;坎寧漢的舞蹈是根據一系列的舞蹈動作,再通過機遇的方式去排列順序,這種編創方式就帶來了坎寧漢舞蹈的抽象性。
默斯·坎寧漢還是一位與時俱進的藝術家,90年代,社會已經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電子計算機時代,已經70歲的默斯·坎寧漢,并未停止對藝術的追求和創新,他用計算機來代替了抽簽的方式,將科技引入了舞蹈中,改變了傳統的編舞方法,為“機遇編舞法”融入新的概念,去除了傳統編舞的邏輯性的束縛。
三、默斯·坎寧漢對舞蹈音樂與舞美的創新之處
默斯·坎寧漢打破了傳統意義的舞臺空間,他使音樂、舞美與舞蹈之間的關系從從屬的地位中獨立出來。在這一變革中一定要提到與之合作的兩位先鋒派藝術家就是約翰·凱奇和羅伯特·勞申伯格。
1.與約翰·凱奇的“機遇”音樂合作的創新
約翰·凱奇是20世紀美國著名先鋒派音樂家和哲學家。他的哲學思想和藝術都對默斯·坎寧漢的影響頗大,20世紀40年代,他開始將佛教禪宗思想和東方的哲學思想融入到了他的音樂創作中,進而創造出了“機遇音樂”,這與默斯·坎寧漢的“機遇編舞法”有異曲同工之處。首先,他打破了傳統音樂的作曲技法和演奏方法,他用《易經》中求卦的方式,投擲數萬次硬幣來創造音樂。其次,在約翰·凱奇的演出過程中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如約翰·凱奇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即無聲的作品《4分33秒》,此樂曲總長度4分33秒,而樂譜中一個音符都沒有,演奏者只是盯著鋼琴,通過三次開合琴蓋來向觀眾示意音樂的三個章節,作品的含義是請觀眾體會在寂靜之中由偶然所帶來的一切聲音。這個作品也就體現出約翰·凱奇對于禪宗思想“空”的理解與追求。約翰·凱奇也是因為這個作品被稱之為“無聲音樂”的開創者。
他與默斯·坎寧漢合作的《空間點》不僅是坎寧漢80年代的代表作品之一,也是能表現約翰·凱奇對于“空”的禪宗思想的追求。在舞蹈中,坎寧漢關注的是動作在空間中“量”的變化,音樂家凱奇在這個舞蹈中使用的是《無聲的論文》,這個作品沒有旋律,只有些聲響,這也體現出約翰·凱奇獨特的藝術風格。
約翰·凱奇的“機遇音樂”和坎寧漢的“機遇舞蹈”都是對傳統藝術的推翻,并把音樂和舞蹈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二人密切合作了半個世紀,直到1992年8月凱奇去世。
2.與羅伯特·勞申伯格的拼貼藝術合作的創新
羅伯特·勞申伯格,美國波普藝術代表人物之一。勞申伯格說“繪畫是藝術也是生活,兩者都不是做出來的東西,我要做的正處于兩者之間。”人們之所以稱羅伯特·勞申伯格的藝術稱之為“拼貼藝術”。是因為在創作過程中,他常將生活中的各種物品、包括廢物,集合到一起,并加以繪畫和拼貼。比如《床》這個作品就是勞申伯格在生活中的用品,枕頭和被上加以繪畫創作而成的,勞申伯格用這類的作品打破了藝術和生活的界限,他用他的拼貼藝術打破了傳統意義上人們對于藝術品的認識。
羅伯特·勞申伯格與約翰·凱奇在創作中相互影響,勞申伯格受凱奇禪宗思想的影響,創作了《空白的畫》,而凱奇則因為這幅畫,從中得到靈感,創作了著名的《4分33秒》。勞申伯格與坎寧漢在藝術上也進行了多次的合作。他也將拼貼藝術還運用在了坎寧漢的舞作中,如《故事》中,他用后臺雜物拼貼稱演員的服裝道具。又比如他會用自己的畫作為舞臺的背景等等。這三位藝術家在藝術探索上的卓越合作,給予后輩以極大的啟發。在傳統的編創過程中,音樂、服裝、道具、舞美等等都會根據編創者的想法進行創作、修改和磨合。而坎寧漢在與其他藝術家合作時,都是獨立進行創作,他給予其他藝術家更多的空間,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也就給他的舞臺藝術帶來更多的可能性,在舞臺上會發生的一切都是未知數。
綜上所述,縱觀現代舞的發展歷程,每一次藝術上的變革都是因為時代發展、社會進步所帶來的個人審美發生改變,從而引發了藝術實踐的變革。更新一代的舞蹈家不滿于照搬傳統,而是勇于打破傳統。坎寧漢一生都在追尋著“變化”,即使步入古稀之年,仍然投身于舞蹈事業中。他用他的創新豐富了現代舞的訓練體系,用他的實踐給予舞蹈新的詮釋和形式,以機遇的方法和先鋒的風格給舞蹈帶來了無限的可能性,奠定和推動了現代舞的發展。
[1]劉青弋.西方現代舞史綱[M].上海音樂出版社,2004.
[2]錢文艷.羅伯特·勞申伯格“結合”藝術中的美學[J].藝術教育,2011(07).
[3]呂藝生.舞蹈學導論[M].上海音樂出版社,2003.
作者單位:哈爾濱師范大學音樂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