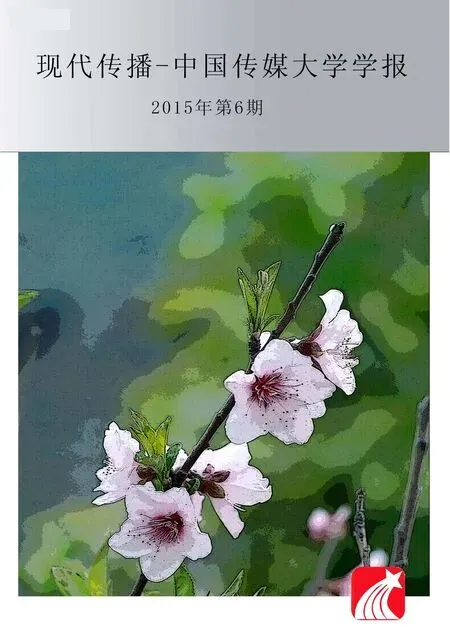網(wǎng)絡(luò)時代的社區(qū)媒體:城市整合的紐帶*
■ 陳娟
網(wǎng)絡(luò)時代的社區(qū)媒體:城市整合的紐帶*
■ 陳娟
對當(dāng)下中國而言,互聯(lián)網(wǎng)對傳統(tǒng)媒體的打擊與現(xiàn)實(shí)社會對城市整合的強(qiáng)烈需求糅雜在一起,共同推動著社區(qū)媒體的出現(xiàn)。本文從社區(qū)媒體的學(xué)理依據(jù)、歷史使命、誰來介入、實(shí)踐路徑這四個層面,對其進(jìn)行了學(xué)術(shù)梳理,并指出,社區(qū)媒體的發(fā)展必須與現(xiàn)實(shí)背景緊密結(jié)合,就當(dāng)下針對外來務(wù)工人員的社區(qū)媒體而言,最有可能的傳播渠道是微信公眾號和廣播,傳播內(nèi)容則是這一群體融入社區(qū)和城市所需的各種信息。
社區(qū)媒體;共同體;媒體轉(zhuǎn)型;心理認(rèn)同
在菲迪南·滕尼斯的《共同體與社會》中,共同體的類型主要是在建立在自然的基礎(chǔ)之上的群體(家庭、宗族)里實(shí)現(xiàn)的,此外,它也可能在小的、歷史形成的聯(lián)合體(村莊、城市)以及在思想的聯(lián)合體(友誼、師徒關(guān)系等)里實(shí)現(xiàn)。①按照社會心理學(xué)家阿米泰·埃奇歐尼(Amitai Etzioni)的概念,社區(qū)指具有共同價值取向和共享社會意義的社會關(guān)系所組成的網(wǎng)絡(luò)。②從兩個學(xué)者對社區(qū)的認(rèn)知來看,社區(qū)應(yīng)是整個社會的基本組成單位,其穩(wěn)定性直接關(guān)乎社會的穩(wěn)定性。
對當(dāng)下中國而言,相當(dāng)一部分社區(qū)并不是共同體。按滕尼斯的定義,共同體建構(gòu)是一個自然、緩慢的過程,它顯然無法應(yīng)對當(dāng)下中國的城市建設(shè)。這就在城市化進(jìn)程中涌現(xiàn)了諸多矛盾,其中最重要的是,被現(xiàn)代化進(jìn)程所卷入的大量農(nóng)業(yè)轉(zhuǎn)移人口,他們已經(jīng)成為城市社區(qū)的一個組成部分,但由于缺乏共同體的建構(gòu),他們的流動性要遠(yuǎn)遠(yuǎn)高于穩(wěn)定性。從實(shí)際觀察來看,這種流動性還在不斷加大。③流動性造成了社會不穩(wěn)定,2014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國務(wù)院印發(fā)《國家新型城鎮(zhèn)化規(guī)劃(2014—2020年)》指出,在城鎮(zhèn)化快速發(fā)展過程中,存在一些必須高度重視并著力解決的突出矛盾,其中之一就是“大量農(nóng)業(yè)轉(zhuǎn)移人口難以融入城市社會,市民化進(jìn)程滯后”。
一、社區(qū)媒體的學(xué)理依據(jù)
1998年起,桑德拉·鮑爾-洛基奇(Sandra Ball-Rokeach)帶領(lǐng)的南加州大學(xué)安能博格傳播學(xué)院(Annenberg School for Communication)的一個課題小組在以人口、文化的多樣化而著稱的洛杉磯市展開一項(xiàng)試圖弄清在21世紀(jì)如何建設(shè)地方社區(qū)的大型研究。④該研究關(guān)注移民們的社區(qū)歸屬感,并探討了有關(guān)傳播技術(shù)與城市社區(qū)的一系列問題。⑤
2013—2014年,本文課題組對珠三角廣州、佛山、深圳、珠海、中山、東莞這六個城市的調(diào)研顯示:社區(qū)的穩(wěn)定性不足以成為城市整合所面臨的最大難題之一,如犯罪率上升、城市管理難度加大等;對于企業(yè)來說,共同體的缺失直接導(dǎo)致用工困難,以往憑借血緣共同體、地緣共同體來完成的招工已解體,新的共同體尚未建構(gòu);而對于城市外來者而言,共同體的缺失導(dǎo)致其社會關(guān)系斷裂,無法完成自身的社會認(rèn)同,失序開始出現(xiàn)。⑥
在中國,城市整合通常被視作公共管理問題。學(xué)者們通常將農(nóng)業(yè)轉(zhuǎn)移人口城市化的障礙劃分為制度壁壘、城市無力承擔(dān)巨額成本、農(nóng)民工素質(zhì)欠缺、生活方式不融合、農(nóng)民自由土地?zé)o法自主買賣等多個視角。以上視角各有其解釋邏輯,但共同問題在于結(jié)構(gòu)功能主義,而結(jié)構(gòu)功能主義的缺陷在于:以結(jié)構(gòu)和功能的方法研究農(nóng)民工,所呈現(xiàn)出的各類問題及分析、解決問題的方案基本呈現(xiàn)“頭痛醫(yī)頭、腳痛醫(yī)腳”的弊病。⑦
新制度主義認(rèn)為,變遷由小變化層層累積而成,外界沖擊也不是必然地帶來組織的變化,而是通過組織內(nèi)部人員認(rèn)知框架和權(quán)力形態(tài)的變化來產(chǎn)生變化。從這個角度出發(fā),要完成外來務(wù)工人員的城市整合,必須要進(jìn)入傳播學(xué)的框架,這也是桑德拉·鮑爾-洛基奇在“媒介系統(tǒng)依賴論”基礎(chǔ)上發(fā)展出的“傳播基礎(chǔ)結(jié)構(gòu)論”。
北卡羅萊納教堂山分校的趙克·勞特瑞(Jock Lauterer)也認(rèn)為,“社區(qū)媒體是美國邊緣群體所能獲得的一個基本救助”⑧。“社區(qū)報紙作為一種連接紐帶日復(fù)一日持續(xù)報道社區(qū)的點(diǎn)滴成就來創(chuàng)造居民之間感情的紐帶,讓公民知道每個人都是社區(qū)的財富,你的付出和參與對社區(qū)很重要,對民主社會的維系也是不可缺少的。”⑨工業(yè)革命至今,人類在農(nóng)業(yè)社會中所培育出來的人際網(wǎng)絡(luò)已經(jīng)被現(xiàn)代社會的各種組織機(jī)構(gòu)所取代,但是,在一個剛剛被城市化的地區(qū)(如中國絕大部分的新興城市),如何建立社區(qū)(包容感和歸屬感)?這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這些新來者以何種親近感、認(rèn)同感與該地區(qū)建立情感上的聯(lián)系?應(yīng)該說,鮑爾-洛基奇及其課題組為我們研究大眾傳媒在中國現(xiàn)代化轉(zhuǎn)型期的社會整合提供了一個鮮明的視角:“歸屬(感)”——依戀感和睦鄰行為——是社區(qū)建構(gòu)的最重要要素⑩,而這種建構(gòu)應(yīng)該通過“傳播”來完成。
二、社區(qū)媒體的歷史使命
在已完成和正在進(jìn)行的城市化進(jìn)程中,在相當(dāng)多的國家和地區(qū),社區(qū)媒體幫助建立、培育并維系了社會,但這種緊密的關(guān)系不可能突然發(fā)生,它必然要經(jīng)過長期培育。對照中國社會,媒體的這一功能顯然缺失,這也意味著,今天中國的社會缺乏媒體這一子系統(tǒng)的粘合。我們認(rèn)為,媒體的這一方向和功能是部分國家、地區(qū)的媒體在面對互聯(lián)網(wǎng)沖擊,將自身的鮮明特征與社區(qū)結(jié)合,致力于服務(wù)特定社會需求的結(jié)果,不僅能創(chuàng)造新的業(yè)務(wù)增長點(diǎn),還能作為公共資源,幫助社區(qū)人民建立情感上的聯(lián)系。
雖然世界各地的局部沖突和悲劇一再重演,但對絕大部分民眾而言,他們生活在一定的區(qū)域內(nèi),只強(qiáng)調(diào)“對某個特定社區(qū)的服務(wù)性和歸屬感”的媒體為自己帶來的服務(wù)。因此,自1996年以來,雖然美國的紙媒發(fā)行量在持續(xù)下滑,但社區(qū)媒體的數(shù)量和發(fā)行量卻在持續(xù)增長:2013年,美國西班牙語報紙(均為社區(qū)媒體)發(fā)行量增長超過30%。在臺灣,一份名為《月光山》的社區(qū)雜志將美農(nóng)地區(qū)的居民(及美農(nóng)出生但現(xiàn)在在外的人員)緊密聯(lián)系在了一起,成為社區(qū)代議機(jī)構(gòu),根植于居民心中。雖然前者取向?yàn)樯矸菡J(rèn)同,后者為地方文化認(rèn)同,但我們必須看到,在規(guī)模擴(kuò)張的現(xiàn)代社會中,社區(qū)媒體之于共同體的建構(gòu)及社會穩(wěn)定性的意義。
臺灣學(xué)者林福岳曾針對社區(qū)媒體的定義提出不同觀點(diǎn),他認(rèn)為應(yīng)該擺脫傳統(tǒng)功能論的視角來看待社區(qū)媒體,簡單而言,并不是去解答“媒介可以為社區(qū)做什么?”,而是將自己視為社區(qū)的成員,站在社區(qū)的立場去問“社區(qū)需要什么樣的媒介?”(11)在此基礎(chǔ)上,劉忠博發(fā)展了社區(qū)媒體理論,他認(rèn)為社區(qū)成員已跳脫“決定自己需要什么媒介”的層次,而是邁向他們自己意識到“自己能成為社區(qū)媒體的一份子”。(12)趙克認(rèn)為,社區(qū)報的主要功能有以下幾點(diǎn):監(jiān)督政府,使公民知曉當(dāng)?shù)卣倪\(yùn)作,這是民主社會媒體的首要職責(zé);通過持續(xù)報道當(dāng)?shù)匦侣勑纬傻纳鐓^(qū)歸屬感,報道普通人的生活讓個人價值得以實(shí)現(xiàn);信息透明和公開有助于為公民提供生活指南,使公民更有效參與社區(qū)活動;作為公眾論壇,社區(qū)報紙不僅要對當(dāng)?shù)厥挛锉磉_(dá)觀點(diǎn),引發(fā)討論更是給普通公民創(chuàng)造發(fā)聲的機(jī)會;社區(qū)報紙對讀者的重要性還體現(xiàn)在提供商業(yè)信息——廣告,報紙必須成為當(dāng)?shù)匦∩虡I(yè)的重要幫手。(13)這些社區(qū)媒體的功能都與當(dāng)下中國的現(xiàn)實(shí)需求密切相關(guān),可以幫助新興城市完成一個個共同體的建構(gòu),從而達(dá)到社會穩(wěn)定的功能。
中國學(xué)者也已發(fā)現(xiàn)了這一走向,如李良榮提出《中國社區(qū)媒體:建構(gòu)社會生活共同體》,陳凱將趙克的理論介紹至中國,趙樂樂、冉華發(fā)表《美國社區(qū)新聞思想流變》。但從目前國內(nèi)這一領(lǐng)域的現(xiàn)有研究來看,則存在以下問題:(1)更偏重社區(qū)媒體的商業(yè)研究;(2)以介紹性材料為主;(3)社區(qū)媒體在中國的本土化研究存在缺失。當(dāng)然,在這一并不繁榮的領(lǐng)域中,也有學(xué)者提出,社區(qū)媒體是否是拯救報業(yè)危機(jī)的有效手段?可以這么表達(dá):在當(dāng)下中國的學(xué)術(shù)界,社區(qū)媒體的生存和發(fā)展空間已呈現(xiàn),然而,其本土化及本土化之后的發(fā)展方向依然是個未知數(shù)。毫無疑問,作為介質(zhì),社區(qū)媒體在“是否能充當(dāng)城市整合的紐帶”已獲得了肯定回答,然而,如何充當(dāng)?桑德拉·鮑爾-洛基奇的研究結(jié)果顯示,每個地區(qū)都有一個獨(dú)特的傳播基礎(chǔ)結(jié)構(gòu)(a unique 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這一研究發(fā)現(xiàn)警示決策者在社區(qū)建設(shè)中不能采用千篇一律的策略(14)。但基于傳播基礎(chǔ)結(jié)構(gòu)理論而誕生的社區(qū)媒體,如何才能扮演好城市整合的紐帶角色?目前看來,社區(qū)媒體需要具有受眾主體自我性質(zhì)的社會組織和其他介入方(如投資方)的合作,并將其視角切換為組織社會學(xué),對媒體本身與社會環(huán)境的結(jié)構(gòu)性關(guān)系有一定的通盤考慮,在此基礎(chǔ)上開展社區(qū)媒體的組織、運(yùn)行和互動。
當(dāng)然,與臺灣、美國不一樣的是,當(dāng)下中國的社區(qū)媒體還面臨的一個任務(wù)是:從工業(yè)化的社會基礎(chǔ)出發(fā)來重構(gòu)社會——基于現(xiàn)實(shí)的需求和發(fā)展的特殊性。
三、社區(qū)媒體的介入者
即便在五、六年前,仍處于“瘦死的駱駝比馬大”狀態(tài)下的傳統(tǒng)媒體還未形成對社區(qū)媒體的看好。今天,中國已有相當(dāng)一部分傳媒集團(tuán)關(guān)注到社區(qū)對自己業(yè)務(wù)的影響力,如浙報集團(tuán)布局“新聞+娛樂+社區(qū)化”全媒體平臺,這也已成為傳統(tǒng)媒體的發(fā)展共識。但從功能、使命而言,這種媒體轉(zhuǎn)型及其功能設(shè)置已和傳統(tǒng)媒體本身的關(guān)系不再呈現(xiàn)相關(guān),而是在新興社會的階層發(fā)展中重新發(fā)展出的一種新的傳播模式。那么,傳統(tǒng)媒體為何要介入這一對自身來說意味著艱難轉(zhuǎn)身的新業(yè)務(wù)?
2014年6月,芝加哥大學(xué)布斯商學(xué)院經(jīng)濟(jì)學(xué)教授馬修·根茨科(Matthew Gentzkow)獲2014年約翰·貝茨·克拉克獎(John Bates Clark Medal)。根茨科的研究指出,2008年到2012年間,雖然網(wǎng)絡(luò)媒體的閱讀時間大幅上升,但紙質(zhì)媒體的閱讀時間卻無顯著下降。這就是說,受眾對傳統(tǒng)媒體所提供的信息的需求并沒有發(fā)生顯著變化。這表示,傳統(tǒng)媒體近來的處境并不完全是由于信息消費(fèi)者向免費(fèi)的網(wǎng)絡(luò)媒體的叛逃,而是與廣告商向后者的遷移更為密切相關(guān)。(15)這也意味著,作為上百年以來的廣告載體,傳統(tǒng)媒體今天已逐漸被免費(fèi)的網(wǎng)絡(luò)媒體取代,傳統(tǒng)媒體的盈利已無法再從廣告中獲得。
因此,在未來相當(dāng)長一段時間內(nèi),在互聯(lián)網(wǎng)已得到普及的國家、地區(qū),只有極少數(shù)特別優(yōu)秀的傳統(tǒng)紙媒才能憑其專業(yè)、卓越的信息供給來維系地位——當(dāng)然,盈利方式也將發(fā)生根本性顛覆(如收取訂閱費(fèi)、提供專門信息),剩下的絕大部分傳統(tǒng)紙媒,則在喪失信息供給地位后喪失廣告商。雖然在上個世紀(jì)90年代中期至2005年前后的媒介高速發(fā)展期,中國的傳統(tǒng)媒介僅憑“信息平臺”便可獲廣告商的親睞,但很快,部分傳統(tǒng)媒體因喪失廣告商而闖入“信息尋租”路,其慘烈不言自喻。我們可以清晰看到,自2010年來,絕大部分傳統(tǒng)媒體使用廣告“斷崖式”下跌為自己的前途做注釋。從這個層面來說,傳統(tǒng)媒體的這一轉(zhuǎn)型具有深刻的社會意義。對于被互聯(lián)網(wǎng)所沖擊的絕大部分傳統(tǒng)媒體而言,在失去傳統(tǒng)的盈利模式和渠道后,社區(qū)化參與共同體的建構(gòu)及城市整合并不失為一個方向。
針對珠三角六個城市外來務(wù)工人員的訪談顯示,外來務(wù)工人員認(rèn)為,本地居民對外來者的容忍度隨時間的推移而不斷降低,換句話說,本地居民在上個世紀(jì)80年代時對外來者的接納度要高于現(xiàn)在。有被訪者表示,“這可能是當(dāng)時他們和我們的差距不算大吧”“或者他們那時候還不知道怎么歧視我們”,但隨著城市和農(nóng)村、大城市和小縣城的差距逐漸拉大,城市所能獲得的公共資源越來越豐盛,本地居民和外來人口之間的鴻溝也在不斷加大,從而導(dǎo)致外來務(wù)工人員融入城市困難。而另外一個有意思的現(xiàn)象是,外來務(wù)工人員認(rèn)為,本地居民對受教育程度較高者的接納度要高于受教育程度較低者,而受教育程度較高者自己也認(rèn)為本地人排斥他們的程度不高。在隨后課題組針對本地居民的訪談中,以上觀點(diǎn)卻被本地居民否認(rèn)了,“他們剛來打工的時候老老實(shí)實(shí)的,就是賺錢回家蓋房子、娶老婆,現(xiàn)在呢,啥壞事都干!你們?nèi)タ纯闯鲎馕菥椭懒恕!薄霸刮覀兛床黄鹚麄儯渴撬麄冏约鹤隽俗屓丝床黄鸬氖掳桑 ?/p>
在這里,身處同一區(qū)域的不同居民之間的矛盾由于溝通不暢而產(chǎn)生、循環(huán)并被打上成見,解決他們之間的傳播偏向是當(dāng)下社區(qū)媒體亟待解決的問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當(dāng)下中國社會的流動性要大于穩(wěn)定性(尤其在新興城市),中國傳統(tǒng)媒體的社區(qū)化將與美國有著極大的差異,怎樣社區(qū)化,在不同社區(qū)制定不同的社區(qū)化方向,這些都是未來的社區(qū)媒體必須考察的問題。此外,調(diào)研也發(fā)現(xiàn),由于大部分的新興城市居民(或外來者)在涉及社區(qū)的基本需求和訴求上缺少共同性,這也為社區(qū)媒體在中國的發(fā)展帶來了新的挑戰(zhàn),如何在諸多需求中覓得平衡?雖然所有的被訪者都認(rèn)為需要一份針對自己的專門媒體,但他們對媒體的方向和自身的需求仍然迷茫。這就意味著,社區(qū)媒體的介入方需要重新認(rèn)識新時代條件下外來者的社會肌理和未來前景,并將這一群體的訴求進(jìn)行整理、發(fā)布,并與社會進(jìn)行溝通。
四、結(jié)語:社區(qū)媒體的實(shí)踐路徑
從調(diào)研結(jié)果來看,現(xiàn)階段珠三角地區(qū)外來務(wù)工人員的訴求集中尚處在“希望被接納”,遠(yuǎn)未上升至“媒體可以為我做什么”階段,更未至“參與城市管理”。這就為現(xiàn)階段的社區(qū)媒體指明了一個方向:進(jìn)行社會關(guān)系的“建構(gòu)”,至少讓這些外來務(wù)工人員意識到當(dāng)下各級職能部門為他們的社會關(guān)系所付出的種種努力——雖然這些努力的效果目前甚微。針對各地職能部門的調(diào)研顯示,由于我們所調(diào)研的這六個城市均屬于發(fā)達(dá)地區(qū),地方政府在外來務(wù)工人員的市民化進(jìn)程建設(shè)中的確做了相當(dāng)多的事,比如免費(fèi)借閱圖書,以非常低的價格觀看省級劇團(tuán)的演出(財政補(bǔ)貼后很多高層次的演出僅10塊錢一張票),有不錯獎品的群眾運(yùn)動會,針對外來務(wù)工人員子弟的社工一對一幫扶,積分落戶,等等,但從這些舉措的實(shí)際效果來看,這些“好事”很難被外來務(wù)工人員獲利,原因很簡單:“這事能落到我頭上?”讓外來務(wù)工人員看到各部門為他們?nèi)谌肷鐓^(qū)和城市所提供的各種信息應(yīng)是當(dāng)下社區(qū)媒體發(fā)布的重要內(nèi)容之一,當(dāng)然,在此基礎(chǔ)上,培育他們對信息的接收、接受和使用能力,也是另外一個重要內(nèi)容。此外,讓外來務(wù)工人員初嘗社區(qū)媒體所帶來的各種便利和好處后,還可逐漸培養(yǎng)他們的表達(dá)能力——這將為他們充分掌握未來發(fā)展的話語權(quán)做準(zhǔn)備。
桑德拉·鮑爾-洛基奇領(lǐng)銜的《傳媒轉(zhuǎn)型》課題組認(rèn)為,因特網(wǎng)已經(jīng)成為更大的傳播結(jié)構(gòu)的一部分。在本課題小組的調(diào)研中,我們也發(fā)現(xiàn),媒介新技術(shù)改變了以往的社會關(guān)系模式,社交網(wǎng)絡(luò)的興起為外來者群體提供了“充分整合的人際模式”,也就是將這些被“脫域”的原子凝聚為一個集體——這個“集體”將個人處于一個個社會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中,起到分散、緩解壓力的作用。(16)對于這些外來務(wù)工人員而言,雖然大部分時候,互聯(lián)網(wǎng)所提供的社交網(wǎng)絡(luò)只能幫助這些新生代外來者虛構(gòu)自己的社會關(guān)系,提供一種類似鴉片式的虛擬環(huán)境,而無助于他們對這個社會進(jìn)行理性判斷,但從媒介的選擇來看,互聯(lián)網(wǎng)毫無疑問也已成為他們獲得各類信息的必要渠道。
與受眾對媒介的接受度及易得性相關(guān),以80后外來務(wù)工人員為核心受眾群的社區(qū)媒體或以公眾微信號為自己主要的內(nèi)容載體,但另一種低成本的傳統(tǒng)媒體也在實(shí)際調(diào)研中進(jìn)入了我們的視野:廣播。相對于其他的傳統(tǒng)媒體如報紙、電視而言,各地廣播媒體更樂意轉(zhuǎn)向社區(qū)媒體,這大致與前些年廣播媒體在報紙、電視的多重壓力下努力突破的姿勢有關(guān),也與普通公眾在收聽廣播時參與度較高,因而早早加入到了社區(qū)建構(gòu)的進(jìn)程相關(guān)。而對于外來務(wù)工人員較為集中的大型企業(yè)、社區(qū)來說,廣播還有助于企業(yè)文化的傳遞,幫助企業(yè)凝聚工人,因而得到了珠三角企業(yè)主的普遍贊賞。
由于社團(tuán)發(fā)育的不成熟,社區(qū)媒體的推廣還面臨著組織架構(gòu)的問題:這一新興的傳播模式不僅要結(jié)合都市報的傳播模式和組織社會學(xué)(19世紀(jì)英法的工團(tuán)主義)的架構(gòu),還要涉及投資結(jié)構(gòu)的可行性、受眾的組織性和自發(fā)性、廣告信息與生活環(huán)境的關(guān)系等等各種因素。
當(dāng)然,由于社區(qū)媒體在中國當(dāng)下的社區(qū)建構(gòu)和城市整合中還只是一個設(shè)想,本文的目的也只是試圖通過傳播來推進(jìn)社會中不同群體、階層之間的認(rèn)同與融合,但整體而言,在互聯(lián)網(wǎng)對傳統(tǒng)媒體的強(qiáng)勢沖擊與當(dāng)下迫在眉睫的現(xiàn)實(shí)需求下,社區(qū)媒體不失為傳統(tǒng)媒體轉(zhuǎn)型的一個新方向。
注釋:
① [德]菲迪南·滕尼斯:《共同體與社會》,林榮遠(yuǎn)譯,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0年版,第52頁。
②⑨(13) 轉(zhuǎn)引自豈凡:《最好的時代,最壞的時代——訪美國社區(qū)報研究專家Jock Lauterer》,《傳媒》,2010年第9期。
③ 通常,1980、1990年代出來打工的人群,他們對企業(yè)的忠誠度要高于現(xiàn)在的打工者;此外,近年來受過高等教育的外來者(如大學(xué)畢業(yè)后留在城市的學(xué)生)的流動性也遠(yuǎn)高于10多年前。
④⑤⑩(14) 王晨燕:《鮑爾-洛基奇的傳播基礎(chǔ)結(jié)構(gòu)理論分析》,中國傳媒大學(xué)第二屆全國新聞學(xué)與傳播學(xué)博士生學(xué)術(shù)研討會會議論文。
⑥ 課題組在廣州、佛山、深圳、珠海、中山、東莞這六個城市課題組的研究共發(fā)放2000份問卷,在2000個受訪對象中選擇了部分對象進(jìn)行深訪。在深訪中,課題組就“你在這個城市是‘陌生人’還是‘新來者’”“你與這個城市之間的關(guān)系”“你融入城市的方式”“你認(rèn)為媒體應(yīng)該如何幫助自己融入城市,在哪方面應(yīng)該突出”“你對城市的認(rèn)知來自媒體么”“進(jìn)入城市后你出現(xiàn)了哪些變化”“你對自己在城市中如何定位”“你覺得自己邊緣么?為什么”“你如何調(diào)節(jié)自己在城市中的邊緣化”“你希望下一代成為城里人么”“媒體對你融入城市有幫助么”等問題進(jìn)行了深入的詢問。訪談時間集中在2013年9-10月和2014年3月。
⑦ 在對以上六座城市相關(guān)部門政府官員進(jìn)行訪問后,課題組發(fā)現(xiàn),教育部門官員提出農(nóng)業(yè)轉(zhuǎn)移人口城市化,他們會提出一些針對性的措施,比如興辦農(nóng)民工子弟學(xué)校,送優(yōu)秀的外來務(wù)工人員讀書,但這些措施往往隔絕了外來者與本地區(qū)的聯(lián)系,根本無法幫助外來者融入城市;再比如各地興建的專門針對外來務(wù)工人員的公寓,也基本類似。
⑧ 此表述來自作者與趙克的私人郵件。
(11) 林福岳:《社區(qū)媒介定位的再思考:從媒介的社區(qū)認(rèn)同功能談起》,《新聞學(xué)研究》(臺灣),1998年第6期。
(12) 劉忠博:《“選擇”:當(dāng)社區(qū)媒體面對?同文化交匯之際——一個從美濃“月光山雜志”社區(qū)報的觀察》,中華傳播學(xué)會會議論文。
(15) 這部分內(nèi)容綜合自:《2014年克拉克獎揭曉》,http://economy.caixin.com/2014-04-28/100671465.html。
(16) 陳娟:《城市融合:媒介與新生代外來工的社會關(guān)系研究》,《南京社會科學(xué)》,2014年第4期。
(作者系華南理工大學(xué)新聞與傳播學(xué)院副教授、新聞傳播系主任)
【責(zé)任編輯:潘可武】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項(xiàng)目“大眾傳媒在中國現(xiàn)代化轉(zhuǎn)型期的社會整合功能研究”(項(xiàng)目編號:11YJC860003)、廣東省新媒體與品牌傳播創(chuàng)新應(yīng)用重點(diǎn)實(shí)驗(yàn)室項(xiàng)目“數(shù)字內(nèi)容產(chǎn)業(yè)與社會發(fā)展研究”(項(xiàng)目編號:2013WSYS0002)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