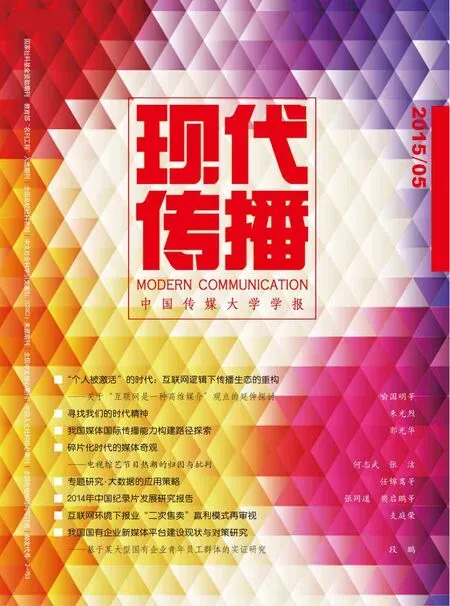大數據時代軍事外宣策略的三重維度
■ 周均
大數據時代軍事外宣策略的三重維度
■ 周均
在復雜的國際傳播格局中,“大數據”已成為世界各國對外展示、觀瞻的重要資源、技術和手段。中國軍事對外宣傳作為國家對外傳播戰略體系的重要組成,仍然以傳統媒體為采編環境和傳播平臺,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軍隊對外發聲效果。在這種情勢下,軍事對外宣傳理應逐漸跳出既定框限,以大數據時代的宣傳規律為準則,在宣傳思維、宣傳話語和宣傳路徑上打造新的對外宣傳格局。
大數據時代;軍事外宣;傳播效果;話語體系
隨著云計算、物聯網、互聯網技術的飛速發展,人類社會的數據量已經呈現出幾何級數增長,這些海量數據不僅在信息領域掀起了一場技術變革,在新聞傳播層面同樣開啟了一個以數據為特征的新時代——大數據時代。當前,社會各界都已把大數據作為行業發展的“金鑰匙”,以適應用戶的接受習慣。軍事對外宣傳作為我軍與國際社會的信息交流活動,也是以受眾思想、態度、行為的改變作為衡量宣傳績效的依歸,理應以大數據時代的傳播規律為標準予以調適,建構大數據時代的軍事對外宣傳新體系。
一、宣傳思維——樹立用數據“說話”的意識
長期以來,由于受技術等因素的限制,包括軍事外宣在內的眾多定量研究基本上都是依賴于抽樣數據、局部數據乃至片面數據,有的時候甚至直接依憑主觀臆想、經驗判斷去推測總體情況。隨著人類社會數據量的急劇增長,加之“隨機樣本”越來越難以框定,大面積的隨機抽樣已然捉襟見肘,“樣本=總體”的研究方法亟待提上日程。
1.更加重視“數據決策”的功能
目前,我軍對外宣傳取得了不少成效,尤其是在搶險救災、國際維和等非戰爭軍事行動中,往往會贏得國際社會好口碑。如在魯甸地震救災中,美聯社記者就稱軍隊行動速度比以前更快,“顯然,軍隊的人員、重型裝備到達災區很早,救援行動展開得很迅速。”①實際上,這種正面評價只是少數情況,更多的仍以負面為主,來源已久的南海爭端就是一個鐵證。長期以來,我軍宣傳決策以經驗判斷為依據的情況并不少見。南海輿論斗爭中,我軍一直秉持歐美國家重法律、東南亞國家重歷史的原則進行宣傳,但結果卻是歐美國家并不認可《開羅宣言》等國際法,而東南亞國家也并不承認我們所陳述的歷史。若引入大數據技術,對所有涉及到的對我軍評價的數據進行分析,就極可能發現以往僅靠經驗或慣例所發現不了的東西,比如哪些受眾更希望還原歷史,哪些受眾更希望遵循法律,如果再以這些結論去制定外宣計劃和方案,其價值將不言自明。
2.更加重視“相關關系”的架構
3.更加重視“混雜數據”的擷取
應當承認,科學化的軍事外宣計劃和方案必然包含著大量結構化、半結構化和非結構化數據,并且后兩者居于主要地位,如社交媒體上的文字、圖片、音頻、視頻等。如此混雜的數據似乎與軍事外宣的“精準性”背道而馳,實則不然,就像美國谷歌公司的翻譯,其之所以廣受世界各國人士青睞,并非擁有一個完美的算法,而恰恰是它接受了來自各處的數據。我軍外宣更多的是致力于國外主流媒體研究,對網民的碎片化數據則缺少相應關注。在對谷俊山、徐才厚等軍隊巨貪落馬的對外宣傳中,的確有不少外媒稱贊中共領導人推動反腐敗工作的決心,但外國民間輿論究竟為何卻不得而知。主流媒體固然是顯示國家傾向的主體工具,但民間輿論場同樣應是展示我軍形象的重要陣地。如果顧此失彼,軍事外宣必將面臨更大的宣傳真空。“如果不接受混亂,剩下95%的非結構化數據都無法被利用,只有接受不精確性,我們才能打開一扇從未涉足的世界的窗戶。”③
二、宣傳話語——尋求用數據“編碼”的信息
美國學者李普曼指出,圖畫一直是最有保證的傳遞思維的方式,其次才是喚起記憶的文字。④“大數據”時代,這一原則仍然適用,軍事外宣要有所建樹,更應對數據進行“可視化”編碼,即制作“數據新聞”,從而提升宣傳效果。
1.數據采集階段,正確處理公開與保密的關系
歐美國家媒體在數據采集方面一直扮演著“領頭羊”的角色,如《衛報》啟動“解讀倫敦騷亂”項目時,除深度訪談參與騷亂的人、警察、普通市民,搜集法庭審理騷亂案件資料及政府關于社會經濟狀況的統計資料外,Twitter上百萬條與騷亂相關的信息也成為重要的數據來源。可以說,這一點對軍事外宣有重要借鑒意義。
但囿于軍隊保密規定需要以及媒體性質本身要求,外宣媒體或很難采集相關數據,或采集到了也不敢隨意使用。因此筆者認為可從以下幾方面考量:一是從國內外政府、軍隊、企業獲取免費的、公開的、官方的數據;二是從用戶數據、自媒體、搜索引擎獲取社會的數據;三是從原創眾包、網絡觀察、實地調查中獲取數據;四是通過較強的數據分析能力和表現能力來彌補數據采集的限制。此外,采集數據還應盡可能采用自主創新工具。“棱鏡門”事件的曝光,實際上就說明過于依賴美國技術,反而會造成“反采集”的局面,某些關鍵信息一旦被其截取并用于外宣領域,對被截取國而言那將是致命打擊。
普通的紋理貼圖技術直接將顏色紋理映射到矩形表面。在光照下,得到的效果如圖11 所示。它使得原來單調的矩形表面有了更豐富的色彩,呈現出了紋理圖中木質地板的效果
2.數據處理階段,正確處理主觀與客觀的關系
價值密度低是大數據其中一個特點,意即在一大堆數據中有用的極可能屈指可數。因此,挑選出對我軍軍事外宣有價值的數據極有必要,比如代表受眾立場態度的數據、代表受眾接受習慣的數據、代表外軍宣傳做法的數據、代表外軍軍事行動的數據等等,過濾掉某些無效數據和失值數據。但由于很多相關信息單憑計算機是無法準確進行分類和排查的,特別是主觀性較強的數據,在計算機軟件進行初次排查之后就只能依靠人工判斷和識別。所以,我們的外宣工作人員應當加強對大數據處理能力的訓練,要弄清數據何時采集、為何采集、怎樣采集、有何作用,從而盡快適應和勝任軍事外宣新的工作任務。當然,數據處理不僅僅只是發現哪些數據有用哪些數據沒用,還要對留存的有用數據進行整合。只有將不同層次的數據進行比照、疊加、相互關聯,才能發現每個數據的深層含義,更好地發掘其中價值。
3.數據呈現階段,正確處理技術與藝術的關系
傳統新聞以文字為主、數據為輔,或數據與文字相輔相成,強調用文字講故事,而大數據時代的數據驅動新聞則是數據在先、文字在后,數據成為講故事的新工具,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新聞生產流程。⑤理論意義上的“數據新聞”是由大數據驅動的,將大數據思維和“可視化”技術鑲嵌在軍事外宣當中,是將外宣話語量化了的報道,是以數據作為表達形式的新聞,它的主要目的是揭示數據與社會、個人之間的重大而復雜關系。云南昆明“3·1”嚴重暴力恐怖事件發生后,人民網“圖解新聞”欄目以圖表的形式,將英國廣播公司、英國每日電訊報、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和美國福克斯新聞四大媒體對昆明事件和倫敦砍殺事件在新聞用詞(定性用詞、描述用詞)方面的區別清晰的呈現了出來,既有縱深感,又不乏知識性。這樣的數據呈現取得了迅速的宣傳效果,3月3日美國官方竟一改之前的措辭,聲稱云南昆明事件是“恐怖主義行徑”。
三、宣傳路徑——打造用數據“制勝”的形式
大數據時代,數據不僅是一種資源,也是一種技術,要有效利用這種資源,就應當正確使用這門技術,即挖掘大數據資源,將其轉化為有實際價值的技術。因此,軍事對外宣傳不僅要運用大數據話語,也應當打造大數據宣傳路徑,盡可能減少無效宣傳,提高命中率。
1.場域選擇由“面上覆蓋”轉向“對點投放”
從抽樣讀者調查到網絡投票統計,從部分外電摘編到專業輿情研究,雖然時代不同、手段不同,但是對外傳播工作從未停止為提高傳播針對性所做的探索。⑥應該說我軍對外宣傳是比較重視針對性的,比如“內外有別”“外外有別”等外宣原則,但即使把目標對象分為不同類別,類別之間、類別內部也需要厘清關系、區別差異,所以以往所倡導的針對性仍然不夠嚴密、科學。
微軟全國有線廣播電視公司網站開發用戶定制服務,即用戶可以按個人需求或喜好定制首頁新聞信息類型。受眾只需第一次登錄時勾選自身關注的新聞類型并保存即可,那么再登時定制界面會自動跳出。⑦顯而易見,若把大數據的這種預測功能運用到軍事外宣中,其宣傳效果絕非以往那種“面上覆蓋”所能相提并論。如不斷收集宣傳對象的引擎搜索軌跡、網頁瀏覽記錄、言論發表情況,從中篩選出對我軍軍事外宣有益成分,然后再為之設計“量身定制型信息”,在宣傳對象下次觸網的時候再及時“送貨上門”,是謂“對點投放”。
2.對象使用由“吸引受眾”轉向“吸收受眾”
以往的軍事外宣一般都將受眾當作“被動的接受者”,在對外宣傳流程上基本上也是以“設計內容、使用技巧、宣傳出去”的步驟為主,總體而言,主要是為了“吸引受眾”,以達到宣傳目的。在今天看來,僅僅把受眾視為單純的對象實際上是一種資源的浪費。
大數據時代,由于社會化媒體的連接,傳統意義上的受傳者與傳播者之間的閾限被打破。如果只是“一廂情愿”地單向宣傳,受眾也可以對我進行“反宣傳”,宣傳效果實際上已被其抵消殆盡。所以,盡管我軍軍事外宣隊伍龐大,但受多重因素影響,公信力、影響力、傳播力始終有限。當下,我軍軍事外宣亟需運用大數據技術吸收“受傳者”,再將其轉換為幫我們宣傳的“傳播者”。如通過挖掘、分析自媒體的大數據,吸收尋覓那些在涉軍敏感事件傳播中于我有利且具有一定影響力的“輿論領袖”,然后整合資源,向其推送我們想要傳播但落地率、致效率較低的信息,力求通過“二次傳播”擴大宣傳效益,從而實現對輿論的掌控。
3.效果評估由“厚積薄發”轉向“邊積邊發”
我軍外宣效果評估通常是在工作結束之后進行,如國防部網站是我軍外宣的重要陣地,但對其宣傳效果的評估往往是階段性的,可能是“一周”“一月”或“一年”,也可能是以某一具體事件(如國防白皮書的發布)發生后的一段時間。⑧即把前一階段所有的宣傳工作進行分析總結,爾后再以分析結果為標準組織下一場宣傳,呈現出“厚積薄發”的特點。然而,這種評估盡管可以形成周期性的經驗,但由于缺乏時效性,又不免會面臨“信息真空”等問題。
如果采用大數據技術,情況可能截然不同。某些信息發布之后,通過觀察和分析網站流量,確定在幾分鐘內這些信息引起了國外關注,最受關注的是哪些內容,哪些內容又得到了外國媒體的回應等等。換言之,引入大數據技術,可以輕松實現對宣傳效果的實時評估和監測,一旦發現于我不利的言論時,就可以立即推送出有針對性的文章,從而對謠言進行駁斥。顯然,這種“邊積邊發”型的效果評估方式更具靈活性和可操作性,有效回避了周期性評估“蓋棺定論”的弊病。
四、結語
大數據給軍事外宣提供的機遇可能遠不止這些,但應該承認,大數據并非萬能之物。首先,大數據是以“概率”說話,絕非精確無疑,畢竟大數據之中或多或少會摻雜失真數據。其次,心理學家認為,大數據創造的模型會將人束縛在算法提供的選項中,過度依賴大數據分析也可能束縛創新。美國互聯網活動家帕里澤稱之為“互聯網濾泡”:互聯網個性化雖然帶來方便,卻將人們局限在自己過往行為模式的“氣泡”中,無法觸及海量信息帶來的無盡可能。⑨
注釋:
① 藍雅歌、王天迷、柳玉鵬:《美媒:中國調動軍隊救災更快已調集中外18顆衛星》,《環球時報》,2014年8月7日。
②③ [英]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肯尼思·庫克耶:《大數據時代》,盛楊燕、周濤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8、38頁。
④ 宮承波、田園:《構建“微時代”的對外傳播體系》,《對外傳播》,2014年第6期。
⑤ 徐銳、萬宏蕾:《數據新聞:大數據時代新聞生產的核心競爭力》,《編輯之友》,2013年第12期。
⑥ 李志健:《試論如何利用大數據提高對外傳播的針對性》,中國網,2013年8月10日。
⑦ 薛中軍:《大數據時代美國新聞傳媒“裂變”效應的借鑒與啟示》,《新聞愛好者》,2013年第6期。
⑧ 陳飛:《大數據對軍事外宣的影響探析》,《軍事記者》,2014年第6期。
⑨ 李宓:《2013,大數據時代的“破”與“立”》,中國軍網,2013年12月17日。
(作者系解放軍南京政治學院軍事新聞傳播系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