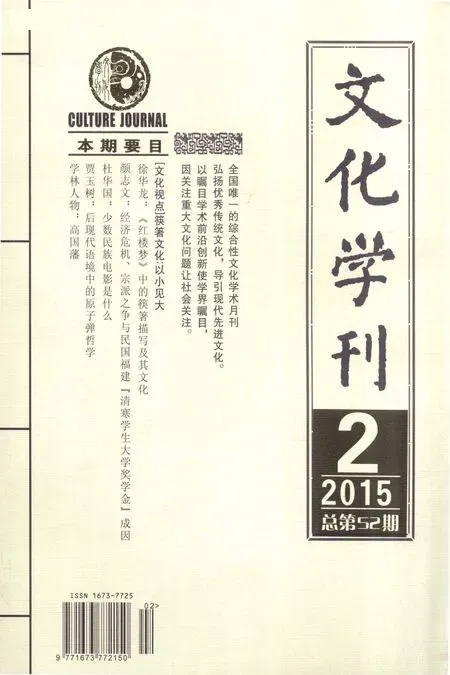從奧斯卡影片譯名中的外來語使用情況看中日兩國文化差異
王婷婷
(沈陽航空航天大學,遼寧 沈陽 110136)
作為文化娛樂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電影的主要受眾是年輕人。年輕人崇尚時尚、追新求異的心理特點決定了他們易于接受新生事物,是外來語的主要使用人群。為了迎合他們這一心理特點,電影譯名中包括外來語在內的新詞使用頻率較高,是外來語研究的重要語料。本文搜集了大量近年奧斯卡電影的中日譯名,分析其中的外來語使用情況,并著力探討外來語背后所折射出的兩國文化特征。
一、從電影譯名看漢語和日語的外來語特點
外來語一般指同使用不同語言的民族交往時,引入的指稱新概念、新思想和新事物,并經過本國語言改造的詞匯。關于外來語的具體界定,學術界尚無統一的定論。狹義的外來語概念只包括音譯詞,而廣義上的外來語概念則將意譯詞也包括在內。本文采用的是廣義的外來語概念,將意譯詞也作為漢語外來語加以考察。
(一)漢語的外來語使用情況
漢語外來語基本上使用漢字書寫(字母詞除外),除舶來色彩最濃厚的音譯詞外,大多數外來語與漢語的固有詞匯區分度不明顯,人們對其外來語身份常常習焉不察。不僅如此,漢語外來語的比例遠低于日語,相對于完善的漢語固有體系,外來語的作用只能說是錦上添花,對漢語的影響有限。鑒于以上原因國內漢語外來語詞典數量較少,使用普及率也不高。除專業人士外,很少有人專門購置。這一點在表1 中也得到了充分體現,25 個電影譯名中僅出現了9 個外來語,除“伴娘”“網絡”外,其余7 個“林肯、雨果、本拉登、安娜卡列尼娜、愛麗絲、派、巴黎”都是人名和地名。

表1 奧斯卡電影的中日兩國譯名
一般來說,外來語的吸收有音譯、意譯、音譯兼意譯等多種方式,“現代漢語的借詞存在著一種傾向,即抗拒音譯轉寫,而樂于接受部分音譯或全意譯”[1]這是由于漢字是意符文字,完全舍棄文字意義的音譯不符合中國人望文生義的思維習慣,在現代漢語中音譯詞往往只是外來語引入過程中的初級形式或過度形式,語形常處于不安定的狀態。蔡基剛指出“根據對《新詞新語詞典》和《現代漢語新詞詞典》的統計,外來詞中的音譯詞不足1.5%”。[2]音譯加類名等音譯兼意譯詞最受青睞,如“酒吧、爵士樂、雞尾酒、艾滋病、芭蕾舞”等,在音譯部分后加上表示詞義歸屬的類名,利于外來語的理解和記憶。《社交網絡》中的“網絡”一詞來源于英語“internet”,它在漢語中還有一個譯詞“因特網”,采用的就是此種方式。
此外,即使是完全音譯的人名、地名、物品名稱等外來語,也力求在字面意義上體現出某種意韻,在漢字的選擇上可謂煞費苦心。如“維他命、奔馳、可口可樂、托福”等詞就通過使用諧音吉祥文字既兼顧了原詞的發音,又順應了漢語的表達習慣。音譯時還常通過漢字的形符來指示詞義類屬,如“茉莉,袈裟、咖啡、檸檬、鉀、鋰、鋅、鐵”等,就是在聲旁表音的基礎上,選用和外來語意義相關的形符偏旁表意。再如外國人名的音譯,女性名字同男性名字使用的漢字不同,僅從漢字就可以判斷性別。女性譯名往往使用帶女字形符等漢民族女性名字常用字,如同樣是“ma”的音,“瑪格麗特、瑪麗、瑪麗蓮”等女性名字使用“瑪”字,有別于“馬克斯、馬克、馬修、馬丁”等男性名字的“馬”字。上表中“安娜卡列尼娜”“愛麗絲”中的“娜”“麗”“絲”等都是中國女性名字中的常見字。
(二)日語的外來語使用情況
眾所周知,日語中外來語數量眾多、來源廣泛、使用頻率高。在雅虎日本網站上輸入“外來語字典(日語為「カタカタ語辭典」)”檢索,顯示出一千多條相關商品鏈接,當中還有面向小學生的漫畫版外來語詞典,外來語在日本人生活中的重要位置可見一斑。據日本學者統計“在日語中,用片假名表記的西洋外來語一般占到12%,從中國借來的漢語詞匯占到44-45%,西洋外來語和漢語構成的混合語大約占到5%,而日語中的和語詞匯(日語固有詞匯)所占的比例不到40%”。[3]需要指出的是,雖然日語中的漢語詞匯來自漢語,但因其已經完全融入日語,與日語的固有詞匯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日本學界一般不將其納入外來語范疇。本文中的日語外來語僅指用片假名表記的西洋外來語。
日語外來語數量龐大這一特點在上表中也得到了充分的體現。25 個影片譯名都使用了外來語,這些外來語都以音譯的方式引入并用表音文字片假名書寫。從詞性角度考察,有名詞、形容詞,甚至還有直接音譯自英語的介詞、冠詞等。與漢語外來語多為名詞形成鮮明對照,日語外來語中存在大量形容詞和動詞,上表中的「ソーシャル(social)」「イングロリアス(inglourious)」「プレシャス(precious)」「ビューティフル(beautiful)」等都是形容詞。此外,來自英語不定冠詞“a”的「ア」出現了2 次、來自定冠詞“the”的「ザ」出現了4 次,分別譯自介詞“in”、“of”的「イン」「オブ」也各出現了2 次。名詞中有外國人名、地名的音譯,如「リンカーン(林肯)」「アンナ?カレーニナ(安娜卡列尼娜)」「ヒューゴ(雨果)」「アリス(愛麗絲)」等,也有從國外引入的新事物名稱,如「ネットワーク(網絡)」等。很多英語原詞用日語固有詞匯是可以翻譯的,但譯名中還是使用了外來語,如「マン(男人)」「アーティスト(藝術家)」「ツリー(樹)」「ライフ(生命)」等。引入外來語時,“一般都是以本國語言中是否存在著相應的詞匯為依據,對于本國語言中早已存在的詞匯則往往會有意識地避開,以避免詞匯量的盲目增多,然而日語在這方面的表現卻有些異乎尋常”。[4]不僅如此,一般認為語言的思維邏輯、語言結構(語序、語法、句型)等是最不容易受到外來文化影響的,但日語甚至將英語中的語法現象也直接用片假名音譯出來。上表中「バスターズ」「セッションズ」「キッズ」「ビギナーズ」就分別對應了英語的“barsterds”“sessions”“kids”“biginners”,「ウィンターズ」來自英語的“winter’s”把日語中本不存在的復數以及所有格“’s”的概念也引入進來。對詞組也是來者不拒,「オールライト」音譯自詞組“all right”。
二、從外來語使用情況看中日兩國的文化差異
語言總是植根于特定的文化之中,是文化的產物也是文化的載體。外來語是吸收外來文化的媒介,外來語的譯借方式和接受程度是文化交流在語言上反映,既是語言現象,也是文化現象。
(一)漢語的文化透視
中國是世界上文明最早的發源地之一,燦爛的古代文明源遠流長,直至近代以前,一直是領先于東亞、甚至整個東方世界的先進國家。中國文明亦稱華夏文明,以黃河流域為發源地,屬內向型內陸文明。華夏文明的締造者華夏民族(漢族舊稱)作為一個相對穩定的古代民族形成于秦漢時期。唐朝時中國國力達到鼎盛,華夏民族以高度發達的封建文明領先于世界,漢語是當時的通用語,漢字以及漢文化遠播至日本、朝鮮半島等地,形成了以漢文化為中心的“中國文化圈”,是東方文化圈的代表。中國文化生生不息地傳承發展,凝聚成無可比擬的文化熏陶力和征服力,面對外來文化時總是呈現出強大的同化能力。縱觀中國歷史,中國與古代的西域各國、印度以及現當代的西方都有過大規模的文化交流,甚至還曾被元朝的蒙古人和清朝的滿族人先后統治達數百年之久,但漢文化均藉由“其厚重密實的內殼抵擋住外來文化的入侵,并且反過來以其強大的涵蓋力包容、同化了外來文化”。[5]以清朝為例,自入關算起它統治中國長達267 年,最后的結果卻是滿族的徹底漢化,時至今日,滿族人和漢族人已鮮有區別,滿語也瀕臨滅絕。
另一方面,強大的同化力與保守性如影隨形。所謂中國,即“中央之邦”,古代中國一直認為自己位于世界的中心,從“胡”“蠻”“夷”等對外族帶有貶義的稱呼中漢民族強烈的心理優越感一覽無余。即使在清朝國力貧瘠、向西方學習的時候,洋務運動的口號“師夷長技以制夷”還是沿襲了“夷”這一稱呼,這種保守性使其在面對外來文化時抵御多于接納,同化多于異化。表現在外來語的引入上,則體現為對外來語同化程度高,在譯借方式上傾向于符合漢語習慣、體現民族自尊感的意譯方式,“始終如一地使用漢字,不斷地挖掘漢字的潛力,這與悠久的中華文化所培育出的中國人對自己文化傳統的執著信念有著密切的關系,因為漢字的徹底使用對中華文化的蓄積是至關重要的”。[6]
(二)日語的文化透視
日本是島國,四面環海,領土不與其它任何國家接壤。四周的海洋形成了防止外敵入侵的天然屏障,歷史上日本只遭到過中國元朝軍隊的進攻,幾乎沒有遭受過來自其它國家的殖民侵略。日本跨入文明時代較晚,古代日本文化處于弱勢地位,是在不斷學習、整合發達國家文化中發展起來的,存在伊始就注定了其文化的開放兼容性。日本是善于學習的民族,其對外來文化的受容并非受迫于外族入侵,而是以自主選擇的形式進行的。從中國漢代起的幾個世紀中,日本都致力于向中國學習,并在中國文化的影響下,經過大化改新完成了歷史上第一次政體統一,仿效唐朝建立起了封建體制的大和朝。近代以后,中國國力衰弱,“歐美風雨馳而東”,日本轉而向西方國家學習,通過明治維新成功實現了由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華麗轉身。二戰后,由于美國軍隊進駐日本的直接影響,以及美國國際地位的上升,因此,日本的學習對象又轉為美國,當時甚至有“脫亞入美”的提法。近代以來的對歐美國家的崇拜情節今天依然存在。日本學者鈴木孝夫指出“本來是日本固有的物品,長期以來也一直使用著非常通達的日語名稱,但是非要用歐美式的詞語來包裝它,賦予它所謂的新鮮感,才變得暢銷。這是否已足以證明在國民的深層心理中存在著這樣一種強烈愿望——對自己固有的形象加以否定,而竭盡全力要與歐美人同化、一體化”。[7]
與語言賴以起源的民族、國家的發展相適應,日語在形成時期屬于劣勢語言。8 世紀前后日本人才在漢字草書以及楷體的偏旁部首的基礎上分別創造出平假名和片假名,并借用了一部分漢字,形成了日本文字的雛形。汪麗影、楊晉指出由于日語在形成時期就大量吸收外來詞匯,因此在創立之初,外來語比例就較大,并直接導致其在發展中一直保持大量吸收外來語的勢頭。[8]后來在向歐美等西方國家學習的過程中,日本在吸收先進文化的同時也大量引入了外來語。語源包括葡萄牙語、西班牙語、荷蘭語、法語、德語、意大利語、拉丁語、英語等眾多語言,甚至還從不同國家借入同一詞義的外來語。此外,日本政府的語言政策也對外來語的大量引入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早在1941 年日本政府就提出“外來詞匯盡可能按照其發音寫成片假名”,“遵循其原音,不用勉強將外來語翻譯成日式詞匯”的政策方針,[9]戰后更是頒布《常用漢字表》,限定了日語中常用漢字的個數,對外來語的使用卻沒有加以限制,從而加速了日語中純音譯外來語的泛濫。
三、結束語
本文通過分析奧斯卡電影的中日兩國譯名中的外來語使用情況,研究兩國的文化差異。雖然中日兩國同屬漢字文化圈,但中國在引入外來語時盡量使用漢字進行意譯,日本則舍棄漢字,采取完全音譯的方式用表音文字片假名進行書寫。外來語譯借方式鮮明地反映了兩國文化的性格特征。源自文化大國的優越感塑造了中國文化的保守性,使它在接觸外國文化時以同化為主;日本文化則具有開放性、包容性和多元性,從早期的師從中國到后來的全盤西化,它都主動地吸收、整合各個時期先進國家的優秀文化來發展和充實自己。
[1]陳原. 社會語言學[M].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299.
[2]蔡基剛.英漢詞化對比與綜合表達法[J]. 山東外語教學,2005,(5):39.
[3][日]田中建彥. 外來語とは何か[M]. 東京:鳥影社,2002.38.
[4]鄭成.試析日語外來語與日本的社會心理[J].日語學習與研究,2001,(4):22.
[5]王婷婷. 從電影譯名看外來文化對中日兩國語言的影響[D].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2005.
[6]修德建. 關于中日兩國語言吸收外來詞的對比研究——以現代漢語和現代日語為主[J].解放軍外國語學報,1995,(1):53.
[7]楊惠媛. 從外來語看日本文化的西方崇拜心與虛榮心[J].日語學習與研究,2003,(4):81.
[8]汪麗影,楊晉. 試比較日、英語中外來語眾多的原因[J]. 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002,(4):30.
[9]李佳桐. 社會變遷中的日語外來語與語言政策[J].語文學刊,2012,(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