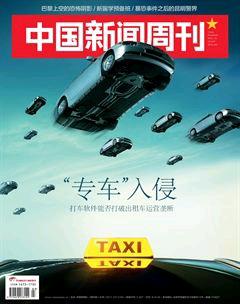新留學(xué)預(yù)備班
楊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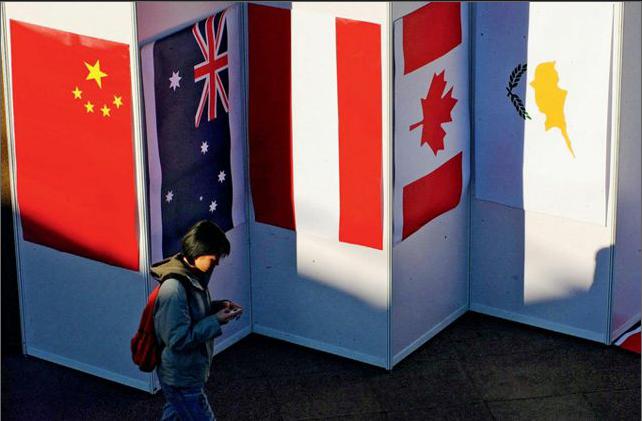
“選國際班,當(dāng)然是為了出國留學(xué)。”北京101中學(xué)國際班的學(xué)生家長朱麗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這是《中國新聞周刊》在作公辦高中國際部調(diào)查過程中,幾乎所有家長的回答。
然而,公立高中的校長們卻不認(rèn)為出國是國際班的辦學(xué)目的。“國際班是高中教育的試驗(yàn)田。”北京三十五中校長朱建民說。北京師范大學(xué)第二附中校長馬驪則表示:“在國際班中試驗(yàn)的融合課程,有利于培養(yǎng)具有國際視野的人才。”
在中國教育在線總編輯陳志文眼中,公辦高中國際班則是一個(gè)混合體。“國際班、國際部是對原來純粹的公辦高中教育體系的一個(gè)有效補(bǔ)充,同時(shí)也在客觀上滿足了家長的需求。”他說。
然而,他也不否認(rèn),現(xiàn)有的公辦高中國際班,正在沖破原有的規(guī)范體系,其中諸多現(xiàn)象,既隱秘,又無法用既有條例予以匡正。
公辦高中國際班誕生十年來,已成為中國高中教育領(lǐng)域最耐人尋味也最復(fù)雜的現(xiàn)象。
一方面,教育界和主管部門希冀通過這一開拓為國內(nèi)高中教育打開一扇門,走向多元化、國際化并引發(fā)自下向上的改革;另一方面,辦學(xué)能力、引進(jìn)渠道、家長訴求、利益驅(qū)動等多重因素,使得公辦高中國際部越來越成為一種新型的留學(xué)預(yù)備班,并引發(fā)對教育公平甚至教育主權(quán)的爭論。
國際化VS出國
很難按圖索驥找出一份指導(dǎo)公辦高中興辦國際班的具體文件。
目前業(yè)內(nèi)人士普遍認(rèn)為,對于公辦高中國際部最早的政策支持,來自2003年發(fā)布的《中外合作辦學(xué)條例》。這份指導(dǎo)性條例明確了“加強(qiáng)教育對外交流與合作”的目的是“促進(jìn)教育事業(yè)的發(fā)展”,并提出了“中等學(xué)歷教育”可以申請?jiān)O(shè)立中外合作辦學(xué)機(jī)構(gòu),由擬設(shè)立機(jī)構(gòu)所在地的省、自治區(qū)、直轄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門審批。
最早一批公辦高中國際班因此興起。不過,鑒于收費(fèi)、生源等原因,那時(shí)的公辦高中國際班只存在于北京、上海這樣一線城市的極少數(shù)中學(xué)內(nèi),其發(fā)展也是緩慢而隱秘的。
第二份促成公辦高中國際班生長的政策性文件,是2010年發(fā)布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2010-2020年)》,其中表明:“鼓勵各級各類學(xué)校開展多種形式的國際交流與合作,加強(qiáng)中小學(xué)對外交流與合作,提高我國教育國際化水平,培養(yǎng)大批國際化人才。”
這份十年發(fā)展戰(zhàn)略,明確提出了“教育國際化”的發(fā)展方向,成為公辦高中國際班的一項(xiàng)指南針。在2008年金融危機(jī)國外高校加大對華招生比例的背景下,公辦高中國際班在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迅猛發(fā)展,并開始向二三線城市蔓延。
據(jù)中國教育在線發(fā)布的《2014年出國留學(xué)趨勢報(bào)告》,截至2013年,北京共有17所公辦高中開設(shè)22個(gè)國際班,計(jì)劃招生人數(shù)達(dá)1355人;而在2009年,北京公辦高中國際班只有9個(gè),招生人數(shù)僅為440人,招生人數(shù)年均增長率超過20%,5年翻了近兩番。在上海51所示范性高中里,開設(shè)國際課程項(xiàng)目的達(dá)24所,占比47%。
二線城市則一起步就進(jìn)入快速發(fā)展階段。截至2012年,南京的公辦高中國際班數(shù)量達(dá)到18個(gè),招生人數(shù)575人,鄭州2010年時(shí)有9所學(xué)校開辦16個(gè)國際班,至2011年,就發(fā)展到共13所中學(xué)24個(gè)國際班。至2014年,在河南周口、江蘇泰州、云南曲靖這樣的非省會城市,也開始出現(xiàn)普通高中國際班的身影。
根據(jù)現(xiàn)有各級相關(guān)規(guī)定,開辦中外合作項(xiàng)目并不繁瑣,除義務(wù)教育和實(shí)施軍事、警察、政治等特殊性質(zhì)教育的機(jī)構(gòu)之外,中外合作辦學(xué)者都可以合作舉辦各級各類教育機(jī)構(gòu)。只要申請學(xué)校符合相關(guān)法律規(guī)定并具備法人資格,提交申請報(bào)告、合作協(xié)議和資產(chǎn)來源證明,在15%啟動資金到位后,即可向教育行政部門申請中外合作辦學(xué)項(xiàng)目,待批準(zhǔn)后即可招生。
目前已有浙江、湖北、安徽、山西等十個(gè)省市對普通高中中外合作辦學(xué)項(xiàng)目出臺了細(xì)化規(guī)定,然而,對于這種“既公且私”的辦學(xué)形式的定義,在許多方面仍是模糊的。比如:它的課程不是統(tǒng)一的,也無須對課程進(jìn)行任何審核與報(bào)備;它的師資管理沒有明確的數(shù)量、比例限制,也沒有對外籍教師的資質(zhì)審核管理制度;收費(fèi)標(biāo)準(zhǔn)則更是混亂,規(guī)定僅僅強(qiáng)調(diào)了教育的公益性,但對于國際班應(yīng)該如何收費(fèi),收費(fèi)應(yīng)如何管理都沒有細(xì)化的條例規(guī)定。
當(dāng)然,目前也尚未出現(xiàn)對公辦高中國際部的投訴。因?yàn)椤敖逃龂H化”的發(fā)展戰(zhàn)略,已被學(xué)校、家長和學(xué)生個(gè)體自身明確為一個(gè)具體目標(biāo):出國。達(dá)成結(jié)果便意味滿意。“去國外大學(xué)沒有想象中那么難,”北京三十五中校長朱建民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僅美國就有四千多所大學(xué),可以滿足各種層次的留學(xué)需求。”這也是諸多公辦高中國外大學(xué)錄取率接近100%的主要原因。
“讓孩子去國外接受本科教育,是我周圍同事的普遍選擇。”朱麗說。她在外企工作,同事中有80%為下一代設(shè)計(jì)的成長路線都是從國際學(xué)校考入國外大學(xué)讀本科。“國際班主要是適應(yīng)語言和學(xué)習(xí)方式。”
《福布斯》雜志中文版聯(lián)合宜信財(cái)富出品的《中國大眾富裕階層財(cái)富白皮書(2013)》顯示,中國資產(chǎn)在10萬美元(約63萬人民幣)至100萬美元(約630萬人民幣)之間的中產(chǎn)階層有270萬人,其中考慮將子女送到國外留學(xué)的占四分之三。
公辦高中國際班于是成了性價(jià)比最高的選擇。相比國際學(xué)校,它可接受中國籍學(xué)生;相比民辦私立學(xué)校,它收費(fèi)較低,且無論從生源、師資,都讓人覺得更可靠、更穩(wěn)定;尤其是,大部分有實(shí)力興辦國際班的公辦高中,多是聲名卓著的重點(diǎn)高中,單靠品牌效應(yīng),已使人信任感頓生。
北京市第四中學(xué)校(以下簡稱四中)校長助理、四中國際校區(qū)管理委員會執(zhí)行委員安迎曾經(jīng)公開表示,四中開辦國際班主要原因就是看到大量的出國需求。他記得,2009至2010學(xué)年,四中高三年級有30多個(gè)學(xué)生計(jì)劃出國讀本科,平均每班有3至5名。這批學(xué)生后來返校時(shí),提到“既準(zhǔn)備高考,又準(zhǔn)備出國”過程的糾結(jié),以及初到國外時(shí)的各種不適應(yīng)。與此同時(shí),中國學(xué)生留學(xué)材料造假頻頻曝光,使四中覺得,公辦高中應(yīng)該在這個(gè)過程中幫助自己的學(xué)生實(shí)現(xiàn)愿望,而不是讓留學(xué)中介機(jī)構(gòu)從中幫助學(xué)生造假。四中國際部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做出的決策。

《中國大眾富裕階層財(cái)富白皮書(2013)》顯示,中國資產(chǎn)在10萬美元(約63萬人民幣)至100萬美元(約630萬人民幣)之間的中產(chǎn)階層有270萬人,其中考慮將子女送到國外留學(xué)的占四分之三。圖/CFP
每年三四月,中考尚未開始,各高中的國際部舉辦的“招生咨詢會”“校園開放日”便已人滿為患。朱麗記得,2014年的十一中學(xué)國際班招生咨詢會,整個(gè)大禮堂被擠得水泄不通,校長、國際部主任及外籍教師在臺上侃侃而談,學(xué)生和家長恨不得把每句話都記下來。而據(jù)媒體報(bào)道,2013年北京四中的國際班招生咨詢報(bào)告會,250人的禮堂,硬是擠進(jìn)了400人,后來不得不開了第二場。北師大二附中PGA高中課程班咨詢會,咨詢家長達(dá)五六千名。
公辦高中國際部的錄取條件也水漲船高。中國教育在線總編輯陳志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剛出現(xiàn)公辦高中國際部時(shí),中考分?jǐn)?shù)線幾乎可以忽略,只要有錢、有意愿,就能入學(xué);但如今,錄取分?jǐn)?shù)線與校本部的分?jǐn)?shù)差已越來越小。據(jù)統(tǒng)計(jì),2013年,北京地區(qū)公辦高中的國際部錄取分?jǐn)?shù)線平均超過510分,最高錄取分?jǐn)?shù)超過530分。錄取標(biāo)準(zhǔn)已與一些北京市重點(diǎn)高中非常接近。北師大二附中校長馬驪對此感受非常明顯。“最初招收的學(xué)生成績都是在490分左右,然而去年最高分已經(jīng)達(dá)到530多分。”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些孩子基礎(chǔ)好成績好,出國目標(biāo)也更明確。”
隱在身后的第三方機(jī)構(gòu)
國際部在學(xué)生及家長面前呈現(xiàn)的面目,大多是中國高中與國外某中學(xué)的合作產(chǎn)物,然而真相是,國內(nèi)除了北大附中、清華附中、上海中學(xué)、深圳中學(xué)四校的國際班(部)是獨(dú)立運(yùn)作,其余經(jīng)教育部審批通過的86所公立高中國際班,與國外中學(xué)的合作辦學(xué),都是通過第三方機(jī)構(gòu)完成的。
第三方機(jī)構(gòu)負(fù)責(zé)提供課程、招聘外籍教師,同時(shí)為這些高中國際班尋找到名義上的外國合作高中。這些第三方機(jī)構(gòu)一方面與國內(nèi)中學(xué)建立合作,另一方面廣發(fā)電子郵件,在海外尋找合作高校。一位業(yè)內(nèi)人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有些國外中學(xué)存在的真正價(jià)值就是讓項(xiàng)目順利通過審批。而曾在美國大使館新聞文化處工作過的殷嘉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不少美國學(xué)校負(fù)責(zé)人曾向他抱怨,每隔幾天會收到來自中國的請求合作郵件,但發(fā)出信件的人往往不是中國學(xué)校,卻是一家商業(yè)公司。
目前一家較有名的承辦中國公辦高中國際合作辦學(xué)項(xiàng)目的第三方機(jī)構(gòu)是狄邦教育集團(tuán)。它極為低調(diào),幾乎不打廣告,卻擁有極為廣泛的合作學(xué)校。狄邦教育拒絕了《中國新聞周刊》的采訪請求。“我們從來不接受采訪。”其辦公室一位女士解釋。但通過其官方網(wǎng)站,可以了解到,自2002年啟動國際高中課程項(xiàng)目以來,至2014年3月,狄邦已與全國29所著名中學(xué)合作,建立了36個(gè)國際課程中心,合作學(xué)校包括人大附中、北京十一學(xué)校、南京金陵中學(xué)、杭州外國語學(xué)校、東北師大附中、成都樹德中學(xué)等重點(diǎn)中學(xu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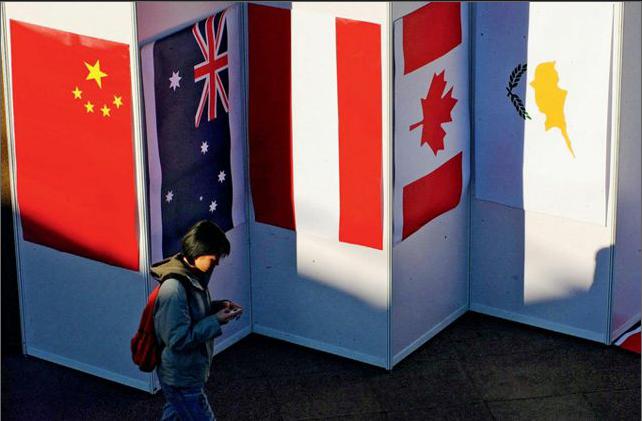
公辦高中國際班的設(shè)立,旨在提高中國教育國際化水平、培養(yǎng)國際化人才,但如今已成為新型留學(xué)預(yù)備班。圖/CFP
另外一家較有名第三方機(jī)構(gòu)叫安生教育。它同樣拒絕接受任何形式的采訪,但從其官網(wǎng)上可以得知,它合作的學(xué)校包括北京四中、上海格致中學(xué)、合肥一中、揚(yáng)州中學(xué)、衡水中學(xué)等。
高中與教育機(jī)構(gòu)的合作方式一般為:各自分工、學(xué)費(fèi)分成。學(xué)校負(fù)責(zé)提供校舍,利用自己的品牌和教育資質(zhì)招生,教育機(jī)構(gòu)則負(fù)責(zé)引進(jìn)課程,招聘外教,提供相應(yīng)的外事服務(wù),以及為國際班畢業(yè)生提供留學(xué)咨詢及代辦事宜。
一位不愿具名的留學(xué)中介人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些第三方教育機(jī)構(gòu)前身都是留學(xué)服務(wù)中介,隨著低齡留學(xué)市場越來越大,與高中合作成為占領(lǐng)留學(xué)中介服務(wù)市場的有效渠道。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學(xué)校國際部負(fù)責(zé)人介紹,一般而言,國際班教學(xué)運(yùn)營成本占學(xué)費(fèi)的40%,剩余的60%,由學(xué)校和第三方機(jī)構(gòu)五五分成。北京公辦高中國際班的平均年學(xué)費(fèi)是8萬元,按此計(jì)算,課程費(fèi)、教師工資等占3.2萬元,剩余的4.8萬元則作為運(yùn)營利潤,由學(xué)校和第三方機(jī)構(gòu)平分。當(dāng)然,具體情況因校而異。實(shí)力強(qiáng)的中學(xué)具有強(qiáng)大的話語權(quán),利潤分成較多,而實(shí)力弱的學(xué)校,最終變成只是出租學(xué)校教室和招生資質(zhì)。據(jù)上述學(xué)校負(fù)責(zé)人了解,有的學(xué)校最終只能分得10%的利潤。
目前國際班學(xué)費(fèi)標(biāo)準(zhǔn),一線城市從8萬至20萬不等,二線城市稍低,每年6萬元至10萬元。此外,還有托福、SAT考試培訓(xùn)費(fèi)用,游學(xué)項(xiàng)目、志愿者服務(wù)、留學(xué)咨詢等各項(xiàng)支出。據(jù)陳志文測算,“取中間數(shù),公辦高中國際班三年,一個(gè)學(xué)生的總投入約為45萬。”
但對于第三方機(jī)構(gòu)來說,學(xué)費(fèi)分成只是其收入的一部分,真正在其業(yè)務(wù)中占大比例的,是其他衍生業(yè)務(wù):假期游學(xué)項(xiàng)目、留學(xué)咨詢服務(wù)、以及托福、SAT等考試培訓(xùn)市場。
對于這種名義上是“中外合作辦學(xué)”,實(shí)則“中中合作辦學(xué)”的現(xiàn)象,眾說紛紜。
陳志文認(rèn)為,不論第三方機(jī)構(gòu)介入的目的如何,但專業(yè)中介機(jī)構(gòu)降低了中外高中合作辦學(xué)的時(shí)間成本,提高了效率,從結(jié)果上看,也推進(jìn)了國內(nèi)中學(xué)教育的國際化發(fā)展,讓很多不知道該怎么操作國際班及國際課程的學(xué)校了解并掌握了國際課程體系。
在他看來,第三方機(jī)構(gòu)介入公辦高中國際班,最重要的隱患是外籍教師的管理。中國學(xué)校要獲得聘請外籍教師的資質(zhì),申請審核過程極為繁瑣,需要提供外籍教師教學(xué)工作管理制度、外教生活管理制度、合格教師制度及外教安全保衛(wèi)管理制度等材料報(bào)備,同時(shí)需要由當(dāng)?shù)赝廪k會同教育廳、公安廳赴申請單位實(shí)地考察,在各項(xiàng)要求通過審批后,才能獲得合法聘請外籍教師的資格認(rèn)可證書。
許多中學(xué)對此望而生畏,轉(zhuǎn)而委托第三方中介機(jī)構(gòu)承擔(dān)聘請外籍教師的工作。“如果校方對外籍教師的聘用和解聘擁有絕對話語權(quán)還好,如果是第三方機(jī)構(gòu)擁有絕對話語權(quán)時(shí),事情就會比較可怕。”陳志文介紹說,他見到過一些學(xué)校的外籍教師是來自菲律賓,馬來西亞這樣母語非英語國家,還有些根本不是老師不懂教育。“說是混混也不為過。”他說,“就是這樣的混混老師,讓多數(shù)中國人誤以為西式教育就是玩。”
外籍教師的穩(wěn)定性,則是國際班面臨的另一個(gè)困境。多數(shù)外籍教師只簽一年合同,合同期滿后就離開或回國,這使得學(xué)生在國際班三年內(nèi),要不斷適應(yīng)新的外籍教師。
在反對者聲音里,北大附中校長助理何道明的觀點(diǎn)最為堅(jiān)決。何道明是美國人,已在中國生活了18年,先后在北大附中、深圳中學(xué)工作,從一名外教,直至學(xué)校高級管理人員。他認(rèn)為,“不論提供的課程與教師管理是否正規(guī),第三方中介機(jī)構(gòu)終究是商業(yè)機(jī)構(gòu)。他們參與公辦高中國際班的運(yùn)營,目標(biāo)不是課程的優(yōu)化改革,而是背后的利潤。”
課程悖論
最大的糾結(jié)在于課程。
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學(xué)校長朱建民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三十五中在籌備國際部前曾經(jīng)做過一些調(diào)研,發(fā)現(xiàn)不少學(xué)校的國際部課程只是單純地將國內(nèi)課程與國際課程做了簡單的疊加。“比如,周一是國家課程中的數(shù)學(xué)課,周二是外教的數(shù)學(xué)課,但兩個(gè)老師中講的課程內(nèi)容可能有一半是相同的。這就是一種資源浪費(fèi),也會削弱學(xué)生的學(xué)習(xí)興趣。”
但也有學(xué)校在引進(jìn)國外課程后,開始了有針對性的教育實(shí)驗(yàn)和改革。比如,北師大二附中采取大英語教學(xué)組的管理方式,中外教共同備課,統(tǒng)一管理,并且根據(jù)中外教的優(yōu)勢分別安排課程,中方英語老師講語法,外教講寫作;廣州廣雅中學(xué)提出廣泛融合的概念。校長葉麗琳向《中國新聞周刊》介紹,在廣雅融合課程體系中,提倡跨學(xué)科融合,比如講到漢字“榕”,語文老師會講述與榕樹有關(guān)的文學(xué)作品,生物老師則會講述榕樹的植物特性,化學(xué)老師會帶領(lǐng)學(xué)生認(rèn)識榕樹葉的化學(xué)成分等。北大附中的改革則是在大量引入西方引導(dǎo)式教學(xué),比如,在學(xué)習(xí)魯迅的文章《祝福》時(shí),老師引導(dǎo)學(xué)生一起討論:“祥林嫂為什么沒有名字?”
然而,除了業(yè)內(nèi)人士關(guān)注這些努力外,家長們似乎并不買單。在許多家長眼中,國際班的課程是否真正國際化并不重要,他們在意的指標(biāo)簡單明確:托福、SAT成績是多少?名校錄取率是多少?
許多家長要求學(xué)校從高一開始就直接上托福、SAT的培訓(xùn)課。陳志文就見到過,托福、SAT等考試培訓(xùn)課程堂而皇之登上許多國際班的課表,成為學(xué)生的必修課程。一位校長私下里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即使不開這樣的課,家長也會讓孩子到外面去上,有些家長干脆在考試前就不讓學(xué)生到校上課,專心在家刷題(通過做大量習(xí)題鞏固知識的做法)或者參加考前培訓(xùn)。作為妥協(xié),有些學(xué)校在考試前兩周利用自習(xí)課的時(shí)間,為學(xué)生們做托福、SAT的考前培訓(xùn)。面對這樣的尷尬,校長們自我安慰說:學(xué)生滿意是我們的辦學(xué)宗旨,為學(xué)生的考試提供幫助也是學(xué)校應(yīng)該做的。
課程與教育多元化的矛盾還體現(xiàn)在國際課程的選擇與分班制度中。
國際班的課程多數(shù)與學(xué)生未來的出國國家方向相匹配。中英班,主要采用A-level課程,中美班,大多采用美國高中課程加AP課程(美國大學(xué)先修課),還有一些學(xué)校引入IB(國際文憑課程),另外一些采用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等國的高中課程。
美國人何道明最為不滿的是對美國AP課程的引入。他說,在美國,AP課程是為學(xué)有余力的高中生提供的大學(xué)先修課程,通過AP考試獲得的學(xué)分,被美國大學(xué)認(rèn)可后可申請免修,也的確會對申請名校產(chǎn)生些輔助作用。“但AP課程并不適用所有學(xué)生,即便是美國,也只有少部分精英學(xué)生學(xué)習(xí)AP課程,并且是自修。”何道明說。但他發(fā)現(xiàn),在中國學(xué)校和家長眼中,AP分?jǐn)?shù)已經(jīng)成了一個(gè)重要的申請工具,一些中學(xué)在高二就開設(shè)AP課程,并且要求學(xué)生必選。 據(jù)《2014年出國留學(xué)趨勢報(bào)告》中的數(shù)據(jù),北京公辦高中的22個(gè)國際班中,共有引進(jìn)來自美國、英國、加拿大等國的7種國際課程體系。其中,AP課程占比高達(dá)63.64%。
常青藤的誘惑
國際班的學(xué)習(xí)并不輕松。苗欣陽在北京十一學(xué)校國際班就讀。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她的初中同學(xué)普遍羨慕她國際班不用參加高考,壓力小,但事實(shí)并非如此。在強(qiáng)大的出國壓力下,國際班每天的作業(yè)不亞于普通高中生,考試前也一樣要大量“刷題”。“更重要的是,我們采用GPA成績單,出勤、作業(yè)、考試都要體現(xiàn)在成績單里。想偷點(diǎn)懶,GPA就會下降。”
GPA是Grade Point Average的縮寫,意思是平均成績點(diǎn)數(shù)。GPA算法很復(fù)雜,涉及到課程數(shù)目、課程得分、課程學(xué)分等等。國外高中設(shè)計(jì)GPA的目的是為了充分體現(xiàn)學(xué)生的學(xué)術(shù)背景以及學(xué)術(shù)能力,但多數(shù)中國學(xué)生要用GPA去敲開常青藤學(xué)校的大門,“拿A”成為他們的全部追求。GPA成了國際班學(xué)生的命根,就像高考是普通高中生的命根一樣。
苗欣陽說,每個(gè)學(xué)期末,同學(xué)們都會認(rèn)真計(jì)算自己得了多少個(gè)A,多少個(gè)B,再估算一下自己的GPA成績。“GPA在4.0以上才有可能申請常青藤。”他們像留學(xué)專家一樣,講解著申請名校的必備條件。“GPA4.0以上,意味著所有功課都要在B以上。”于是,每次考試、每次作業(yè)他們都必須嚴(yán)陣以待。“這兒和普通高中的最大不同是這里沒有臨考沖刺——這里每天都在沖刺。”苗欣陽的同學(xué)易美娜說。
每一分都很關(guān)鍵。老師們也會巧妙地利用成績左右學(xué)生行為,缺勤扣5分,參加社團(tuán)活動加2分。易美娜還記得,一次期中考試前,社會實(shí)踐老師要求去同學(xué)們都要參加自編舞劇活動,條件是參加者每人記2個(gè)學(xué)分。“就是為了那2分,我也得去啊!”易美娜說,“復(fù)習(xí)只得靠晚上熬夜。”
熬夜,成為國際班學(xué)生的正常生活狀態(tài)。易美娜說,十二點(diǎn)一點(diǎn)睡覺是常有的事,她年輕的圓臉上掛著和年齡不符的黑眼圈。朱麗的兒子李哲,剛剛上高一,但是每天十點(diǎn)半宿舍熄燈時(shí),都無法完成當(dāng)天的作業(yè),只好在被窩里用手電筒繼續(xù)。但他很樂觀,認(rèn)為這不是課業(yè)太重,而是自己還未完全適應(yīng)。
除了成績單,壓力還來自父母。
通常,朱麗小心翼翼地隱藏起自己的焦慮,她說還是孩子快樂最重要。另一位國際班家長金葉也強(qiáng)調(diào),并不是非要考入常青藤。但是不經(jīng)意間,對常青藤的渴望還是會流露出來。“畢竟花了這么多錢,孩子也付出了不少辛苦,如果只是排名一般的學(xué)校就沒什么意義了”;“本來也可以考上國內(nèi)不錯的大學(xué),往美國考,就算不是常青藤,排名也不能太差”。
私下聚在一起時(shí),家長們最喜歡聊的就是破格錄取的故事。家長群里最近的熱點(diǎn)故事是:一位SAT只考了1800分的學(xué)生,最終被哈佛大學(xué)破格錄取。他的敲門磚是熱衷公益活動,并且在面試時(shí)表示:希望在哈佛學(xué)習(xí)的目的,是掌握幫助窮人的技能。
“學(xué)校排名是中國家長最關(guān)心的。”美國大使館新聞文化處教育項(xiàng)目官員畢安亦有同感,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美國除了擁有常青藤盟校,還有很多非常好的文理學(xué)院和社區(qū)大學(xué)。但盡管美國大使館不斷在赴美留學(xué)家長交流活動中推薦這些學(xué)校,它們?nèi)匀缓苌俦恢袊议L看中。”
盡管如此,易美娜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至少對于她個(gè)人,這些壓力是充滿正能量的。“我們知道這些事情非做不可,這點(diǎn)對于將來讀大學(xué)很重要。因?yàn)槟菚r(shí)候就沒有家長跟在后面揪著領(lǐng)子監(jiān)督你,你必須學(xué)會對自己套上腳鐐手銬,逼著自己用功學(xué)習(xí)……”
復(fù)雜的未來
教育的特殊性,以及中國的特殊國情,使得公辦高中國際班似乎正在越來越走向它的反面。
2014年11月,考察過中國高中教育的英國Kings Ely中學(xué)校長米克格賴斯在中英中小學(xué)校長圓桌論壇上表示,“中國很多提供A-Level課程的學(xué)校,往往沒有達(dá)到英國要求的廣度,通常只開設(shè)中國學(xué)生能夠得到高分的數(shù)理化和英語課程,確保學(xué)生能夠申請到國外就夠了。”
在這場由廣東教育研究院組織的會議上,英國博士山學(xué)校(Box Hill School)校長科瑞頓·勞德也表示:“如果我是大學(xué)招生辦的老師,我看到這樣兩名中國學(xué)生:一個(gè)在中國接受A-Level課程培訓(xùn),一個(gè)在英國私立學(xué)校讀書,他們成績相當(dāng),而只剩最后一個(gè)席位,我肯定會留給在英國有中學(xué)就讀經(jīng)歷的學(xué)生,因?yàn)樗私庥恼Z言、文化,在學(xué)術(shù)和生活上經(jīng)驗(yàn)豐富。這個(gè)經(jīng)驗(yàn)?zāi)軌驇椭谟拇髮W(xué)里更快地獲得成功。”
美國北卡羅萊納州立大學(xué)副校長李白煉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如果兩名來自中國的本科入學(xué)申請者成績相當(dāng),一個(gè)是普通畢業(yè)生,一個(gè)是國際班學(xué)生,他會選擇普通高中畢業(yè)生。“選擇國際班的學(xué)生大多是為了逃避高考。但真正優(yōu)秀的孩子,是不會放棄高考這個(gè)途徑的。”
事實(shí)上,關(guān)于公辦高中國際班的爭論在國內(nèi)始終存在。一種觀點(diǎn)認(rèn)為,公辦國際班的高收費(fèi)與教育的公益屬性背道而馳。而且,這會造成新的教育不公,導(dǎo)致教育貴族化,經(jīng)濟(jì)差距帶來的所受教育質(zhì)量的差距與鴻溝,則會造成下一代人在經(jīng)濟(jì)水平上的再度分化。
北京市政協(xié)委員、北京電影學(xué)院黨委書記籍之偉,曾數(shù)次提交公辦中學(xué)不應(yīng)舉辦國際班的提案。他認(rèn)為,公立高中辦國際班相當(dāng)于部分人通過多交錢,占用本應(yīng)公平分配的優(yōu)質(zhì)教育資源,是一種變相的擇校。教育部門審批公立高中國際班應(yīng)當(dāng)謹(jǐn)慎,少批甚至不批,把這項(xiàng)職能交給民辦教育機(jī)構(gòu)。
更嚴(yán)重的觀念,是提出了教育主權(quán)的問題。上海市教委基礎(chǔ)教育處處長倪閔景多次對媒體表示,學(xué)生形成價(jià)值觀在高中教育中起著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放棄本土課程,照搬國際課程的做法,對學(xué)生的文化認(rèn)同、知識結(jié)構(gòu)等方面都會產(chǎn)生不可預(yù)估的風(fēng)險(xiǎn)。
然而長期關(guān)注這一現(xiàn)象的北京師范大學(xué)教授袁桂林則持謹(jǐn)慎的樂觀態(tài)度。一方面,他認(rèn)為目前公辦高中國際班確實(shí)存在不少問題。“現(xiàn)在高中階段的中外合作辦學(xué),還沒有明確的成本核算機(jī)制,外籍教師的人數(shù)、工資等,都沒有明確的法律依據(jù)和有效監(jiān)管,因此高中國際班收費(fèi)比較混亂,也帶來一些現(xiàn)實(shí)問題。”
但另一方面,他認(rèn)為,公辦高中國際班符合中國教育多樣化發(fā)展的需求,“中國除了職業(yè)高中、普通高中、綜合高中和特色高中之外,國際化也可以成為高中的一個(gè)種類。”同時(shí),他也認(rèn)為,國際班引進(jìn)的課程體系、外教等資源,隨著時(shí)間的推移,還是會對學(xué)校的方方面面產(chǎn)生有益的影響。
已有一些公辦高中正在自行努力將國際班項(xiàng)目變得更有進(jìn)步意義。據(jù)報(bào)道,2014年6月20日,在北京市海淀區(qū)基礎(chǔ)教育國際化校長論壇上,八一中學(xué)校長沈軍、101中學(xué)校長郭涵都指出,高中國際化,決不僅僅是辦一個(gè)課程班滿足少部分學(xué)生的需要,而是面向所有學(xué)生的國際化,讓所有學(xué)生受益。一個(gè)正在發(fā)生的實(shí)例是,北京十一中學(xué)已開始將國際班課程和教學(xué)方式向普通高中移植,如走班制教學(xué)、按教學(xué)深度和廣度劃分課程層次、向?qū)W生提供人性化的選課制等。
然而與此同時(shí),各地紛紛收緊對公辦高中國際班的規(guī)范。2014年3月,北京市教委宣布不再審批新的公辦高中國際班,浙江、安徽、黑龍江、吉林等地將公辦高中國際班的審批權(quán)收歸到省級統(tǒng)籌;地方教育部門也開始關(guān)注國際班的課程審批。比如上海市教委明確規(guī)定,中外融合課程方案、課程計(jì)劃及其教材須經(jīng)審查,其中國家課程中的語文、思想政治、歷史和地理四門課程應(yīng)為必修課程,且國際課程班不得單獨(dú)收費(fèi)。
“國際化”還是“出國化”,教育改革或只是從“應(yīng)試高考”轉(zhuǎn)為“洋應(yīng)試”,這場由教育管理部門、公辦高中、第三方教育機(jī)構(gòu)、教師、家長及學(xué)生多方共同參與的教育實(shí)驗(yàn)仍然在繼續(xù)。一如中國的其他領(lǐng)域,這場“摸石頭過河”的嘗試前景復(fù)雜,而更加困難的是,這個(gè)嘗試,尚沒有一個(gè)標(biāo)準(zhǔn)來判斷其成功,亦或失敗。
(應(yīng)受訪者要求,文中采訪學(xué)生及家長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