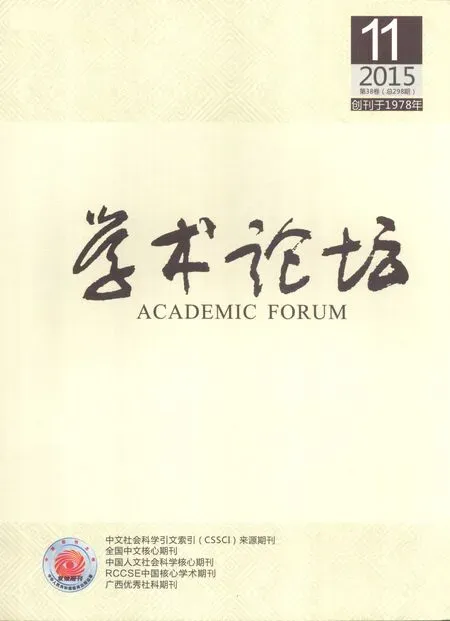儒家人權思想及其創造性轉化
黃 英
一、問題的提出與產生的背景
“儒家”與“人權”的淵源可以追溯到近代西方人權理論誕生前夕。 “早在17、18 世紀,儒家思想就已經在遙遠的歐洲與人權觀念發生了聯系,促進了歐洲近代人權觀念的產生。 ”[1]這就是國人引以為豪的“東學西漸”。 然而,時移勢易,鴉片戰爭以后,西學強勢東漸,以“人權”為核心的西方文化又反過來成為批判和討伐中國傳統儒學的利器。新文化運動中,“儒家”與“人權”被認為是不共戴天的兩極,“不塞不流,不止不行”①,勢若水火。 如今,人們又破天荒地發明了“儒家人權思想”這樣的新詞,并如火如荼地探討如何將其進行“創造性轉化”以適應現代社會的需要。 那么,問題來了:“儒家”與“人權”百年來的恩怨究竟因何而起? “儒家人權思想”這一表述是否言之有據? “創造性轉化”有何新意和深意? “儒家人權思想”又如何進行“創造性轉化”? 而這一系列問題的產生都與近代中國面臨的“大變局”息息相關。
近代中國的“大變局”乃是春秋戰國以來中國社會面臨的第二次歷史變遷,是數千年一遇的具有整體性、根本性、革命性、長期性的歷史巨變[2](P29-30)。“大變局”顛覆并摧毀了傳統儒學,且幾乎釀成亡國滅種的慘劇, 中國從此進入曲折而艱難的社會轉型期,“現代化” 成為救亡圖存乃至強國富民的唯一法門,“中國的出路有而且只有一條, 就是中國的現代化”[3](P146)。 為此,晚清以來的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國民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乃至新中國成立后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以及當前的改革開放,無一不是中華民族為了走出大變局、實現現代化而做出的努力。 “儒家人權思想及其創造性轉化”便是這種努力在思想文化領域的反映,是近代中國“大變局”背景下產生的新思路和新課題。
百年來,圍繞“儒家人權思想”及其“創造性轉化”,學術界展開了激烈的交鋒和論戰,爭議的焦點有三:第一,傳統儒家到底有沒有人權思想? 第二,儒家人權思想能否進行創造性轉化? 第三,儒家人權思想如何進行創造性轉化?
二、傳統儒家是否具有人權思想
傳統儒家到底有沒有現代人權思想? 這一問題自“五四”以來就備受關注。 各種說法紛至沓來,聚訟紛紜,先后出現了“古無有也”“古已有之”和“本無后有”三派觀點。
早期的思想家,無論是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還是新儒家,都毅然決然地堅持“古無有也”的觀點, 認為中國古代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產生 “權利”的意識和觀念。 梁啟超、嵇文甫和梁漱溟即是該派的主要代表①由于當時“人權”話語尚不流行,相關的論著常以“權利”和“民權”代之。。 梁啟超指出:“民權之說,中國古無有也。法家尊權而不尊民,儒家重民而不重權,道墨兩家此問題置諸度外,故皆無稱焉。 ”[4](P228)嵇文甫認為,民權思想的產生必須具備相應的條件,那就是近代工商業(即資本主義)的發達與第三等級(即資產階級)的出現,這在中國古代小農經濟條件下是不可能實現的,因而他確信中國古代沒有民權思想[5](P446-474)。 梁漱溟也斷言:“人權自由之觀念,誠非中國所有。 ”他還進一步解釋了產生這種現象的根源:“中國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個人永不被發現這一點上。一個人簡直沒有站在自己立場說話機會,多少感情要求被壓抑,被抹殺。 ”[6](P232,238)這些論證一針見血,入木三分,直指中國文化的軟肋,因而極具說服力。 時至今日,仍有不少國內外學者堅持這種看法②國內學者如陳弘毅(香港大學)、叢日云(中國政法大學)和喬清舉(南開大學)等始終堅持“古無有也”的觀點,國外的比較法學者如德國的K·茨威格特、H·克茨,美國的H·W·埃爾曼,法國的勒內·達維德,以及漢學家李約瑟和史華慈等也都否認中國古代有人權觀念。。
然而,傳統畢竟是一個民族的根基,尤其是儒家思想,經過兩千多年的積淀,已然成為整個民族的文化基因和精神依托。 割裂了儒家思想與現代文明的聯系,何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因此,20世紀末,國學研究持續高熱,在傳統中發掘有價值的思想資源,并將它們與現代文明相對接,成為新時代的普遍共識,“傳統儒家到底有沒有人權思想”的問題再度引發關注和熱議,相繼產生了“古已有之”和“本無后有”兩派觀點。
“古已有之”派與“古無有也”派相對立,其主張可大致分為萌芽說、部分說和豐富說三種。 萌芽說以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姜廣輝為代表, 認為中國古代沒有明確的“權利”觀念,儒家所具有的只是一些人權思想的萌芽。 部分說認為傳統儒學中含有現代意義上的第二、三代人權,其“民本”、“仁政”、“富民教民”、“制民恒產”等思想就是基本生存權和發展權, 但缺乏現代人權思想中最最核心的部分,即第一代人權所主張的公民權和政治權。大陸學者陳來、李存山和臺灣學者李明輝都曾持此觀點③參見陳來:《孔夫子與現代世界》,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第21-34 頁; 李存山:《儒家的民本與人權》陳啟智、張樹驊:《儒家傳統與人權·民主思想》,齊魯書社, 2004 年第83-96 頁;李明輝:《儒家視野下的政治思想》,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第47-65 頁。。此外,更多的學者傾向于認為傳統儒家蘊含著豐富的人權思想,如倡言良心自由和人格尊嚴、主張法律平等和公正處罰,堅持思想言論自由、反對治心,以及推崇愛國和大同世界等,谷春德、湯恩佳、李世安、陳志尚、林桂榛等為其代表④參見陳啟智、張樹驊:《儒家傳統與人權·民主思想》,齊魯書社,2004 年第23-28 頁;中國人權研究會:《東方文化與人權發展》,東方出版社,2004 年第139-148,164-171,172-180,198-204 頁;林桂榛:《話說儒家思想與人權標準》,聯合早報,2010 年3 月22 日。。
相形之下,“本無后有”派的觀點相對持正公允,因而最終為人們所接受。 他們強調指出:人權思想作為現代社會的普世價值,不僅中國古代沒有,包括西方在內的整個古代社會都沒有。 但是,“本無”并不排斥“后有”,因為“對任何一個傳統來說,都會有些東西是其本來沒有而將來也難以接納的;同時也都會有些東西是其本來所沒有而后來或將來可以接納的”[7](P29)。陳來、陳弘毅、李明輝、俞吾金、喬清舉等都是該派的領軍人物⑤參見陳來:《孔夫子與現代世界》,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第21-34;李明輝:《儒家視野下的政治思想》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第47-65 頁;陳弘毅:《中國文化傳統與現代人權觀念》,法學,1999 年第5 期;俞吾金:《西方的人權理論與儒家的人的學說》學術界,2004 年第2期;喬清舉:《論儒家思想與人權的關系》,《現代哲學》,2010 年第6 期。。 至此,“傳統儒家有沒有人權思想”的問題已經迎刃而解,研究的重點轉入下一環節。
三、儒家人權思想能否進行創造性轉化?
“創造性轉化” 由臺灣學者林毓生率先提出,意指在當今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將傳統文化中的某些思想加以重組或改造,使之既符合時代精神,又保持民族特色。 “創造性轉化”是我國傳統文化面臨的重大課題, 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 而儒家能否開創出自己的人權學說,首先要看“儒家”與“人權”之間能否進行“創造性轉化”。 這一問題經過近20 年的探索, 在西方漢學家、海外新儒家以及國內學界的共同努力下,已經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達成了如下共識:
(一)傳統思想與現代文明的結合是可能的,也是必須的。“一個傳統是可以逐漸演化的,甚至可以更新自己。 ”[8]儒學作為一個開放而非封閉的體系,接受和吸收人權思想并非沒有可能:“把人權語言還原后的內容與儒家思想進行交談,便可發現,已有的人權國際公約的內容, 沒有什么是儒家精神立場上所不可接受的。 ”[7](P32)進一步說,儒學要復興,實現自身的現代化,也必須走與人權等現代文明相結合的道路。
(二)傳統儒家有豐富的思想資源可以直接與第二、三代人權理論相對接。 人權學說自17、18 世紀由歐洲啟蒙思想家創立以來,經過三百多年的發展,至今已形成比較系統的三代人權理論,即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以及發展權、環境權與和平權。其中第二、三代人權更多地體現為民生和集體人權的內容,與傳統儒家所倡導的仁愛、民本、中庸、協和、立人達人、天人合一等精神完全契合,可以直接轉化為與現代人權思想。
(三)傳統儒家還有一些思想資源可以促進第四代人權理論的開發。 當今世界價值多元、訴求各異,且國際經濟政治發展極不平衡,以致貧富差距、霸權主義、恐怖主義、氣候變化、環境危機等全球性問題不斷滋生蔓延,嚴重危及人類的和平與可持續發展。 有鑒于此,有學者提出應該進一步發展現代人權理論,開出第四代人權,而儒家思想中的某些精髓(如絜矩之道)正好可以作為第四代人權的理論支點①如喬清舉認為:“儒家思想不僅可以轉化(為人權思想),而且從當今人類的存在狀況來看,它還具有‘校正’現代人權觀念,形成第四代人權觀念的價值”。 參見喬清舉:《論儒家思想與人權的關系》,《現代哲學》,2010 年第6 期。。
(四)傳統儒家的本質精神與第一代人權理論的要求背道而馳。 傳統儒學始終以維護宗法等級和君主專制為終極目標, 極力倡導忠孝節義綱常倫理以壓制個人權利和民主自由。 在這樣的思想鉗制下,根本不可能產生與“權力”抗衡的“權利”意識,也不可能形成具有獨立人格的“公民”,而只能是封建帝王一人之下的“臣民”,這與第一代人權理論中的公民權與政治權顯然是格格不入的。即使是備受推崇的所謂“民本”,其本質也只是為民做主、吊民伐罪,并非真正意義上的“民主”。 因此, 傳統儒學與第一代人權理論之間存在重大分歧和本質沖突, 如何進行創造性轉化以化解二者的矛盾,成為儒家人權思想理論建構的關鍵。
四、儒家人權思想如何進行創造性轉化?
誠如論者所言, 傳統儒學的基本精神與第一代人權理論是根本對立互不相容的。 首先,儒家以維護宗法等級秩序和君主專制制度為最高宗旨,所謂的“民本”僅僅是實現這一終極目標的手段,這與現代人權理論捍衛人的尊嚴和基本權利的主張是本末倒置的。 其次,儒家特別強調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的等級觀念和忠孝節義等綱常倫理, 人權理論則旨在維護個人的尊嚴和價值, 因而極力主張自由平等和人格獨立。 再則, 儒家宣揚家國同構,重視群體利益,排斥個人主義和功利主義,而后者正是現代人權理論的核心和基礎。 對比分析后不難看出,傳統儒學的立論根基存在重大缺陷,不僅有違人權理論,而且嚴重背離時代精神,必須做出重大調整和實質改變,才能順應時代的發展,完成與第一代人權理論的對接, 進而開創出自己的人權學說。
(一)援“法”入“儒”,接受現代法治理論,轉變德主刑輔觀念,將儒家人權思想的理想落到實處。“儒家哲學作為一個精神傳統是有活力的,但高遠的理想難以落實,于是造成了當前的困境。 ”[9](P3)事實上,這也是儒學的歷史困境,中國兩千多年的治亂循環不啻為儒家治平理想一再落空的明證。 而“高遠的理想”之所以“難以落實”,就是因為缺乏相應的制度安排和程序保障, 在更深層面上則是由于對“法”的認識過于狹隘和偏頗,將“法”等同于“嚴刑峻法”,忽視了法的行為矯正功能和社會治理功能,從而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人治、德治和禮治,進而為君主專制所利用和操縱,導致一治一亂的惡性循環。 另一方面,“人權”本身也不是空洞的口號,它包含著明確而具體的內容,需要通過法律加以規范和保護。 因此,儒家必須重視和充實“法”的觀念,跳出德主刑輔的思維窠臼,摒棄傳統的人治模式,用現代法治的理念和方式將“儒家人權思想”的愿景加以嚴格而縝密的貫徹落實,才能避免該理論最終不流于空談。
(二)棄“君”守“民”,吸收平等自由觀念,拓展民本主義內涵,使儒家人權思想的內核飽滿完整。傳統儒家雖然重民愛民,倡導民貴君輕,但更加強調“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主張“天生民而立之君”,在“民”之上另設一個“君”來主宰其命運,并且要求“民”絕對服從“君”的統治。 這種無條件的順從和效忠不僅助長了“君”的獨斷專行和肆意妄為,也從根本上剝奪了“民”的權利和自由。 因此,儒家的“民本”不過是一具抽掉了“民治(by the people)”之實的空殼,徒有“民有(of the people)”和“民享(for the people)”之名。 更可怕的是,這樣的“民有”和“民享”在事實上也是靠不住的,因為能不能“有”和能不能“享”全在“君”的一念之間,是“君”的恩賜和施舍,可有可無,可多可少,甚至可予可奪。 由是觀之,果斷而徹底地拋棄“君”本位,固守“民”本位,同時摒棄宗法等級觀念,引入自由平等思想,讓每一個人做自己的主人,才是儒家唯一正確的抉擇。 “儒家的民本思想經過批判繼承,吐故納新,揚棄其落后的等級尊卑觀念,承認人人生而自由平等,具有不可剝奪的公民和政治權利,便可以同‘第一代人權’的觀念相契合。 ”[10](P93)惟其如此, 也才能保證儒家人權思想的精神內核飽滿而完整,長久而穩定。
(三)重“義”尊“利”,融入當今權利語境,走出重義輕利誤區,為儒家人權思想的發展謀求空間。傳統儒家勇于擔當,“仁以為己任”,義利之說不僅被譽為儒家第一要義,也塑造了中華民族“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的傳統美德。 然而,這種重義輕利的價值取向明顯有悖于當今的權利本位觀,也與儒家人權思想的要求自相抵牾。 更有甚者,在傳統儒家的觀念里,“義”與“利”在很多情況下都是根本對立而無法并存的。 因此,“舍小利存大義”、“因公義去私利”甚至“存天理去人欲”都被認為是理所當然,“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更被視為最大的“義”而大肆宣揚。 于今觀之,這些觀念都因過于偏頗而嚴重背離了時代精神, 更無法與現代人權理論相接榫。 因此,必須徹底顛覆傳統儒家的義利觀,走出重義輕利的誤區,在當今流行的權利話語框架下,承認“利”的正當性,把“利”擺在與“義”同等重要的位置,甚至視“大利”為“大義”,這才能夠為儒家開創出自己的人權思想謀求適當的發展空間。 反之,一味地抬高“義”而貶低“利”,將使儒家人權思想的理論無以立足。
當然,在傳統儒家的思想寶庫中,還有很多與人權相關的精髓(如仁愛、忠恕、人性、天爵等)值得我們認真檢視,在當今的多元文化背景下進一步加以提煉和創造性轉化,以豐富和完善儒家人權思想。 此外,近年來,儒家以“孝悌”為核心的家庭倫理觀也得到了某些西方漢學家的青睞,認為由此可以為儒家闡釋人權開啟新的通道[11](P94-95)。
五、結 語
綜上所述,“儒家人權思想及其創造性轉化”是儒學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重要命題, 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大變局”背景下產生的新思路和新課題。 該命題的提出和論證表明,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傳統文化經過百年的沉寂和反省, 已經走出了挫敗、迷惘和困惑,走上了與現代文明相結合的道路, 而這也正是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傳統文化復興的必由之路。 如今,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崛起的號角已經吹響, 民族復興的步伐愈益堅定,但是,中國的發展顯然不宜過分依賴經濟和軍事,而應該更加注重文化、制度等軟實力的建設,以提高國民素質、提升國家形象。 因此,有理由相信,“儒家人權思想”及其創造性轉化的研究,對于儒學和傳統文化的復興, 以及在更大程度上對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乃至“中國夢”的實現,都具有至為重大的意義。 正如金耀基先生所言:“對于中國的現代化運動,我們沒有權利做一個旁觀者,我們必須以良心、智能與熱忱加以擁抱。 ”[3](P156)
[1] 喬清舉.論儒家思想與人權的關系[ J].現代哲學,2010,(6).
[2] 程燎原.中國法治政體問題初探[M].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2.
[3] 金耀基.從傳統到現代[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4] 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M].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
[5] 嵇文甫. 中國歷史上曾有過民權思想么[A].嵇文甫. 嵇文甫文集(上)[C].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6] 梁漱溟. 中國文化要義[M].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7] 陳來. 孔夫子與現代世界[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8] 陳弘毅.中國文化傳統與現代人權觀念[ J].法學,1999,(5).
[9] 劉述先. 儒家思想的轉型與展望[M].石家莊:河北出版傳媒集團公司,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
[10] 李存山.儒家的民本與人權[A].陳啟智,張樹驊. 儒家傳統與人權·民主思想[C].濟南: 齊魯書社,2004.
[11] 沈美華.人權的儒學進路[ J].韓銳,劉曉英,譯.現代哲學,20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