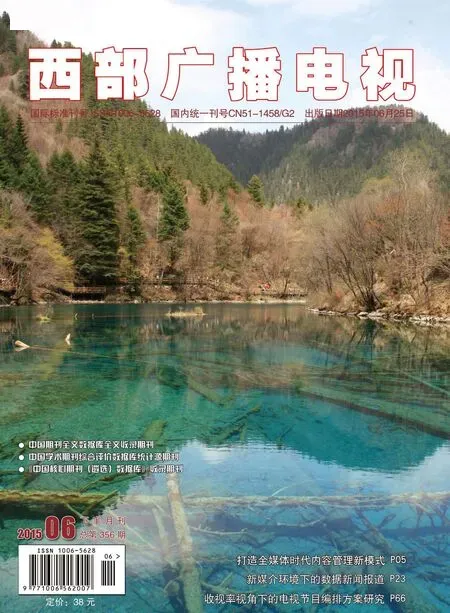時間與空間——論新媒體強制性傳播的兩個維度
鄧 鵬
(作者單位:寧波大學)
時間與空間——論新媒體強制性傳播的兩個維度
鄧 鵬
(作者單位:寧波大學)
摘 要:新媒體從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潛移默化地改變著我們的生活節奏和生活環境,成為我們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文從時間環境、空間環境的視角分析新媒體對現實環境的改造,描述了新媒體影響下人們的生活狀態。在新媒體環境下,如何趨利避害,在人與媒介環境之間共建一種良好的媒介文化生態,是研究的重要旨趣。
關鍵詞:新媒體;強制性傳播;技術入侵;時空改造
新媒體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某一形式的新媒體是相對于在它產生之前已經存在的媒體而言的。當下,我們把新的技術支撐體系下出現的如數字雜志、數字報紙、數字廣播、手機短信、網絡、數字電影電視、觸摸媒體等媒體形態,稱為新媒體。媒體的發展歷程不是新舊替代的過程,而是一個并存、融合發展的過程。麥克盧漢曾說過:媒介是人體的延伸。媒介成為人們感知外部世界的重要中介,新媒體的普及,使人們擁有了更加先進的工具來感知外部世界。媒介的發展是一把雙刃劍,它在給我們生活帶來極大便利的同時,也帶來諸多不利的影響。以公共汽車中的移動電視媒體為例,其相對狹小封閉、動靜結合、高頻次重復傳播的特點造成了其信息傳播上的強制性傾向[1]。在新舊媒體成為一種無所不在的生活景觀時,不論我們身在何時何地,都能感受到新媒體傳播的強大威力。
1 時間侵略:習慣性使用甚至成癮
新媒體對我們的包圍,形成各種形式的“時間消費機器”:在家里可以在電腦上聊天、購物、玩游戲、看視頻等;在公交車、火車、地鐵里我們“被”聽和看車載的移動電視;在路上我們可以看手機新聞、刷微博、聊QQ、逛微信朋友圈,也可以看路邊的廣告屏和裝飾在樓宇間的廣告電子屏幕。以移動電視為例,有學者曾提出移動電視文化生態的負效應,表現為在現有電視資源外建立了新的完整電視頻道,“高度”地利用了受眾的零余時間,在受眾心理需求中加入了強迫性的因素,并指出其本質上是公共空間對私人空間的侵犯,是典型的非生態,是對電視生態功能的錯亂重組[2]。
個人越通過使用媒介來滿足需求,媒介在個人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就越重要,而媒介對個人的影響也就越大。一般而言,適度的媒介依賴對個人獲取信息及情感表達有益,過度則可能是病態行為,甚至有可能產生“媒介成癮綜合癥”,導致心理異常,并產生一定的生理不適應[3]。當下是“注意力經濟”的時代,不管我們走到哪里,新媒體背后的商業大手都想盡方法占用我們的時間和注意力,受眾和受眾被占用的時間成為一種商品,被媒體背后的傳播者轉手倒賣。新媒體已經成為我們了解外部的一個重要途徑,學會使用新媒體甚至說用好新媒體已經成為我們適應現代快節奏社會生活的一項重要的技能,這是時代對個人提出的要求,也是個人自我發展的需要。如果基于生活的基本信息需求產生的這種對新媒體的使用存在很大的受眾的主觀能動性,那么以娛樂休閑為主的新媒體的使用行為則體現了新媒體自身娛樂功能對受眾的一種“吸附力”,這種“吸附力”以強大的娛樂攻勢,以各種形式愉悅大眾,獲取時間消費和金錢消費產生的利益。
2 景觀的改造:新媒體的空間侵略
新媒體的普及帶來了兩種全新的生活景觀,一種是固定的,如依附于高樓大廈的樓宇電視廣告牌、家用臺式電腦、數字電視等媒體,另一種是移動的,比如平板電腦、手機、車載移動電視等媒體。這兩種形式的新媒體都在入侵我們的生活空間。新媒體的普及重新定義了我們的生活空間景觀。以各種“屏”為代表的新媒體作為新的景觀的同時也作為呈現景觀的景觀。我國傳播學者邵培仁先生曾說,“景觀的意義并非與生俱來,而是人們給予自己的世界觀及與他人的關系創造、表述和解釋的結果”,“景觀及其意義的差異性,除了依賴于各種政治或權力機構對城市空間的重構外,媒介的再現和闡釋也是重要的原因”[4]。某種意義上而言,新興媒介的普及呈現著一種如居伊·德波在他的《景觀社會》中所論及的“景觀的龐大堆積”的狀態。商業利益是這種狀態改變和發展的背后推動力。“工業時代的商品生產方式的主導地位已經讓位于‘媒介時代’的景觀生產方式。通俗地說來,工業時代生產的商品因為有用才能賣出去,而‘媒介時代’的商品因為‘看到’才能賣出去。[5]”新媒體借助于新的技術在空間中極力呈現的各種娛樂、資訊、廣告等信息,成為一種無所不在的存在。
新媒體的景觀改造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借助于廣泛普及的強大終端,在受眾的周圍營造“擬態環境”,二是在傳統的地理空間中,重新建構建筑和重構建筑景觀。無論人們處于何種位置,其個體社會化習慣都受到所處環境場域背后無形的權力和資本直接或間接的支配和影響。無論何時何地,當我們一睜開眼,就難以回避新媒體對我們的包圍,我們成了“強制性傳播”的受者。如果這種“強制性傳播”是有益的,我們就成為受益者,
而如果是有害的,我們就成了無辜的受害者。不論是有害還是無害或者中性,我們的生活空間正被新媒體的聲影喧囂占據越來越多的領地。
3 信息入侵導致的空間包圍和時間延滯
當我們縱身于新媒體的環境中時,各種各樣的信息吸引著我們的注意力,我們或主動或被動地接受各種注意力的牽引,成為流變的時空環境中被扭曲的人。我們的大腦成為了一個處理各類信息的場域,而各種媒介成了無時不刻不在傾倒信息的機器。新媒體提供而被受眾接受的碎片化信息和形成的散碎議程,成為我們自由獨立思考的重大干擾。在這樣的環境下,人們對新媒體的“預期得越多,他生活得就越少;他將自己認同為需求的主導影像越多,他對自己的生存和欲望就理解得越少。景觀與行動的主體的疏離,觀眾在哪里都感到不自在,因為景觀無處不在[6]”。從現實和虛擬空間對人們的生活狀態進行支配和影響,顯然,不論你是否愿意,當受眾需要花更多的時間去逃避或處理信息的時候,自主獨立的思考就會被左右,而陷入一種消極被動的狀態。
4 結語
移動、戶外新媒體營造全新的傳媒生態,媒介成為無所不在的“擬態環境”構建者,“把關人”的利益追求成為左右媒介生態空間進化的重要因素,“娛樂至死”的背后,技術改寫人的社會理性而促使工具理性人的成長。新媒體環境下的“魔彈論”回歸,展示著一種全新的媒介生態。從傳播者、傳播方式、傳播過程到受眾、反饋傳播過程,以及整個傳播過程中的各種信息和外在力的干擾,新媒體在其中扮演者重要角色,同時也以各種方式不斷改寫著媒介環境。在新媒體形成的大環境下,學界對于新媒體的研究多立足于描述性諸如新媒體特征、種類等方面,新媒體應用,如微博營銷、微信營銷等方面,而立足于批判視角,對于新媒體對我們的生產生活產生的消極影響的批判性研究較少。描述現象和探索應用并不是我們追求的終點,如何在新媒體環境下形成一種良好的人居生態才是終極旨趣。
參考文獻:
[1]李正良,盧佳.公共汽車媒體的強制性傳播研究[J].新聞愛好者,2011,(11):20-21.
[2]蔡貽象.移動電視的文化憂慮[J].電影藝術,2005,(4):90-93.
[3]葛自發.新媒體對“積極受眾”的建構與解構[J].當代傳播,2014,(1):71-73.
[4]邵培仁.景觀:媒介對世界的描述與解釋[J].當代傳播,2010,(4):4-7.
[5]劉力永.景觀社會:媒介時代的一種批判話語[J].北方論叢,2006,(6):48-51.
[6]居伊·德波.景觀社會[M].王昭鳳, 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9-10.
作者簡介:鄧鵬,寧波大學人文與傳媒學院在讀碩士,研究方向:文藝與新傳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