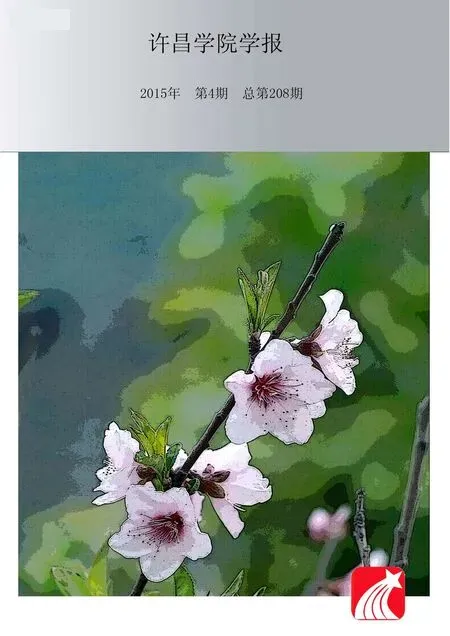徐幹“齊氣”新解
——以徐幹與荀學的關系為中心視角
胡 清 清
(西華師范大學 文學院,四川 南充 637000)
徐幹“齊氣”新解
——以徐幹與荀學的關系為中心視角
胡 清 清
(西華師范大學 文學院,四川 南充 637000)
曹丕頗以徐幹之“齊氣”為嫌,應是由于徐幹所秉持的一份儒士氣導致其在個性氣質以及文學創作方面有諸多規范和節制,這和曹丕本人以及時代風氣頗不相宜。而在如何搭建“齊氣”與“儒士氣”的關系問題上,荀學則起到了橋梁的作用。荀子為齊國儒生之首,徐幹對其借鑒甚多,故不妨將“齊氣”視為“荀子之氣”。
齊氣;儒家;荀子
“齊氣”一詞由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批評徐幹之時提出,然而究竟何指,至今仍破費思量。目前學界的研究思路大抵沿著以下兩個方面展開。一是從地域角度出發,學者們往往先指出齊地、齊人有何特征,而徐幹是齊人,故理應也有這些特征。如最早李善在《文選》注中提出“齊俗文體舒緩,而徐幹亦有斯累”,到后來郭紹虞援引各家之說論證齊風舒緩,再到后來譚家健指出“齊人的氣質特點乃是舒緩。徐幹的‘齊氣’,看來是指其氣質而言”。[1]二是從文字學層面考察“齊”的義指,得出“齊”字的涵義。如志洋的“莊肅之氣”,[2]黃曉令的“齊一之氣、平平之氣、乃至俗氣”,[3]124吳孟夏的釋“齊”為“中”,認為徐幹個性“通脫不夠”,[4]216還有項念東的“齊平之氣、端直之氣”。[5]55考察徐幹為人為文,可知其與時代風氣頗多捍格之處,故而引起曹丕微辭。究其緣由,則當歸結于其所秉持的一份儒士之氣。然而“儒士氣”與“齊氣”有何關聯?在此一點上,筆者認為“荀學”搭建了兩者之間的關聯。荀子為戰國末期大儒,曾三次出任齊國稷下學宮祭酒,實為齊國儒生之首,而徐幹對荀子借鑒甚多,故不妨可將徐幹之“齊氣”視為“荀子之氣”。
一、徐幹儒學學養及其與荀學的關系
何為儒者?班固《漢書·藝文志》說:“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為高。”顯然徐幹與儒者的身份定位是十分相符的。作為建安文人集團的成員之一,徐幹較其他成員更為突出的一個特點也就是他的這一份儒家君子人格。無論是從個性氣質還是從價值追求上來說,徐幹都深受儒家思想影響,故后世亦多視之以醇儒形象,如北宋曾鞏在《中論序》中說:“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又如清周中孚《鄭堂讀書記》也稱:“蓋是時惟偉長著書,無忝儒者本色。”而最能體現徐幹學術思想的即《中論》一書,歷代著錄除《宋史》卷二百五《藝文志》列為雜家外均將其列入儒家。[6]400-403《中論》一書作為徐幹的寄意之作,我們可從中探究其儒家學養。
孔子歿后,儒家以孟、荀為最醇,[7]15而孟荀的很多思路并不一樣,他們分別繼承孔子思想而又有所發展。徐幹儒家學養的主要來源就是孔孟荀先秦儒家思想,而尤其對于荀子,徐幹的借鑒和吸收頗多。這一點,徐湘霖在《中論校注》一書中已有指出。以下從具體的思想主張出發探討徐幹儒學學養與荀學的關系。
(一)關于社會秩序的建立
社會秩序問題是一個國家最根本也是儒者最為關心的問題。關于建立社會秩序,儒家向來主張“禮治”。而在此基礎上,孔子找到了“仁”這一心理本原,來作為實現“克己復禮”的途徑。孟子則進一步繼承孔子的精神,提出了“性善說”和“仁政”。孔孟的思路大體一致,即建立社會秩序不是依靠外在的法律約束而是依靠人內在的道德自律意識和外在的禮儀象征形式維持。[8]151然而荀子的思路卻與此不同。相比孔孟的理想主義,荀子對現實有著更加清醒的認識。他倡言性惡,雖一方面重視禮樂的垂戒示警意義和理性的道德調節,然另一方面也重視現世治理中的實用功利。[8]152故荀子提出“法后王,統禮義,一制度”的政治見解,形成兼涉“內圣”、側重“外王”的治世理論。[9]5《王制》篇說:“聽政之大分:以善至者,待之以禮;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漸賞慶以先之,嚴刑罰以防之”。“刑”和“賞”是法家思想里兩個重要的范疇,由此可以看出荀子的思路不再僅僅是儒者的人文主義。傳統的儒者執著于理想而不切實用,但荀子的思路中蘊涵了十分實用的,既可以用之于道德自律,又可以推之于法律管束的意識形態意味。[8]154顯然,徐幹關于建立社會秩序的理論深受荀學思想影響。作為儒者,徐幹既強調修養一己之道德,又十分稱善禮樂的教化作用。然而徐幹也深刻認識到外在刑罰存在的必要,《賞罰》篇言“天生烝民,其性一也。刻肌虧體,所同惡也;被文垂藻,所同好也。” 徐幹認為趨利避害是人的本性,而這也就道明了賞罰得以實行的依據。故他在此一篇中開宗明義地指出:“政治大綱有二,二者何也。賞罰之謂也。人君明乎賞罰之道,則治不難矣。”又在《遣交》篇稱“昔圣王之治其民也,任之以九職,糾之以八刑,導之以五禮,訓之以六樂,敎之以三物,習之以六容”。由此可以看出徐幹的治國治民之方承繼荀子“禮法并用”的思想。
(二)對于人性的判斷
對于人性的基本估計,有兩種截然相反的態度,一種是孟子所持的“性善說”,另一種則是荀子倡言的“性惡說”,荀子在《性惡》一篇,開頭就給予說明——“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荀子認為人性生而有好利、有疾惡、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如果順從之,則會導致爭奪、亂理乃至歸于暴的結果。因此荀子一方面特別強調教育和學習,依靠后天的熏染、修養來使人們養成遵守規則、服從秩序的習慣,[8]153另一方面則特別注意“禮”對人的規范和節制。通觀《中論》一書,徐幹在人性問題上并未作出明確判斷,然而基于對人性的看法而引申的主張,徐幹則大多沿著荀子的思路。在《治學》篇中,徐幹指出“民之初載,其蒙未知”,但他對人性當中的“瑕疵”與“惡”卻有著比較清楚的認識。在《修本》篇中,徐幹說“夫珠之含礫,瑾之挾瑕,斯其性與?良工為之以純其性,若夫素然。故觀二物之旣純,而知仁德之可粹也。”徐幹認為珠玉之性是有瑕疵的,然良工可以純其性,人之性也是有瑕疵的,而通過修身則可以使仁德純粹。在《虛道》篇中他又說“夫惡猶疾也,攻之則益悛,不攻則日甚。故君子之興善也,將以攻惡也。惡不廢則善不興,自然之道也”。徐幹認為人性當中的善與惡起著陰長陽消的變化,所以他也十分注重后天的學習和修養,認為君子之所以能夠成德立行,都是“學”的緣故。[10]1與此同時,和荀子一樣,徐幹也特別注重“禮”對人的規范和節制。這一點將在下文詳加分析。
(三)對待“禮”的態度
荀子對于“禮”是十分重視的,荀子之學可謂就是“隆禮”之學。他在《修身》篇中說“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勃亂提僈;食飲、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觸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眾而野。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小到言語舉動,大到治國安邦,作為言行道德規范的最高標準乃至修身治國的根本,“禮”在荀子的思想中幾乎無處不在。而徐幹對于“禮”的重視也并不亞于荀子。在《法象》篇中,徐幹說:“故立必磬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軌,折旋中矩;視不離乎結繪之間,言不越乎表著之位;聲氣可范,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貴,述作有方,動靜有常,帥禮不荒,故為萬夫之望也。”由此可知,徐幹亦將“禮”視為言行動作之則,時刻不敢媟慢。又說“夫禮也者,人之急也,可終身蹈,而不可須臾離也。須臾離則慆慢之行臻焉,須臾忘則慆慢之心生焉,況無禮而可以終始乎!”這和《論語·里仁》篇所說的“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以及《中庸》里說的“道也者,不可須臾離者也”的句式相同,然而不可須臾離的對象卻由“仁”、“道”換成了“禮”,可見徐幹的思想中對于“禮”的重視是和荀子一致的。
(四)對待“名”的態度
“名”的實際內涵其實是一套語言系統,現象世界無一不是由語言指稱的,[8]183所以“名”有著指稱世界的意義。荀子說“名定而實辨”,[11]414也就是說名稱一旦確定,那么實際事物就能分辨了。然而一旦名稱的管理松懈,名與實的指稱發生混亂,就會導致民眾產生疑惑,而社會秩序也會因此混亂。所以荀子非常痛恨亂名的行為,在《正名》篇中,他指出亂名的罪行:“故析辭擅作名以亂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訟,則謂之大奸,其罪猶為符節、度量之罪也。”在對待“辯說”這一問題的態度上荀子向來是謹慎的,然而當“圣王沒,天下亂,奸言起,君子無勢以臨之,無刑以禁之”的時候,辯說也就成了必要,所謂“實不喻然后命,命不喻然后期,期不喻然后說,說不喻然后辨。”徐幹在“辯說”和“亂名”的問題上承襲了荀子的態度。在《核辯》篇中,徐幹批判了只為“屈人之口”的辯說,指明辯的意義在于“為言別”,即“為其善分別事類而明處之也”。這便與荀子弄清名物事理的正名思想相一致。而對于“亂名”的行為,徐幹的態度更是毫不留情,在《核辯》一篇中他明言“先王之法,析言破律,亂名改作者,殺之;行僻而堅,言偽而辯,記丑而博,順非而澤者,亦殺之”。
此外,在一些具體問題的看法上,徐幹也承繼了荀學一路的思想。如對于“學”的強調,對于“智”、“權衡”的看重以及對于尚賢使能的重視等等。由此可以看出,徐幹的儒家學養與荀學一路的關系。
二、徐幹儒學學養對其文風的滲透與影響
把儒家君子人格作為理想與追求的徐干對于儒家思想是不遺余力去奉行的,故其儒家學養必也滲透影響到其文學創作。鑒于此,孫寶先生在《徐幹儒學文藝觀與創作關系述論》一文中,根據徐幹在《中論》一文中所體現出來的文藝思想,提煉歸納出了他的儒學文藝觀,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首先,注重個人創造的藝德觀;其次,以言為貴、言為徳藻的重言觀;再次,以立志為先、博達中正的才學觀。可以看到因受其所秉持的儒家學養的影響,徐幹雖也重視“藝”、“言”、“才”,但對待它們的態度卻始終以儒學價值觀念為指導。在《藝紀》一篇中,徐幹指出“藝者所以旌智、飾能、統事、御群也”,“藝者以事成德者也”,徳是人的根干,而藝則是徳的枝葉,習藝是為了成德。這就賦予了“藝”以儒家所強調的價值功能,與孔子在評價《詩》時所提出的“興觀群怨”說是一致的。此外,《藝紀》篇又說:“故恭恪廉讓,藝之情也;中和平直,藝之實也;齊敏不匱,藝之華也;威儀孔時,藝之飾也。”這些都是出于儒家思想而對“藝”所作的限定,與“溫柔敦厚”的詩教也是相一致的。對于“言”,徐幹也十分謹慎,《法象》篇稱“君子口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雖妻妾不可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可得而狎也”。《核辯》篇又指出“茍美其聲氣、繁其辭令,如激風之至,如暴雨之集”的論辯只是屈人口舌而已。徐幹的才學觀,亦是突出以儒學為核心的知識論和價值論。總之,徐幹的文藝觀以儒家經典為核心的學識為基礎,以儒學價值觀構建的德性為旨歸,[12]115倘若與儒家價值無涉,徐幹的態度就會是像無名氏在《中論序》所說的“見辭人美麗之文并時而作,曾無闡弘大義,敷散道教,上求圣人之中,下救流俗之昏者,故廢詩賦頌銘贊之文”了。
徐幹的儒學文藝思想是從《中論》一書中提煉出的,因而也在《中論》的創作中體現得最為明顯,當然這種影響也會擴展至其詩賦創作。下面就分別從這兩個方面闡述徐幹儒學文藝觀在文學創作中的體現。
首先,《中論》一書在文風上體現出宗摹荀子的特色。《中論》一書承繼《孟子》、《荀子》的子書撰制傳統,[12]115而無論是在篇目安排、遣詞造句以及辭采意氣方面,《中論》都對《荀子》借鑒頗多。首先在篇目安排上,《荀子》和《中論》都以修身為要,而《中論》開篇便言《治學》,顯然承自《荀子·勸學》。在用詞方面,《中論》中的很多名物語詞都來自《荀子》,如《法象》篇的“行必由檢”的“檢”字作為“法式、法度”的意義就來自于《荀子·儒效》篇“禮者,人主之所以為人臣寸、尺、尋、丈檢式也”的“檢”字;又如《修本》篇中的“慮人而不自慮者謂之瞀”的“瞀”字也是來自于《荀子·非十二子》一篇中的“瞀儒”一詞。故孫啟治在給《中論》作注解之時,就經常引用楊倞給《荀子》作的注。在句法方面,直接引用《荀子》的例子有《考偽》篇的“盜名不如盜貨”、《貴言》篇的“禮恭,然后可與言道之方;辭順,然后可與言道之理”。而如《藝紀》篇“故寶玉之山土木必潤”一句則化用了《荀子·勸學》篇中的“玉在山而草木潤”;《爵祿》篇中的“夫登高而建旌,則其所視者廣矣;順風而振鐸,則其所聞者遠矣。非旌色之益明,非鐸聲之益遠也,所托者然也”一句化用了《荀子·勸學》篇中的“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等句。在辭采意氣方面,《中論》一書頗有荀子之氣,近人徐仁甫在《讀<中論>札 》一書中就直接指出:“偉長法荀卿為文,縟而不繁,徐而不迫,雍容靜穆,藹然儒者之度。蓋入而能出者,故雖有模擬,不可得而尋其跡,斯善擷屬文采者矣。”[13]327
其次,在詩賦創作方面,因受儒學文藝觀的影響,徐幹在內容、情感以及文采辭藻方面都有所節制。在創作內容上,與建安七子其他成員相比,徐幹較少游宴、奉命之作。偶爾有如《車渠碗賦》這樣的同題奉命之作,徐幹亦是寥寥數語作結,不作夸飾奉承之語,顯示了其一份不同流俗的儒家君子人格。在情感表達上,徐幹因受到“禮”的節制而不夠激越,始終以“中和”為持守,保持著一份儒者應有的“哀而不傷”、“怨而不怒”的氣度,此點對比徐幹與劉禎的贈答詩即可體察。劉禎為人慷慨任氣,在《贈徐幹》一詩中將自己對“拘禁”甚嚴的不滿以及對友人的思念之情都充分地表達出來。相較之下,徐幹在《答劉禎詩》中雖也說“我思一何篤,其愁如三春”,然其詩風高簡渾樸,情感亦較含蓄收斂。在文采辭藻方面,徐幹主張“闡弘大義,敷散道教”,并不喜辭人美麗之文,因而他的的作品大多語詞質實。鐘嶸在《詩品》中評徐幹曰:“偉長與公干往復,雖曰以莛扣鐘,亦能間雅矣。”鐘嶸在文學批評上比較注重情采,“以莛扣鐘”大略即指情感表達與辭采方面而言。
三、曹丕“齊氣”論與建安、黃初文氣轉換
中國古代的文學思想以儒家思想為理論基礎,十分重視文學的政教功能,因而有諸多束縛,然至建安、黃初時期則有了一個較大的轉變。這首先得益于儒學的衰弱。漢末的亂世對于抱守儒家治世理想的文人士大夫來說,無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儒學價值體系的崩頹,使他們失去了賴以支撐的精神支柱,人生信仰也隨之坍塌,所以他們不得不去尋找新的精神依托。而就是在這樣的當口,人們的眼光開始轉向自身的人生價值,這種轉向開拓了知識分子的精神空間,是而人的覺醒以及文學的自覺也就成為了歷史必然。魯迅認為曹丕的時代是文學的自覺時代,在這個時代里,儒家思想對文人頭腦的束縛松弛了,文學不再僅僅只是政教的工具和附庸。隨著文章日益為人所重視,它本身的審美作用也得到了充分肯定。對于作者來說,它不再需要弘揚大義,也可以僅僅作為一種宣泄情志、自我娛樂的方式。而在情感與辭采方面,也大大擺脫了先前儒家思想的限制。建安時代的作者,由于感念世亂,渴望建功立業,故其作品激情回蕩,大多慷慨任氣,勁健有力。[14]32總的來說,他們都是以情感激蕩、文辭華麗為美的。這一時代正如劉勰在《文心雕龍·時序》篇所說“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三曹和七子在文學領域大放異彩,并且形成了“雅好慷慨,梗概多氣”的時代風貌。至此中國文學又掀開新的一頁,如大幕開啟,引人注目的是臺上人物的歌哭笑罵,或裂眥長嘯,或風情萬種,性情揮灑,淋漓盡致,使人看到了濃烈的情感。[15]126
作為曹魏政權的統治者,曹丕當然是引領時代風氣的一個關鍵人物。時風的轉換除卻儒道中衰的原因,也得力于統治者的提倡。《晉書·傅玄傳》中,傅玄上疏稱:“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 曹丕確實是一個文士氣頗重且慕通達的人,他的生活作風及人生態度偏向于隨意、自然,甚至是有意識對抗和破壞儒家禮法制度。[16]188和謹言慎行、絲毫不敢違背禮制的徐幹相比,曹丕以言語為笑樂、在喪禮之上學驢鳴、在曹操死后喪不廢樂等,都是縱情任性的表現。陳寅恪先生曾將曹氏的社會階級歸于非儒家寒族。[17]1可見在曹丕的思想中,儒家的成分并不是很多,自然他的文學理念也不會在儒家的規范之下。在《典論·論文》一篇中,曹丕對于文學對個人人生的價值有著明確的認識,認為文章“乃不朽之盛事”。在辭采方面,他也明確提出“詩賦欲麗”的主張。
徐幹身懷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政治理想,并不以文學自稱,然曹丕是將其作為文人加以評價的。他的文氣說,以“氣”論人,當說某作家具有某種氣時,雖是指其作品而言,但也兼指作家本人的氣質,總的說來,“氣”應該就是指評論對象總的風貌給人的一種總的印象與感受。[14]30曹丕說徐幹“時有齊氣”,即是如此。徐幹因受儒家道德價值規范,在為人為文方面諸多限制。清初陳祚明曾評價徐幹的擬古詩“偉長詩,別能造語,匠意轉掉,若不欲以聲韻經心,故奇勁之氣高迥越眾,如廣坐少年中,一老踞席兀傲不言,時或勃然吐詞,可以驚駭四筵矣。”[18]699此語雖是對其擬古詩的褒獎,從中也可想見徐幹平日持中沉潛的儒士風范。而這對于意氣風發的時代以及隨意通脫的曹丕來說卻是頗不相宜的,因而他對徐幹頗有微辭也就可想而知了。
[1] 譚家健.試談曹丕的典論·論文[J].新建設,1964(2):93-103.
[2] 志洋.釋“齊氣”[N].光明日報,1960-11-20.
[3] 黃曉令.典論·論文中的“齊氣“一解[J].文學評論,1982(6):123-124.
[4] 吳孟夏.曹丕“文氣“說淺析[A].建安文學研究文集[C].合肥:黃山書社,1984.
[5] 項念東.典論·論文“齊氣”研究略評[A].古代文學理論研究21輯[C].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
[6] 孫啟治.中論解詁附錄二目錄提要[M].北京:中華書局,2014.
[7] 錢大昕.跋荀子,轉引自王先謙荀子集解[M].北京:中華書局,1988.
[8]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一卷[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
[9] 房登科.禮法同行天下——治荀子禮法思想研究[D].揚州大學,2004.
[10]孫啟治. 治學第一[M].中論解詁.北京:中華書局,2014.
[11]王先謙.荀子集解上[M].北京:中華書局,1988.
[12]孫寶.儒學嬗變與魏晉文風建構[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
[13]徐湘霖.中論校注[M].成都:巴蜀書社,2000.
[14]王運熙、顧易生.中國文學批評通史二·魏晉南北朝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5]汪春泓.“徐幹時有齊氣”新解[A].中國詩學第五輯[C],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7.
[16]王永平、胡學春.魏文帝曹丕之“慕通達”及其原因與影響考論[J].求索,2005(11):188-192.
[17]萬繩楠整理.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M].合肥:黃山書社,2000.
[18]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七,續修四庫全書第1591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責任編輯:石長平
2014-12-25
胡清清(1990—),女,浙江金華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魏晉南北朝文學。
I206
A
1671-9824(2015)04-005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