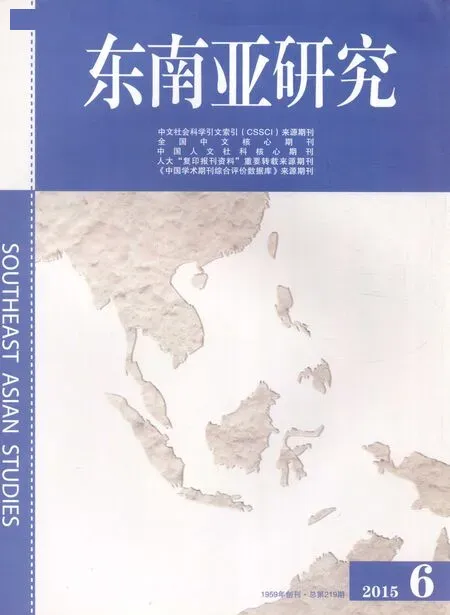韓國流行文化在東南亞的傳播分析*
吳杰偉
(北京大學東方文學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1)
?
韓國流行文化在東南亞的傳播分析*
吳杰偉
(北京大學東方文學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關鍵詞]韓國;流行文化;東南亞;傳播;本地化;文化交流
[摘要]20世紀末,韓國流行文化產品成為東南亞民眾休閑和娛樂的主要選擇之一。進入21世紀以后,以電視劇、音樂、電影、時尚產品等文化形式為代表的“韓流”在東南亞地區得到廣泛傳播。本文主要考察韓國流行文化在東南亞傳播和被接受的過程,分析韓國流行文化傳播的主要途徑,討論韓國流行文化在東南亞廣泛傳播的原因。本文認為,韓國流行文化運用區域化(東方化)的形式包裝全球化的主題,運用互聯網技術拓寬傳播途徑,充分利用東南亞地區相對寬松的社會環境,在東南亞地區獲得充分的傳播。在中國政府提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戰略的背景下,韓國流行文化的傳播模式對中國文化戰略具有積極的借鑒意義。
Cultural Analysis on the Spread of Korean Wave in Southeast Asia
Wu Jiewei
(Research Center of Eastern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Korean Wave (Hallyu) appeared in Southeast Asia by the end of 20 centuries and became a popular choice for relaxation and entertainment in this region. In past 10 years, the Korean Wave has swept Southeast Asia from the TV drama, film, music, fashion and other genres. A major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the spread of the Korean Wave in Southeast Asia, and discuss the spreading and acceptance of pop culture in a modern community.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Korean Wave is a regional response to the growing globalization in Korean localized way, which including traditional values, oriental figures, romantic stories, etc. In addition, this paper notice that the impact from digital technology and immigration to the Korean Wave in Southeast Asia.
一研究背景
20世紀80年代,韓國經濟得到迅猛發展,提升了韓國的國家形象。1988年漢城奧運會①2005年,“漢城”更名為“首爾”。此處沿用當時的中文表達方式。的成功舉辦,極大地提升了韓國民眾的民族自豪感。20世紀90年代末,韓國的偶像組合HOT、NRG、Baby Vox的海報布滿中國大街小巷,引領中國青少年的穿著打扮。也是在這個時期,“韓流”(Korean Wave)開始出現在中國的新聞報道中。進入21世紀,韓國流行文化(Pop Culture)也逐步在東南亞地區建立影響,2005年韓劇《大長今》的熱播更是成為韓國流行文化在東南亞地區廣泛傳播的助推劑。
隨著韓國流行文化在亞洲的傳播,韓國流行文化逐漸成為研究韓國社會和文化的一個重要視角,并在21世紀初達到研究的高峰。對東南亞“韓流”現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韓國流行文化興起的原因、韓國流行文化在東南亞傳播的模式及其對當地社會所產生的影響等三個方面。沈都寶(Shim Doobo)的《韓流在東南亞》、徐鐘碩(Suh Chung-Sok)等人的《韓流在東南亞:關于韓國文化產品的文化相似性和全球化分析》、夏洛·史迪雅迪(Charlotte Setijadi)的《質疑文化相似性:東亞電視劇在印尼》、鄭裴智(Chung Peichi)的《在東南亞地區共同打造“韓流”:數字化融合與亞洲媒體區域化》和武洪先(Vu Hong Tien)等的《以電視劇為媒:韓國電視劇對越南婦女婚姻觀念影響的分析》等研究成果分別從文化傳播、文化相似性、文化的本土化等角度分析了韓流在東南亞傳播的原因和影響*詳見Shim, Doobo, “Korean Wave in Southeast Asia”, Kyoto Review of Southeast Asia, Issue 11, 2011; Suh, Chung-Sok, etr., “The Korean Wave in Southeast Asia: An Analysis of Cultural Proximity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Korean Cultural Products”, KAREC Discussion Paper, Vol.7, No.2, 2006; Setijadi, Charlotte, “Questioning Proximity: East Asian TV Dramas in Indonesia”, Media Asia, Vol.32, Issue 4, 2005; Chung, Peichi, “Co-Creating Korean Wave in Southeast Asia: Digital Convergence and Asia’s Media Regionalization”, Journal of Creative Communications, Vol.8, No.2-3, 2013; Hong Tien Vu & Tien-Tsung Lee, “Soap Operas as a Matchmaker: A Cultivation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South Korean TV Dramas on Vietnamese Women’s Marital Intention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Vol.90, No.2, 2013.。
隨著中國政府提出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倡議,中國文化在東南亞傳播的過程中,將會與韓國流行文化在東南亞地區再次發生重疊,通過研究韓國流行文化在東南亞傳播的內容、途徑和效果,可以為中國文化擴大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提供積極的借鑒。
二韓國流行文化在東南亞的傳播情況
20世紀60年代,韓國政府開始實施以流行文化為中心的文化政策,最初的目的是為了提升國內年輕人的民族文化自豪感,以平衡西方文化對韓國社會的沖擊。文化政策在國內取得較好的效果之后,1998年,韓國政府成立韓國文化產業振興院(KOCCA),以促進文化商品如電影、游戲、藝術、音樂和動畫等出口到國外。韓國電視劇和電影就是得益于文化產業振興政策,率先走向東南亞地區。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東南亞地區的電視臺在引進電視節目的過程中,偏向于選擇價格相對比較便宜的產品。韓國電視劇的價格只有日本電視劇的1/4,是香港電視劇價格的1/10,更加符合東南亞地區的市場需要。1998年,《星夢奇緣》(Stars in My Heart,又譯《星星在我心》,韓國文化廣播公司)在越南電視臺播出以后,韓國電視劇的播出量越來越大,甚至占越南電視劇總時長的40%。

表1 韓國電視節目出口數據統計表
說明:金額單位為千美元,節目時長單位為集,括號里的數字為所占比例。
資料來源:Park, Young Seaon, “Trade in cultural goods: a case of the Korean wave in Asia”,JournalofEastAsianeconomicintegration, Vol.18, No.1, 2014, p.96.
通過在傳播內容和傳播方式方面的努力,韓國流行文化在東南亞地區呈現出迅猛發展的態勢。從表1對日本、中國(包括中國香港和中國臺灣)和東南亞(包括新加坡、越南、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泰國、菲律賓、柬埔寨等7個國家)的相關統計數據可以看出,日本是近年來韓國電視節目的主要出口地,從2001年至2011年,出口金額增長了80多倍,節目時長增長了5倍多。對中國市場方面,雖然出口金額和節目時長都在增加,但是所占比例則在下降。而在東南亞地區,韓國電視節目出口金額和節目時長都在不斷增加,雖然出口金額的比例保持在10%左右,但是節目總時長則在不斷增加。2011年,雖然韓國電視節目對日本的出口金額占60.4%,但節目時長只占27.3%;出口到東南亞的電視節目金額雖然只占9.9%,節目總時長卻占30.4%。這其中有出口到日本的電視節目價格較高的因素,但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韓國電視劇在東南亞地區的“出鏡率”要遠遠高于東北亞地區。
韓國流行文化的影響力不僅表現在經濟收益方面,在外交方面也發揮積極的作用,成為文化外交的重要手段。韓國政府充分利用韓國明星在越南的社會影響力,助力外交活動。2001年,越南國家主席陳德良訪問韓國時,金大中總統邀請韓國演員張東健和女演員金南珠參加晚宴。韓國明星的人氣也促成了韓國政府和其他東南亞國家之間更緊密的關系。2001年,韓國偶像團體U-KISS赴新加坡參加一個為慶祝兩國建交而舉辦的青少年音樂會。馬來西亞的很多民眾也在長期的韓國流行文化消費中,建立起了對韓國的良好印象。
從傳播的范圍看,韓國文化在東南亞半島地區主要在越南和泰國具有較大影響,在海島地區的影響則主要集中在菲律賓和印尼。1992年,韓國與越南建立外交關系,韓國電視劇作為兩國文化外交的手段,20世紀90年代中葉開始進入越南的電視臺。隨著越南民眾對韓國電視劇喜愛程度的提高,韓國電視劇由政府輸出轉變成商業輸出。如果說韓國政府通過外交手段打破了韓國流行文化在越南傳播的壁壘,那么韓國商業公司則通過文化產品營銷為韓國流行文化的傳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愛上女主播》是韓國電視劇在泰國電視臺的首秀,但比較成功的電視劇是iTV在2002年播出的《藍色生死戀》,這部韓劇擊敗了美國和中國電視劇,成為當年泰國收視率最高的外國電視劇。《情定大飯店》、《冬日戀歌》等電視劇都取得了較高的收視率,從而吸引更多的泰國電視頻道購買韓國電視劇的版權。2005年的《大長今》更是吸引了社會上不同年齡和背景的觀眾,成為民眾日常交流的主題。2002年,電影《我的野蠻女友》在泰國取得巨大成功,隨后相繼有一些韓國電影進入泰國市場,同時也有一部分韓國電影,如《無血無淚》、《人民公敵》等,以DVD的形式進入泰國市場。伴隨著電視劇的熱播,韓國的音樂組合也在泰國逐漸受到觀眾的歡迎。而在老撾,民眾喜歡韓國電視劇的原因在于韓劇運用現代的風格描繪寧靜、浪漫的都市生活,提供了他們向往的生活。
雖然進入印尼的時間較早,但是韓國流行文化在印尼的影響力沒有在泰國的那么大。由于印尼民眾對文化產品的購買力相對較弱,韓國流行文化在印尼市場一直沒有得到穩定和系統的發展。韓國流行文化對印尼的影響集中在電視劇方面,韓國的偶像明星也曾在印尼舉辦演出活動,但演出活動的影響力主要取決于電視劇的影響力。韓國電視劇《浪漫滿屋》、《大長今》和《我的名字是金三順》在菲律賓播出時收視率都超過40%,成為菲律賓前五位最流行的電視劇。菲律賓的電視臺開始模仿韓國電視劇的內容和制作模式,投資攝制本地化的電視劇。ABS-CBN電視臺就曾在2012年模仿韓劇拍攝了青春偶像劇《公主和我》。韓國電視劇進入馬來西亞,是通過馬來西亞華人與中國大陸、臺灣和香港的貿易活動傳播到吉隆坡(華人約占總人口40%)地區,然后再在馬來西亞的華人社會中傳播,進而傳播到馬來人和印度人群體中〗。
從產品類型的角度看,韓國文化進入東南亞地區,首先從電視劇開始,然后是電影和流行音樂,進而是電子娛樂產品和生活方式的傳播。
韓國流行音樂(K-pop)是韓國文化的代表形式之一。K-pop在東南亞開始流行的時候,互聯網技術已經得到充分發展,視頻網站YouTube和社交網站Facebook對其傳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如果說電視劇是“第一代”韓國流行文化的核心,那么,2010年以后,流行音樂就成為“第二代”韓國流行文化的核心。樸載相《江南Style》的MV最初是為了本國觀眾制作的,但通過YouTube在歐洲受到熱捧,并通過美國歌星T-Pain的個人社交網站擴大了傳播范圍,隨后才逐漸在亞洲地區流傳開來。韓國JYP娛樂公司選擇泰國歌手尼坤(泰、美雙重國籍)作為2PM樂隊的成員,獲得很多泰國聽眾的支持,也拉近了韓國音樂與泰國聽眾之間的距離。韓國有500余家網絡游戲企業,每年開發的網絡游戲產品達到300款,由于國內市場的飽和,眾多企業開始考慮向其他國家拓展。韓國網絡游戲在東南亞地區占有重要地位,例如2009年,韓國游戲在泰國、菲律賓和越南的玩家人數占總數的80%。印尼的網絡游戲產品主要來自韓國、中國、臺灣及歐洲,其中韓國游戲產品市場占有率為40%,玩家占比為80%。韓國生活方式和生活用品,如飲食、化妝品等,在東南亞地區也很受歡迎。20世紀之前,東南亞人很少知道韓國的美容產品,大多數青少年購買的化妝品來自日本或歐洲國家,而現在,東南亞的青少年經常使用韓國化妝品。同時,到韓國旅游的東南亞游客數量逐年上升。例如2011年,有12.5萬印尼游客到韓國旅游,比2010年增長了15%。韓國旅游局將拍攝電視劇的場地建成主題公園,吸引大量的東南亞游客在拍攝場景中體驗韓國文化。
三韓國流行文化在東南亞的傳播方式
韓國流行文化是亞洲對全球化做出的反應,也是全球化在韓國的本地化過程。韓國流行文化從制作到傳播,始終堅持兩個方面的結合:在內容上,堅持全球化與本土化相結合;在傳播途徑上,堅持數字化傳播與移民傳播相結合。
在內容方面,盡管有的文藝評論家批評韓國電影從美國和日本借鑒了過多的商業因素,但總體而言,韓國的文化產品根植于傳統的東方文化,特別是其中的情感因素、家庭關系和儒家思想,吸引了很多東南亞受眾。不過,雖然韓國文化體現的是東方文化,深入觀察還是可以發現,韓國流行文化是用一種東方的表達方式,呈現全球化的主題,主要表現在:
第一,用集體主義的主題闡釋個人主義行為。眾多韓國電視劇雖然很強調家庭或集體的觀念,但是表現的主人公都以個人奮斗為主線,甚至是強調個人對于家庭或集體的反抗。韓國的音樂組合雖然人數眾多,但組合存在的時間一般很短,歌手短暫參與組合后,很快就獨立發展。
第二,用東方的面孔傳達西方的生活方式。都市化的生活、明顯的同質化的特點,這些是西方文化傳播到東方世界之后受到的批評,韓國流行文化恰恰就具有這些西方文化的特點。不過,韓國流行文化很巧妙地換上了東方的面孔,并且在文化產品中表現出對西方生活方式的充分享受,從而很好地規避了西方文化面臨的阻礙,滿足東南亞民眾對于理想生活的想象。
第三,用年輕人的視角看待社會問題。雖然韓劇中也有家庭倫理劇,并且諸多文化形態都非常積極地表現對于長者的尊重,但是,韓國流行文化產品的主角一般都是年輕人,基本上都是站在年輕人的角度觀察社會問題和人際關系。
在傳播途徑方面,韓國電視劇和電影都需要通過機構傳播,而音樂則是通過互聯網進行傳播。2009年,Rain在雅加達演出時,很多印尼歌迷就通過互聯網欣賞他的表演。2010年Wonder Girl的音樂會也延用了這種成功模式現在可以經常看到新加坡的女孩在地鐵上用手機看韓國流行樂隊的照片,也可以看到泰國的大學生在三星的手機或平板上看韓國的電視劇。數字技術的發展使韓國流行文化的傳播途徑得到極大的擴展。除了技術手段,韓國人大量移民東南亞地區,也是促使韓國流行文化在東南亞廣泛傳播的原因。20世紀90年代,大量的韓國移民進入東南亞地區。這些新移民與早期由于戰爭和政治原因而移民的人不同,其移民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東南亞地區的經濟發展機會。在韓國新移民中,很多移民就從事與韓國流行文化傳播有關的工作。2013年,東南亞地區有韓國移民273,088人,約占韓國海外移民的3.90%。雖然數量并不是特別多,但是東南亞已經成為繼中國、美國、日本和加拿大之后韓國移民最多的地區。此外,韓國也是東南亞地區主要的旅游客源地。2008年,前往菲律賓旅游的韓國人數超過前往美國旅游的人數,韓國成為菲律賓最大的旅游客源地。菲律賓和馬來西亞都有很好的英語學習環境,生活成本較低,從而吸引了很多韓國留學生到這兩個國家學習。還有很多韓國的退休老人將菲律賓和馬來西亞作為養老的居住地。東南亞地區的“韓國城”(Korean Town)也應運而生。2009年,韓國政府開始在東南亞地區設立“韓國文化中心”(Korean Culture Center),如越南河內(2006年,早于韓國政府2009年出臺設立“韓國文化中心”的政策)、印尼雅加達(2011年)、菲律賓馬尼拉(2011年)和泰國曼谷(2013年)。
四東南亞接受韓國流行文化的原因
20世紀90年代,隨著東南亞地區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在工業產品主要依靠發達國家的情況下,文化產品成為“反帝”和“反殖”的主要標簽。在本地文化產品無法與西方文化產品競爭的環境中,本地化的東方文化產品成為替代性的選擇,最初是香港的娛樂產品,隨后是韓國的娛樂產品。東南亞地區對于周邊經濟比較發達國家的文化比較感興趣,同時,也更喜歡輕松、雷同、簡單、節奏慢和冗長的娛樂節目。東南亞民眾的這兩種偏好,正好符合韓國文化產品的突出特點,因此,可以說,韓國文化產品進入東南亞地區,正好迎合了東南亞宏觀社會環境和微觀受眾群體的需要。
雖然都是表現全球化的主題,但東南亞觀眾從韓國的電視劇中找到了更多的文化相似性,更偏好韓國的文化產品,而不是西方的文化產品。韓國藝人與東南亞人類似的長相和文化根基,給越南女性觀眾造成了“光鮮亮麗”的生活錯覺,成為大量越南女性嫁給韓國人的原因之一。萬隆一所大學的學生瑪麗莎(Marisa)說:“我很喜歡東亞,尤其是來自韓國的電視劇,因為我感覺故事是如此的真實,他們談論愛情、家庭問題和友誼。我真的很喜歡這一點。此外,韓國的演員都是那么好看!我喜歡韓國演員裴勇俊。我希望有一天可以嫁給一個看起來像裴勇俊的韓國男人。”與西方的電視劇不同,韓國的電視劇避開有爭議的問題,如同性戀、吸毒和賣淫,以明顯的男性和女性(既年輕又單身)之間純潔永恒的愛情、三角戀、利他主義、親情、友情、人間的溫情、人性的弱點、寬恕與和解、善良戰勝邪惡等主題作為核心思想。另一方面,東南亞觀眾也把韓國影視作品中長者保護女主角,幫助其完成生活的目標,理解成東南亞傳統社會中的“庇護”(patron-client)關系。“韓國電視連續劇和我們的關系更密切,美國的電視劇,如《比佛利山莊》或《欲望都市》很有意思,但他們太不現實。”
審查制度的放松也減少了韓國流行文化產品進入東南亞國家的阻礙。新加坡1981年成立了審查制度檢討委員會(Censorship Review Committee),檢討審查政策和法律,以適應不斷變化的時代。1998年,印尼的審查制度出現了明顯的松動,原來在電影中會被刪除的政治內容開始可以出現在屏幕上。2001年的印尼電影《愛情怎么了》(Ada apa dengan Cinta)中就有印尼大學教授因撰寫批評社會腐敗的論文而被解聘的情節,而這樣的情節在以往的審查中都是會被刪除的。另外,關于年輕人的愛情故事或者關于青春期主題的電影,也都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逐漸流行開來。這種變化直接為韓國偶像劇和青春愛情電影提供了便利。
同時,技術的進步更減少了韓國流行文化傳播的壁壘,加快了韓國流行文化傳播的速度。隨著互聯網的普及,東南亞地區的觀眾通過互聯網和DVD在家里觀看影視產品的比例和人數迅速增加。通過三星、LG等通信產品,韓國流行文化進入了原來很難進入的市場。韓國在數字技術產業方面的成功,從另一個角度促進了韓國流行文化的傳播。通過互聯網和數字技術、數字點播技術(VOD),觀眾比傳統的電視觀眾更活躍。而這些在互聯網上活躍的觀眾還能通過社交網絡帶動另外的觀眾加入,成為新的受眾群體。這也是韓國流行文化中,電視劇比電影更加流行的原因之一。
2005年,韓國的國際婚姻數量是4.24萬對,創紀錄地達到登記婚姻人數的13.5%。此后,韓國國際婚姻的數量和比例都逐年下降,2014年國際婚姻有2.33萬對,占登記婚姻人數的7.6%。從2004至2014年,韓國國際婚姻人數有36.5萬對,達到登記婚姻人數的10.2%。超過80%的外國新娘來自中國、越南、菲律賓、柬埔寨、泰國和蒙古國。2009年,在韓國的外國新娘中,34.1%來自中國,21.8%來自越南。2011年,來自越南的外國新娘(7,636人)超過了來自中國的外國新娘(7,549)。雖然促使東南亞婦女遠嫁國外的原因很多,嫁到韓國的外國新娘的婚姻狀況也并不是非常美滿,出現了離婚率較高、文化適應、語言障礙、家庭暴力等問題,但是這些嫁到韓國的東南亞新娘,在客觀上是文化傳播的接受者,同時也是文化傳播的參與者,她們對家鄉的其他婦女具有示范和引領的效應,從而吸引更多的東南亞婦女與韓國人結婚。
結語
電視劇、電影和流行音樂是拉動韓國流行文化傳播的三駕馬車,數字化技術、互聯網技術和雙向移民活動是韓國流行文化在東南亞傳播的主要途徑。“全球化的思維,本地化的行動”是韓國流行文化在東南亞傳播的內在理念,從而實現了韓國流行文化與東南亞文化之間的緊密結合。通過傳播內容、傳播模式和傳播途徑的一系列舉措,形成了韓國流行文化在東南亞廣泛傳播的局面。韓國流行文化選擇了新技術、新媒體作為傳播手段,以年輕人作為主要的傳播對象,因此,在傳播過程中呈現間歇性廣泛傳播的特點,即在相隔一段時間之后出現一個流傳范圍很廣的文化產品(如電視劇《大長今》、歌曲《Nobody》、《江南Style》等),這些文化產品成為韓國流行文化顯著的標簽和標志性的符號,帶動了韓國流行文化的整體傳播。
除了傳播速度快的特點外,韓國流行文化還有強烈的同質化的特點。從傳播的內容上看,主要是表現愛情故事和現代生活主題的流行文化;從接受者的角度看,受眾人群主要是20-30歲的年輕人。有年輕人追逐、跟隨,那就是時尚和潮流;沒有人跟隨,這些時尚和潮流就消失了。年輕受眾的好奇心一般很難持久,東南亞地區又善于接受各種外來文化,因此,一旦東南亞民眾對同質化的韓國流行文化產品失去興趣,韓國流行文化的對外整體形象就會出現危機。韓國政府充分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已經開始對韓國流行文化的對外傳播進行更新,不僅出口文化產品到東南亞地區,而且參與東南亞文化產業的運作,利用韓國制作文化產品的經驗與東南亞進行合作,將韓國流行文化的影響從臺前滲透到幕后。
對比中國文化和韓國文化在東南亞的影響,可以看出,歷史上,中國文化曾經對東南亞產生影響,并且這種影響并非集中在哲學、宗教方面,而是在日常生活方面(具體表現為中式的飲食、音樂、戲劇等,其實在中國最典型的是教育,但教育在東南亞的受重視程度不如東北亞地區),表面上看似乎隨處可見,但其實并不持久,而且需要不斷地注入新的內容。韓國文化在東南亞傳播過程中選擇了流行文化作為主要的傳播內容,從優勢的角度而言,傳播的速度很快;但從劣勢的角度而言,傳播的持久度和深入程度難以維系,需要更加堅實的社會支撐。韓國文化在東南亞流行一段時間之后,就需要通過移民、通婚和韓國商品,為文化傳播構筑社會基礎,將對文化的傳播轉變成對社會的影響,將對精神世界(或“想象世界”,Image World)的影響轉變成對現實世界(Real World)的影響。
由于東南亞地區在文化發展過程中善于吸收各種外來文化,所以一直以來都不缺乏文化傳播的土壤。從全球化的角度而言,韓國流行文化在東南亞的傳播,主要是以文化商品的傳播結合大量的移民,逐漸確立其在東南亞的影響力。而中國也可利用中國文化在東南亞的歷史基礎,借鑒韓國流行文化的傳播方式和表現形式,在新的歷史時期繼續保持中國文化的影響。
【注釋】
[1]Andrea Matles Savada & William Shaw eds.,SouthKorea:ACountryStudy,Washington,D.C.: Federal Research Division,Library of Congress,1992,p.138.
[2]Jang,Gunjoo & Paik,Won K.,“Korean Wave as Tool for Korea’s New Cultural Diplomacy”,AdvancesinAppliedSociology,Vol.2,No.3, 2012,pp.196-202.
[3]Kim,Yeojin,“A possibility of the Korean wave renaissance construction through K-pop: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Korean wave as a cultural development”,Hastingscommunicationsandentertainmentlawjournal,Vol.36,No.1,2014,p.63.
[4]向勇、權基永:《國政方向與政策制定:韓國文化產業政策史研究》,《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8期。
[5]Noppadol Saleepoch,TheEffectofKoreanWaveonTradebetweenThailandandSouthKorea,MA Thesis,Chulalongkorn University,2009,pp.67-68.
[6]Hong Tien Vu & Tien-Tsung Lee,“Soap Operas as a Matchmaker: A Cultivation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South Korean TV Dramas on Vietnamese Women’s Marital Intentions”,Journalism&MassCommunicationQuarterly,Vol.90,No.2,2013,p.309.
[7]Shim,Doobo,“Hybridity and the rise of Korean popular culture in Asia”,MediaCultureSociety,Vol.28,No.1,2006,p.30.
[8]Shim,Doobo,“Korean Wave in Southeast Asia”,KyotoReviewofSoutheastAsia,Issue 11,March 2011.
[9]Chung,Peichi,“Co-Creating Korean Wave in Southeast Asia: Digital Convergence and Asia’s Media Regionalization”,JournalofCreativeCommunications,Vol.8,No.2-3,2013,p.201.
[10] Cho,Chul ho,“Korean Wave in Malaysia and Changes of the Korea-Malaysia relations”,MalaysianJournalofMediaStudies,Vol.12,No.1,2010,pp.1-14.
[11] Suh Chung-Sok,Cho Young-Dal & Kwon Seung-Ho,“The Korean Wave in Southeast Asia: An Analysis of Cultural Proximity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Korean Cultural Products”,KARECDiscussionPaper,Vol.7,No.2,2006,pp.5-6.
[12] Korea Herald ed.,Koreanwave,Jimoondang,2008,p.48.
[13] Damrong Thandee,“Second Korean Waves in Thailand”,KoreaTimes,November 21,2005.
[14] Noppadol Saleepoch,op. cit.,p.68.
[15] Lee Yohan & Vilayphone Somsamone,“The Korean Wave and Lao People’s Perception of Korea”,TheReviewofKoreanStudies,Vol.4,No.1,March 2011,pp.117-119.
[16] Syamsuddin,Mukhtasar,“Hallyu and Indonesia (Hallyu Status in Indonesia and Its Impact)”,Paper presented in the Seminar on Cultural Cooperation & Korean Wave (Hallyu),Hotel Borobudur Jakarta,Friday,December14,2012.
[17] Chung,Peichi,op.cit.,p.201.
[18] Suh,Chung-Sok,op.cit.,pp.5-6.
[19] Noppadol Saleepoch,op.cit.,pp.72-73.
[20] Jin,Dal Yong,Korea’sonlinegamingempire,London: MIT Press,2010,p.38.
[21] Asina Pornwasin,“Korean firm takes 23 percent stake in Ini3 Digital”,TheNation,March 5,2014,http://www.nationmultimedia.com/business/Korean-firm-takes-23percent-stake-in-Ini3-Digital-30228344.html
[22] Anonymous,“Korean wave helps draw more tourists from Indonesia”,TheJakartaPost,March 24,2012,http://www.thejakartapost.com/news/2012/03/24/korean-wave-helps-draw-more-tourists-indonesia.html
[23] Noppadol Saleepoch,op.cit.,p.75.
[24] Syamsuddin,Mukhtasar, op.cit..
[25] Jung,Sun,“K-pop,Indonesian fandom,and social media”,TransformativeWorksandCultures,Vol.8,2011.
[26] 筆者根據韓國政府網站提供的數據(轉引自維基百科中關于韓國離散人群的內容,https://en. wikipedia.org/wiki/Korean_diaspora)統計菲律賓、越南、印尼、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柬埔寨的韓國移民人數所得。
[27] “Koreans Flock to the Philippines to Learn English”,KoreaTimes,2009-09-13,http://www.koreatimes.co.kr/www/news/nation/2009/09/117_51729.html;Gutierrez,Jason,“Top education for less in the Philippines”,Philippine Inquirer/Agence France-Presse,http://globalnation.inquirer. net/2975/top-education-for-less-in-the-philippines-2,2015-11-29.
[28] Garcia,Cathy Rose A.,“More Koreans Look to Retire in Philippines”,TheKoreaTimes,2006-07-03, http://web.archive.org/web/20070224181342/http:/times. hankooki.com/lpage/special/200607/kt2006070314293511440.htm, 2015-11-29;Cho,Chul ho,“Korean Wave in Malaysia and Changes of the Korea-Malaysia relations”,MalaysianJournalofMediaStudies,Vol.12,No.1,2010,p.2.
[29] Choi,Jinhee,TheSouthKoreanFilmRenaissance:LocalHitmakersGlobalProvocateurs,Middletow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2010,p.35.
[30] Hong Tien Vu & Tien-Tsung Lee,“Soap Operas as a Matchmaker: A Cultivation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South Korean TV Dramas on Vietnamese Women’s Marital Intentions”,Journalism&MassCommunicationQuarterly,Vol.90,No.2,2013,p.322.
[31] Setijadi,Charlotte,“Questioning Proximity: East Asian TV Dramas in Indonesia”,MediaAsia,Vol.32,Issue 4,2005,p.197.
[32] Hyun-key Kim Hogarth,“The Korean Wave: An Asian Reaction to Western-Dominated Globalization”,PerspectivesonGlobalDevelopmentandTechnology,No.12,2013,pp.136-137.
[33] Setijadi,Charlotte,“Questioning Proximity: East Asian TV Dramas in Indonesia”,MediaAsia,Vol.32,No.4,2005,p.198.
[34] Jan Uhde & Yvonne Ng Uhde,“Singapore: Development,Challenges,and Projections”,Anne Tereska Ciecko,ed.,ContemporaryAsianCinema,New York: Berg,2006,p.80.
[35] Krishna Sen,“Indonesia: Screen a Nation in the Post-New Order”,in Anne Tereska Ciecko ed.,ContemporaryAsianCinema,New York: Berg,2006,p.103.
[36] Anne Tereska Ciecko,“Theorizing Asian Cinema”,in Anne Tereska Ciecko ed.,ContemporaryAsianCinema,New York: Berg,2006,p.28.
[37] 韓國國家統計局網站,http://kostat.go.kr/portal/english/news/1/1/index.board?bmode=read&bSeq=&aSeq=335937&pageNo=1&rowNum=10&navCount=10&currPg=&sTarget=title&sTxt=marri, November 29, 2015.
[38] Andrei Lankov,“International marriages”,http://www.koreatimes.co.kr/www/news/opinon/2012/10/165_90454.html, 2015-11-29.
[39] Nho,Choong Rai, etc.,“Trends of studies on Southeast Asian women married to Korean men”,Unpublishe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East Asian Social Policy 5th Conference: Welfare Reform in East Asia,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Taipei,November 3-4,2008.
【責任編輯:吳宏娟】
Keywords:Korean; Korean Wave; Southeast Asia; Spread;Localization; Culture Communication
[中圖分類號]G131.26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6099(2015)06-008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