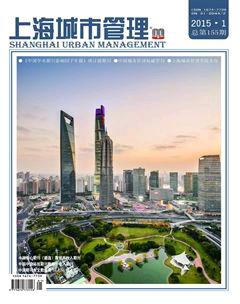城市化進程中土地流轉(zhuǎn)與公平高效的策略選擇
賀雪峰
導讀:最近一個時期的中央農(nóng)村政策極為強調(diào)培育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工商資本、種糧大戶、家庭農(nóng)場和農(nóng)民合作社,都被作為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而受到政策扶持。培育職業(yè)農(nóng)民,鼓勵懂技術有資本的年輕人返鄉(xiāng)從事農(nóng)業(yè),也在政策扶持之列。農(nóng)村人口城市化必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并且進城的大部分農(nóng)民工都可能在年老時返鄉(xiāng),因為他們很難在城市獲得體面安居的就業(yè)與收入條件。
一、職業(yè)農(nóng)民與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
誰來種糧的問題引起社會高度關注,這是有道理的,因為農(nóng)村中青年人大量進城,留在農(nóng)村從事農(nóng)業(yè)的大多為中老年人,中國農(nóng)業(yè)越來越成為老人農(nóng)業(yè)的態(tài)勢。靠老人種田來養(yǎng)活13億中國人,本能上就覺得不可靠,就會有憂慮。
正是基于這種憂慮,最近一個時期的中央農(nóng)村政策極為強調(diào)培育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工商資本、種糧大戶、家庭農(nóng)場和農(nóng)民合作社,都被作為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而受到政策扶持。培育職業(yè)農(nóng)民,鼓勵懂技術有資本的年輕人返鄉(xiāng)從事農(nóng)業(yè),也在政策扶持之列。相對地,當前主要耕種自家承包地的大約2億多戶農(nóng)戶受到冷落,甚至已被一些地方政府列入抓緊時間消滅的對象。地方政府通過政策和財政支持推動農(nóng)民耕地向大戶集中,以形成農(nóng)業(yè)規(guī)模經(jīng)營。因為政府推動正規(guī)的土地流轉(zhuǎn),且政府給經(jīng)營面積達到一定規(guī)模(比如100畝)的大戶以財政補貼,而提高了農(nóng)地流轉(zhuǎn)的租金。之前通過自發(fā)流入耕地形成了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的農(nóng)戶現(xiàn)在不得不退出之前流入土地,因為僅僅種自家承包地,就無法獲得維持基本體面生活的收入,就不得不離開村莊,進城務工經(jīng)商。
地方政府支持分散小農(nóng)將土地流轉(zhuǎn)給大戶還有更多原因,其中一個原因是,過去向分散的、剩余很少的農(nóng)民收錢很難,現(xiàn)在給農(nóng)民分錢也很難。要求農(nóng)民種雙季稻以提高復種指數(shù),多打糧食,農(nóng)民卻沒有積極性,即使給農(nóng)民補貼也不起作用。何況,針對分散小農(nóng),根本就沒有辦法統(tǒng)計播種面積以據(jù)實補貼,而只可能按畝補貼,從而無法發(fā)揮農(nóng)業(yè)補貼調(diào)動農(nóng)民種糧積極性的作用。并且,農(nóng)民不僅經(jīng)營面積狹小,而且地塊分散,抗旱、排澇、機耕、植保都很困難,政府也很難為他們提供有效的服務,因此不如將農(nóng)民分散的土地流轉(zhuǎn)集中到大戶手中,政府為有一定規(guī)模的大戶提供支持就有了針對性和可能性,也可以提高支農(nóng)資金的使用效率。一旦地方政府將主要資源用于為大戶提供服務時,這樣一個針對大戶再造出來的服務體系就會替代過去雖然脆弱但終究還有的為分散小農(nóng)服務的體系,其結果是,分散小農(nóng)發(fā)現(xiàn),他們越來越難以經(jīng)營自家一畝三分地了,他們只能將土地流轉(zhuǎn)出去,否則別無出路。
現(xiàn)在的問題是,在國家政策和財政支持下,中國農(nóng)地都流轉(zhuǎn)給了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中國大約20億畝耕地最多也就能容納2000萬個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按一個家庭農(nóng)場平均100畝來計算),那么,當前農(nóng)村2億農(nóng)戶離開土地后能到哪里去?怎么辦呢?
二、自給自足與農(nóng)村人口城市化
中國現(xiàn)在有2億多農(nóng)戶、6億多農(nóng)村人口,另外還有大約2億進城務工的農(nóng)民工,這些農(nóng)民工與農(nóng)村和農(nóng)業(yè)還有千絲萬縷聯(lián)系,父母仍然種田,他們或年老、或進城失敗仍要返鄉(xiāng)。
目前中國農(nóng)業(yè)GDP占全部GDP的比重只有9%多一點,其中牧業(yè)和養(yǎng)殖業(yè)已大部分被工商資本所占有,留給9億農(nóng)民的主要是大宗農(nóng)產(chǎn)品的種植業(yè)和經(jīng)濟作物的種植。其中最重要的是占全部耕地70%的用于種糧的土地大都仍然由農(nóng)戶耕種,這個糧食GDP雖然占比不高,對千家萬戶農(nóng)戶卻十分重要,因為當前全國農(nóng)民家庭中,一半以上收入仍然來自農(nóng)業(yè)。不僅如此,正是農(nóng)戶經(jīng)營自家“人均一畝三分、戶均不足十畝”的承包地,而獲得了農(nóng)村自給自足經(jīng)濟的可能性,他們住房不要錢,吃菜不要錢,吃蛋吃魚也可以不要錢。他們還可以借此經(jīng)營副業(yè),撈魚摸蝦,養(yǎng)雞養(yǎng)鴨,從而獲得收入。拜托小規(guī)模農(nóng)業(yè),主要是種糧,農(nóng)民家庭中進城無優(yōu)勢的中老年人通過從土里刨食,而展開了一個豐富的自給自足經(jīng)濟,算收入也許不高,算生活質(zhì)量、算生活指數(shù)評價卻不低。
相對當前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技術條件,農(nóng)民勞均適宜耕種面積為30~50畝,一對夫妻耕種50畝土地是完全沒有問題的。當前農(nóng)業(yè)勞動力有2億多,加上年齡超過65歲但仍然從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勞動力,農(nóng)業(yè)勞動力少說也有3億。3億農(nóng)業(yè)勞動力耕種20億畝耕地,勞均只有不到七畝,可謂勞多地少,是無地可種而不是有地無人種啊!
農(nóng)村人口城市化必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并且進城的大部分農(nóng)民工都可能在年老時返鄉(xiāng),因為他們很難在城市獲得體面安居的就業(yè)與收入條件。在還有9億人口要依托農(nóng)業(yè)和農(nóng)村的情況下,政策推動農(nóng)民將土地流轉(zhuǎn)給大戶經(jīng)營,要搞規(guī)模農(nóng)業(yè),甚至要搞農(nóng)業(yè)現(xiàn)代化,實在不是時候。
當前仍在從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尤其從事大宗農(nóng)產(chǎn)品種植的主要有兩個群體。一是無進城就業(yè)優(yōu)勢的中老年人,他們從事農(nóng)業(yè)正好。這部分中老年人的年輕子女進城務工經(jīng)商,他們種自家的承包地。這樣就可以通過代際分工的同時獲得務農(nóng)與務工的兩筆收入。二是因為種種原因無法離開農(nóng)村的中青年人,如父母太老,這部分中青年人通過流入親朋鄰里承包地,可以達到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并獲得不低于外出務工的收入。這兩個群體種田的一個最重要特點是精耕細作,照顧莊稼就像照顧自家子女一樣,春種秋收,每天都要到田間巡視(農(nóng)民叫“巡田”),因此,這些人種田的畝產(chǎn)遠高于規(guī)模經(jīng)營。農(nóng)業(yè)部有人說中國十分之一的規(guī)模經(jīng)營生產(chǎn)了全國20%的糧食,這種說法有極大模糊性,因為他們是用中國產(chǎn)量最高的10%的種糧耕地產(chǎn)出來講生產(chǎn)了全國20%的糧食,但實際上,全國只有不到70%的耕地種糧,且凡是規(guī)模經(jīng)營耕地都是最高產(chǎn)的一等耕地,其產(chǎn)量本來就高,這樣的耕地或這10%的種糧耕地若由農(nóng)戶來種,其產(chǎn)糧一定可以超過目前全國糧食總產(chǎn)的20%。
農(nóng)民種糧可以高產(chǎn),同時可以獲得種糧收入。正是有了種糧這個主業(yè),農(nóng)民可以在農(nóng)閑時開展各種副業(yè),搞自給自足經(jīng)濟,利用農(nóng)閑在熟人社會中迎來送往,精心編織熟人社會的人情網(wǎng)絡,這個人情網(wǎng)絡不僅為農(nóng)民提供了社會資本,而且為他們提供了人生意義,即熟人社會中的身體安全和心理安全乃至最終落葉歸根的終極價值,都是極其重要的。
一旦失去耕地,失去農(nóng)業(yè),不再種糧食,所有建筑在農(nóng)民種田基礎上的經(jīng)濟社會的宗教意義就會全都失去基礎,農(nóng)民就不再可以在農(nóng)村呆得住,他們也就會失去故鄉(xiāng),但城市顯然還容納不下他們。因此,糧食只能主要仍然由2億多戶農(nóng)戶來種,而不能指望所謂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來種。
三、轉(zhuǎn)移資源與就地城市化
當前中國70%的耕地仍然種糧食,且絕大部分耕地仍然由小農(nóng)來種。糧食可以算是一種典型的標準化的大宗農(nóng)產(chǎn)品,種糧所需農(nóng)資也幾乎都是標準化的大宗商品,農(nóng)民可以輕易從市場上購得,而農(nóng)戶生產(chǎn)的糧食國家則以保護價收購,因此,對于種糧的農(nóng)民來講,基本上不存在與市場對接的問題。
農(nóng)民種糧,最大的困難是如何與大生產(chǎn)對接。當前中國農(nóng)村“人均一畝三分、戶均不過十畝”且分散的小規(guī)模細碎承包耕地,在生產(chǎn)環(huán)節(jié)存在諸多一家一戶“辦不好、不好辦、辦起來不合算”的事情。在取消農(nóng)業(yè)稅前,基層村社組織為了向農(nóng)民收取稅費,就必須回應農(nóng)民生產(chǎn)中遇到的各種困難,并積極為解決農(nóng)民的這些困難提供服務。收取的稅費中也有主要為農(nóng)戶提供公共服務的“共同生產(chǎn)費”一項。取消農(nóng)業(yè)稅后,國家不再向農(nóng)民收取稅費,也不再關切農(nóng)民在生產(chǎn)中所存在的各種困難,而只希望通過大量轉(zhuǎn)移資源來達到政策目標,其極端表現(xiàn)就是當前全國各地方政府正試圖通過財政支持所謂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來打敗小農(nóng)、淘汰小農(nóng)的實踐。這種做法當然是很值得爭議的。
當前中央農(nóng)村政策必須真正轉(zhuǎn)移到為2億多戶小農(nóng)尤其是糧農(nóng)服務的軌道上來,積極回應小農(nóng)的需要,解決他們在生產(chǎn)中面臨的困難,尤其是重視村社組織和自上而下為小農(nóng)提供社會化的服務體系的作用。從解決農(nóng)民問題和解決糧食問題的角度,必須扶持2億多戶小農(nóng)種糧,要讓小農(nóng)繼續(xù)成為中國種糧的主體,使得農(nóng)村人口城市化更多地體現(xiàn)為就地城市化。
責任編輯:張 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