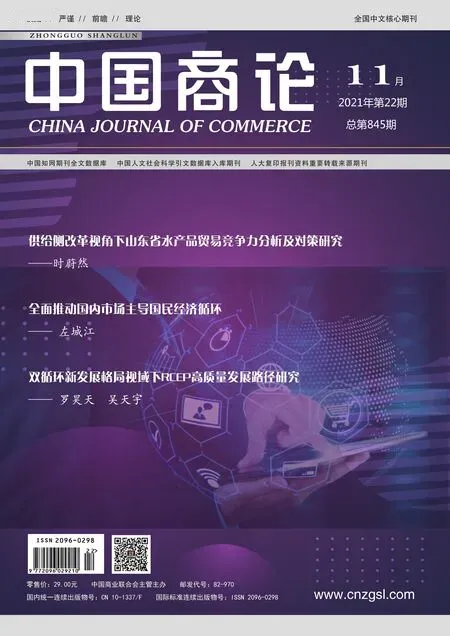國際經濟新形勢下我國金融市場發展研究
天津社會科學院現代企業研究所 趙云峰
隨著中國金融市場與世界金融市場一體化程度的加深,外部事件對中國金融市場的溢出效應也逐步增強。2007~2009年金融危機期間以及后危機時期發達經濟體的調整策略、經濟特征與發展軌跡的變化,形成了中國金融市場上同時期一系列金融改革與創新的外生動力。縱觀金融創新發展的進程,不難發現全方位、多層次的金融創新已經成為一種常態。而金融創新對金融穩定的影響是全面的,不僅有直接效應也有間接效應,這種復雜關系不僅體現在兩者之間的多重互動關系,還體現在普遍的時滯性和動態非線性關系。因此,運用復雜系統論的觀點,結合制度經濟學、金融學相關理論,對金融創新背景下的金融穩定內涵、穩定機制進行系統地研究,理清金融創新對金融穩定的直接、間接影響機理,具有較強的理論研究價值和意義。
1 國際經濟形式對我國金融環境的影響
2007~2009年金融危機發生后,發達國家的去杠桿化以及其他調整措施對我國經濟的溢出效應非常顯著。一方面,由于中國屬于外向型經濟體,發達經濟體的去杠桿化導致中國外部需求大幅減少,使中國轉而依賴內需拉動經濟;另一方面,由于去杠桿化導致國際資本市場上資金減少,同時賬戶盈余減少,導致人民幣承受著較大的貶值壓力。在此背景下,結合中國危機時期的相關政策與經濟環境,后危機時期中國金融市場上出現了包括影子銀行、利率市場化改革、互聯網金融在內的一系列金融改革與創新。
1.1 影子銀行體系
發達市場的影子銀行多表現為資產證券化等業務,而我國目前影子銀行本質上仍是信貸和類貸款業務,例如理財產品和信托產品等,杠桿率并不高,并且這些業務受到監管機構的嚴格監管,根據是否受監管和監管部門的不同,對我國廣義影子銀行體系包含的機構和業務進行分類。
與發達市場不同,中國影子銀行來源于對傳統金融體系的補強以及監管套利。為了應對2007~2009年金融危機的沖擊,中國政府實施了一系列信貸擴張與經濟刺激政策。新增的海量信貨資源絕大多數被配置在基礎設施與房地產投資中,在此過程中商業銀行成為信貨投放的主力。由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權、財權不匹配,并且地方政府不得自主發債,地方政府不得不建立投融資平臺公司來代其承擔籌措資金與基建投資的功能,債務的清償完全依賴土地財政的可持續性。然而,在全球金融機構去杠桿以及金融監管強化的趨勢下,中國銀行業監管機構開始限制銀行體系的信貨過度投放,采用更為嚴格的監管指標約束商業銀行的行為,例如大幅提高資本充足率要求。同時,土地財政的不可持續以及資產價格下跌讓監管機構開始對金融風險的形成產生警覺。然而。基礎設施投融資領域仍保持著旺盛的中長期后續資金需求。為了完成“出表”、規避存貸比指標,商業銀行采用理財產品以及與信托公司等非銀行金融機構合作,實現信貸“借道”投放,也就形成了“非標準化債權資產”。此類業務占據目前中國影子銀行規模相當大的比例。可見,影子銀行的產生有其必然性。
從供給角度來看,金融創新和監管套利是直接動機,國內高儲蓄率帶來的充裕流動性提供了資金來源;從需求的角度來看,傳統金融體系的信貸規模受到嚴格限制,無法滿足地方政府、房地產行業和中小企業旺盛的融資需求。當前我國金融體系存在的隱形擔保為影子銀行提供了保障,拓寬了投融資渠道,提高了融資效率,改善了市場定價機制扭曲,促進了實體經濟的發展。但是,從風險的角度來看,影子銀行導致大量資金投向資金周轉周期較長的基礎設施與產能過剩領域,容易在經濟結構調整過程中形成債務風險隱患,同時由于影子銀行具有信用創造功能,加大了宏觀調控的難度。
1.2 利率市場化改革與人民幣國際化
自1993年中國共產黨的十四大以來,中國利率市場化進程一直穩步推進,自2008年起開始提速,目前已全面放開貸款利率。利率市場化進程在金融危機后迅速加快,是多方面動因合力的結果。
首先,發達國家的去杠桿化與經濟疲軟導致中國長期依賴的出口需求銳減。為了重新尋找可持續的經濟增長點,中國試圖提高經濟內生增長動力。提高金融體系的資源配置效率,改革資源調配機制,是經濟轉型下的必然要求。其次,業已存在的影子銀行形成利率市場化改革的微觀基礎,金融創新是利率改革的“倒逼”動力。最后,當中國經濟經歷調整、增速結構性下滑時,發達經濟體開始緩慢復蘇,造成短期資本從新興經濟體流出。
中國的利率市場化會反映真實的資本回報率,可以對資本回流產生一定的疏解作用。利率市場化改革的過程同時也是從行政手段調節金融向幣場化轉變的過程,而人民幣國際化可促使改革進程加快,增加金融市場深度。人民幣國際化能促進中國經濟的三個轉型:第一,從出口導向型轉向內需型。人民幣國際化能夠有效降低外貿及倚靠外國原材料進口企業的成本,提高企業盈利水平,加強國內居民的有效購買力。并拓寬中國內需增長的外部供給。第二,從制造業為王轉向服務業。香港離岸市場的建立和國內資本市場的逐漸完善都會對中國金融服務業產生巨大的推進作用。第三,從依賴國外直接投資到中國企業“走出去”。人民幣國際化將推動更多的私人企業對海外投資,促進中國企業海外投資逐步向高附加值產業轉型。
1.3 自貿區金融
2013年8月22日,中國國務院正式批準設立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擬作為金融深化與經濟體制市場化改革和開放的橋頭堡。對于金融機構來說,自貿區以金融支持貿易與投資的便利化,成為中國金融市場與國際金融市場相銜接的接口。自貿區的建立背景包括三個方面:第一,受到發達國家經濟疲軟的影響,中國失去了消化產能的外部市場,嚴重挑戰了中國所依賴的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第二,以自貿區的示范效應推動中國經濟增長從政府主導向市場主導轉變。第三,從外部環境來看,中國面臨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壓力。美國正在推動泛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實現資本自由流動。中國以自貿區作為全面開放的實驗樣本,率先突破轉換政府職能、開放金融服務業,讓國內金融機構提前接受高標準的考驗。
1.4 互聯網金融與貨幣市場基金
互聯網金融的興起,對已有的金融資源形成重構,為金融行業帶來顯著的“鰓魚效應”,深刻地改變了金融服務的業態與發展軌跡。互聯網金融的出現讓金融服務的成本更低、交易更加便捷、更加普惠。以“大數據”為基礎的風險管理理念,減弱了借貸雙方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從而顯著降低交易與信貸成本。貨幣市場基金在互聯網金融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貨幣市場基金的發展一定程度上沖擊了銀行體系的穩定性,加劇銀行體系的流動性風險。由于貨幣市場基金的相對高利率,存款從銀行流向貨幣市場基金,抬高存貨比,銀行對存款的需求上升,又推高存款利率,形成負反饋。隨著貨幣市場基金的規模越來越大,T+0取現的功能使墊資的基金公司杠桿率變高,面臨的流動性風險加大。同時,貨幣市場基金還面臨著未來高利率無法維持時遭遇大規模贖回的擠兌風險。
2 中國金融發展的新局面
2014年IMF的全球金融穩定報告提出,全球市場正在“從流動性驅動向增長驅動轉變”。中國經濟正處于培養內生增長動力的關鍵時期,市場化改革引致的金融創新為經濟帶來活力與效率,但同時也孕育了新的風險,這些風險可劃分為系統性風險和期限錯配及流動性風險。中國目前面臨的系統性風險主要集中于銀行體系,影子銀行的信用鏈條最終也會傳導到傳統銀行體系。
首先,由于中國金融體系中間接融資比重過大,風險高度集中于銀行體系,經濟體的周期性波動與結構性調整在短期內都會對銀行資產質量造成巨大影響。房地產與地方投融資平臺是銀行體系面臨的最大風險暴露區域,土地財政的不可持續與房地產市場調整都會對銀行體系造成沖擊。
其次,影子銀行與傳統金融體系之間并未建立風險隔離機制,導致影子銀行風險可能傳導到傳統金融體系內部,從而引發系統性風險。
最后,銀行同業業務已成為金融部門系統性風險的重要聚集點。在影子銀行與監管機制的博弈過程中,理財產品、銀信合作、銀保合作等渠道逐步被監管機制所限制,商業銀行利用同業借貨業務,將信貨資產轉化為同業資產,借此減少風險資本計提。隨著同業業務規模大漲,這些資產中蘊含的高風險資產已成為系統性風險的潛在引爆點。期限錯配主要表現在短期資金配置到長期項目中,從而形成流動性風險。
近年來由于需求下滑、應收賬款增加,中國企業短期貸款、票據融資增長迅速。通過理財產品資產池的滾動發行,短期資金被大量配置到基礎設施與房地產等長期投資項目中。期限錯配顯著增加了微觀企業、影子銀行與正規金融體系的流動性風險與脆弱性。在此背景下,如果出現貨幣緊縮以及利率高企等沖擊,企業的資金鏈將非常脆弱,而期限錯配又相應放大了流動性風險對實體經濟與金融市場的沖擊。此外,互聯網金融。特別是貨幣市場基金的發展,增加了銀行體系的流動性風險。金融自由化改革的背景下金融創新的發展速度,大大超過金融機構的風險管理能力與金融體系的消化能力,并且領先于監管體制的應對速度,這是形成上述金融風險的主要原因。
2008年以來,中國宏觀經濟政策與監管政策對金融體系的影響催生以下風險。首先,經濟刺激政策導致融資平臺和公共部門杠桿率大幅上升,民營企業的融資渠道受到擠占。得到更多資源支持的公共部門參與經濟,其粗放式發展與低效率造成了嚴重的產能過剩。其次,刺激政策退出時,貨幣政策與監管政策大幅快速收緊,導致整個金融體系流動性緊缺,抬高了資本成本,直接催生了影子銀行體系與銀行表外業務創新。在信貨政策突然轉向時,去杠桿的著力點是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和房地產行業,而這些中長期項目對后續資金的依賴程度較高。由于后續現金流不足,在建項目不得不以“短貨長用”來維持,直接造成地方債務風險激增。
[1] 高曉紅,王靜.金融創新與貨幣政策:沖突與變革[J].上海金融,2002(7).
[2] 劉俊民,王國忠.虛擬經濟穩定性、系統風險與經濟安全[J].南開經濟研究,2004(6).
[3] 劉莉,唐小我.股票指數波動率的估計方法及其應用[J].電子科技大學學報,2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