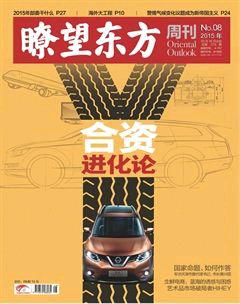APP如何收廢品
張靜
“收編”個體收廢品者,并非必須給他們身份和工資
將“身份證”——錄有用戶信息的二維碼貼上裝滿廢紙的塑料袋,用APP“收廢品”掃描,然后將塑料袋扔進定制的可回收垃圾桶。
藍色的回收桶入口處,“廢品換禮品”的字樣很醒目。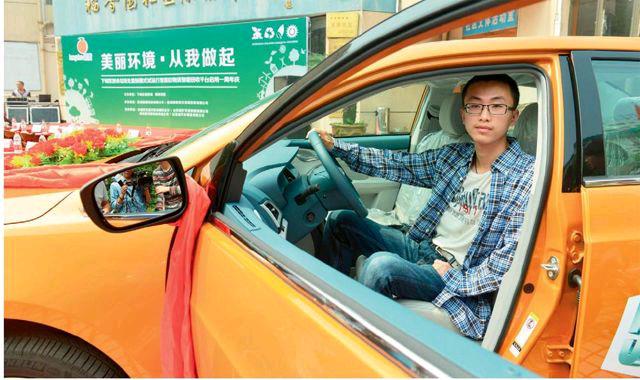
很快,“收廢品”的個人賬戶里就會增加相應積分,它們可以用來充話費、換洗衣液洗發水或直接提現。
這個基于手機APP的資源回收系統,來自還在讀大學時的朱方濤“躺在宿舍的床上靈機一動”的創意——他并不知道國外有個“再生銀行”,只是在學校里看到了利用移動互聯網收廢品方式推行的空間。
而這成為他現在的創業機會。
從校園轉戰社區
“最初我們的首要目標顧客是最前衛、環保意識最強的大學生群體。因為那時我們自己就是大學生,對大學生處理寢室垃圾的煩惱感同身受。垃圾多,寢室空間小,小量分類垃圾又投送無門。”朱方濤對《瞭望東方周刊》說。
但還沒走出校園的朱方濤就栽了第一個跟頭。
2014年6月,朱方濤的收廢品計劃剛開始試運行,學校后勤部門就設了一個很高的門檻:要承包學校的廢品回收,應繳納超過四萬元的承包費。
朱方濤只好與學校已有的收廢品者合作,收效甚微。
“學校里網絡很差,下載APP需要用手機流量,用戶就減少了很多。下載后APP的使用率也不高,學生的環保意識沒有想象的那么強。他們還是習慣有了垃圾就丟,沒有回收的概念。”朱方濤說,“我們又拿不出滴滴打車那么多的補貼,而且收廢品和打車不一樣,廢品的利益值不足以促使學生去做垃圾分類。”
朱方濤也曾嘗試進入中學,但中小學出于安全考慮,禁止一切校外人員進入。
于是他轉戰社區。而他們所在的杭州新城區,有完整的安保系統以及已經形成的收廢品個人承包模式,只能從還有“漏洞”可鉆的老小區入手。
從2014年2月到5月,朱方濤和他的四個小伙伴用了三個月時間調研,走過老城區七個街道的每條巷子。
他們在公園里給老人發名片,介紹“收廢品”APP的回收模式,了解老年人的需求。與當地收廢品者接觸,建立超過400人的檔案,包括家鄉、年齡、工作年限等,現在這份檔案的名錄已增加到三萬人。
收編“破爛王”
在公益組織活動中,一位農場主決定為“收廢品”投入資金,后來又有快遞業老板加入。他們還得到過政府創業資金和其他人的資金投入。這個“收廢品”的APP創業團隊,最年長的34歲,最小的朱方濤生于1992年。
朱方濤用籌集來的錢購置了第一批廢品回收“標配”設備,包括電腦、打印機、電子秤、價值1000多元的廢品回收箱20個,以及10萬個二維碼標簽。
難點是與現有的收廢品者談合作,既不能觸動他們的既有利益,還要把他們“收編”過來規范化管理。為此,朱方濤不止一次進了派出所。
某次,一位65歲的阿姨要把廢品賣給朱方濤。社區里干了很多年的收廢品者認為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侵害,拉著朱方濤要去物業理論,結果招來了警察。
解決的辦法是讓他們賺更多的錢。
和朱方濤合作后,這位收廢品者每天都能有10單生意“無縫連接”,剩余時間可以再做其他客戶的回收。
“原來他每天最多跑三個小區,現在可以跑五個小區,每個小區多收20%,每個月就能多賺三四千元。”朱方濤介紹。
“收廢品”每個月還會再給對方1000元左右的回收份額。這種方法效果顯著,從2014年6月推進第一個小區開始到現在,“收廢品”已經收編了30人,覆蓋了杭州老城區三個街道、七萬人口。“收廢品”還為這些人上了社保。
為了規范收廢品團隊,每輛回收車上都有價值300元的定位器,這不到一萬元的開支成了“收廢品”的第二筆大開銷。
即便是這樣,還會出現作假情況。明明收了10個瓶子卻拿回5個,差價只能由“收廢品”自己承擔。
廢品“通吃”的APP
“收廢品”受歡迎,因為回收箱對數量不挑三揀四,同時也全覆蓋了幾乎所有的廢品種類。
打開“收廢品”,每一個種類的廢品價目清晰可見:每市斤塑料0.8元,鐵制品1元,紙料0.4元,鋁材2元,小家電1元,布料0.2元,黃銅10元,完整衣服10元……
1個積分等于0.1元。2014年5月,朱方濤團隊與杭州文新街道合作,將新金都城市花園作為第一個居民小區試點,一個月回收廢品2.5噸。
不管回收箱是否裝滿,每星期朱方濤的團隊都會開著小面包車走兩三趟,將廢品帶走,然后分揀稱重,輸入積分。
30人的回收團隊,每人每天可以收1.5車廢品,每車能載700斤。
“廢品從用戶手中收到師傅那里,師傅賣給小轉運站,小轉運站再賣給大轉運站,最后賣給再生企業。”朱方濤說,杭州以往的玻璃廢品主要收啤酒瓶,而且只要西湖牌啤酒的酒瓶。
為了突破制約,朱方濤團隊與富陽市富倫造紙廠這個全國最大的牛奶盒回收企業達成合作協議,每市斤0.025元從用戶手中收到的牛奶盒,0.05元賣給造紙廠。
廢品價目隨著市場行情不斷變化,“收廢品”要實時跟蹤當地廢品價格,保證不能虧本。
2014年11月塑料瓶還是0.06元一個,12月就跌到了0.03元。鋁合金因為含有稀有金屬成分,漲了20%。
“收廢品”目前實踐最好的杭州,是全國較早推行垃圾分類的試點城市之一。
2010年3月,杭州啟動垃圾分類試點工作,將垃圾分為有害垃圾、可回收垃圾、廚房垃圾和其他垃圾,分別對應紅、藍、綠、黃四種顏色的垃圾桶。
目前,杭州市區垃圾分類的生活小區已占市區生活小區總數的98%,負責分類垃圾回收的“清潔直運”每天能夠回收“廚房垃圾”350噸,“其他垃圾”450噸,這些垃圾占杭州每日垃圾處理量的14%。
四年的試點,客觀上為“收廢品”的推廣打下了基礎。
雖然目前用手機下單自助投遞垃圾的用戶還沒完全覆蓋,但2014年12月仍是“收廢品”成果最好的月份——共收了472.5噸廢品。
社區服務打包模式
2014年杭州市的日均垃圾量已超過8000噸。照此速度增長,杭州最大的垃圾填埋場將在5年內達到極限。
早在2013年3月,杭州市下城區朝暉街道的7個社區就啟動了垃圾分類智能回收平臺,也是通過參與垃圾回收換取積分,兌換獎品。有市民拿到了所在街道的最高積分,獲得比亞迪汽車5年使用權。
除了回收廢舊物資,杭州也開始在社區推行餐廚垃圾集成化處理設備。居民只需將有機廚余垃圾裝入社區統一發放的垃圾袋中,投放到回收垃圾桶內即可。
設備將自動進行智能處理,每天可處理300公斤廚余垃圾,在20小時內轉變為有機肥料。
據試點社區的垃圾回收處估算,一旦所有社區配置廢舊物資回收平臺,則下城區每年至少可減少生活垃圾500噸。
與垃圾分類智能回收平臺相比,“收廢品”的規模和影響力似乎小了點,但積分兌換禮品的模式,已經被杭州市人大常委會采用。
根據目前正審議的《杭州市生活垃圾分類與減量條例(草案)》,杭州將逐步推行生活垃圾分類投放實名登記制度,對執行生活垃圾分類規定規范有效的居民,予以累積計分,所有積分可以兌換相關獎勵。
但朱方濤的雄心并不止于單純收廢品,“等我們收到更多廢品時,就做一個大型回收站,然后逐步做成初步的原料加工廠,自己做回收處理再生企業一條龍。”
2014年“收廢品”支出30萬元。除了投資方的資金,朱方濤團隊唯一賺錢的渠道,就是從每個收廢品者的每一單生意中分成1元。
30人每天能做10單,一個月“收廢品”因此能賺9.3萬元。
上海么柚網絡科技有限公司是給朱方濤做“收廢品”APP的方案解決公司,執行副總裁李楊在接受《瞭望東方周刊》采訪時分析了“收廢品”APP的前景:“APP要盈利,使用要高頻率,人群足夠多。‘收廢品的使用頻率不夠高,但是社會價值高,可以作為窗口推進社區增值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