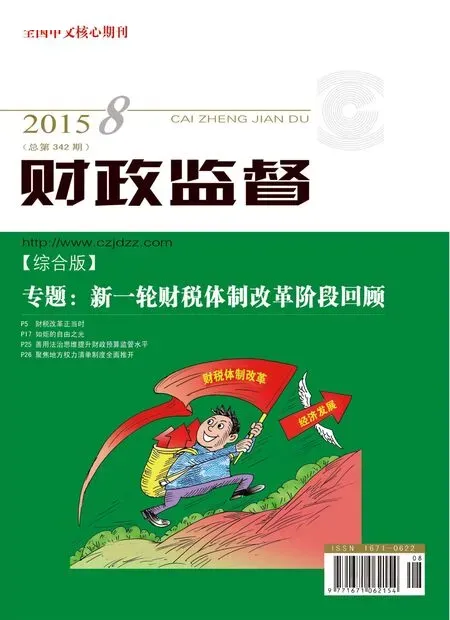尋找通往自由和幸福之路
●孫興全/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副教授
尋找通往自由和幸福之路
●孫興全/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副教授
1974年諾貝爾獎經濟學獎由兩個學術思想分歧極大的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馮·哈耶克和岡納·繆爾達爾共同分享。后者是瑞典福利國家的理論創始人之一和福利國家的政策和制度“設計師”,可謂理論界稱為“民主社會主義”或“第三條道路”的重要思想家,前者則是最徹底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各種社會主義思潮和現代福利國家最激烈的批評者,他稱福利國家、計劃經濟是“通往奴役之路”。為什么學術界能對如此“對立”的思想給以同樣的尊重?
我想,繆爾達爾的“社會主義思想”和福利制度的設計有成功之處,北歐、西歐的“民主社會主義”的巨大成就可以為證。哈耶克的思想同樣偉大,尋找通向自由的道路上,他對自由市場的堅守和對國家主義的批評和警示尤為可貴,這既有自由市場經濟給世界帶來的繁榮為證,也有計劃經濟在社會實踐中受到的重大挫折甚至釀成巨大災難為證。經濟系統及至整個社會的目標是什么?是以人為目標而不是視人為工具和手段,是實現人的自由和幸福而非一種標榜為高尚的社會目標,在這一共同追求之下,方法和道路是可以選擇的。也就是說,在通往自由和幸福之路上,“社會主義”因素多一點還是少一點,自由市場徹底一些還是政府干預多一些,這無疑可以且需要爭論。自由市場的力量和政府干預的力度如何組合歷來都是經濟學家爭論的焦點之一,也正是因為這樣的思想交鋒并影響一個個國家的制度和政策,才能避免社會前行路上的更多危險。從這一意義上講,出現兩個“共同點最少”的經濟學家分享諾貝爾經濟學獎并非不可理解。
回想比哈耶克和繆爾達爾獲獎早一個世紀馬克思、恩格斯發表的《共產黨宣言》中列舉的各種社會主義思潮,馬克思、恩格斯天才地發現了若干“反動的社會主義”,包括他們稱之為“德國的或‘真正的’的社會主義”這一種。這種宣稱德意志民族“最為優秀”并詛咒自由主義及其社會實踐的所謂“社會主義”,后來發展成給德國和全世界帶來巨大災難的“國家社會主義”(法西斯)。對打著社會主義旗號帶著人民“通往奴役之路”的警示并非自哈耶克始,一個世紀前,馬克思、恩格斯就天才地預見到“通往奴役之路”,并向世人作出了警示。可惜的是,德國等國家卻未能避免。
同樣是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筆下留情,沒有將由知識精英和人道主義者這樣的思想家們提出的“社會主義”主張劃歸“反動”之列,我想這并非沒有原因。馬克思、恩格斯將這類思想家的“社會主義”主張稱為“保守的或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盡管馬克思、恩格斯厭惡他們反對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實現社會變革的觀點,但他們試圖通過社會改良提高工人福利,節省統治費用和財政開支,甚至要給囚犯提供單身牢房,不同樣是對人類通往幸福和自由之路的探索嗎?這種社會主義的未來就是今天的“民主社會主義”,馬克思、恩格斯不一定預見到它在北歐、西歐諸國給人民帶來了高福利和高度自由,至少也沒有對這種探索全盤否定。作為瑞典福利國家的理論創始人之一和福利國家的政策和制度“設計師”的繆爾達爾在學術上努力的價值也不可否認。
哈耶克也認為具有人道主義色彩的絕大多數“社會主義者”都是自由主義的信徒,盡管如此,哈耶克還是堅持抨擊所有的“社會主義者”的主張包括福利國家制度。在他的著作中,他抨擊極權主義的暴政,更著力于厘清一些堅信自己不會走向國家社會主義并與國家社會主義劃清界限的“社會主義者”觀念中隱藏的“通向奴役之路”的危險。在他看來,一些國家干預和計劃經濟思想觀念看似有益無害,且“容易贏得多數”,同樣是“作惡者”,他提醒這些人,如果清楚他們的極權主義經濟政策的后果他們自己也會“不寒而栗而退避三舍”。哈耶克的價值之一在于嚴防哪怕是出于良好愿望而將人民當作棋子一樣擺布和計劃、規劃的 “致命的自負”,以所謂高尚的社會目標來抑制個人目標,限制人們的經濟自由和自由選擇。他反對國家對于經濟生活的干預,反對計劃經濟。哈耶克20余本著作中的最后一本著作的名稱就是《致命的自負》。他認為:“大凡認為一切有效的生活形式都產生于深思熟慮設計的人,大凡認為任何不是有意識設計的東西都無助于人的目的的人,幾乎必然是自由之敵。”
自由被哈耶克視為最重要的社會目標,社會好壞的標準在于實現自由的程度。只有通過自由市場,才能實現這一目標,形成保證人的自由的“自然秩序”。 看看人類的歷史進程,的確是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占統治地位的歷史階段,以人們人身自由的普遍獲得為基礎,自主決策、自由契約、平等競爭、自愿交易成為社會經濟生活的常態。政治和經濟層面的相對自由,極大地擴展了人們自由選擇的空間,私域形態和私人生活變得史無前例的豐富多彩。與此同時,市場經濟進一步發展,人們的自由意志日漸覺醒并更廣泛地在公域中體現出來,人們的權利意識開始取代臣民意識和奴仆意識,少數人對公共權力和公域活動的壟斷被打破,公民對政府、市民社會對政治國家不再是被動的仆從關系,而是一種相互制約、平衡發展的互動關系。一方面是公民權利的增長和市民社會地位的上升,公民可以參與選擇和要求國家提供什么樣的公域,另一方面市場具有自發的社會秩序調節功能,社會秩序無須僅賴于政治控制,人們生活中的政治因素也部分被市場經濟所取代,國家也有條件對私域活動“松綁”,使得政府和政治國家的統治、掠奪性質淡化,日漸成為良好社會秩序的提供者和社會服務者。總之,市場經濟為公域、私域和諧共生、各得其所、各展其能提供了可能,并在當前的主要市場經濟國家成為現實。
相反的例證是計劃經濟體制之下,經濟上由國家人為配置社會資源,生產依靠國家的指令,社會財富主要由政府壟斷和分配;政治上實行中央集權制和“專政”;私人生活空間極為狹窄,很大程度上處于集體化、組織化、單位化的狀態,還經常被卷入“政治掛帥”、“階級斗爭為綱”、“國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政治狂熱和國家主義的大敘事之中,世俗生活和個人利益被置于無足輕重的地位。在公域、私域關系上,這種模式使得政治公域獨大,權力意志主宰經濟和社會生活,市民社會無法形成或有名無實而無所作為,市場私域受到空前的排斥,私人利益最大限度地被壓制,私人生活則因個人螺絲釘式的工具化而幾無選擇。所以,它形成了一種公域基本吞沒或遮蓋私域的社會結構。哈耶克對社會結構的這種分析揭示了“通往奴役之路”的現實存在,也是我們理解其思想價值的重要方面。
在哈耶克看來,通向自由之路,要靠自由市場,也要“秩序”。 秩序理論從秩序的形成視角,將秩序分為自發秩序(或自然秩序等)和建構秩序。自發秩序是指由系統內部,它是作為人的行為的結果而不是人為(有意識)設計的產物。自發秩序被認為具有效率特征和自由特征。建構秩序則是系統外強加的秩序,是一種計劃秩序、人造秩序,是為一定的目的特意設計出來的。從自由主義大師們的分析可以看出,他們更加看重自發性秩序的效率,對建構秩序則十分警惕并主張嚴防其對自發秩序的限制。自發性秩序是有效率的,當然并不排除建構秩序的必要性,只是應將其嚴加限制。不同的領域應有不同的秩序。實踐也證明,行政完全控制經濟的秩序已然越界,將不同領域的秩序都納入“整體建構”,哪怕出自最良好的愿望,也不會取得好的社會效果。建構秩序最好局限于公域之內,并要能保障私域和社會的自發秩序的生長。
哈耶克和繆爾達爾的分歧或許沒有想象的那么大。似乎是這么一種情形,在通向自由之路上,繆爾達爾和哈耶克都在前行,只是哈耶克更重視他的另一種使命:不斷提醒同行者別太自負,時刻注意前面是否有致命的陷阱。
(本欄目責任編輯:阮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