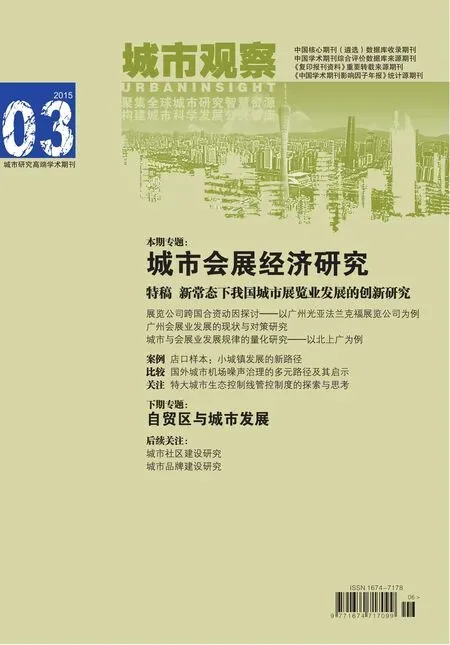社會化養老趨勢下家庭照料的作用及支持體系研究
◎ 陳 蓉 胡 琪
一、引言
20世紀大部分西方發達國家相繼進入老齡社會,老年照料問題越來越受到重視。我國于20世紀末進入老齡社會,人口老齡化進程起點晚于西方發達國家,但我國人口老齡化速度之快在人類發展史上實屬罕見,且我國也是老年人口最多的國家。我國必須在經濟社會發展相對滯后、時間緊迫、照料需求激增且巨大的情勢下做出應對,因而對于經濟、社會、政府、家庭,老年照料都是一個非常艱巨的挑戰。
一般來說,老年照料可以分為社會照料和家庭照料兩大類。為實現最優的照料模式,以最小的成本為老年人提供優質的照料服務,各國的老年照料都在走向社會和回歸家庭之間不斷權衡[1]。我國有著悠久的家庭養老傳統,在相當長時間內家庭一直承擔著主要的養老職能,以配偶、子女等家庭成員或者其他親戚等提供非正式照料為主要的照料方式。隨著人口老齡化態勢的顯現并日益嚴峻,加之家庭結構的小型化、家庭的養老功能日漸式微,僅靠家庭提供非正式照料顯然難以滿足老年人的需求。老年照料需求走向社會成為必然趨勢。我國的養老事業規劃和實踐發展,開始強調政府引導與社會參與相結合、家庭養老與社會養老相結合,以構建居家為基礎、社區為依托、機構為支撐的社會養老服務體系為發展方向。
養老社會化是必然的趨勢和發展的方向。那么,在這個過程中、尤其是現階段我國的社會化養老服務體系建立尚處于初級階段,社會老年照料資源是否能夠滿足需求?家庭照料在現階段以及養老社會化發展的整個過程中是否還能夠發揮重要作用?如果可以,那么在廣泛發展正式照料的同時,如何采取支持政策鼓勵家庭成員承擔部分照料,繼續發揮家庭在老年照料中的作用?本文以上海為例,依據多次社會調查數據和相關統計資料,借鑒國內外相關實踐經驗,嘗試回答這些問題。
二、老年照料需求激增且巨大,僅靠社會照料難以滿足需求
(一)人口老齡化、高齡化與家庭小型化、空巢化交織,老年照料需求總量巨大
上海早在1979年就進入老齡化社會,比全國提前20年。目前,上海已進入人口老齡化深度發展、高齡化加速發展階段。2013年,上海市60歲及以上戶籍老年人口達到了387.62萬,占總戶籍人口的27.1%,其中80歲及以上高齡老年人口71.55萬,占總老年人口的18.5%。據預測,2010-2025年的15年都將是上海老齡人口的快速增長期。與此同時,人口老齡化、高齡化與家庭小型化、空巢化相遇。據統計,當前上海市戶籍人口中的獨生子女家庭約有300多萬個,獨生子女父母600多萬人,占戶籍人口約四成多。隨著時間推移,獨生子女父母正陸續進入退休和老年時期,新增老年人口中約有80%以上為獨生子女父母。根據2013年上海市老年人口和老齡事業監測統計信息,2013年末上海市“純老家庭”老年人90.43萬人,即戶籍老年人口中有近四分之一(23.3%)的老人生活在空巢老年家庭。規模巨大的老年人口,特別是大量的獨生子女老年父母和空巢家庭老人,使得老年照料需求的總量巨大。
(二)老人(尤其是失能失智老人)對醫療、護理、康復等專業性要求高的需求強烈
人口老齡化態勢日益嚴峻的情勢下,老年照料需求內容也在分化,目前老年人的實際養老需求可以分為醫療需求、護理需求和生活類需求。隨著人口高齡化和疾病譜的改變,老年人對以老年護理和康復為主的醫療服務需求呈現急劇上升的趨勢。國家統計局上海調查總隊2013年對2248位60歲以上老年人的社區服務需求調查結果顯示,受訪者對醫療保健類服務的需求度最高,達79.6 %,且年齡越大、收入水平越高、生活自理能力越差,對醫療保健類服務的需求度越高①。此外,隨著年齡的增長,老年人中生活部分能自理、完全不能自理的比重上升,失智的患病率也上升。據估算,上海共有失能失智老年人約41萬②,約17萬失智老人中50%的人患病程度已達中度或重度[2]。失能、失智、高齡老人的照料、護理和康復成為養老最大的難題。
(三)社會(社區)照料資源供給有限,難以滿足需求
盡管從全國來看,當前上海的養老社會化程度和水平都走在前列,但與國際水平比較,仍是處于初級階段,社會化的養老資源總量供給仍然短缺,結構配比、尤其是專業性的服務提供依然有很大缺口,難以滿足老年人的需求。以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為例,2007-2013年上海享受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的老年人規模從13.5萬增至28.2萬,但社區居家養老服務人員數量卻基本維持在3萬人左右,人均服務老年人人數從4.8個增至9.1個,甚至有些街道每個人負責11~12個老年人。服務人員的缺乏使得老年人無法得到精心照料。以家庭病床和家庭醫生為例,2010年上海為老年人開設家庭病床4.08萬張,而需求量達到16.9萬張;2013年上海共有3212位家庭醫生,按照每人負責2000-2500名居民來測算,遠遠無法滿足需求[3]。從對失智老人的照料來看,據測算,上海每12位失智老人僅擁有1張護理床位③,全市養老機構和醫療護理機構分別收住了失智老人4757例、5215例,合計不足1萬人[2],即約有16萬失智老人缺乏專門機構照料。
三、家庭照料仍發揮著重要作用,也亟需社會支持
(一)從老年人的意愿來看,家庭(居家)養老仍是首選的養老方式
目前,國際上積極應對老齡化的理念中提倡最大限度讓老年人留在家里養老。盡管在社會化養老程度已經很高的發達國家,家庭照料仍是大部分老人首選的養老方式,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且多方面鼓勵和支持家庭為老年人提供照料,機構養老是“不得已”的選擇。比如,瑞典通過各種專業護理,讓老人能夠盡可能延長繼續在自己家中生活的時間,而且鼓勵家庭和子女重新承擔起一部分照料老年人的工作。
在我國,歷來有家庭養老的傳統,盡管當前傳統的家庭養老功能正日趨弱化,但對于大多數老年人來說,家庭養老仍是他們的首選養老方式。在上海這樣的國際大都市情況依然如此。2013年國家統計局上海調查總隊的養老意向調查結果顯示,有67.3%的受訪者傾向于“傳統家庭養老”,21.2%傾向“社區居家養老”,另有11.1%和0.4%則傾向“機構養老”和“其他方式養老”。
(二)目前的養老服務格局中,家庭仍是主要的力量
目前,上海實行的是“9073”的養老模式,90%的老年人通過自我照料和社區服務實現居家養老,7%的老年人通過社區的各種專業化服務實現社區照料養老,3%的老年人入住養老機構集中養老,即有97%的老人將通過居家養老服務和社區養老服務實現“家門口養老”。顯而易見,自我照料、居家養老都是以家庭為基礎和核心的,住在家里根據需要接受部分社會化的服務;事實上,即使是社區照料養老也離不開家庭的參與。在養老社會資源短缺的現階段,家庭仍然是提供養老照料的主要力量,家庭照料仍是主要的照料方式之一。
(三)家庭照料亟需得到社會支持和鼓勵
為了了解家庭在提供老年照料方面面臨的主要困難和需要的幫助,更好地提供社會支持,筆者于2014年9-10月在上海市中心城區的某街道的15個居委會,開展了“居家老年人的家庭非正規照料者調查”。與大多數以老年人為調查對象的社會調查不同,此次調查以主要提供家庭照料的成員為調查對象,具體是指以家庭成員為主要照料者的、需要生活照料支持的、選擇居家養老的老人的家庭非正規照料者。經過兩個月的調查,共獲得了300個樣本的信息。
調查結果顯示,(1)家庭非正規照料者以女性為主(占64.8%);(2)32.1%的照料者是被照料老人的女兒,24.4%是兒子,17.1%是配偶,12%是媳婦,2.7%是女婿,還有9.7%的其他人員;(3)98%的照料者反映照料老人有壓力;(4)老人對上門護理和康復類服務、上門醫療服務和陪醫服務的需求度非常高;(5)但是,家庭非正規照料以家務類和老人身體生活照料類為主,幾乎沒有人可以提供醫療、護理、康復類照料;(6)照料者亟需獲得社會支持,希望有更多的社會性上門服務項目、更好的服務人員、便利的養老服務一站通平臺、對家庭照料者給予經濟支持、并進行技能培訓。
上海自2000年以來十多年的探索實踐表明,在養老服務社會化的初期,社會老年照料的服務能力、資源供給還遠遠不能與日益增長的需求相適應,家庭照料發揮著重要作用,家庭照料者需要得到支持和幫助。養老服務社會化是發展的方向,也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社會化養老服務體系固然可以直接以老人為服務對象,但更重要的是要把老人所在的家庭作為一個整體,通過向家庭提供全方位的服務,采取多種措施支持家庭照顧者,維持家庭的照顧能力,以達到照顧老人的目的。筆者認為,養老社會化不是替代家庭養老功能,而是幫助家庭更好地履行養老責任,通過合理地搭配家庭照料和社會照料功能,以最小化的成本和最大的收益為老年人提供照料。
四、構建鼓勵家庭成員提供照料的社會支持體系
(一)出臺支持家庭照料的政策規定和法律保障
《老年人權益保障法》中明確指出,“國家建立健全家庭養老支持政策,鼓勵家庭成員與老年人共同生活或者就近居住,為老年人隨配偶或者贍養人遷徙提供條件,為家庭成員照料老年人提供幫助”。然而,目前我國家庭養老支持政策尚不健全,甚至有一些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加速削弱了本已弱化的家庭養老功能。比如,對普通住房標準的規定,優惠政策更多傾向于小戶型,并不鼓勵三代同堂。再如,限制生育數量的計劃生育政策的執行和長期宣傳,使得少生優生的生育觀念已經深入人心,出現了越來越多的4-2-1家庭,即使現在政策允許“單獨夫妻”可以生育兩個孩子,符合條件的家庭也只有少部分愿意生兩個孩子。又如,個人所得稅的征收也沒有考慮個人所在家庭的狀況及其需要承擔的家庭責任。
人人都會老,家家都有老人。應考慮建立健全家庭養老支持政策,增強家庭的養老功能。筆者有幾點思考和建議。一是,可以考慮在經適房、廉租屋等住房資源配置時,對于子女愿意與老人共同居住的家庭給予適當的傾斜;還可以考慮推出敬老公積金計劃,鼓勵子女與父母同住,提高子女贍養老人的積極性。二是,近期鼓勵市民按照政策生育,即通過宣傳和一系列措施,鼓勵目前已經滿足生育兩個孩子條件的夫妻生育兩個孩子;同時,考慮適時調整限制數量的生育政策。三是,嘗試以家庭為單位的稅收政策,比如在征收個人所得稅時,將有養老或撫幼需求的家庭的經濟成本考慮在內,對這些家庭給予稅收優惠。
(二)完善以鼓勵居家為導向的醫保梯度支付政策
以鼓勵居家養老為導向,以統一的老年照護需求評估為基礎,醫保部門可以采取多種支付方式和手段,以實現鼓勵居家養老、居家護理的政策目標。可以考慮:一是對老年護理院長期住院病人,實行醫保支付比例“梯度遞減”;二是對養老機構內設護理床位,設定不高于居家老年護理的報銷比例;三是設置差異化的醫保支付起付線和封頂線,使居家護理的實際報銷比例進一步高于機構護理;四是對居家護理老人的醫保自負部分設立減負政策,降低部分低收入居家老人的費用負擔。
(三)通過提供居家養老服務幫助家庭養老
根據老年人的健康狀況,進行合理規劃,將醫療、保健、康復類資源配備到家庭,幫助在家養老的老人及其家庭成員。對于健康老年人主要是健康促進、預防等,可以通過健康講座、健康咨詢等方式提供服務;對于有慢性病的老年人,社區建立健康檔案,提供慢性病管理;對處于疾病恢復期、住在家里康復的老年人,提供上門康復服務;對于功能殘疾需要長期照護的居家老年人提供康復和護理服務等。社區的各類資源充分發揮照料作用,社區日間照料中心以生活不能完全自理、日常生活需要一定照料的半失能老年人、失智老人為主,承擔起專業的護理、照料和保健康復服務;居家養老服務社主要提供家政服務和基礎生活照料服務;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家庭病床和家庭醫生等提供醫療護理服務。
(四)對家庭非正規照料者給予支持
支持承擔照料的家庭成員,主要可以從提供替代性照顧服務、照料技能培訓、心理支持、經濟補貼等幾個方面著手。替代性照顧服務支持是國外比較常見的支持家庭非正規照料者的做法。鼓勵部分床位供給充裕的養老機構和社區照料中心提供老年人短期入住床位,為長期照料老人的家庭成員定期或者在其有需要時提供臨時性代替服務,也即喘息式服務。依托專業醫療機構、社區內的養老機構、助老服務社等專業社會組織,為照顧老人的家庭成員或家政人員提供培訓,可以充分提高照料者能力和照料的質量,特別在當前正規照料隊伍人員短缺的情勢下,能夠充分挖掘照料資源。家庭成員照料者尤其是長期照料者面臨非常大的心理壓力,依托專業組織對其進行心理慰藉和情感支持,緩解他們的心理壓力,有助于其身心健康。家庭非正規照料者由于照料老人而占用的時間、失去的工作或晉升機會、損失的收入是一種機會成本,且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時間資源的越發稀缺性、職業競爭的日益激烈,這種機會成本也在大大提高。家庭內部的照料難以用貨幣的形式進行市場化的衡量,但這種類型的照料也應該得到認可和鼓勵,因此,可以通過向長期照料老人的家庭成員提供經濟補貼的方式承認他們的部分付出,調動家庭成員提供照料的積極性。
注釋:
①數據來源:上海市統計局網站,http://www.stats-sh.gov.cn/fxbg/201310/262208.html②數據來源:光明網,http://health.gmw.cn/2014-09/25/content_13364474.htm
③數據來源:光明網,http://health.gmw.cn/2014-09/25/content_13364474.htm
[1]劉柏惠,寇恩惠.社會化養老趨勢下社會照料與家庭照料的關系[J].人口與經濟,2015(1):22-33.
[2]張云.上海市失智老人社會支持體系研究[D].復旦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
[3]劉華.“醫養融合”重在融合現有資源[N].東方早報,2014,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