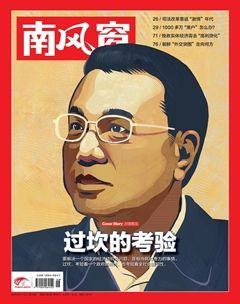1000多萬“黑戶”怎么辦?
萬海遠

2014年6月9日,廣東惠州,一個黑戶家庭,11歲的三女兒在家中照看兩個弟弟。
根據國務院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全國在2010年至少有1300余萬人沒有戶口,占中國所有人口的1%。4年之后,如果再加上被漏統計的人群,“黑戶”的總量可能要遠超過這個規(guī)模。
從調查結果來看,成功對戶口進行漂白的成本取決于不同的“黑戶”成因。總體來看,大學畢業(yè)生因為檔案接續(xù)而導致的“黑戶”漂白成本最高,但是成功漂白的可能性也最大;其次是不按計劃超生和非婚生育的“黑戶”個體,他們往往需要進行很多的協調、辦理各種證明等,最后成功漂白的可能性很低。調查結果也表明,超生而無法繳納社會撫養(yǎng)費或其他罰款,是阻止很多“黑戶”去主動辦理戶口的原因,比例上最高,其次是往返交通費和協調過程中發(fā)生的一些費用過高,使得“黑戶”群體沒有很強的動力去漂白自己的身份。
追尋1300多萬“黑戶”問題的歷史背景,在于一些制度設計的漏洞和不規(guī)范的基層執(zhí)法,由此積聚了難以面對卻無法回避的社會矛盾。戶籍制度的初衷是管理人口,而“黑戶”的存在卻可能給社會管理帶來各種問題。
從樣本的主要分布來看,“黑戶”樣本主要生活在農村,占57.8%;其次是13.7%的大學畢業(yè)生“黑戶”,其主要在工作地、原戶籍所在地和學校之間往返;再次是在不同城市進行流浪的“黑戶”樣本,占13.2%。
具體來說,女性群體占多數。在中國農村,傳統的觀念是要多生男孩,男性在封閉社會中的地位也顯著更高。因此,對于新生的男性嬰兒或兒童,家長為其主動去派出所登記的可能性就更高,從而其成為“黑戶”的比例顯著低于女性。除了大學畢業(yè)生由于戶口檔案接續(xù)而導致的“黑戶”外,其他原因導致的“黑戶”個體普遍都接受非常少的教育,文盲或完全沒有接受正規(guī)教育的比例高達44.2%,而為小學教育程度的也達到30.7%以上。
由于受教育程度很低,而且?guī)缀鯖]有出過遠門,大多數“黑戶”幾乎沒有機會說普通話,能熟練使用普通話的比例也非常之低,不太會講和完全不會講的比例加起來占比一半。
從調查結果來看,“黑戶”群體的心理健康狀況普遍較差。由于沒有途徑實現受教育的權利,大部分不能上學的“黑戶”孩子都散布在村莊里,常年沒有工作,缺少父母的照顧,因此也特別容易受到其他孩子的歧視。長期下來,“黑孩子”很容易養(yǎng)成自卑、自閉、沒有安全感、缺乏合作精神的性格特征,成為“問題少年”的幾率也大增。另外,在中國經濟增長和人口流動管制放松的前提下,一些“黑二代”也在很大程度上流動到了城市,通常從事最苦最累的工作,卻無法享受到正常公民的各項權利。總體上看,“黑戶”作為一個不被社會承認其客觀存在的群體,在心理上沒有認同感和存在感,性格比較自卑,通常缺乏與外界的溝通,甚至不愛與陌生人說話,心理健康程度較低。
根據調查數據,“黑戶”個體沒有工作的比例達43.8%(含從事農業(yè)活動);而在擁有穩(wěn)定工作的群體中,仍有37.4%的“黑戶”從來沒有簽訂過勞動合同,因此他們就業(yè)的基本權利很難得到保障。
“黑戶”個體是權利被剝奪的弱勢群體,由于長期被排斥在主流社會之外,他們沒有歸屬感,容易產生報復社會心理。而一旦心理底線被激化,他們隨時成為社會的定時炸彈。而且,由于“黑戶”群體中的一些違法人員長期習慣地游離于公眾視線之外,他們“反偵察”的能力更高,“人間蒸發(fā)”而不被發(fā)現的概率更大,因此容易成為一些非法組織努力爭取的對象。在新疆、云南發(fā)生的多起暴恐襲擊事件表明,很多恐怖組織正是看中了“黑戶”個體“看不見、摸不著、找不到”的特征,偏向于雇傭“黑戶”個體從事暴恐活動。所以,“黑戶”個體一旦被某些非法組織利用,會給防治和處理暴恐事件帶來極大的困擾,并增加新的社會不穩(wěn)定因素。
在當前,絕大部分中小企業(yè)都沒有承接戶口管理的能力,但是農民工和大學生又那么多,如何制定相關政策來鼓勵大學生到中小企業(yè)工作甚至創(chuàng)業(yè),相關的戶籍制度必須銜接上。而且,人口遷徙到外地之后,如果戶籍管理無法進行無縫對接,“黑戶”現象就會不可避免,由此對流動激勵構成負面影響,并成為個人和企業(yè)的發(fā)展障礙。
我們在調查中還發(fā)現,在城鄉(xiāng)戶籍統籌的背景下,城市的戶籍價值慢慢削弱;相反,農村戶籍的價值卻日益增加。所以,附著在農村土地上的福利和補貼吸引了大量的城郊甚至城鎮(zhèn)人口申請“非轉農”,倒城鎮(zhèn)化現象嚴重。在這種情況下,一些農村出去而沒有工作的畢業(yè)生,就會申請回到農村從事農業(yè)活動。
然而,當地派出所的規(guī)定是,縱然回村從事農業(yè)活動或自營勞動,也不能落成當地戶口,因為這會讓他們鎮(zhèn)的城鎮(zhèn)化率不斷走低。一些戶籍管理部門為了完成城鎮(zhèn)化的考核指標,輕易地把居民的農業(yè)戶口改成了非農業(yè)戶口,同時還不允許外遷的農村籍大學畢業(yè)生返回農村從事農業(yè)活動,也不允許他們把戶口遷回成當地戶口,以此來提高城鎮(zhèn)化率。這一做法,往往會帶來農村大學畢業(yè)生不能回遷而把檔案自留,由此帶來大量的“黑戶”現象發(fā)生。
在這種情況下,那些沒有工作、沒有農田、沒有宅基地的畢業(yè)生,在成為“黑戶”的同時,生存狀態(tài)堪憂。而且,在調查中我們發(fā)現,個別地方的城鎮(zhèn)化存在盲目的、運動式發(fā)展苗頭。雖然城鎮(zhèn)化率在快速上升,但是“被”城鎮(zhèn)化的居民卻并沒有享受到城鎮(zhèn)化所帶來的好處。雖然在戶口簿上被轉化成城鎮(zhèn)居民,但他們依然沒有好的住房,依然沒有優(yōu)質的社會保障,孩子也依然沒有享受到好的教育。換句話說,居民所得到的城鎮(zhèn)化不是真正有質量的城鎮(zhèn)化,而是盲目追求數量的城鎮(zhèn)化。
在當前,所有的證明如準生證、出生證、身份證、暫住證、未婚證、流動人口證、健康證、失業(yè)證、乞討證等,都離不開戶口。對一些部門來說,各種證明是為了管理方便的需要,但是有些非人性化的政策設計、復雜的辦理手續(xù),使得公民不得不為“驗明正身”而付出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在調查過程中,一個顯著的事實是,有十多個部門在管理戶籍,這一方面使得部門分割嚴重、互相推諉扯皮現象嚴重,而且不同部門之間互相牽制;不同的部門有不同的規(guī)定,經常還自相矛盾,讓居民陷入自我證明的死結中去。
這需要我們進一步改革和完善相關政策,從而讓他們不再接受“沒有戶口”的懲罰。
由于戶籍制度具有公民個人信息收集、確認、登記和身份識別的功能,諸如所在地證明、遷移證明、未婚證明等等都以它為基礎。然而,由于各種政策或證明權力被分散到不同的部門,各個證明之間又互相影響,若其中一個證件丟失,可能導致所有的證明無法辦理,這在客觀上加大了“黑戶”發(fā)生的比率。
這一點,我們可以借鑒美國的經驗,只擁有唯一且終生不變的社保卡號,并把所有的相關信息全部集成到一張芯片上,由此居民可以方便地走遍全國,并自由地搬家和換工作。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可以利用信息化、互聯網和高科技的力量,把戶口和檔案都共享到網絡,然后把所有這些信息全部集成到一張卡內。同時,根據不同部門的權限而獲取不同等級的信息,這樣就不會出現某個證明丟失而導致“黑戶”群體激增的現象。
1984年以后戶籍的福利功能得到強化;同時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戶口政策被用來當作強化人口管理的基本工具和手段。由于多年來“新生兒落戶”與“超生罰款”捆綁成為通行政策,有大量的家庭為逃避罰款,而沒有及時到派出所辦理落戶手續(xù),這在客觀上帶來780萬新生兒沒有戶口,并成為“黑戶”產生的源頭。從這個角度來說,“黑戶”問題的根源還在于戶籍制度的附加功能,因此我們建議戶籍管理部門強化對公民基本信息進行收集、確認和登記的管理功能,把當前戶籍的利益分配功能還原為只是簡單的信息收集功能,把與其不相關的計生罰款或相關的福利補貼功能全部剝離開來。
而大學畢業(yè)生戶籍檔案的接續(xù),不僅涉及人口計生、勞動保障、公安等部門,而且牽涉區(qū)縣內部、城市間或不同省份間的部門銜接,尤其包括高校、企業(yè)和人才交流中心等。因此,如果地區(qū)間、部門間的協調配合出現問題,那么戶籍的接續(xù)是難以有效完成的,“黑戶”現象的發(fā)生就不可避免。所以,我們要簡化行政手續(xù),協調部門間的政策規(guī)定,建議統一由居民最后流入地或最后一站派出所來協助個體進行檔案追查,由他們作為第一責任機構來協助個體進行檔案搜尋,由此優(yōu)化居民接續(xù)戶籍所需要的各種手續(xù),減少推諉扯皮現象,從而提高居民對戶口檔案搜尋的有效性,并從源頭上減少“黑戶”群體的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