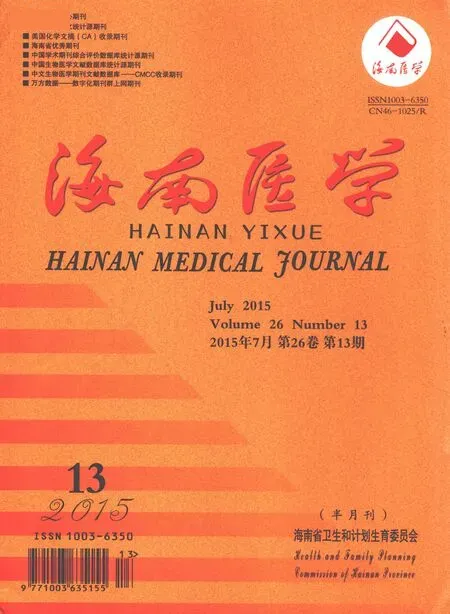下頸椎非融合技術(shù)的研究進(jìn)展
禤天航,曹正霖,王 剛,關(guān)宏剛
(1.佛山市中醫(yī)院脊柱外科,廣東 佛山 528000;2.廣州中醫(yī)藥大學(xué),廣東 廣州 510403)
下頸椎非融合技術(shù)的研究進(jìn)展
禤天航1,2,曹正霖1,王 剛1,關(guān)宏剛1
(1.佛山市中醫(yī)院脊柱外科,廣東 佛山 528000;2.廣州中醫(yī)藥大學(xué),廣東 廣州 510403)
頸椎疾病的治療當(dāng)中,脊柱融合術(shù)(Spinal fusion)是常用的手術(shù)方式,但隨著眾多脊柱融合術(shù)后并發(fā)癥的出現(xiàn),人民逐步把研究的目光轉(zhuǎn)移至非融合術(shù)(Non-spinal fusion)。與傳統(tǒng)的融合術(shù)相比,非融合技術(shù)不僅僅能重新建立脊柱穩(wěn)定性,還能保持手術(shù)節(jié)段的運(yùn)動(dòng)功能以及預(yù)防鄰近節(jié)段的退變。
非融合技術(shù);下頸椎;人工髓核;椎間盤置換;動(dòng)態(tài)固定系統(tǒng)
近年來,脊柱非融合技術(shù)受到極大的關(guān)注,在下頸椎領(lǐng)域也得到廣泛的臨床應(yīng)用與研究,下頸椎因其活動(dòng)度較大、受力相腰椎對(duì)較小的特點(diǎn),常常受到非融合術(shù)者的青睞,目前,其主要的術(shù)式有人工髓核置換術(shù)、全椎間盤置換術(shù)、動(dòng)態(tài)系統(tǒng)固定術(shù)等,現(xiàn)將下頸椎非融合技術(shù)的研究進(jìn)展綜述如下:
1 人工髓核置換術(shù)
人工髓核假體是研究的熱點(diǎn),單純的人工髓核置換術(shù)既能在內(nèi)窺鏡下微創(chuàng)進(jìn)行,操作簡便,又能有效恢復(fù)椎間高度,最大限度保持纖維環(huán)的完整性。但該項(xiàng)技術(shù)主要應(yīng)用于腰椎,頸椎較少,報(bào)道的資料也不多。人工髓核置入后的移位是最常見的并發(fā)癥,并且可引起吞咽困難、脊髓受壓等癥狀,究其原因,頸椎活動(dòng)度較大,無牢固的固定裝置,僅僅靠纖維環(huán)及周圍韌帶組織難以維持,人工髓核置入后可向前或向后突出,而且,國外人工髓核與國人的解剖有差異性,并不能牢固地使髓核穩(wěn)于椎間隙當(dāng)中。所以人們也在尋求一個(gè)穩(wěn)定的人工頸髓核置換術(shù)。目前人工髓核假體主要分為預(yù)制型與原位聚合型的假體,前者是預(yù)先做好相關(guān)形狀的假體成型后再植入體內(nèi),其優(yōu)點(diǎn)是它與正常髓核有著生物相似性,對(duì)恢復(fù)椎間高度有一定優(yōu)勢(shì),但其缺點(diǎn)是要切除過多的纖維環(huán),植入物存在被擠出的可能,而且其匹配性較差。后者是注射型液態(tài)假體,注射后才在體內(nèi)形成相關(guān)形狀,其優(yōu)點(diǎn)是對(duì)纖維環(huán)、終板切除較少,與術(shù)區(qū)結(jié)構(gòu)有著良好的匹配性,且還能促進(jìn)髓核再生。但其缺點(diǎn)是恢復(fù)椎間高度能力有限、易于滲漏、聚合放熱損傷纖維環(huán)與終板,甚至有毒性作用[1]。
1.1 人工髓核置換術(shù)的適應(yīng)證與禁忌證 目前其適應(yīng)證及禁忌證較為嚴(yán)格[2],其適應(yīng)證主要有:(1) 18~65周歲;(2)單節(jié)段病變且由椎間盤突出引起的相關(guān)癥狀;(3)保守治療6個(gè)月以上無效;(4)癥狀體征與影像學(xué)資料需一致。與此同時(shí),其禁忌證為:伴有明顯椎管狹窄、頸椎不穩(wěn)、畸形、感染、腫瘤、多節(jié)段病變、纖維環(huán)缺失等。
1.2 頸人工髓核置換術(shù)臨床研究進(jìn)展成果 頸人工髓核在較早已有研究,徐印坎等[3]制造的人工頸髓核假體有較好的生物相容性,其人工頸髓核置換術(shù)病例術(shù)后早期取得不錯(cuò)的效果,而隨后,他隨訪發(fā)現(xiàn)髓核置換術(shù)3年以上的患者進(jìn)行影像學(xué)檢查發(fā)現(xiàn)50%左右病例出現(xiàn)椎體前骨痂,手術(shù)椎節(jié)失去活動(dòng)能力,但人工髓核還可以保持椎間隙高度,療效仍優(yōu)良。為評(píng)價(jià)人工髓核的可行性[4]。王文軍等[5]對(duì)人工髓核置換術(shù)作出了生物力學(xué)評(píng)價(jià),肯定了它的生物力學(xué)意義,他們發(fā)現(xiàn)人工髓核的植入使頸椎活動(dòng)時(shí)各方向的穩(wěn)定性都得到顯著的加強(qiáng),不但使椎間隙高度增大,各韌帶及纖維環(huán)的張力有一定程度的恢復(fù),還可在頸椎負(fù)重時(shí)分散相關(guān)應(yīng)力而不至于椎間隙變窄,且減輕雙側(cè)小關(guān)節(jié)應(yīng)力集中。而與此同時(shí),如何維持人工髓核的穩(wěn)定性是人們目前研究得較多的方向,李宏偉等[6]研制了頸椎人工髓核柔性穩(wěn)定一體化系統(tǒng),該系統(tǒng)由超高分子量的聚乙烯構(gòu)成的翼狀韌帶、人工髓核和連接系帶組成,翼狀韌帶主要起人工韌帶作用,彌補(bǔ)術(shù)中對(duì)前縱韌帶的破壞,系帶為連接人工髓核和翼狀韌帶的部分,其牽拉作用可有效防止髓核脫入椎管,同時(shí)有利于頸椎術(shù)后功能鍛煉。彭偉等[7]把頸椎柔性穩(wěn)定一體化系統(tǒng)試驗(yàn)于狗的頸椎,并在0 N和100 N軸向載荷下測(cè)量標(biāo)本椎間隙高度,他們發(fā)現(xiàn)柔性穩(wěn)定一體化系統(tǒng)能有效撐開椎間隙,維持椎間高度,防止椎管容積減少,保持頸椎單位功能狀態(tài)。另外,如何少破壞纖維環(huán)去進(jìn)行髓核的置換,這也是髓核置換的熱點(diǎn)之一。總之,頸髓核置換術(shù)已經(jīng)得到越來越多研究證實(shí)了其生物力學(xué)安全性與可行性,但廣泛應(yīng)用于臨床,仍需不斷探索。
2 全椎間盤置換術(shù)
全椎間盤置換術(shù)(Total disc replacement,TDR),就是將人工假體替代切除的椎間盤,使其功能有效地保留下來。大量的生物力學(xué)表明ACDF能增加相鄰節(jié)段退變的風(fēng)險(xiǎn),有臨床研究[8]報(bào)道ACDF術(shù)后10年隨訪節(jié)段退變風(fēng)險(xiǎn)可達(dá)25.6%,頸椎間盤置換術(shù)不僅僅使減壓術(shù)后頸椎活動(dòng)得以保留阻止臨近節(jié)段的應(yīng)力,而且也避免了頸椎固定及取自體髂骨時(shí)所帶來的潛在風(fēng)險(xiǎn)。所以臨床上在頸椎病手術(shù)選擇中,全椎間盤置換術(shù)無疑是一個(gè)很好的選擇。
2.1 假體的分類 目前臨床上常見的假體有BRYAN假體、Prestige假體、PRODISC-C假體、PCM假體、M6假體、Discover假體等。BRYAN假體是一個(gè)由里層的聚氨酯和外層的鈦合金外殼構(gòu)成的雙關(guān)節(jié)金屬聚合體,與骨面接觸的是鈦結(jié)構(gòu),呈多孔狀,有效保證了假體的穩(wěn)定性,其瞬間旋轉(zhuǎn)軸是可變的,屬于半限制結(jié)構(gòu)。Sasso等[9]通過前瞻性研究發(fā)現(xiàn)在術(shù)后2年隨訪Bryan假體置換在NDI、VAS評(píng)分及SF-36,翻修率方面要顯著優(yōu)于ACDF組。Prestige假體是金屬對(duì)金屬球窩關(guān)節(jié),目前比較新的是PrestigeST和Prestige LP假體,它有著更小更穩(wěn)定的前翼。Mummaneni等[10]曾對(duì)PrestigeST假體手術(shù)與ACDF手術(shù)進(jìn)行比較。2年隨訪顯示出前者對(duì)臨近節(jié)段退變治療更具優(yōu)勢(shì)。Prodisc-C假體由兩側(cè)鈷-鉻合金終板以及中央高分子聚乙烯材料構(gòu)成,其球窩結(jié)構(gòu)能有效保證活動(dòng)度。但是鈷-鉻合金材料對(duì)難以進(jìn)行術(shù)后MRI復(fù)查。Murrey等[11]應(yīng)用前瞻性多中心隨機(jī)對(duì)照研究對(duì)單節(jié)段頸椎病患者應(yīng)用Prodisc-C植入,2年隨訪療效較ACDF滿意。PCM假體是由鈷-鉻合金構(gòu)成的終板與聚乙烯構(gòu)成的滑動(dòng)內(nèi)核構(gòu)成,植入的過程可以保留上下椎體的骨質(zhì),避免對(duì)骨質(zhì)的過度削除。同樣該假體也為非限制性假體。M6假體的髓核是彈性的聚合物,纖維環(huán)是聚乙烯材料,兩端的三棱齒能穩(wěn)定地咬住上下椎體,防止假體移位。Discover假體由鈦合金的上下終板、聚乙烯髓核組成的非限制性球窩假體。這種假體活動(dòng)功能較大,有利于最大限度恢復(fù)術(shù)后頸椎活動(dòng)功能。
2.2 全椎間盤置換術(shù)的手術(shù)適應(yīng)證、禁忌證及并發(fā)癥 該手術(shù)適應(yīng)證為:單個(gè)節(jié)段或穩(wěn)定型2個(gè)節(jié)段的脊髓型及神經(jīng)根型頸椎病,且不伴椎管狹窄、節(jié)段性不穩(wěn)及骨質(zhì)疏松。禁忌證為:節(jié)段不穩(wěn)定,過屈過伸側(cè)位X線片顯示椎體間前后滑移≥3 mm;椎間隙狹窄,椎間隙高度丟失嚴(yán)重;嚴(yán)重的骨質(zhì)疏松癥;椎體腫瘤,椎體椎間隙感染等。其并發(fā)癥為:(1)假體松動(dòng),人工椎間盤置換失敗的原因可能是長期摩擦產(chǎn)生碎屑,使細(xì)胞產(chǎn)生炎癥反應(yīng),導(dǎo)致骨質(zhì)吸收受阻,假體松動(dòng)不穩(wěn)。另一方面,假體的磨損也是造成假體松動(dòng)的原因之一;(2)異位骨化,目前原因還沒能明確,目前大多推測(cè)認(rèn)為主要是假體偏小引起的。韓慧等[12]報(bào)道了1例患者在術(shù)后1年假體周圍出現(xiàn)異位骨化,椎體活動(dòng)度消失,他們作多番探究,認(rèn)為其原因是假體過小引起的。蔣濤等[13]也報(bào)道了他們?cè)谝焕齒線發(fā)現(xiàn)Bryan假體在2年后出現(xiàn)異位骨化,5年后出現(xiàn)自發(fā)融合。同樣術(shù)中的出血及殘余碎骨也是異位骨化的原因之一,故有經(jīng)驗(yàn)的醫(yī)生常在術(shù)中用冰鹽水沖洗術(shù)口,既可以止血,也可以沖掉碎骨塊。當(dāng)然,全椎間盤置換的近期效果也是相對(duì)令人滿意的。
2.3 全椎間盤置換術(shù)臨床研究進(jìn)展成果 在臨床與比較ACDF比較方面,各學(xué)者得出結(jié)論也相對(duì)一致,均認(rèn)為TDR療效是更值得肯定的。Yao等[14]進(jìn)行了全椎間盤置換與融合進(jìn)行Meta分析的比較,發(fā)現(xiàn)TDR手術(shù)組在VAS評(píng)分及ODI指數(shù)均優(yōu)于ACDF組,且手術(shù)時(shí)間及出血量無明顯差異。Zhang等[15]對(duì)TDR與ACDF進(jìn)行了前瞻隨機(jī)多中心控制試驗(yàn),也證實(shí)了TDR在FSU角度和預(yù)防臨近節(jié)段方面更具優(yōu)勢(shì)。Zhu等[16]發(fā)現(xiàn)頸椎前路ACDF術(shù)式術(shù)后活動(dòng)度明顯下降,DCI活動(dòng)度較術(shù)前有輕微下降,TDR組術(shù)前術(shù)后活動(dòng)度基本無差異,與此同時(shí),人們對(duì)多節(jié)段椎間盤置換療效與手術(shù)問題較關(guān)心,前者由Davis等[17]通過前瞻性多中心隨機(jī)對(duì)照試驗(yàn)證實(shí)行多節(jié)段手術(shù)也是安全而有效的,而后者則通過McAnany等[18]建立的Markov模型證實(shí)了其相對(duì)于ACDF有更好的手術(shù)成本效益。當(dāng)然,頸椎全椎間盤置換術(shù)的長期效果仍需長期隨訪驗(yàn)證,目前我們更多應(yīng)該考慮的問題是如何降低人工假體的價(jià)格以及如何盡量避免自發(fā)融合與自體骨化,不過相信將來這一項(xiàng)技術(shù)將越發(fā)成熟,在材料設(shè)計(jì)及置入技術(shù)方面將會(huì)有更進(jìn)一步的發(fā)展。
3 頸椎動(dòng)態(tài)穩(wěn)定器
頸椎動(dòng)態(tài)穩(wěn)定器(Dynamic cervical implant,DCI)是在人工椎間盤非融合技術(shù)基礎(chǔ)上發(fā)展而來的,目前主要使用的材料為鈦合金一體化假體,呈“U”型,能有效輔助頸椎屈伸活動(dòng),又可以防止其過度運(yùn)動(dòng),前方的倒齒能防止穩(wěn)定器移位,適應(yīng)證更廣,避免ACDF帶來的并發(fā)癥,而且其吸收震蕩、緩解植入物與上下椎體軸向應(yīng)力等功能是椎間盤置換術(shù)所不具備的。早在2002年Guy Matgé便設(shè)計(jì)應(yīng)用于臨床,2005年P(guān)aradigm Spine設(shè)計(jì)出第二代產(chǎn)品,到目前為止,產(chǎn)品不斷在更新應(yīng)用于臨床,并取得不錯(cuò)的效果。
3.1 適應(yīng)證與禁忌證 其主要適應(yīng)證:(1)退行性頸椎間盤疾病,尤其是C3~7頸椎間盤突出;(2)頸椎管狹窄癥。禁忌證:(1)嚴(yán)重骨質(zhì)疏松患者;(2)頸椎嚴(yán)重不穩(wěn)定;(3)椎體創(chuàng)傷或者腫瘤;(4)頸椎有自主融合節(jié)段患者。雖說嚴(yán)重的骨質(zhì)疏松癥是其禁忌證,但是周少波等[19]仍成功把其應(yīng)用于骨質(zhì)疏松患者上面,而且取得不錯(cuò)的效果,所以結(jié)合個(gè)體化情況選擇使用DCI才是安全而準(zhǔn)確的選擇。
3.2 臨床研究進(jìn)展 盡管該技術(shù)還處于比較初級(jí)的階段,不過從其在臨床上的應(yīng)用結(jié)果來看,還是令人滿意的。Wang等[20]在單節(jié)段的椎間盤突出使用了這一項(xiàng)技術(shù),并進(jìn)行了24個(gè)月的隨訪,他們發(fā)現(xiàn)術(shù)后JOA指數(shù)、VAS評(píng)分、NDI和SF-36等均較術(shù)前明顯改善,差異有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椎間高度明顯增加,不僅僅消除椎間盤壓迫癥狀,還能保持頸椎活動(dòng)度。而Matgé等[21]也通過多中心大樣本前瞻性對(duì)DCI進(jìn)行短期并發(fā)癥的研究,未發(fā)現(xiàn)有頸椎動(dòng)態(tài)穩(wěn)定器斷裂、移位等現(xiàn)象。侯振揚(yáng)等[22]也對(duì)5例頸椎DCI患者進(jìn)行效果隨訪,臨床效果也相當(dāng)滿意,影像學(xué)復(fù)查未見穩(wěn)定器移位、下移。最近李永寧等[23]也展示了他們使用頸椎DCI的成果,13例患者均獲隨訪,12例患者術(shù)后個(gè)1月其頸肩臂痛及上肢相應(yīng)區(qū)域麻木、肌力下降等癥狀體征明顯改善,術(shù)后平均PSI評(píng)分為1.6分,手術(shù)有效率為100%,術(shù)后活動(dòng)度減少(0.66±0.36)°,差異無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但遠(yuǎn)期效果與遠(yuǎn)期并發(fā)癥出現(xiàn)的隨訪還是有所欠缺,同時(shí)目前病例相對(duì)較少,國內(nèi)僅有為數(shù)不多的大醫(yī)院開展該項(xiàng)手術(shù),發(fā)展相對(duì)緩慢。不過其諸多的優(yōu)勢(shì)使得DCI技術(shù)有著廣闊的市場前景。
4 展望
綜上所述,非融合技術(shù)已經(jīng)在國內(nèi)外深入開展與研究,近20年來,該項(xiàng)技術(shù)在下頸椎的應(yīng)用也得到不斷發(fā)展和完善,其優(yōu)點(diǎn)是顯而易見的,它不僅僅能提供穩(wěn)定的內(nèi)固定,而且還能使手術(shù)節(jié)段活動(dòng)功能得以保留并有效降低鄰近節(jié)段的退變,雖然目前還缺少長期的隨訪及未知并發(fā)癥的出現(xiàn),而且在全國廣泛開展該項(xiàng)手術(shù)進(jìn)程緩慢,但是其早中期不錯(cuò)的效果、值得肯定的生物力學(xué)結(jié)構(gòu)、低鄰近節(jié)段退變率使得該項(xiàng)技術(shù)有著光明的未來。
[1]李海俠,鄒德威,陸 明.人工髓核假體的研究進(jìn)展及其發(fā)展的方向[J].中國組織工程研究與臨床康復(fù),2011,15(13):2429-2433.
[2]張 強(qiáng),鄒德威.人工髓核的研究進(jìn)展[J].山東醫(yī)藥,2009,49 (48):1-2.
[3]徐印坎,徐玉良,盧 立,等.人工髓核置換術(shù)治療頸椎間盤突出癥[J].骨與關(guān)節(jié)損傷雜志,1992,7(2):73-74.
[4]徐印坎,侯鐵勝,冉永欣,等.頸椎間盤人工髓核置換[J].頸腰痛雜志,2001,22(3):177-180.
[5]王文軍,周江南,梁秋發(fā),等.頸椎椎間盤人工髓核置換術(shù)的生物力學(xué)評(píng)價(jià)[J].中國臨床解剖學(xué)雜志,2002,20(5):383-385.
[6]李宏偉,馬遠(yuǎn)征,薛海濱,等.頸椎人工髓核柔性穩(wěn)定一體化系統(tǒng)的設(shè)計(jì)和制備[J].中國組織工程研究與臨床康復(fù),2009,13(43): 8450-8453.
[7]彭 偉,馬遠(yuǎn)征,薛海濱,等.頸椎柔性穩(wěn)定一體化系統(tǒng)對(duì)維持犬頸椎間隙高度作用的研究[J].創(chuàng)傷外科雜志,2011,13(3):241-243.
[8]Hilibrand AS,Carlson GD,Palumbo MA,et al.Radiculopathy and myelopathy at segments adjacent to the site of a previous anterior cervical arthrodesis[J].Bone Joint Surg Am,1999,81(4): 519-528.
[9]Sasso RC,Smucker JD,Hacker RJ,et al.Artificial disc versus fusion:a prospective,randomized study with 2-year follow-up on 99 patients[J].Spine(Phila Pa 1976),2007,32(26):2933-2942.
[10]Mummaneni PV,Burkus JK,Haid RW,et al.Clinical and radiographic analysis of cervical disc arthroplasty compared with allograft fusion:a randomized controlled clinical trial[J].J Neurosurg Spine,2007,6(3):198-209.
[11]Murrey D,Janssen M,Delamarter R,et al.Results of the prospective,randomized,controlled multicenter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investigational device exemption study of the ProDisc-C total disc replacement versus anterior discectomy and fus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1-level symptomatic cervical disc disease[J].Spine J,2009,9(4):275-286.
[12]韓 慧,董榮華,曹富江.Bryan人工頸椎間盤置換近期療效分析[J].中國矯形外科雜志,2009,17(15):1152-1154.
[13]蔣 濤,任先軍,王衛(wèi)東,等.Bryan人工頸推推間盤置換術(shù)后中長期臨床療效及相關(guān)問題分析[J].脊柱外科雜志,2011,9(5): 268-272.
[14]姚立煒,王天儀,劉 洋,等.腰椎融合和腰椎間盤置換治療腰椎間盤退變性病變療效比較的Meta分析[J].中華外科雜志,2014,52 (5):370-375.
[15]Zhang HX,Shao YD,Chen Y,et al.A prospective,randomised,controlled multicentre study comparing cervical disc replacement with anterior cervical decompression and fusion[J].Int Orthop,2014,38 (12):2533-2541.
[16]Zhu R,Yang H,Wang Z,et al.Comparisons of three anterior cervical surgeries in treating cervical spondylotic myelopathy[J].BMC Musculoskelet Disord,2014,15:233.
[17]Davis RJ,Nunley PD,Kim KD,et al.Two-level total disc replacement with Mobi-C cervical artificial disc versus anterior discectomy and fusion:a prospective,randomized,controlled multicenter clinical trial with 4-year follow-up results[J].J Neurosurg Spine,2014, 7:1-11.
[18]McAnany SJ,Overley S,Baird EO,et al.The 5-year cost-effectiveness of anterior cervical discectomy and fusion and cervical disc replacement:A markov analysis[J].Spine(Phila Pa 1976),2014,39 (23):1924-1933.
[19]周少波,朱六龍,何齊芳.動(dòng)態(tài)穩(wěn)定器在頸椎病合并骨質(zhì)疏松中的應(yīng)用[J].中華全科醫(yī)學(xué),2014,12(1):26-27.
[20]Wang L,Song YM,Liu LM,et al.Clinical and radiographic outcomes of dynamic cervical implant replacement for treatment of single-level degenerative cervical disc disease:a 24-month follow-up [J].Eur Spine J,2014,23(8):1680-1687.
[21]Matgé G,Eif M,Herdmann J,et al.Dynamic cervical implant (DCITM):clinical results from an international multicenter prospective study[J].Paradigm Spine,2009,1:1-3.
[22]侯振揚(yáng),徐耀增,錢忠來,等.頸椎動(dòng)態(tài)穩(wěn)定器置入治療頸椎病5例:非融合術(shù)后彈性動(dòng)態(tài)固定效果隨訪[J].中國組織工程研究與臨床康復(fù),2010,14(30):5678-5681.
[23]李永寧,劉立岷,宋躍明,等.使用頸椎動(dòng)態(tài)穩(wěn)定器非融合頸椎的早期療效分析[J].西部醫(yī)學(xué),2014,26(6):778-780.
R687.3
A
1003—6350(2015)13—1946—03
10.3969/j.issn.1003-6350.2015.13.0701
2014-11-20)
曹正霖。E-mail:fstcmcaozhenglin@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