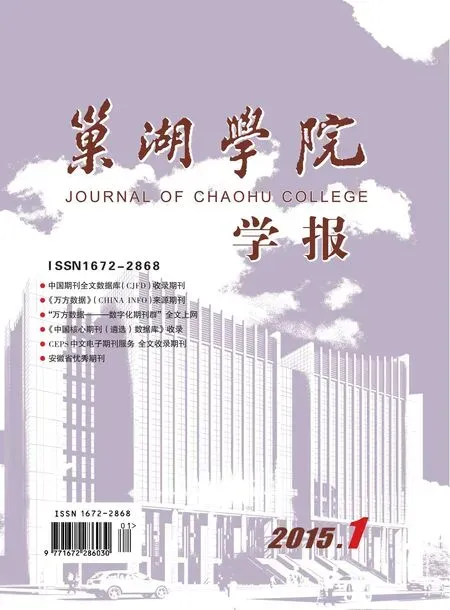一曲女性覺醒與解放的頌歌
——從兩組女性形象析安吉拉·卡特《與狼為伴》中的女權思想
林鴻
(安徽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安徽 蕪湖 241000)
一曲女性覺醒與解放的頌歌
——從兩組女性形象析安吉拉·卡特《與狼為伴》中的女權思想
林鴻
(安徽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安徽 蕪湖 241000)
《與狼為伴》是安吉拉·卡特根據之前的童話故事《小紅帽》而改編的短篇小說。卡特看到了許多傳統的童話故事中因受父權文化影響而存在的歪曲女性的成分,故而對其進行改寫,并在其中注入了女權主義思想。在《與狼為伴》中,卡特保留了原童話中諸如小女孩和其外婆這些女性角色,并塑造了另外幾個女性形象。大體而言,故事中的女性角色可以概括為兩類:一類是保守、消極、軟弱的傳統女性,另一類是覺醒并富于反抗精神的新女性。通過對這兩組女性角色的不同命運進行分析,可以探究卡特在這篇小說中傾注的女權主義思想。在這篇小說中,卡特批判了父權體制下傳統女性保守、被動的思想,謳歌了覺醒與解放了的新女性。
安吉拉·卡特;《與狼為伴》;女權思想
1 引言
童話故事通常都具有一定的警告或教育意義。但在傳統價值觀和父權文化的影響之下,許多傳統的童話故事帶有消極、負面的因素。作為當代著名的女性主義作家,安吉拉·卡特對文學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及其地位十分關注。在其許多作品中,卡特均傾注了她的女權主義思想。在翻譯童話故事的過程中,她意識到了許多童話故事中存在的歪曲女性的成分。“她根據女權主義思想以及當代人的價值觀和興趣對它們進行改寫,為這些故事注入了新的意義和生命”[1]。《與狼為伴》便是其這種改寫之下的成果。在其哥特式女權主義的改寫之下,卡特打破了傳統的禁忌,賦予這一古老的故事以新的意義。通過這種方式,她對父權制思想提出挑戰并顛覆了傳統童話故事中所謂的“理性”和“常識”的根基。在《與狼為伴》中,卡特塑造了兩類女性。通過對這兩類女性不同的命運安排,卡特成功地表達了她的女權主義思想。
2 卡特改寫童話故事的背景和意圖
《與狼為伴》最初源自夏爾·佩羅的童話名篇《小紅帽》,后經過了格林兄弟的加工與修改。在佩羅版的《小紅帽》中,狼吃掉了小女孩的外婆,而小女孩也被穿著外婆的衣服的狼所欺騙并與之共眠,整個故事以小女孩被狼吞食的悲慘命運結尾。佩羅是為17世紀法國“太陽王”的王室貴族而寫,旨在捍衛宮廷道德觀念。他的作品傳達了資產階級貴族價值觀的重要性和優越性,同時“帶有強烈的男性主導色彩和其對女性偏見”[2]。格林兄弟的版本創作于19世紀,刪去了佩羅版《小紅帽》中的性和宮廷貴族道德觀念成分,將之潤色成一個新的童話故事。格林版的《小紅帽》旨在教育兒童遵守父權文化之下成人所規定的責任規范標準。在這一版本中,小紅帽的母親曾告誡小紅帽要聽話,徑直走路去外婆家。小紅帽也承諾會聽從母親。但是她很快就偏離了母親告訴她要走的路,輕信了狼的建議,在中間停下來采了一束花準備送給外婆。對感官享受的沉溺和對母親的違背導致了她和外婆的悲劇。格林版的《小紅帽》在結尾處增加了一個情節,即一個路過的獵人殺死了狼,小女孩幸運地得救,從而使這則童話故事變成了一則家庭寓言,以期符合19世紀新興資產階級的道德倫理和維多利亞時期的大眾審美。全新的故事結尾既給了小女孩改過自新的機會,又懲罰了萬惡的狼,進而向整個社會宣揚了惡行終將受到懲罰的道德觀念,擴大了這則童話故事的教育意義。然而,在這兩個版本的《小紅帽》中,女性均被刻畫為軟弱、被動的角色。她們或是成為受害者,或是等待男性的救贖。
隨著社會的發展,女權主義運動開始在世界范圍內蔓延。20世紀60年代更是掀起了女性主義的第二次浪潮。在其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著作《第二性》中,法國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提出了她的著名論斷:“女人并非生而為女人,女人是后天塑造的”[3]。緊隨其后,許多女權主義者將視線轉向被視為女孩們的首要訓練手冊的童話故事。隨著新女性意識的覺醒和發展,許多作家開始對佩羅和格林兄弟的古典童話故事表示不滿,安吉拉·卡特就屬于這一類群體。“她以有一定見識的成年人為受眾,對童話故事進行改寫,將恐怖的幻象和性喜劇融入自己的故事當中”[4]。她將佩羅版和格林版的《小紅帽》結合起來,創作了一個全新的短篇小說,并在其中著力刻畫了兩類對比鮮明的女性人物。通過對這兩類不同命運的女性人物的塑造,卡特顛覆了傳統的父權制思想,傳達了一系列新穎而獨特的女性主義價值觀。在卡特的版本中,被動、保守、依賴他人的傳統女性面臨死亡,勇敢、機智、強大的新女性則能為生命而戰,追求自己的幸福。同時,她“將性加入童話故事中……打破了傳統童話故事的束縛……將女性從被動變成主動,從消極變成積極,從羞怯變成勇敢,從隱蔽變成明晰,進而將文學作品中的女性還原至她們本來的面目,并將女性和男性置于平等的地位”[5]。
2 傳統女性之死
在《與狼為伴》中,卡特塑造了兩個順從的傳統女性:一個是在廚房里被狼吃掉的婦女,另一個則是小女孩的外婆。她們遵循傳統的社會規范和宗教價值觀念,過著保守的生活,但卻最終難逃被狼吃掉的厄運。
故事中第一個出現的女性人物是一個典型的傳統家庭婦女,“她正在自己家的廚房里做通心面的時候被狼吃掉了”[6]。在廚房里做飯是家庭事務的象征。根據父權社會的傳統觀點,女性的生活空間一般僅局限于家庭內部,而那些活躍在社交場合的女性則被貶低甚至蔑視。實際上,19世紀女性的生活是非常受局限的,幾乎與社會隔絕,因而“在傳統的童話故事中,人們很難找到走出家庭、踏入社會的女性”[7]。人們不期待女性養家糊口,女性每天只能為家庭事務奔波。在《與狼為伴》中,森林成為社會的隱喻,它只屬于男性,而狼則代表了社會上邪惡的男性,他們誘惑和毀滅女性。人們對狼的懼怕象征著現實生活中人們對危險的男性的懼怕。狼和叢林一起對被驅逐出社會之外而局限于家庭內部的女性構成威脅。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與狼為伴》的第一部分對危險的狼和森林的介紹,實際上傳達的是外部社會的危險。狼是可幻化成人形的食肉動物,它“既狡猾又兇猛”[6],而且 “在夜晚森林中所充斥的所有危險當中,包括幽靈和妖怪在內……狼是最危險的,因為它從不聽從理智”[6],連狼叫“本身就是一種殺戮”[6]。在“沒有人的森林當中,人們常常會遇到危險”,因為蓬亂的樹枝“在你的周圍纏作一團,將粗心的行人騙入迷網之中,似乎這些植被本身就和這些生活在這里的狼串通在一起”,而作者也在這里勸誡行人走過這里時要格外小心,因為“一旦你偏離了正路,,狼就會把你吃掉”[6]。兇狠的狼和危險的森林象征著只屬于男性的外部世界,限定了女性的生活區域,似乎女性只有呆在家里才能避免危險。然而,卡特最終給這個遵守傳統社會規范的女性安排了死亡的命運,從而傳達出順從以及保守的生活方式并不能給女性帶來安全的觀點。盡管人們努力將狼拒之門外,它還是“有辦法進入你的家里”[6]。廚房里的女人代表著傳統居家型女性,盡管沒有走出房門,她終究沒能逃脫被狼吃掉的命運。因此,遵從傳統社會規范的女性處于社會的弱勢地位并淪為受害者。
故事中第二個也是最為重要的傳統女性人物是年老體衰的外婆。她虔誠地過著獨居生活:“她以《圣經》為伴,是一個虔誠的老婦人”[6]她依靠一個男孩為她生火,以度過寒冷的夜晚。“外婆家中的細節給人以安全和井井有條的感覺,似乎可以防止狼的進入”[8]。她房間里的落地大擺鐘以及結婚之前做的拼布棉被均是傳統生活方式的象征。然而,虔誠、順從以及保守的生活方式并沒將她從狼人的口中救下。卡特對這一傳統女性死亡時的描述頗具諷刺意味,“老奶奶,你可將你的《圣經》和圍裙砸向他,你不是認為那樣可以抵抗這些可怕的禍害么。快把耶穌和他的母親以及天上的天使都叫來保護你,但這些對你都沒有用”[8]。同時,卡特有意安排小女孩的外婆看見狼人的裸體,甚至生殖器——“這個老婦人在這世上最后的所見是一個年輕的男人,他眼如煤渣,如石般裸露著,向她的床邊走來”[6]。這一安排無疑是對傳統社會虔誠而保守的生活方式的大膽挑戰。“傳統女性恪守貞潔,認為只要虔信宗教、崇尚理性,她們就可以保護自己。事實是這些因素根本就不起任何作用。她們只會被男性的欲望所吞噬”[9]。故事中外婆的死亡充分表明了父權制體系下傳統社會價值觀對女性的摧殘。一味地遵從社會傳統以及虔誠、保守的生活并不能給女性帶來安全。
綜上所述,在《與狼為伴》中,廚房中的女人以及年老虔誠的外婆代表著第一類女性—順從、居家的傳統女性。借由她們的死亡,卡特試圖表明這一類女性在社會中找不到留身之所,進而傳達了她深刻的女性主義觀點。她“試圖告訴人們這些行為模式和價值觀念在對抗邪惡時并不是萬能的,對女性而言尤其如此”[10]。
3 新女性的反抗與存活
在《與狼為伴》中,還有另外一類女性。她們勇敢、明智,在性問題上也很開明,與前一類女性形成鮮明對比。她們用自己的力量進行反抗,為自己爭取生命和權利,并最終為自己的生存贏得了足夠的空間。她們是卡特所頌揚的新女性的代表。
這一類女性的第一個代表人物是女巫。由于遭到拋棄,她“將一整個婚禮上的人都變成了狼”并且“出于怨恨,常常讓它們在晚間蹲坐在她的小屋邊為她嚎叫,用它們的痛苦為她吟唱小夜曲”[6]。這里,遭到背叛的女巫能夠向造成她悲慘處境的男人復仇,女性第一次扭轉了其受害者的身份,轉而變為他人命運的操縱者。她再也不是服從男性欲望和命令的傳統女性,不再順從男性的控制。相反,她敢于反抗,甚至可以控制男性的命運。女巫這一女性人物的塑造充分體現了卡特鮮明的女性主義觀點。
故事中的第二個新女性是一個年輕女性。在其新婚當晚,她的丈夫“為了體面”[6]堅持要求出去小便,從此消失不見。這里,通常被賦予為傳統女性特征之一的靦腆羞澀被轉到了男性身上。當她意識到她的丈夫不會再回來之后,這個“明智的”女孩擦干眼淚,另嫁他人,過著平靜的生活。然而一天,她的第一個丈夫變成狼人回來了。了解情形之后,這個狼人甚為憤怒,很快變成狼形,想要“給這個娼婦一個教訓”[6]。他咬掉了女人大兒子的一條腿,但這個女人在其第二個丈夫的幫助下,迅速地用斧頭殺死了狼人。這里,女性不再消極等待失蹤的丈夫,而是積極追求自己的幸福。面對男性的壓制,她也不再一味地順從,而是敢于反抗。所有這些都是對女性必須以男性為中心的傳統觀念的反抗。
故事中這一類新女性最為重要的代表是故事的主人公——小女孩。在卡特的改寫之下,小女孩被賦予了一些新的特點,以傳達作者的女性主義觀。首先,不再像傳統童話故事中的小女孩那般幼稚,卡特版的小女孩頗有主見,勇敢而機敏。佩羅版和格林版的《小紅帽》中,均是小女孩的母親讓小女孩去看望外婆。但在 《與狼為伴》中,小女孩自己堅持要求去看望外婆,她隨身帶著刀具作為防范,“確信野獸傷害不了她”[6]。到達外婆的住處時,她很快就發現獵人其實是狼人并意識到自己處于危險之中。但她臨危不懼,“因為害怕幫不了她”[6]。當狼人說他有巨大而尖銳的牙齒,可以吃掉她的時候,“她大笑,相信自己不會是任何人的盤中餐。她盯著他的臉大笑,脫掉了他的衣服,將之扔進火中”[6]。其次,卡特版的小女孩主動追求愛情,不再像傳統女性那般被動。初次遇見幻化成年輕而帥氣的獵人的狼人的時候,小女孩被他深深地吸引,“她從未見過長得如此俊俏的男子”[6]。與之同行的時候,小女孩一點也不害怕。他們開著玩笑,一路歡聲笑語。她把裝著刀的籃子交給了狼人,甚至故意在路上閑蕩以保證狼人贏得自己的一吻。當她到達外婆家,看到火爐邊只有外婆一人的時候,她甚至有些失望。因此,卡特版的小女孩不再羞怯被動。相反,她是一個思想解放了的新女性,能夠勇敢地表達和追求自己的愛情。當意識到自己處于危險之中,她鎮定自若,表現得極為主動。她脫掉了自己的衣服,將母親和外婆為她織的紅圍巾扔進火爐中。“她自如地吻著他”,并“替他解開了襯衫的衣領”[6]。這些動作都象征著小女孩徹底擺脫傳統束縛,積極爭取自由。此外,小女孩的童貞和青春期由原來的不利條件變成了有利條件。她剛剛成熟到可以成為一個女人,剛剛開始行經,是“一顆未破的卵,一個密封的容器……她有一把刀,她不害怕任何事情”[6]。童貞給了小女孩力量,因為“只有純潔的肉體才能安撫他”[6]。憑借其性吸引力,她成功地將兇惡的狼人馴服。根據故事第一部分的暗示,小女孩將狼人的襯衣扔進火中這一動作可以讓狼人永遠地保持狼形。而在故事的結尾,小女孩“甜蜜地沉睡在外婆的床上,在狼溫柔的腳掌之間”[6],對外婆的尸體發出的嗒嗒作響之聲恍若未聞。在傳統的父權文化之下,性被視為一種禁忌。但在《與狼為伴》中,性不再是一件需要隱藏的罪惡之事。相反,它成為了女性的一種優勢,女性借之使自己強大。卡特對小女孩性欲的自由描寫及其對之在性愛中占主導地位以及性作為一種挽救小女孩生命的優勢力量的安排均是其鮮明的女性主義觀點的體現。
簡言之,卡特在《與狼為伴》中刻畫了一類強大、覺醒而解放了的新女性。她們能夠用自己的力量贏取生命、追求幸福,與故事中順從、軟弱的傳統女性形成鮮明對比。她們最終的成功表明了卡特鮮明的女性主義思想。值得注意的是,卡特所倡導的并不是男性與女性的完全對立。在小說結尾處,兇惡的狼變得溫柔,小女孩也可甜蜜地與之共眠,所有的沖突以和諧結尾。此外,狼人的生日是圣誕節前夜,因此小說結尾處圣誕節前夜的時間設置可視作狼人新生的預示。小說開放的結局表明卡特所倡導的是和諧的兩性關系,這也正與小說的標題——《與狼為伴》相吻合。“卡特的女性主義觀是基于廣泛的童話故事和辛辣的諷刺之下的理性之上的”[11]。
4 結語
通過以上對《與狼為伴》中兩類女性人物不同命運的分析可以看出,卡特在其對童話故事進行改寫的過程中注入了自己的女性主義觀點。“在她全新的故事中,她批判了以男性為中心的價值觀和傳統的倫理道德,加入了許多值得注意的細節”[12]。她看出了父權文化影響之下西方許多童話故事中存在的對女性的偏見,并試圖加以修正。在《與狼為伴》中,她成功地塑造了兩類女性人物,進而傳達了她的女性主義觀點。那些順從和恪守傳統價值觀的傳統女性終究不能改變她們受害者的命運。在充滿危險的世界中,她們無法得以存活。而那些敢于用自己的力量贏取生命、追求幸福的新女性則成功地為自己爭取了生命和權利。通過改寫,卡特傳達出這樣一種觀點,即面對社會的不公和他人的摧殘,女性不應消極地等待滅亡或是他人的救贖,而應拿起武器,拯救自己。只有依靠自己,女性才能改變自己的命運,逃離壓迫者的欺凌。與此同時,卡特并不宣揚兩性的完全對立或是絕對的女性霸權,她倡導的是和諧的兩性關系。這也正是卡特在對童話故事進行改寫過程中的獨特和發人深省之處。
[1]田祥斌.安吉拉·卡特現代童話的魅力[J].外國文學研究,2004,(6):20.
[2]張帆.從童話故事《小紅帽》看女性形象在歷史中的發展和演變[J].遼寧科技大學學報,2012,(2):223.
[3]Simone de Beauvoir.The Second Sex[M].New York:Knopf,1953:144.
[4]Sanders,Andrew.The Short Oxford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616.
[5]張中載.二十世紀英國文學:小說研究[M].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1:405.
[6]Gilbert,M.Sandra&Gubar,Susan.The Norton Anthology of Literature by Women:The Tradition in England[M].New York:W.W.Norton&Company Ltd.,1985:2327、2326、2327、2327、2327、2327、2331、2332、2328、2328、2329、2329、2333、2334、2330、2334、2330、2334、2334.
[7]呂芳慧,呂海峰.西方童話中女性形象的演變[J].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學報,2007,(4):33.
[8]Swyt,Wendy.“Wolfings”:Angela Carter's Becoming-Narrative[J].Studies in Short Fiction,1996,(33):319.
[9]武田田.生態女性主義思潮中的溫馨小品——論《與狼為伴》中的兩性欲望與自然之關系[J].北京林業大學學報,2010,(4):119.
[10]王虹.隱喻、道德與童話新編——評安吉拉·卡特的新編童話《與狼為伴》[J].四川外語學院學報,2000,(2):26.
[11]Day,Aidan.Angela Carter:The Rational Glass[M].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8:12.
[12]王卉,姚振軍.論《與狼為伴》的互文性[J].大連海事大學學報,2009,(6):132.
I106.4
A
1672-2868(2015)01-0144-04
2014-12-06
林鴻(1988-),女,安徽六安人。安徽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學。
楊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