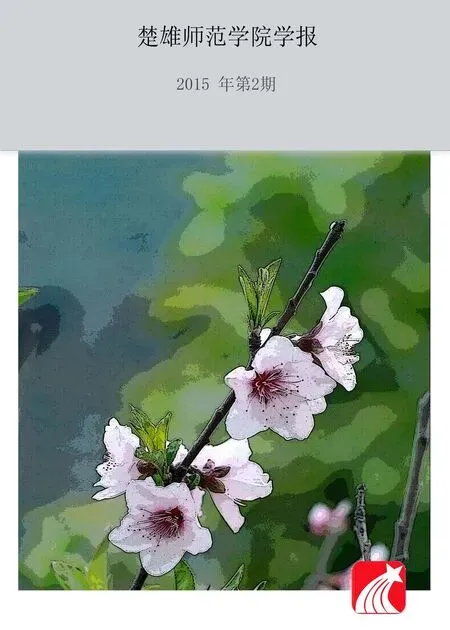“夢(mèng)”與“病”的雙重交構(gòu):《吶喊·自序》思想內(nèi)涵再解讀
孫擁軍,馬建榮
(河南理工大學(xué),河南 焦作 454000;楚雄師范學(xué)院,云南 楚雄 675000)
《吶喊·自序》是魯迅在1922年為其第一部小說(shuō)集《吶喊》所寫的一篇序言。多年來(lái),從事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的學(xué)者們過(guò)多地將視角關(guān)注于這部小說(shuō)集的研讀與解析,關(guān)注于小說(shuō)集中的作品之于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的價(jià)值和意義,以及這部小說(shuō)集對(duì)于中國(guó)現(xiàn)代小說(shuō)的發(fā)展在思想與內(nèi)容上的開創(chuàng)性。而很少去思索這篇簡(jiǎn)短精悍的序言對(duì)于這部小說(shuō)集的整體價(jià)值,以及它在研究者探究魯迅思想體系形成時(shí)所給予的史料學(xué)價(jià)值。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致使這篇序言的真正價(jià)值和意義還無(wú)法全面呈現(xiàn),從而成為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研究史上的缺憾。本文試通過(guò)對(duì)這篇序言的再度解讀,重新探討魯迅前期思想體系的發(fā)展歷程,呈現(xiàn)出這篇序言之于《吶喊》以及魯迅其他作品的史料學(xué)價(jià)值,為研究者更深入的研究提供借鑒,以豐富和完善魯迅學(xué)的研究。
一
在這篇被魯迅研究大家錢理群先生譽(yù)為“解讀魯迅小說(shuō)的一把鑰匙”[1](P138)的序言中,魯迅先生以舊事重提的方式記述了青少年時(shí)代的坎坷人生經(jīng)歷,以及他從實(shí)業(yè)救國(guó)走上文學(xué)啟蒙道路的曲折心路歷程,并較為清晰地勾勒出其前期思想的發(fā)展脈絡(luò)。
魯迅先生開篇詳細(xì)講述了他和文學(xué)結(jié)緣的偶然性,在一次次對(duì)自己的理想的質(zhì)疑、否定與重構(gòu)中,最終由醫(yī)學(xué)實(shí)業(yè)救國(guó)走上文學(xué)啟蒙之路。從魯迅先生人生經(jīng)歷的表述,我們?cè)谶M(jìn)行其早期思想形成歷程研究時(shí),不難看出他走上文學(xué)啟蒙道路似乎出于偶然,那就是其在日本仙臺(tái)醫(yī)學(xué)專修學(xué)院學(xué)習(xí)期間,由于受到在課堂上所放映的時(shí)事幻燈片的深刻影響。當(dāng)看到久違的中國(guó)同胞在日俄戰(zhàn)爭(zhēng)中因做俄國(guó)人的間諜,被日本軍人抓住殺頭示眾的場(chǎng)景時(shí),魯迅深感“醫(yī)學(xué)并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guó)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wú)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擁有健壯體格而靈魂麻木的國(guó)民是中華民族最大的不幸與悲哀。“幻燈片事件”促使魯迅先生重新思索自我的人生之路,再度思考中華民族危在旦夕的命運(yùn)和前途,最終,魯迅先生毅然放棄了自己原本實(shí)業(yè)救國(guó)的人生理想而走上文學(xué)啟蒙之路。正如其所言:“我的夢(mèng)很美滿,預(yù)備卒業(yè)回來(lái),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戰(zhàn)爭(zhēng)時(shí)候便去當(dāng)軍醫(yī),一面又促進(jìn)了國(guó)人對(duì)于維新的信仰。”最后他放棄了對(duì)醫(yī)學(xué)的追求,離開仙臺(tái)到東京開展文藝運(yùn)動(dòng),利用文藝來(lái)啟蒙和拯救精神麻木的愚昧國(guó)民。因而,從這一視角出發(fā),研究者視乎可以說(shuō)魯迅的棄醫(yī)從文、開展文學(xué)啟蒙運(yùn)動(dòng)是出于偶然。
其實(shí),從魯迅先生的自述來(lái)看,我們可以感悟到其與文學(xué)的結(jié)緣看似偶然,但在偶然中也蘊(yùn)含著一種必然。正如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史上第一位魯迅批評(píng)家李長(zhǎng)之所說(shuō):“在這種視乎神秘意味之下,我們又見到魯迅。他學(xué)過(guò)醫(yī),可是終于弄到文學(xué)上來(lái)了;他身從小康之家而墜入困頓,他生長(zhǎng)于代表著中國(guó)一般的執(zhí)拗的農(nóng)民性的魯鎮(zhèn),這視乎都是偶然的,然而這卻在影響了、形成了他的思想、性格和文藝作品。”[2](P2)在序言中,魯迅先生開篇就敘述了其家族“從小康人家墜入困頓”這段不堪回首的經(jīng)歷,它給魯迅先生的人生帶來(lái)了至為深遠(yuǎn)的影響。
魯迅家道中落源于其祖父周福清的科考舞弊事件,因遭人告發(fā),祖父被下監(jiān)蘇州,家族財(cái)產(chǎn)數(shù)次被抄。又加上魯迅的父親周伯夷也因此事重病臥床,年幼的魯迅不得不每天往返于質(zhì)鋪與藥店之間,使其在家道的變故中,看到了世人的真面目和世態(tài)炎涼。如其所說(shuō):“我有四年多,曾經(jīng)常常,——幾乎是每天,出入于質(zhì)鋪和藥店里,年紀(jì)可是忘卻了,總之是藥店的柜臺(tái)正和我一樣高,質(zhì)鋪的是比我高一倍,我從一倍高的柜臺(tái)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在侮蔑里接了錢,再到一樣高的柜臺(tái)上給我久病的父親去買藥。”家族環(huán)境的變化給魯迅帶來(lái)深刻的影響,使魯迅在思想深處不得不用新的視角來(lái)思索自我的人生歷程。
由于科考舞弊事件,周家多次被查抄,魯迅的母親也因此經(jīng)常帶著魯迅兄弟到鄉(xiāng)下去避難。在這避難的經(jīng)歷中,魯迅有機(jī)會(huì)接觸到社會(huì)最底層的農(nóng)民,感觸到農(nóng)民的生命體驗(yàn)和生活歷程,從而成為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史上第一位最了解農(nóng)民的作家。他看到生活在宗法制鄉(xiāng)土中國(guó)的農(nóng)民所受的非人苦難和難以言表的人性摧殘,同時(shí)也看到了數(shù)千年來(lái)封建倫理給農(nóng)民思想深處帶來(lái)的種種難以剔除的民族劣根與陋病。這些青少年時(shí)期的人生經(jīng)歷和生存感悟,都成為魯迅進(jìn)行文學(xué)創(chuàng)作時(shí)取之不盡的源泉。
二
從魯迅對(duì)生活瑣事的講述中,研究者不難看出這篇序言的兩個(gè)關(guān)鍵詞:“夢(mèng)”和“病”。它們貫穿始終,并且魯迅先生早期思想體系的形成也與這兩個(gè)關(guān)鍵詞息息相關(guān)。
《吶喊·自序》開篇,魯迅先生就寫到“我在年青時(shí)候也曾經(jīng)做過(guò)許多夢(mèng),后來(lái)大半忘卻了,但自己也并不以為可惜。”接著,依次敘述了其青少年時(shí)期歷經(jīng)的多次夢(mèng)想的破滅與重新燃起希望的過(guò)程。魯迅在其家道中落以前,也曾經(jīng)和當(dāng)時(shí)的讀書人一樣有著科舉應(yīng)試的夢(mèng)想,期待有朝一日金榜題名,光宗耀祖。但由于家道的變故,使其走科舉應(yīng)試這條人生之路成為一種奢望,而且由于家道的徹底中落,致使他繼續(xù)完成學(xué)業(yè)都成為問(wèn)題。因而,魯迅最終無(wú)奈選擇了與當(dāng)時(shí)讀書人相異的一條人生之路:“我要到N進(jìn)K學(xué)堂去了,仿佛是想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這是一條被人稱之為與科舉制度相異的道路,“因?yàn)槟菚r(shí)讀書應(yīng)試是正路,所謂學(xué)洋務(wù),社會(huì)上便以為是一種走投無(wú)路的人,只得將靈魂賣給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
魯迅先生在科舉應(yīng)試?yán)硐肫茰绾螅衷诮^境中重新燃起新的人生夢(mèng)想,誠(chéng)然,這條學(xué)洋務(wù)之路也是魯迅人生夢(mèng)想中最無(wú)奈的選擇。家道的中落,生活的窘迫與拮據(jù),已經(jīng)讓其別無(wú)選擇。魯迅的母親變賣了首飾,“辦了八元的川資”,讓魯迅去礦務(wù)學(xué)堂讀洋務(wù)。在南京讀書期間,魯迅接觸到與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不同的西方文化,使其思想發(fā)生深刻的轉(zhuǎn)變,原本完成學(xué)業(yè)的夢(mèng)想又再一次被更改。正如魯迅在《吶喊·自序》里所說(shuō):“在這學(xué)堂里,我才知道世上還有所謂格致,算學(xué),地理,歷史,繪圖和體操。我還記得先前的醫(yī)生的議論和方藥,和現(xiàn)在所知道的比較起來(lái),便漸漸的悟得中醫(yī)不過(guò)是一種有意的或無(wú)意的騙子,同時(shí)又很起了對(duì)于被騙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從譯出的歷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維新是大半發(fā)端于西方醫(yī)學(xué)的事實(shí)。”魯迅的人生之夢(mèng)再次由完成學(xué)業(yè)轉(zhuǎn)變?yōu)閷?shí)業(yè)救國(guó),他要學(xué)習(xí)醫(yī)學(xué),救治像父親一樣的病態(tài)軀體。從這段文字的表述中,不難看出魯迅對(duì)其實(shí)業(yè)救國(guó)的夢(mèng)想有著完美的憧憬。然而,由于仙臺(tái)“幻燈片事件”,魯迅先生不得不再次修正自己的人生理想,最終走上文學(xué)啟蒙之路。由此看來(lái),魯迅先生早期人生之路充滿著很多的夢(mèng)想,在其人生的變故和不平凡的經(jīng)歷中,他不斷修正著自我的人生方向,最終將自我的人生夢(mèng)想與中華民族的前途與命運(yùn)緊緊連在一起,構(gòu)建起早期的思想體系。
在文學(xué)啟蒙的道路上,魯迅夢(mèng)想的實(shí)現(xiàn)也至為艱難。魯迅離開仙臺(tái)到東京開始文藝運(yùn)動(dòng),他邀約幾個(gè)文學(xué)同仁共同創(chuàng)辦《新生》雜志,想以文學(xué)的形式喚醒處于精神麻木的愚昧國(guó)民,對(duì)他們進(jìn)行啟蒙與拯救。而在當(dāng)時(shí)眾多的晚清留學(xué)生中,卻難以找到幾個(gè)從事文學(xué)的同仁,大多數(shù)留學(xué)生都抱著實(shí)業(yè)救國(guó)的理想,選擇實(shí)用學(xué)科“師夷長(zhǎng)技以制夷”。在這種狀況下,魯迅還是找到幾個(gè)有著文學(xué)理想的同仁,開展文學(xué)啟蒙運(yùn)動(dòng),但最終因?yàn)椤疤幼吡速Y本”而使《新生》雜志夭折。這場(chǎng)文學(xué)啟蒙運(yùn)動(dòng)的經(jīng)歷,使魯迅深感在中國(guó)進(jìn)行文學(xué)啟蒙運(yùn)動(dòng)的艱難,以及個(gè)人內(nèi)心深處的無(wú)比寂寞與孤單。但他還是繼續(xù)堅(jiān)持自我的人生理想,堅(jiān)定了自我的文學(xué)信念,與其弟周作人再度開展文學(xué)啟蒙運(yùn)動(dòng),進(jìn)行翻譯活動(dòng),合譯《域外小說(shuō)集》。從日本回國(guó)后,雖然沉寂近十年,應(yīng)《新青年》雜志的約稿,他創(chuàng)作了從1918年的《狂人日記》到1922年的《社戲》共十四篇小說(shuō),集結(jié)成《吶喊》小說(shuō)集,重新走上以“國(guó)民性批判與改造”為核心的文學(xué)啟蒙之路。魯迅以“吶喊”為其第一部小說(shuō)集命名,以期喚醒沉睡在“鐵屋子”里面的麻木國(guó)民的靈魂,“創(chuàng)造這中國(guó)歷史上未曾有過(guò)的第三樣時(shí)代”,[3](P212)創(chuàng)造中華民族新的希望。同時(shí),給革命的啟蒙先驅(qū)以精神的慰藉和勇氣,堅(jiān)定他們勇往直前的不朽信念。在一次次受挫過(guò)程中,魯迅不斷對(duì)自我的人生夢(mèng)想進(jìn)行苦苦思索,不斷進(jìn)行自我的追問(wèn)與反省,最終建構(gòu)起以“國(guó)民性批判與改造”為核心的“人學(xué)”思想體系,完善著自我對(duì)中華民族最美人性的追尋。
在這篇序言中,魯迅先生重復(fù)敘述著另外一個(gè)關(guān)鍵詞——病。魯迅從自己父親的病談起,對(duì)庸醫(yī)誤人的經(jīng)歷刻骨銘心,認(rèn)為他們不僅無(wú)法消除病人的肉體痛苦,而且還給病者家人帶來(lái)精神創(chuàng)傷。 《吶喊》中的兩篇小說(shuō)《藥》、《明天》,描寫了喪子之痛給兩個(gè)家庭帶來(lái)了巨大的創(chuàng)傷,當(dāng)魯迅先生在進(jìn)行國(guó)民性批判的同時(shí),我們也可以感受到他對(duì)庸醫(yī)誤人的無(wú)比憎恨,這與其早年的人生經(jīng)歷有著極大的淵源。但給魯迅帶來(lái)最深刻人生思索的還不是國(guó)民肉體之痛,而是數(shù)千年來(lái)生活在封建宗法制度下國(guó)民病態(tài)的靈魂。對(duì)于《吶喊》這部小說(shuō)集里的人物,魯迅曾說(shuō)小說(shuō)的取材“多來(lái)自病態(tài)的社會(huì)的不幸的人們,意思是揭出痛苦,引起療救的注意”。[4](P512)阿 Q、七斤、華老栓、閏土、單四嫂、孔乙己、陳士成……這群思想愚昧、精神麻木、滿身陋病的舊中國(guó)國(guó)民,似乎從久遠(yuǎn)的歷史中向我們走來(lái),他們備受封建思想的毒害而毫無(wú)覺醒,魯迅正是在“哀其不幸,怒其不爭(zhēng)”的同時(shí),以文學(xué)的啟蒙喚醒這些沉睡中的愚弱國(guó)民的魂靈,探求著中華民族未來(lái)的脊梁。然而,魯迅對(duì)病態(tài)國(guó)民的啟蒙之路至為艱難,尤其是數(shù)次啟蒙后,這些國(guó)民仍然表現(xiàn)出的“靈魂的沉默”,讓魯迅深感國(guó)民精神之病比肉體之病更可怕。因此,魯迅在其作品中,也清醒地認(rèn)識(shí)到對(duì)這些民眾思想啟蒙的艱難性和復(fù)雜性,要徹底改變愚昧民眾的思想并非一日之功,在對(duì)國(guó)民啟蒙的絕望中,他自身也進(jìn)行著痛苦的思索與反省。《吶喊》中的幾多篇章都體現(xiàn)著魯迅對(duì)其文學(xué)啟蒙運(yùn)動(dòng)的自我矛盾與自我質(zhì)疑。如在《藥》中,革命者夏瑜對(duì)獄卒紅眼睛阿義進(jìn)行啟蒙時(shí),我們難以忘卻阿義“這大清的天下是我們大家的。這是人話么?”的經(jīng)典叫喊;在《故鄉(xiāng)》中,魯迅要搬家進(jìn)城離開紹興去北京,讓童年的好友閏土來(lái)挑揀些需要的物品,閏土選擇了“一副香爐和燭臺(tái)”以及可以做沙地肥料的“所有草木灰”。閏土的這些選擇使魯迅深深體味到現(xiàn)代知識(shí)分子對(duì)民眾啟蒙的艱難,以及啟蒙者與被啟蒙者之間在內(nèi)心深處的巨大隔閡,魯迅試圖用自我的吶喊,喚醒閏土等這些沉睡中麻木國(guó)民的靈魂,催其走向新生。然而,閏土對(duì)魯迅不理解,他把希望寄托在神靈的佑護(hù)中,以期來(lái)年取得好的收成。從這一視角而言,魯迅以及“五四”時(shí)期的知識(shí)分子對(duì)民眾的啟蒙并沒有獲得民眾的真正理解,對(duì)民眾的啟蒙其實(shí)是知識(shí)分子實(shí)現(xiàn)了自我的啟蒙,無(wú)奈中他們發(fā)出“救救孩子”的呼聲,哀嘆這群“暫時(shí)坐穩(wěn)了奴隸”[3](P212)的人們。在這一層面上,我們看到魯迅這一代“五四”知識(shí)分子對(duì)民眾啟蒙道路的無(wú)奈與無(wú)助,他們只能寄托于將來(lái)的知識(shí)者完成這一歷史使命。
三
魯迅的《吶喊·自序》,給研究者“提供了一個(gè)窺視魯迅內(nèi)心世界的難得機(jī)會(huì),一條魯迅精神發(fā)展的明晰線索。”[1](P139)研究者在探求魯迅早期思想體系發(fā)展歷程的同時(shí),探究出他畢生孜孜不倦地進(jìn)行國(guó)民性批判與改造的真正原因。魯迅以文學(xué)為工具對(duì)民眾進(jìn)行啟蒙,總是將他的筆觸聚焦于愚弱國(guó)民的靈魂深處,力求改變國(guó)民麻木的精神狀態(tài)和思想深處的愚昧,喚醒沉睡在宗法制中國(guó)病態(tài)社會(huì)—— “鐵屋子”里的沉默靈魂,洗滌、去除數(shù)千年來(lái)滯留于國(guó)民內(nèi)心深處的封建思想,使他們成為精神和思想健全的人,也就是魯迅先生所說(shuō)的未來(lái)“民族的脊梁”。
據(jù)魯迅好友許壽裳在其回憶錄中記述,魯迅在日本弘文學(xué)院學(xué)習(xí)期間已經(jīng)開始思索國(guó)民性改造問(wèn)題,那時(shí)魯迅就常和他談起這樣三個(gè)互相聯(lián)系的問(wèn)題:一、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國(guó)國(guó)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5](P39)由此而言,什么是“理想的人性”,這不僅是魯迅對(duì)中國(guó)國(guó)民性問(wèn)題整體思考中的一個(gè)有機(jī)部分,而且也是其畢生進(jìn)行國(guó)民性批判的最終追尋目標(biāo)。正如他在《中國(guó)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一文中所說(shuō):“我們從古以來(lái),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qǐng)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guó)的脊梁。”[6](P226)為了這一歷史使命,文學(xué)啟蒙之路雖然艱難,面對(duì)國(guó)民“沉默的靈魂”,魯迅并沒有減弱國(guó)民拯救意識(shí),他堅(jiān)信“就許有若干人要沉默,沉默而痛苦,然而新的生命就會(huì)在這苦痛的沉默里萌芽。”[7](P205)因而,其一如既往地堅(jiān)持自我的文學(xué)啟蒙之路,探求著中華民族的未來(lái)。
總之,通過(guò)對(duì)這篇序言的解析,我們可以感受到魯迅坎坷的人生經(jīng)歷,不斷隨時(shí)代、環(huán)境而變更的夢(mèng)想。在感受生存的尊嚴(yán)與人生奮進(jìn)的歷程中,魯迅精神一直充滿著反抗與思索,對(duì)民族生存有著濃重的憂患意識(shí),對(duì)社會(huì)變革抱著強(qiáng)烈的渴望。因而,要真正領(lǐng)悟到魯迅先生憂憤深廣的思想體系,就必須從這篇序言入手,以給予研究者更深層次的不懈思索。
[1]錢理群.走進(jìn)當(dāng)代的魯迅 [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9.
[2]李長(zhǎng)之.魯迅批判 [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
[3]魯迅.魯迅全集:第1卷 [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1.
[4]魯迅.魯迅全集:第4卷 [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1.
[5]許壽裳.回憶魯迅 [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1.
[6]魯迅.魯迅全集:第6卷 [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1.
[7]魯迅.魯迅全集:第3卷 [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