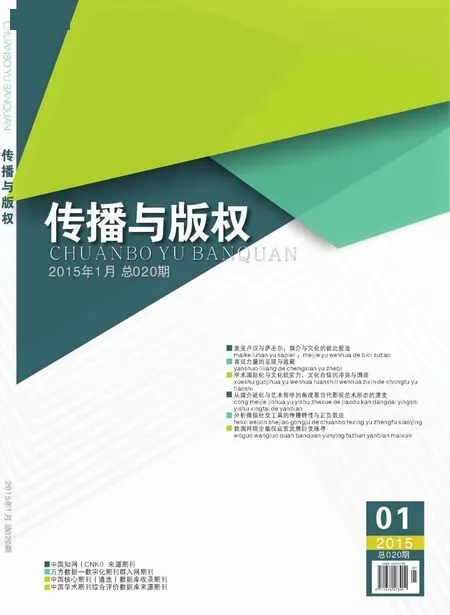虛擬生存中人的異化和主體性喪失
何 睿
虛擬生存中人的異化和主體性喪失
何 睿
[摘 要]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虛擬生存成為一種重要的生存方式,網絡在給人們帶來便利的同時也改變了人們傳統的生存方式。長期虛擬生存造成了人的異化、主體性的喪失。本文以虛擬生存的表象出發,剖析虛擬導致異化的深層原因,并對此提出合理化建議。
[關鍵詞]網絡;虛擬生存;異化;信息
[作 者]何睿,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研究生。
互聯網營造了虛擬空間,人類因此而誕生出一種虛擬的網絡生存方式。麥克盧漢曾說“媒介是人身體的延伸”,網絡幾乎成為身體的一部分,代替人們看、聽、說,甚至影響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虛擬化的生存方式正前所未有地挑戰傳統的生存方式。原本應該給人帶來便利的網絡是否束縛了人本身?看著人們甘愿將自己的時間和精力放在網絡世界中,醉心于網絡絢麗的幻境,大批的“網絡土豆”因此產生的時候,我們是否應該反思?
一
與傳統的三種存在形式不同,虛擬存在是基于虛擬空間而非現實環境的個體活動的總和,其顯著特點便是身體的嚴重“不在場”。這種精神與肉體分離的狀態在虛擬世界中普遍存在著,網絡數字技術將人腦對信息的加工和反饋的速度提高到一種極高的速度,人的行為似乎已無法控制,當身體處于一種靜止或者長期靜止的狀態時,思維的交感神經卻是高度活躍。大腦甚至可以在任何一個需要的時候“浮”出軀體,去索取和反饋信息。這便是虛擬的生存,身體對于交往的重要性微乎其微,甚至還成為思維的阻礙,肉體與精神不再是相融的一元狀態,而是相分離的二元狀態。此外,對身體缺位的另一種理解,則是虛擬語境中身體的不在場。日常交流中,身體的參與是維持連貫的自我認同的基本途徑①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第111頁。,身體缺位的互動,則必然是以一種虛擬的身份交流。按照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的人格構成理論,虛擬語境則是抽離了人用以規范“本我”的“自我”和“超我”,在現實中被嚴重壓抑的“本我”,在被放之于自由,在虛擬的生存中經歷了人格的斷裂。
另一方面,虛擬生存的繁榮勢必對現實生存造成巨大的沖擊,在虛擬生存的“擠壓”下,對現實認知的扭曲在所難免。馬克思在其認識論中指出,人認識世界的途徑有直接和間接兩種,即通過自己的實踐和他人傳授或閱讀書籍等了解世界。賽博空間所提供的虛擬實踐無疑將作為現實實踐的補充和延伸,它降低了實踐的成本,提高了效率且過程更具互動性,在這樣的優勢下,人們日漸依賴于網絡,這使得一些人逐漸喪失了在虛擬與現實之間轉換的能力與意愿。然而任何人都無法脫離現實的生存,虛擬與現實邏輯、秩序的不同,以及自身在兩個世界中的反差,使人內心產生巨大的壓力。
毫無疑問,網絡世界被廣泛地認為是一個相對自由的空間,在虛擬世界中可以暢所欲言。網絡給我們提供了更多的選擇,更鮮有現實中那些規則和制度,然而是否僅憑一個虛擬的身份就可以獲得自由?非也。信息的不對稱在網絡環境下不但沒有減小反而增大,媒介相對于受眾,更接近信息源,掌握更多的信息。在傳播的過程中,媒介先將信息進行篩選,有選擇性地傳播,而后才是受眾“按需接受”,受眾的所謂自由選擇只不過是具有微觀上的主動,媒介作為“把關人”的地位并未改變。正是由于傳授關系的失衡,網絡表面所呈現的“言論自由”其實質不過是“把關人”的話語霸權。一方面,受眾接觸信息幾乎通過媒介,進而按照媒介所給定的框架那樣思維;另一方面,雖然媒介意見多是以眾人的口吻出現,但有時事實并非如此。網絡輿論霸權的環境下,人們無法得到相應的話語平臺和權威形象,言論自由更無從談起。此外,有學者做過調查,媒介對輿論議程設置的影響在網絡環境下依然存在,網絡也許不能控制網民們如何思維,但很大程度上可以決定他們想些什么。
二
馬克思將人的屬性歸為社會屬性、自然屬性和精
神屬性,相應地構成了人的社會存在、自然(物質)存在和精神存在。然而在數字化時代的今天,人的存在方式正面臨著種種變革甚至是顛覆。虛擬存在已經成為以上三種傳統的存在方式以外的第四種,滲透在學習、生活、工作等種種領域,成為人們一種重要的生活甚至生存方式。尼葛洛龐帝曾在《數字化生存》中這樣寫道“計算不再只和計算機有關,它決定了我們的生存方式”。網絡作為繼電視之后的第五大媒介,其本身不過只是一種信息工具或者內容載體。但就其工具的本質而言,僅憑這些優越性能也很難讓使用者們為之著迷,甚至沉溺其中。然而,又是什么使人在虛擬生存中喪失了主體性甚至被異化,卻不以為然?透過表象,也許可以找到深藏在其背后的癥結所在。
科技的進步和經濟的發展使世界變成了一個“地球村”,同時也步入了消費社會。網絡成為商業重地,虛擬與現實的市場不謀而合。網絡為大眾提供了交際、娛樂、購物的平臺,改變了人們的消費文化生活方式。大眾傳媒與消費社會緊密相連,網絡已成為當今消費體系中最為重要的一部分,不僅充斥著商業廣告來刺激消費,而且將所提供的娛樂、社交、通訊變成商業項目,一步一步把網絡文化打造成商品,并且以商業運作的方式指導著文化的走向。在過去的二十年間,網絡已由供少數人消費的媒介變成了大眾媒介,引領著社會的消費文化,同時不斷刺激著人們的欲望,一遍遍的網頁刷新、視頻下載、QQ通訊……人們在享受網絡信息的同時,已經被打包賣給了廣告商。①張品良:《網絡文化傳播》,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因此,對于運作網絡的資本來說,只有將更多人的“大腦”拖到網絡的虛擬世界中,并且停留更長的時間,才有可能獲得更多的利潤,為此,資本不惜成本的將虛擬世界營造得更加豐富絢爛,以培養更多的潛在消費者,甚至視法律與道德于不顧。
然而,簡單地指責網絡甚至資本的不負責任是不公平的,對生活在都市中的個體來說,需要一個能夠自我宣泄的場合,網絡的出現正好成為他們逃離現實的方式。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曾對130位美國青少年進行跟蹤調查。結果表明美國的孩子大多不經常上網,他們不迷戀網絡。有的孩子說,既然我們有父母、兄弟姐妹,還有那么多朋友,跟他們聊天都覺得時間不夠,為什么還要在網上和一個陌生人聊天呢?②王德峰:《網絡的虛擬性可以造成異化》,《上海教育》,2006年Z2期,第52-53頁。相較而言,性格與生活經歷有欠缺的個體在面對網絡的誘惑時更易“上鉤”。與之相反,據調查顯示,我國青少年網癮比例達到13.2%,他們長期沉迷于虛擬世界,借此逃避現實世界,離開網絡后又陷入深深的不安,于是陷入了“逃避——沉溺——進一步逃避”的惡性循環,這正體現了他們精神世界的不完整。③樊葵:《媒介崇拜》,中國傳媒出版社,2008年,第23頁。在分析那些每日沉迷于虛擬世界的人的“病因”時也許應該審視一下,他們在現實生活中是不是出了什么問題,以至于需要逃到網絡中去尋求補償。
除了上述資本與人性的因素外,社會文化導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人對網絡的崇拜。隨著“信息時代”被廣泛認同,信息被社會和媒體賦予了過多的意義,其內涵變得廣泛而模糊,原本作為內容載體的信息被片面地誤認為是觀念、經驗甚至知識。西方的經驗主義認為,感覺和經驗是人認識外部世界的唯一途徑,培根的所謂“知識就是力量”,正是說知識來源于經驗事實。時至今日,信息被泛化的曲解,替代了事實經驗而成為人們認知世界探索真理的起點,對事實的重視變成了對信息的追逐。此外,同為西方哲學科學重要理論基礎的理性主義,也與信息崇拜不期而遇。理性主義認為,經驗是個性的,不可靠的,是會導致謬誤的。笛卡爾曾說“我思故我在”,認為人清楚明白的觀念是天賦的,具有普遍性和自然性的。對于理性觀念,理性主義者們都認為理性是分辨和達到真理的唯一途徑。然而,當信息被等同于觀念、思想,人們對信息的崇拜便取代了對理性的敬仰。20世紀中期以來,信息技術飛速發展,然而人腦對于信息的識別和思考能力卻沒有相應增長,面對如潮的信息,人們能做的只有機械地收集、記憶,根本來不及思考,計算機似乎比人腦更能從容應對潮流。信息的高速生產和傳播刺激著人們對信息的需求,似乎更多的信息意味著更豐富的思維材料、更可靠的結果,對海量信息的形式上占有成了每個“在線族”最重要的事,不斷地查看郵箱、通訊錄,每一條信息的遺漏都會對其帶來不同程度的焦慮感。網絡的存在無限放大了信息的能量,人的客體化和信息的主題化增加了人們的“被奴役”,對信息的崇拜必然導致對信息機器的過分依賴。④李紅梅:《網絡虛擬性對人的全面發展的阻抗》,《蘭州學刊》,2009年第11期,第62-64頁。
三
隨著網絡的普及,其危害和問題也越來越多,然而我們不能“因噎廢食”。在這場人與機器,現實與虛擬的博弈中,我們如何做到保持自身主體性的完整,這需要政府、社會和我們受眾自身的多方努力。
一是健全適用于網絡的法律制度。政府作為一個國家的管理者,應該宏觀的從法律的角度規范網絡中的“生存”模式,從形式上縮小虛擬與現實的區別。虛擬生存較之于現實生存,更加“無限”與“無序”,然而網絡世界也是人們生活的一部分,參與其中的主體也是現實中的個體,因此也需要法律的規范與約束,具體而
言,政府可以對網絡媒介的各個環節進行監督,一方面積極地管理和引導;另一方面干預其財政和干部任免,進行強制管理。
二是社會主流文化的理性回歸。人之所以為人,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人具有社會屬性,社會對人的影響從始至終,科技的急劇變革使得社會的觀念發生扭曲,社會有責任使其主流文化回歸理性,注重人格的完整性,追求知識和真理。另外,應該建立起正確的真實與虛擬的關系。一方面不能以現實打壓虛擬,另一方面更不能以虛擬消解現實。虛擬應該是以現實為基礎,是現實的延伸和補充。
三是媒介素養的加強。作為個體,加強自身的認識和判斷能力,才是抵御異化的最有效方法。想要游刃于虛擬和現實,則需要具有一定的信息判斷和識別的能力,只有在確立了自身在虛擬實踐中的主體地位,才能擺脫信息的壓力,從而在海量信息中過濾無效信息,自主地選擇有助于自身需要和發展的信息,擺脫各種不合理性的限制,實現人在虛擬網絡中的自由生存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