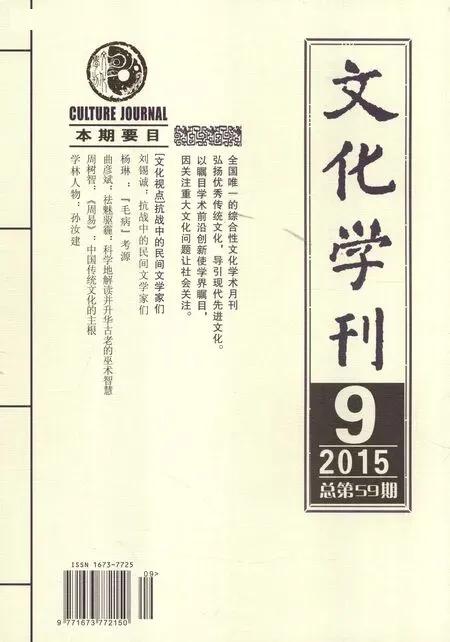從《鹽鐵論》看西漢儒學的演化
葉根虎
(安康學院,陜西 安康 725000)
從《鹽鐵論》看西漢儒學的演化
葉根虎
(安康學院,陜西 安康 725000)
關于漢代選擇儒學作為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的原因,古今學者多有論述,但鮮有從《鹽鐵論》展開論述。本文以《鹽鐵論》為主,以其他漢代史籍為輔作為研究材料,認為西漢儒學在與政治的交互關系中,經歷了由“儒學”向“儒術”的演化;同時,執行法家政策的政治家們也參與到對儒學的選擇性闡釋與改造中,發掘出“秋殺”一詞,為法家政策找到儒學的理論根據,使儒學成為一種富有包容性的學說,逐漸被官方接納與認可,最終成為統治中國數千年的主流意識形態。
儒學;儒術;秋殺
鹽鐵會議召開于漢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根據當代學者考證,《鹽鐵論》成書時間“應該不早于公元前66年,其大體時間約早公元前66年之公元前 49年之間,是鹽鐵會議后20年著成的”[1],屬于西漢著作,在考查西漢的儒學演化上,有著時間上的切近性。《鹽鐵論》的性質,經當代學者考證,并非桓寬臆造之書,[2]“基本上忠實了鹽鐵會議的論辯記錄”[3],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以此為材料,當可以得出相對科學可靠的結論。
一
首先看鹽鐵會議的背景。為什么偏在昭帝始元六年召開鹽鐵會議?導火線是杜延年向霍光建議“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宜修孝文時政,示以簡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于是“光納其言,舉賢良,議罷酒榷鹽鐵”,[4]似乎是為了讓百姓休養生息。但細讀霍光本傳,很容易得到另外的答案,即幫派斗爭的需要。武帝后元二年春(前87年)崩,將昭帝(時八歲)托付給大臣霍光、金日磾、桑弘羊、上官桀,但后來上官桀、桑弘羊與燕王旦都因種種原因怨恨霍光,并組成集團,反對霍光。在昭帝 14歲時,即始元六年(前81),三人趁霍光休假,向皇帝奏報霍光的違制之舉,認為其有篡逆之心,應予以罷免。此次由于皇帝的支持而未能成功,但“后桀黨與有譖光著,上輒怒曰……”[5],可見黨派斗爭從未停止。斗爭的結果是上官桀“(始元二年)正月壬寅封,五年,元鳳元年,反,誅”;[6]“二月乙卯,搜粟都尉桑弘羊為御史大夫,七年坐謀反誅”;[7]始元七年即前80年,即召開鹽鐵會議的第二年,向霍光告發這次謀反的正是杜延年。從這個角度看,杜延年的進言很難說是為百姓,還是為同黨出謀劃策。可見,前81年鹽鐵會議的召開,是上官桀派與霍光派于前81到前80年一系列激烈斗爭事件中的一件。這個激烈的幫派斗爭的背景,是我們理解《鹽鐵論》內容必須要考慮的。
二
參加會議的人明顯分成兩個派別,即雇傭文人賢良文學派和桑弘羊。他們實際上可以代表兩種思想路線,一種是掌握儒學,想靠儒學取得仕進的文人,一種是推行法家路線的當權派。這次激烈的思想交鋒都曝露出各自存在的問題,但卻都對推進儒學與政權結合,并成為國家意識形態起了很大的作用。
先說賢良文學們展現出的儒家學說。儒家面臨的問題是怎樣在國家意識形態方面有影響,將其融于國家行政體制中,即儒家如何當權。武帝時設立了《易》博士,《書》歐陽氏博士,《禮經》博士,《詩》三家博士,但博士只是“具官待問”[8]而已,根本沒有掌握實權。儒家在朝廷擁有顯赫地位的僅高祖時的叔孫通和武帝期的公孫弘。而公孫弘本人也只是“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9]傾心于吏事,于儒學不甚用心。武帝朝所詔用的賢良趙綰、王臧草明堂位未就,就被趙太后視為方術之學,設法賜死。[10]儒家在朝廷中沒有傾心推行儒學并有廣泛社會影響的人物,這對儒學的長久發展不利。
儒家的優勢在于國家有意識地扶植儒學,如設經學博士,“至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11]儒學的影響在逐漸擴大,儒學的勢力也在慢慢成長。由于儒家長久以來重視教育,在文化傳播上有影響力,如儒家提出的理想治世圖景,《禮記》中的大同,無為而治的黃帝等三王之世,以及被董仲舒美化的上古大治之世,“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奸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12]甚至具體到“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余年”。[13]這些思想甚至成為整個社會的共同理想,連武帝本人的詔書中,也宣稱以儒家的治世圖景作為行政的終極目的。
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燭,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外肅眘,北發渠搜,氐羌徠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嗚乎,何施而至此與![14]
有詔書確認,說明儒家的思想在社會上已被普遍承認,為什么儒家在國家政權中缺乏影響力?因為,在統治者看來,儒學本身“迂遠難行”,這成了儒學進入國家行政機構的最大障礙。秦始皇準備封禪時,儒生進言“蒲車上山,埽地而祭,席用葅秸”,[15]被始皇認為難施用而廢黜儒生。這種情況在武帝時又上演了一遍。在草封禪議上,武帝對儒生寄予厚望,結果儒生拘于古《詩》《書》而不敢創新,又有派系之爭,武帝給他們封禪禮器予以示范,結果依然讓武帝大失所望。武帝甚至連“采儒術以文之”的作用都沒有達到,于是“絀偃、霸,而盡罷諸儒不用”,[16]儒生在武帝那里失寵。在《鹽鐵論》中,大夫們也認為儒者言論“信往而乖于今,道古而不合于世務”,[17]理論與現實差距過大,真正原因,是上層懷疑儒者的行政能力,懷疑儒學在面對具體行政事務時的通變能力。在《鹽鐵論》中發現,儒者的代表賢良和文學也確實暴露出了這樣的問題。
丞相曰:先王之道,軼久而難復,賢良、文學之言,深遠而難行。夫稱上圣之高行,道至德之美言,非當世之所能及也。愿聞方今之急務,可復行于政,使百姓咸足于衣食,無乏困之憂,風雨時,五谷熟,螟螣不生,天下安樂,盜賊不起,流人還歸,各反其田里,吏皆廉正,敬以奉職,元元各得其理也。[18]
丞相提出了幾個具體問題,包括流民多、盜賊多、官吏貪污等,以及思考有沒有辦法解決這些問題。但賢良立即反擊:“先王之道,何遠之有”。接著舉歷史事例來證明施行仁義,成效卓著,運用的說辭與先秦士人用的大致相同,對具體問題無一涉及,這只能說明他們的學識與眼界還在古儒學那里。大夫也問:“諸生上無以似先王,下無以似近秦,令有司可以舉而行當世,安蒸庶而寧邊境者乎?”[19]
文學又開始重復仁義,并無新見。大夫們在給皇帝的奏章中稱“賢良文學不明縣官事”,[20]這固然有法家長期把持政權、儒家對政權運作不熟悉的原因,但也說明儒家缺乏一種把儒學與國家具體行政事務相結合的理論,可以套用當今俗語,即缺乏把儒學理論與具體的漢朝國情相結合的理論創新。
其實,儒學早已在尋求改變。早在陸賈的《新書》中,就有了“書不必起仲尼之門,藥不必起扁鵲之方,合之者善,可以為法,因世而權行”[21]這樣的求變思維。至《春秋繁露》,有“絀夏、親周、故宋”[22]之說,運用三統循環說解釋歷史,同時大講災異,實際上是儒學系統對漢代具體情況作出的“常用于常,變用于變”[23]的努力。后董仲舒對儒學進行了大改造。在《春秋繁露》及《漢書·董仲舒傳》中,董仲舒確立了兩個文化根基,一是天人感應,二是《春秋》。這套理論將王的權力解釋為根植于“天”,剝奪了王權的個人屬性,即把王權的性質由王本人所擁有的私權,改變為王代“天”執政,實際上成為天地宇宙所共有的公權。這為儒家參與世俗政權留下了空間。同時以天道陰陽與四季更替比于行政之德刑,同時廣開天人相與的模擬象征思維模式,為行政行為提供了寬廣的可與實際情況相適應、相契合的解釋理論,也為具體的行政行為開展留出了空間。①由于篇幅所限,董仲舒的具體理論貢獻,容筆者另文詳述。這套理論,比較完滿地完成了時代留給儒家的課題,完成了“儒學”向“儒術”的轉型。[24]在這一轉型過程中,陰陽理論與天人相與理論,成為儒學與時代特征相結合而形成的新儒學。
但為什么這套理論在《鹽鐵論》中沒有被賢良文學提及?王利器先生在《鹽鐵論校注·前言》中列舉了大量例子,說明“他們是地地道道地繼承了董仲舒的衣缽”。[25]縱觀《鹽鐵論》,賢良文學們言論的主題有三點:(1)攻擊武帝的政策;(2)宣揚董仲舒的“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即宣揚純道德,反對利欲;(3)宣揚仁義,反對任法。可見其的確是經過事先準備。吳慧先生也認為“賢良原已被稱為‘子大夫’。文學之所以得‘咸取列大夫’,這種不尋常的‘恩遇’,很可能就是攻擊桑弘羊賣力所得的報酬。估計霍光等人在事先已封官許愿,同他們在會下已達成了這筆交易的”。[26]那么,論調其實早已確定,會上只是施展,以及個人的臨場發揮。但這恰恰說明了純學理在面對世俗政權時的弱勢地位。學術只有作為工具,作為“器”,才能慢慢被政權接納。董仲舒的學說最終被接納,當然還與推行法家政策的政治家在為自己尋找行政理論根據時的選擇性闡釋有關。
三
法家政策在武昭時期,面臨的問題是,由于長期對匈奴的戰爭,已經使“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27]邊費不足,頒布的鹽鐵、酒榷、均輸政策,已導致“一官傷千里”;[28]用什伍連坐之法來控制人民,使“一人有罪,州里驚駭,十家奔亡”;[29]告緡法導致“逋流皆在大家,吏正畏憚,不敢篤責,刻急細民;細民不堪,流亡遠去,中家為之絕出,后亡者為先亡者服事;錄民數創于惡吏,故相仿效,去尤甚而就少愈者多”。[30]從富裕大戶到貧窮百姓,都加入到逃亡行列。而出錢出糧捐官除罪,這些出錢買得官職的人,想方設法謀取利益,導致“公用彌多而為者徇私,上下兼求,百姓不堪,抏弊而縱法,故憯急之臣進,而見知、廢格之法起”,[31]直接導致了人民的武力反抗,也迫使皇帝選用酷吏對人民實行鎮壓。這種政策反而導致矛盾更加激化,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國家發兵征討,這些人散亂失亡,復又嘯聚山林,至無可奈何。沈命法又使府吏避匿盜情不報,致使盜賊數量更多。總之,純法家政策已難以為繼。對于這種混亂局面,從皇帝到大臣都在尋求解決良方,于是召開鹽鐵會議,放下身段向儒者求教,而儒生并沒有給召開會議的官僚以滿意的答復,倒是大夫們對儒家,尤其是董仲舒的那套集陰陽、數術和五行于一體的理論很感興趣。細究其言論,得知這種興趣來源于三點。
第一,這套理論可以為具體的行政行為找到依據。如“大夫曰:五行,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隴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幽州有積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無而通萬物也”,[32]大夫們以此來論證自己均輸政策的合理性。
第二,可以把失敗的行政行為委之于“天數”,為推諉責任找借口。“水旱,天之所為,饑穰,陰陽之運也,非人力。故太歲之數在陽為旱,在陰為水。六歲一饑,十二歲一荒。天道然,殆非獨有司之罪也”。[33]
第三,終極原因,可以為法治的存在找到理論依據,其實是爭取法家在政權中存在的合理性,保存法家在政權中的位置。在《鹽鐵論》中,大夫和賢良文學可以展開對話與溝通的,是在談論陰陽五行與行政的對應,其中大夫有一段。
大夫曰:金生于巳,刑罰小加,故薺麥夏死。《易》曰:“履霜,堅冰至。”秋始降霜,草木隕零,合冬行誅,萬物畢藏。春夏生長,利以行仁。秋冬殺藏,利以施刑。故非其時而樹,雖生不成。秋冬行德,是謂逆天道。《月令》:“涼風至,殺氣動,蜻蛚鳴,衣裘成。天子行微刑,始貙蔞,以順天令。”文學同四時,合陰陽,尚德而除刑,如此,則鷹隼不鷙,猛獸不攫,秋不搜狝,冬不田狩者也。[34]
大夫的這段話,首先是說明了四季有生養刑殺,所以為政應仿效天地之陰陽,即四季,依次行政,僅有生養而無刑殺是不對的。把當時流行的俗語“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中的“秋收”換成“秋殺”,則刑法、刑罰就有了天地自然的依據。其次,對儒家所尊奉為寶典的經書廣征博引,這里面體現出的這些執政的官僚們對儒家文化的改造與創新,實際上并不亞于儒家自己的創造。由于他們是出于行政目的而利用儒家文化,因此對文化的創造更有目的性和針對性,這種目的性和針對性有時就會轉化為創新性。宣帝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35]王利器先生也認為:“王霸之分,方興未艾,其實漢宣帝所舉的一個‘雜’字,就全部道出了這個問題實質之所在”。[36]這與漢武帝的“取儒術以文之”的傾向一致。鹽鐵會議后,僅廢酒榷,未廢鹽鐵,說明鹽鐵會議的實質是派系斗爭。政權在尋找能支持行政行為的理論,而理論也逐漸向政權靠攏,這就是儒學在演化過程中的形態。
《鹽鐵論》中,無論賢良文學,還是御史、大夫,都對儒家學說廣泛引用,且大夫、御史對陰陽五行與行政對應的強烈興趣,皇帝詔書中對陰陽的談論,都說明將選擇董仲舒陰陽化的儒學作為武帝以后國家的主導意識形態,這是劇烈政治斗爭的結果,是整個漢代政治家和知識界的共同選擇。
[1]黑琨.《鹽鐵論》成書時間考[J].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3):76-79.
[2]龍文玲.《鹽鐵論》四十二至五十九篇非桓寬臆造——以《鹽鐵論》引書用書之考查為中心[J].首都師范大學學報,2012,(6):113-119.
[3]王永《鹽鐵論》之名義與作者之著作目的考論——兼論所謂“臆造“問題[J].貴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3):69-75.
[4][5][6][7][9][10][11][12][13][14][35][漢]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2. 2664.2936.691.791.2618.3608.2515.2520. 2510.160-161.277.
[8][15][16][27][漢]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59.3117.1366.1397.3141.
[17][18][19][20][25][28][29][30][31][32][33][34][36]王利器.鹽鐵論校注(定本)[M].北京:中華書局,1992.130.455.507.463. 9.69.580.192.132.42.428.557.22.
[21]王利器.新語校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6.44.
[22][23][清]蘇輿著.春秋繁露義證[M].鐘哲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2.53.
[24]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1卷)[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256.
[26]吳慧.桑弘羊研究[M].濟南:齊魯書社,1981.480.
【責任編輯:周 丹】
I206.2
A
1673-7725(2015)09-0203-05
2015-06-25
葉根虎(1979-),男,陜西渭南人,講師,主要從事中國文化與文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