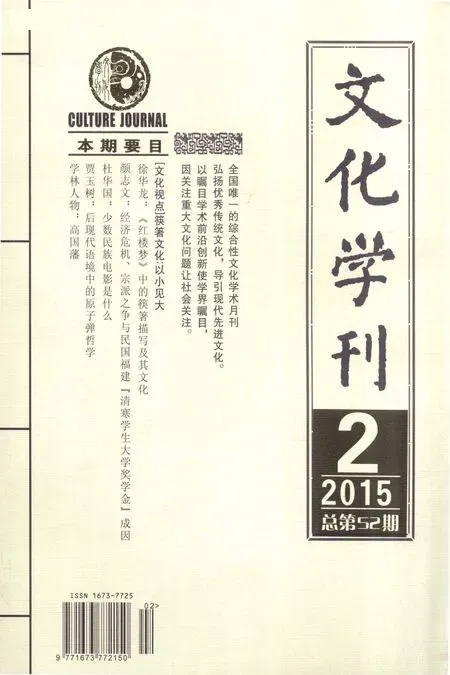托馬斯·哈代動物書寫詩歌中的生態倫理觀解析
姜慧玲
(大連外國語大學公共外語教研部,遼寧 大連 110644)
一、引言
托馬斯·哈代(1840-1928)是19 世紀末20 世紀初英國卓越的文學大師,他不僅在小說方面成就斐然,還被譽為英國“現代詩歌之父”。哈代是英國傳統的鄉村生活、鄉土文化的最后代言人,他的自然詩歌充滿了對家鄉的熱愛和濃厚的鄉土精神,而他的動物書寫詩歌則表現了對動物處境的憂慮,對人類中心主義的控訴,以及對人與動物和諧共處的生態理想的追求。
二、哈代的生態倫理觀緣起
“生態倫理學”是20 世紀初期興起的一種新型倫理學,其核心在于倫理學的“道德批判問題”。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在英國的開展,純樸的鄉村風景逐漸被城市文明代替,人類中心主義大行其道,和諧生態受到威脅。作為20 世紀初期維多利亞時代的見證人,哈代大部分時間在風景秀美的多塞特郡鄉村度過,隨著城市文明對鄉村生活的取代,他開始看到人與自然關系的失衡,人類的道德倫理也經受考驗。
達爾文的進化論對哈代有巨大影響,其核心觀點是,人與動物有共同的根,人與動物的和諧相處才會使生態實現平衡。在這一觀點的影響下,哈代把人類的倫理擴大到所有動物,他關心動物,鞭笞人類破壞動物的行為,倡導人與動物和諧相處。哈代的生態倫理觀尤其表現在他的動物書寫詩歌中。
三、哈代動物書寫詩歌中生態倫理觀的體現
在哈代的動物書寫詩歌中,哈代賦予動物以感情和智慧,將人類的倫理擴大到動物。他不僅對動物充滿了悲憫意識,還對人類對動物的殘害行為進行了尖銳的批判,他所憧憬的是人與動物的和諧統一,這顯示了他作為生態意識者與人文主義者的深刻性。
哈代擅長寫鳥類,在《關在鳥籠的金翅雀》一詩中,哈代描寫了一只金翅雀遭遺棄的情景:“在教堂墓地的新墳上,/我看到一只鳥籠,/關著一只金翅雀/是誰把它遺棄在新墳”在這首詩里,哈代表達了對金翅雀處境的憂慮和哀愁。《被刺瞎了雙眼的鳥》中的鳥的命運更加凄慘,它的眼睛被人類殘忍地刺瞎,雖然生存痛苦,卻沒有放棄生存意志:“默默忍受著生活的一切,/不為邪惡環境煩惱,高唱生活的歡歌”。哈代賦予了鳥以堅強的人格特征,更表達出對鳥的生存困境的憐憫與同情。
在《供捕獵的鳥的困惑》中,哈代從鳥的視角揭示了人類的無情。令“捕獵鳥”困惑恐懼的是,人類朋友不再如往日般溫情善良,反而表現出極端的殘酷無情,哈代通過詩句“他們不是過去給我們食物的那些人”在第四和第七行重復,表達了對人類殘酷的悲憤與控訴。哈代對人類中心主義的憤怒之情在《一包包肉》一詩中得到極大的宣泄:“這些人如此怪異,冷酷,貪婪,卑鄙,/把它們帶入險惡之地/它們要么死在屠夫刀下,/要么被農夫套上犁鏵。”在《捕鳥人之子》一詩中,哈代通過父與子的對話表達了人類對動物持有的兩種截然相反的態度,兒子象征著人性中的善良和天真,而他的父親則象征著殘忍和世故,詩歌結尾以兒子的死亡結束,這說明人類在為與動物保持和諧的關系中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在哈代看來,動物是作為生態共同體的一分子存在,人與動物、自然是和諧統一的。在《郊外白雪》中,哈代做了這樣的書寫:“臺階是變白的斜坡,/一直黑貓身材瘦弱,/他睜大眼睛,渺茫地向上攀登,/于是我們把它接入屋中。”在這里,人與黑貓同時出現,人與動物和諧統一。在《黑暗中的鶇鳥》一詩中,前兩節詩人描寫了一個荒涼、凄慘冷漠的樹叢,然而在第三節出現了希望之聲,詩人這樣評論道:“這是一只鶇鳥,瘦弱、老衰,/羽毛被陳風吹亂,卻決心把它的心靈敞開,傾瀉向濃濃的黑暗”[1]。在蒼茫凄愴的世界上,有別于詩中“我”的悲涼心情,鶇鳥唱出了一曲無限歡欣的黃昏之歌,顯示了它面對大自然苦難的堅強樂觀精神[2]。在哈代看來,人類應該從鶇鳥身上學到一種剛毅而頑強的生存意志,同時也有義務和責任來拯救生態危機,并對人與動物的和諧統一充滿信心。
四、結語
綜上所述,哈代所處的社會歷史背景和他從鄉村到城市的生活經歷決定了其在詩歌作品中對動物和自然的關注,他的動物書寫詩歌既有對動物的憐惜與同情,又有對人類中心主義的批判,同時也有對人與動物和諧相處的生態理想。哈代動物書寫詩歌中的人文思想和生態意識將越來越受到文學界和生態學者的重視,同時也給當代的詩歌創作和文學生態學跨學科研究以啟示。
[1]顏學軍. 論哈代的自然詩[J].外國文學評論,2002,(1):32-40.
[2]張炳飛. 論哈代的自然觀——由哈代詩歌的鳥意象談起[J]. 紹興文理學院學報,2005,(6):6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