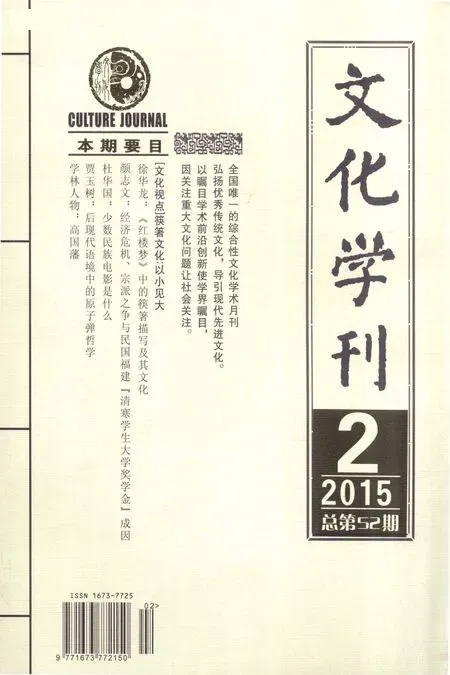少數(shù)民族電影是什么
杜華國
(云南民族大學藝術學院,云南 昆明 650031)
電影是什么?在《電影是什么?》一書中,安德烈·巴贊從藝術類型本體論出發(fā)探討了“電影”與“戲劇”“繪畫”類型特征上的交叉與分離,論述了電影作為“第七藝術”的“攝影影像本體”“我性”,論證了“戲劇”“繪畫”相對“電影”的“他性”。“攝影影像具有獨特的形似范疇,這也就決定了它有別于繪畫,而遵循自己的美學原則。攝影的美學潛在特性在于揭示真實。在外部世界的背景中分辨出濕漉漉人行道上的倒影或一個孩子的手勢,這無須我的指點;攝影機鏡頭擺脫了我們對客體的習慣看法和偏見,清除了我的感覺蒙在客體上的精神銹斑,唯有這種冷眼旁觀的鏡頭能夠還世界以純真的原貌,吸引我的注意力,從而激起我的眷戀。”[1]一如電影的“我性”要從藝術類型本體論出發(fā)一樣,筆者認為也應從電影類型本體論出發(fā),闡釋“少數(shù)民族電影”的“我性”,厘別與其他電影類型的“他性”。
一、“少數(shù)民族電影”概念的混亂現(xiàn)狀
學界、業(yè)界一直沒有對“少數(shù)民族電影”作出明確界定,影響較大的觀點是王志敏在《少數(shù)民族電影的概念界定問題》一文中提出的“三原則”:文化原則、作者原則、題材原則。民族電影、少數(shù)民族電影、少數(shù)民族題材電影相互指代是學界、業(yè)界的慣常做法。“民族電影理論體系的發(fā)展需要總體和宏觀的建構(gòu),但如果缺少具體的研究,宏觀的建構(gòu)便會顯得空泛。”[2]這里的“民族電影”泛指中國電影。“《盜馬賊》沿襲《獵場札撒》風范,全部啟用藏族非職業(yè)演員,角色與演員合二為一,演員們的日常生活就是角色的表演內(nèi)容。……通過這部同樣極少對白的少數(shù)民族題材影片,田壯壯繼續(xù)著自己對‘他者’世界的探討。”[3]“田壯壯的少數(shù)民族電影創(chuàng)作呈示了兩種特征:一是追尋宗教,二是平視角度。”[4]“正是出于對少數(shù)族群和非主流文化的尊重,田壯壯的民族電影悠遠而單純,不居高臨下,不妄加評論,沉靜的影像充滿冥想的張力,它們逆轉(zhuǎn)了1949年以來的少數(shù)民族電影的漢化傾向,以沒有‘外在’偏見的表述留下了獨特的人文價值和地緣紀錄。”[5]上述“少數(shù)民族題材電影”“少數(shù)民族電影”“民族電影”所指相同。在饒曙光《中國少數(shù)民族電影史》中,第一章標題“曲折中發(fā)展的少數(shù)民族題材電影創(chuàng)作(1960—1966)”的“少數(shù)民族題材電影”與第七章標題“新世紀少數(shù)民族電影創(chuàng)作(2000—2010)”的“少數(shù)民族電影”內(nèi)涵一致,綜上可以看出“少數(shù)民族電影”適用的混亂現(xiàn)狀。
二、類型電影與電影類型
不像文學、戲劇、繪畫、音樂、舞蹈、雕塑的“生日”無法考證,電影從1895年誕生至今只有一百多年的時間,在藝術界是最年輕的類別,類型在文學領域的研究從亞里士多德時期就開始了,電影的類型研究借鑒了文學類型研究的成熟體系。類型電影是高度模式化的影片,是依隨美國好萊塢制片廠制度建立的產(chǎn)物,類型電影的產(chǎn)生是為了方便制片商在某種“規(guī)范”(類型片)指導下流水線生產(chǎn)影片,以期獲得最大利潤,可以說類型電影就是商業(yè)片的代名詞。“從上世紀20年代到50年代,好萊塢的制片廠制度便是好萊塢最重要的組織形式,它為好萊塢提供了必要的經(jīng)濟學基礎和穩(wěn)定性,更使好萊塢可以生產(chǎn)出在攝影機運動、剪輯、敘述方式和影片類型等方面可以迅速得以辨識的、具有相同風格的影片。類型電影實質(zhì)上是一種拍片方法,是一種藝術產(chǎn)品標準化的規(guī)范。”[6]類型電影是制片商與觀眾的縫合握手體系,當看到《音樂之聲》(羅伯特·懷斯,1964)類型介紹為歌舞片時,觀眾就會想到“音樂,歌舞在影片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成為影片敘事、表意、抒情的重要藝術元素,也是觀眾觀賞的興趣中心。”[7]類型電影的概念傳達,需要制片商和觀眾的“前呼后應”,“類型電影作為一種通俗敘事藝術,與其說它是為了公眾而制造的,不如說它就是由公眾所制造出來的。”[8]電影之類型經(jīng)歷了從類型電影到電影類型的所指嬗變,時下類型電影已擺脫了經(jīng)典好萊塢時期大制片廠生產(chǎn)管理模式,衍變成了電影類型,筆者認為,時下類型電影指的就是電影類型。電影類型的劃分一般從“觀念”與“范式”兩個維度來界定,“觀念”指的是主題方面,是該類型片共同體現(xiàn)著的價值趨向;“范式”指的是形式結(jié)構(gòu)方面,比如歌舞片中的“歌舞”、西部片中的“西部牛仔”等。
類型電影和電影類型的區(qū)別是,類型電影的制作主體是制片商,而電影類型的制作主體則是理論學者。影片制作前類型電影就存在于制片商的意念里,影片按某套“觀念”“范式”制作完成后類型電影宣告造就。電影類型是影片制作完成后,理論學者按類型片劃分標準將其歸屬,可以看出,類型電影是“含義先于存在”,電影類型是“存在先于含義”。值得注意的是,隨著電影類型的不斷演繹變化,相對穩(wěn)定的判斷標尺——“觀念”與“范式”的界限也愈來愈模糊。《阿甘正傳》(羅伯特·澤米吉斯,1994)有著政治片和愛情片的雙重“觀念”與“范式”。“政治片(Political Film)是以現(xiàn)實生活中的重大的政治事件或者重大的社會問題為題材,將某一社會或國家的社會政治問題作為故事主線,藝術地傳達導演的政治觀點和政治主張的電影類型。”[9]《阿甘正傳》展映的種族歧視、垮掉派、水門事件、總統(tǒng)被刺、越南戰(zhàn)爭等事件貫穿了整部影片,可以說該片是一部承載了美國沉重社會政治問題的政治片。“愛情片(Romantic Film)是以愛情、婚姻、家庭為主要內(nèi)容的故事片的統(tǒng)稱。”[10]阿甘和珍妮青梅竹馬、兩小無猜度過了天真無邪的童年時光,在美國社會急劇轉(zhuǎn)型期,兩人幾度悲歡離合。待鉛華洗盡,驀然回首,珍妮發(fā)現(xiàn)最值得愛的男人——阿甘還在原地等著她,有情人終成眷屬,不得不說該片也是一部凄美感人的愛情片。當一部影片出現(xiàn)了兩種或兩種以上的“觀念”與“范式”(主題的多義性)該如何“定型”呢?筆者認為,類型歸屬要看影片最顯著的“主控主題”、最明顯的“類型癥候”。意大利影片《美麗人生》(羅伯托·貝尼尼,1997),猶太青年圭多突破身份勇敢追求多拉的壯舉令人欽佩,為兒子的“美麗人生”免受泯滅人性法西斯暴行影響,這個外表弱小的父親做出了一系列錚錚硬漢行為,直至付出生命,濃濃父愛呼之欲出。該電影出現(xiàn)了三種“觀念”“范式”,該片是“戰(zhàn)爭片”“兒童片”還是“愛情片”呢?筆者看來,男女主人公美好愛情、婚姻的破滅,圭多為塑造兒子的“美麗心靈”不得不“欣然赴死”,一切悲劇的根源都指向了戰(zhàn)爭,創(chuàng)作者最想傳達給觀眾的是對戰(zhàn)爭荒誕、殘酷的反思和救贖,因此,該片應歸入“戰(zhàn)爭片”。
三、少數(shù)民族電影的“我性”
筆者對王志敏的“少數(shù)民族電影”界定持不同意見,按其原則蜚聲海內(nèi)外的經(jīng)典影片《五朵金花》(王家乙,1959)就不屬于“少數(shù)民族電影”,因為導演不是少數(shù)民族,不符合“作者原則”。章家瑞的“紅河三部曲”——《婼瑪?shù)氖邭q》(2003)、《花腰新娘》(2005)、《紅河》(2009)也不屬于“少數(shù)民族電影”,因為導演也不是少數(shù)民族。不難發(fā)現(xiàn),“作者原則”有著邏輯悖論和粗糙修辭:少數(shù)民族導演烏蘭塔娜(蒙古族)可以創(chuàng)作非少數(shù)民族電影(如《暖春》,2003),漢族導演為什么不能創(chuàng)作“少數(shù)民族電影”呢?
類型作為電影學科的研究視角,經(jīng)過幾十年的發(fā)展日臻成熟,國內(nèi)外都有豐碩的理論成果,比如沈國芳的《觀念與范式——類型電影研究》、卡明斯基的《美國電影的類型》等。類型片的概念界定不能缺少理論學者的聲音,其概念界定應由制作者、理論學者及有一定電影知識素養(yǎng)的觀眾共同完成。“‘少數(shù)民族電影’是中國電影史上一個具有深厚傳統(tǒng)的電影準類型。”[11]可以看出“少數(shù)民族電影”是類型視域下的稱謂,因此其概念定義應在類型范疇內(nèi)進行。“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相對于其它地區(qū)來說,其生存經(jīng)驗獨特、人文環(huán)境復雜、生產(chǎn)力關系贏弱,當代中國正處于大發(fā)展、大變革時期,勢必對少數(shù)民族的文化產(chǎn)生深遠影響,少數(shù)民族文化在潛滋暗長地變遷著。放眼當代中國文化進程,少數(shù)民族文化的變遷,更多是文化的進化。中國少數(shù)民族電影應該更多地關注少數(shù)民族文化的變遷、進化。紀錄少數(shù)民族文化進程— —是中國少數(shù)民族電影最重要的適格功能。”[12]“少數(shù)民族電影”應該紀錄急遽變遷的少數(shù)民族社會文化,也唯以紀錄少數(shù)民族社會文化為宗旨的影片才是“少數(shù)民族電影”。“文化”的概念廣受爭議,英國文化人類學家泰勒給“文化”(culture)的定義影響深遠,“他在《原始文化》一書中說道:‘文化是一個復合的整體,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人類在社會里所獲得的一切能力與習慣。’”[13]筆者試著給少數(shù)民族電影下個定義:少數(shù)民族電影是以紀錄少數(shù)民族社會文化為主旨(觀念);在形式結(jié)構(gòu)(范式)上,少數(shù)民族電影中往往有著一貫的類型人物(角色是少數(shù)民族)、類型環(huán)境(故事發(fā)生在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類型對白(少數(shù)民族語言)等;理論學者及有一定電影知識素養(yǎng)的觀眾也認為是少數(shù)民族電影的影片。
四、少數(shù)民族題材電影、少數(shù)民族母語電影、民族電影、影視人類學片的“他性”
題材是指“電影劇本所反映的生活現(xiàn)象的對象、性質(zhì)和范圍。如‘農(nóng)村題材’‘工業(yè)題材’‘歷史題材’‘戰(zhàn)爭題材等’”[14],筆者看來,題材和類型毫無關聯(lián),少數(shù)民族電影可以是農(nóng)村題材(如《五朵金花》),可以是歷史題材(如《暴風中的雄鷹》,王逸,1957),可以是宗教題材(如《靜靜的嘛呢石》,萬瑪才旦,2006)乃至神話傳說(如《阿詩瑪》,劉瓊,1964);反之,《李時珍》(沈浮,1956)是“歷史題材”,在類型視角下則屬于“傳記片”,《邊寨烽火》(林農(nóng),1957)是“少數(shù)民族題材”,在類型視角下則屬于“反特片”。筆者認為,少數(shù)民族題材電影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指涉獵少數(shù)民族社會文化因子的影片,狹義指涉獵的少數(shù)民族社會文化份量不足以構(gòu)成少數(shù)民族電影的影片。少數(shù)民族社會文化在少數(shù)民族電影中是主旨訴求,在少數(shù)民族題材電影中只是被涉獵,廣義少數(shù)民族題材電影是包含少數(shù)民族電影的。
少數(shù)民族母語電影最顯著的特征是使用少數(shù)民族語言對白,中國少數(shù)民族電影自誕生到新世紀初一直是“普通話”對白,政策的松綁對少數(shù)民族母語電影的誕生起了推波助瀾作用,廣電總局2003年出臺的四大改革政策和2004年的《關于加快電影產(chǎn)業(yè)發(fā)展的若干意見》等文件放松了電影行業(yè)的“國有事業(yè)”屬性,不僅民營資本可以進入電影產(chǎn)業(yè),電影制作也不再“上綱上線”。此背景下,或出于展示“原生態(tài)”“原汁原味”抑或制作成本考慮,2005年始一批少數(shù)民族母語電影應運而生。電影作為“現(xiàn)實的漸近線”,少數(shù)民族母語電影的少數(shù)民族語言對白不僅是紀實美學的契合需要,更是少數(shù)民族文化自覺的意識體現(xiàn)。時下學界、業(yè)界把少數(shù)民族母語電影統(tǒng)統(tǒng)歸入少數(shù)民族電影,筆者以為不然,少數(shù)民族母語影片是否能歸納入少數(shù)民族電影,要看其是否以展示少數(shù)民族社會文化為宗旨。《黑駿馬》(謝飛,1995)是蒙古語對白,影片中不乏廣袤的草原、蒙古包、馬頭琴等蒙古族社會文化因子,該片“貌似”少數(shù)民族電影,但該片的主題是贊美堅韌、豁達的生命力,謳歌穿越世俗的人性大愛、大美。因此該片不屬于少數(shù)民族電影,而是少數(shù)民族題材電影。
斯大林對“民族”是這樣定義的:“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jīng)濟生活以及表現(xiàn)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zhì)的穩(wěn)定的共同體。”[15]民族在我國的探討始于民族學領域,文藝領域的民族承襲了其民族學涵義,因此,我們探討民族電影和少數(shù)民族電影的語義區(qū)別,不能繞開民族學民族的含義。時下民族學使用的“民族”大致有兩類內(nèi)涵:“第一是在特定的場合與條件下,專指現(xiàn)存少數(shù)民族,相當于英文的 minority。如“民族地區(qū)”“民族教育”“民族語言”“民族人口”“民族聚居區(qū)”“民族散居區(qū)”等等,都是專指少數(shù)民族的概念表達。第二是在特定的文脈中,“民族”一詞也能用于指稱像“中華民族”(Chinese nation)這樣的對象范疇。……“民族民主革命”“民族解放戰(zhàn)爭”“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等就是指的這一層面的概念。”[16]“民族教育”指的是“少數(shù)民族”教育,而“民族解放戰(zhàn)爭”卻指的是“中華民族”解放戰(zhàn)爭。筆者認為,所謂“在特定的場合與條件下”“在特定的文脈中”其實是民族概念濫用后的“墨守成規(guī)”,民族的民族學語義模糊順延到了電影領域,從而導致了民族電影和少數(shù)民族電影的雙向歧義。全球語境下民族電影(National Cinema)指的是一個國家的電影,“在西方,‘民族電影’是指與好萊塢電影相對立的電影事業(yè)。”[17]我國電影理論研究不能僅局限于國內(nèi),當面向全球語境的北京國際電影季民族電影周的“民族電影”指稱著少數(shù)民族電影時,必然會引起涵義歧義。筆者認為,民族電影與少數(shù)民族電影應該區(qū)分開來:民族電影泛指一個國家的電影,少數(shù)民族電影指的是某少數(shù)民族電影。
顧名思義,影視人類學是以照片、影片等影像媒介為主要手段研究人類學的一門學科。“和文字資料不同,影像雖然也是二手資料,但是相對而言,比田野調(diào)查筆記更具有客觀性和直觀性。避免了由于文字敘述的不準確和含糊性導致的理解障礙。”[18]少數(shù)民族電影的紀錄媒介只能是動態(tài)影像,而影視人類學不僅以動態(tài)影像為媒介,照片等也是重要的紀錄手段。筆者認為,在動態(tài)影像上,影視人類學片有狹義、廣義之分,狹義影視人類學片就是民族志記錄片,比如對云南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潞西縣德昂族水鼓制作過程的記錄,而廣義影視人類學片不是“原汁原味”地紀錄,它是經(jīng)過人類學者依自己訴求選擇紀錄而結(jié)構(gòu)出的藝術樣式。“在概念上,‘紀錄’涵蓋了整理擇取、講道敘綱,也就是有主題、有闡釋、有選擇、非虛構(gòu)地講述生活中的真實。”[19]也就是說,廣義影視人類學片有著強烈的主觀色彩,少數(shù)民族電影和狹義影視人類學片的區(qū)別顯而易見,其與廣義影視人類學片的區(qū)別在于后者要求畫面絕對真實,不能有“虛構(gòu)性”和“文學性”等藝術修飾痕跡。“怎么區(qū)別對于我們以外的真實世界的記錄和對于僅僅存在于我們頭腦中的世界的建構(gòu)?后者被我們稱之為虛構(gòu)”[20],而少數(shù)民族電影是“藝術作品”,是“虛構(gòu)”的。
五、結(jié)語
少數(shù)民族電影作為民族電影的一朵奇葩,如清水下明石般熠熠耀閃的明珠鑲嵌在民族電影歷史長河中,如畫旖旎的自然風貌、多彩斑斕的服飾、純潔爛漫的愛情、肅穆神秘的民俗……濃郁的少數(shù)民族風情總是讓異族人回味再三。中國少數(shù)民族電影已然走過六十年光陰,無論是“將紛繁的類型電影分成比較穩(wěn)定的類型群組:西部片、歌舞片、科幻片、戰(zhàn)爭片、愛情片、傳記片、強盜片、政治片等”[21],還是陳林俠在《中國類型電影的知識結(jié)構(gòu)及其跨文化比較》一書中把國產(chǎn)類型電影分為倫理片、戰(zhàn)爭片、愛情片、恐怖片、武俠片、喜劇片、槍戰(zhàn)片、災難片,少數(shù)民族電影芳跡難覓。從電影類型本體論出發(fā),以類型片維度審視,是對少數(shù)民族電影內(nèi)涵的追本溯源。少數(shù)民族電影概念的確定不僅給電影類型研究增添了新家丁、開拓了新視域,這對其學科自身的發(fā)展也具有深遠意義。
[1][法]安德烈·巴贊.電影是什么[M].崔君衍譯.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
[2]沈小風.20世紀90年代電影批評研究[M].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9.
[3][4][5]楊遠嬰.電影作者與文化再現(xiàn)——中國電影導演譜系研尋[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5.
[6]黃文達.外國電影史教程[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2011.
[7][9][10][21]沈國芳.觀念與范式——類型電影研究[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5.
[8]吳瓊.中國電影的類型研究[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5.
[11][17]胡譜忠.命名與修辭:中國少數(shù)民族題材電影的“元問題”[J].影視藝術,2014,(02):10-20.
[12]杜華國.中國少數(shù)民族電影適格功能探析[J].電影評介,2013,(15):42—44.
[13]王四代,王子華.云南民族文化概要[M].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6.
[14]許南明,富瀾等.電影藝術詞典[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5.
[15][蘇]斯大林.斯大林全集(第二卷)[M].中央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16]孫秋云.文化人類學教程[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18]鄧衛(wèi)榮,劉靜.影視人類學——思想與實驗[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19]焦小惠.紀錄片的再現(xiàn)與表現(xiàn)[J].電視研究,2001,(10):36—38.
[20][加]安德烈·戈德羅,[法]弗朗索瓦·若斯特.什么是電影敘事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