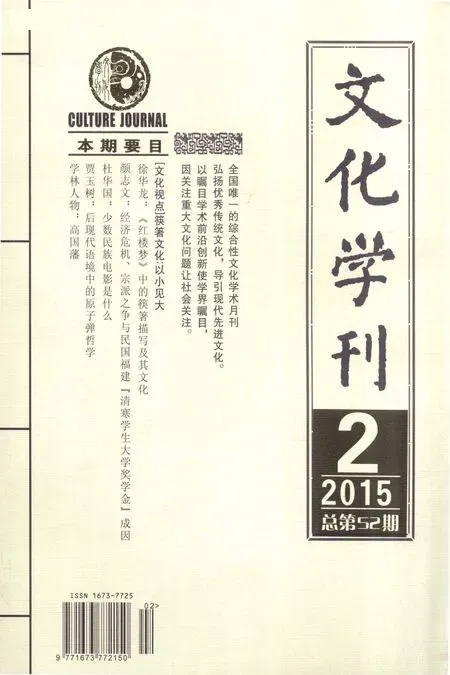不作為犯罪義務之先行行為的來源
董思穎
(江西財經大學法學院,江西 南昌 330000)
一、不作為犯罪義務來源概述
所謂不作為犯罪,是指行為人負有實施某種積極行為的特定法律義務,并且能夠實行而不實行的危害行為。筆者認為不作為犯罪的義務來源可以包括幾種:法律明文的規定;職務或業務上的義務;先行行為引起的義務;特定的重大的道德義務。當前,將道德義務作為不作為犯罪的義務來源是符合我國國情的,而且外國已有立法例,如德國、法國等國有見危不救罪。筆者在此僅對先行行為引起的法律義務和道德義務能否成為不作為犯罪的作為義務來源這兩方面進行探討。
二、先行行為中“行為”的認定
先行行為一旦產生了危險,就構成不作為犯罪的義務來源,應當分兩種情形來考察:
第一種是刑法在對犯罪行為規定了結果加重犯或者發生嚴重結果即構成重罪,就應當將加重的危害結果評價在結果加重犯或者另一重罪中。例如交通肇事罪中對行為人逃逸致使受害者死亡的處罰,行為人已構成交通肇事罪,他的過失犯罪行為將受害人置于危險中,但行為人沒有施行救助,反而逃逸致受害者死亡,此時對行為人的處罰并沒有因其犯罪行為逃逸產生的救助義務而另外對其進行故意殺人罪的處罰,只是作為交通肇事罪的加重犯進行處理,在這種情形下,犯罪行為并沒有成為不作為犯罪義務之先行行為來源的一種[1]。
第二種是在刑法沒有規定結果加重犯或成立重罪的情形下,犯罪行為也可以成為先行行為的一種來源。例如行為人在進行非法砍伐國家珍貴樹木,但是在砍伐時樹木砸到路人,傷勢嚴重,行為人明知不立即進行救助會導致受害人死亡的后果,但其沒有施行相應的救助,產生了路人死亡的后果。行為人砍伐國家珍貴樹木的情形已經構成非法采伐國家重點保護植物罪,但該罪并沒有將造成死亡的結果評價在該罪的構成要件中。在這種情況下,應當將該犯罪行為視為導致行為人負有積極搶救的義務,從而構成不作為的故意殺人罪或過失致人死亡罪,進行數罪并罰。
三、先行行為是否限于有責
所謂有責是指由于當事人先前實施的行為違反了法律規定而導致其負有刑事責任,即為有責。所謂無責即當事人實施的行為沒有違反法律的規定,也沒有義務去承擔什么責任,即無責。對于先行行為是不是應當包括有責和無責行為還是僅限于有責行為,我國刑事法理論上還沒有形成一致的意見。在支持僅限于有責行為的人看來,作為先行行為的行為人必須要有法律上的主觀方面的意志,也就是說先行行為必須是行為人基于主觀意愿的情況下而實施的行為,只有符合行為人主觀愿望和客觀實際行為一致的情形,才能夠使先行行為作為法律事實之一的法律行為。
本方認為,先行行為是否有責只是對先行行為本身的法律評價,對于這種法律評價和先行行為能否產生特定的積極作為義務并沒有必然的關系。例如:張三在去游泳的路上,鄰居的小孩李四也跟著張三一同去游泳,張三未知可否,但是后來李四溺水向張三求救,張三還未來得及進行救助,李四已溺水而亡,在此過程中,由于張三對于李四的跟從沒有明確表態,因此其應當對李四的溺水負擔一定的法律責任。上述案例中張三未知可否的行為本身并不對李四的跟從行為負有責任,但是該司考案例中對于無責的先行行為也將其作為不作為犯罪義務先行行為的來源,行為人就應當進行阻止危險后果的發生。
四、特定道德義務能否成為不作為義務來源
當前,我國刑事法理論通說認為特定的道德義務不能成為不作為犯罪義務的來源[2]。違反道德上的義務必然要受到道德上的譴責,但不能由于行為應當承擔法律責任乃至相應的刑事責任就應當將道德義務納入不作為犯罪義務的來源,如果一旦納入就必然會導致刑法處罰范圍的擴大,與罪刑法定原則相違背。
對于道德義務能不能成為不作為犯罪義務的來源不能一概而論,但不可否認的是對于特定的道德義務應當納入。在社會道德的等級體系中,存在著一類社會有序化的基本要求,一類是更高層次有助于人類和社會進步的原則。那么,相對來說法律作為調整社會關系的最后一道防線,一直被視為社會道德的低層次即維護社會有序化的基本要求,人人都應當遵守,而另一類的社會道德層次較高,不具有法律適用的普遍性,只能依靠內心崇高的信仰來進行調整[3]。法律應當將一些特定的道德義務作為不作為犯罪的義務來源進行重新劃定,以維護良好的社會道德。
總之,對于不作為犯罪義務之先行行為的來源的研究還不是很成熟,對于犯罪行為以及無責行為,特別是對特定道德義務能否上升為法律義務也有待司法實踐的進步來進行驗證。
[1]趙秉志. 中國刑法案例與學理研究(總綱篇)[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159.
[2]林泰,柳立業.論不作為犯罪的義務來源[J].寧波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7,(1):61-64.
[3]馬克昌.犯罪通論[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