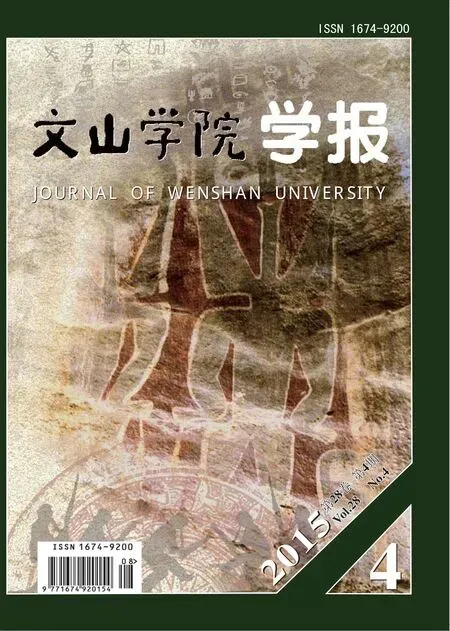西疇“女子太陽節”的歷史內涵及文化意義
黃金東
(中央民族大學 圖書館,北京 100081)
西疇“女子太陽節”的歷史內涵及文化意義
黃金東
(中央民族大學 圖書館,北京 100081)
摘要:“女子太陽節”是云南省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西疇縣湯果村壯族傳承了數千年歷史的一項重要民俗活動,以其獨特的女性特征吸引著世人的目光,入選了“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女子太陽節”與當地自然地理環境有一定的關系,它根源于百越及其后裔壯族創造的悠久歷史文化,包含著深厚的歷史內涵。對“女子太陽節”的保護和傳承有著重要的文化意義。
關鍵詞:太陽崇拜;女子太陽節;歷史內涵;文化意義
太陽崇拜是上古時期的一種普遍現象,幾乎存在于世界各個民族的發展歷程中。人類學家愛德華·伯內特·泰勒(Edward Burnett Tyor)曾在其著作《原始文化》中說到,“凡是陽光照耀到的地方,都有太陽崇拜的存在。”[1]198英國宗教學家、太陽神話理論的創造者麥克斯·繆勒(Max Muller)甚至說:“一切神話均源于太陽。”[2]18他提出,人類所塑造出的最早的神是太陽神,最早的崇拜形式是太陽崇拜。太陽神話是一切神話的核心,一切神話都是由太陽神話派生出來的。太陽從僅僅是個發光的天體變成世界的創造者、保護者、統治者和獎賞者,實際上變成一個神,一個至高無上的神。[3]186
伴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太陽崇拜逐步衰退,在世界許多地方只留有一些遺跡。然而,在云南省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西疇縣一個叫“湯果”的小山村里,卻完整保留了數千年來的太陽崇拜習俗,這里有內涵豐富的神話傳說,有完整的傳承儀式,且以其獨特的“女性特征”吸引著世人的目光。
每年的農歷二月初一,湯果村及其周邊村寨年滿16歲的壯族女子都穿著節日盛裝參加太陽節,整個活動過程男性不能參加。此外,男性還要承擔所有的家務,并為女性準備晚餐。因此,也稱為“女子太陽節”。“女子太陽節”活動的中心內容為祭請太陽儀式,包括女人沐浴凈身換裝、祭請太陽、送太陽、清理祭祀場地、擺設供品、唱誦《祭太陽古歌》、分享供品等內容。 這種女子沐浴凈身祭祀太陽及其完整的祭祀儀式在中國各民族崇拜、祭祀太陽文化當中具有唯一性,別具特色,充滿了神秘的魅力。2014年11月,西疇縣“女子太陽山祭祀”被列入“第四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西疇“女子太陽節”作為一項重要的民俗傳統文化現象,有著深厚的歷史內涵和重要的文化意義。
一、西疇“女子太陽節”深厚的歷史內涵
(一)它與當地特殊的自然地理環境有一定的關系
在人類解釋自然現象的水平相對較低的遠古時期,人類的思維基本上都是從自身所處的自然環境為起點的,面對無法解釋卻又深受影響的自然外在物,世界一些地區的人們產生了最質樸的自然崇拜,并根據想象繁衍出了關于日月星辰的神話。在此基礎上,產生了太陽崇拜。但并不是世界所有地區的人們都會產生對太陽的崇拜,這與其所處的地理環境有一定的關系。在特別需要陽光的寒冷地帶或者太陽對人們生產活動有重要影響的地方,對太陽的崇拜可能更普遍一些,如古老的斯堪的那維亞人普遍信仰日神,如今,北歐挪威的特羅姆瑟人在每年的1月21日仍過隆重的太陽節。相反,居于赤道或沙漠地區的民族則可能因為酷熱干燥而敵視太陽,甚至視之為惡神。泰勒認為赤道地帶的人常常把太陽視為自己共同的敵人……在澳大利亞內地沙漠地區,土著人用巫術控制太陽,表明他們也不需要這位過分施放熱量的神靈。[1]725
西疇縣地處云南省東南部,在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中部偏南,地理坐標為北緯23°05',東經104°58',北回歸線橫穿整個縣境。氣候冬無嚴寒,夏無酷熱,溫濕多雨,干雨季分明。湯果村則依山傍水,面對稻田和河流,背靠大山和森林,年平均氣溫15.9攝氏度,年降水量1297毫米。在這樣的自然環境中,人們對太陽的感受是較為舒服的。更重要的是西疇所處的地理環境非常適合水稻栽培,處于“那”文化圈中,有著悠久的稻作農耕傳統,而進入農耕文明正是太陽崇拜產生的重要原因。
(二)它是壯族及其先民悠久稻作文化的體現
太陽崇拜是古代農耕民族的普遍信仰,與農耕有著密切的聯系。在人類靠采集和狩獵為生的遠古時期,對太陽的感受并沒有那么強烈,也就不容易產生對太陽的崇拜。而進入了新石器時代以后,人類能夠進行生產性的生產(農業和畜牧業)以后,太陽對人有了直接的利害關系,人們才感覺到自己的勞動成果受到太陽的制約,從而促使人們較多地思考太陽,猜想太陽。在無法解釋太陽運行規律的時代,人們逐漸把太陽人格化,同時視之為神而加以禮敬或祭祀。[4]148高福進也認為,農耕文明使人類生活趨于穩定且更有規律性,與此適應的是太陽的升落與晝夜交替,四季更新對農業生產的直接影響使得人們充分感受到太陽的巨大威力,因此,太陽神作為農業主神幾乎為所有古代農耕部落所信仰。[5]34
每年的6月24日是居住于秘魯的印第安人祭祀太陽神的節日,它源于一個古老的傳說:遠古時期,古印第安人過著狩獵生活,生活非常勉強,隨著人口越來越多,他們的日子也越來越艱難。直到有一天,太陽神把金犁和種子賜給他們,使他們得以開始農耕,才過上有保障的安定生活。由此當地人產生了太陽崇拜,每到收獲季節,印第安人就到神廟里舉行祭祀儀式。久而久之,便形成太陽節。同樣,新西蘭土著毛利人也有他們的祖先與英雄瑪尤伊(Maul)曾捉住了太陽,使其從此規律地運行,以免造成旱澇的傳說故事。中國古神話“后羿射日”也反映了太陽與農業的直接聯系,“十日并出,焦禾稼,殺草木,民無所食”[6]318。這些神話傳說都展示了同樣的一種聯系:即太陽崇拜與農耕現實生活的密切聯系。
云南西疇屬壯族文化區域,湯果村所有村民都是壯族土著。歷史上,壯族及其先民創造了燦爛的稻作文化,對世界稻作文明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據推測,壯族人工栽培水稻的歷史長達12000~20000年左右。[7]覃乃昌指出:壯族地區農業是獨立起源的,嶺南地區的農業由壯族先民創造,但并不是獨立發展,在發展過程中與其他民族有著許多的聯系,與周邊民族互相影響。[8]由此展開,他認為,我國存在著一個東起廣東省的中部偏東,湖南省南部,西至緬甸南部和印度東北部的阿薩姆邦,北至云南中部、貴州南部,南至泰國南部、越南中部和我國的海南省的“那”文化圈。[9]
毫無疑問,云南西疇正處于“那”文化圈中,是“那”文化發展的源頭之一。“西疇”古壯語稱“董布那”,意為“大山坡上的稻田”。西疇縣內出土了石器時代的有肩石斧、有段石錛以及石鏟等工具。此外,西疇縣境內仍分布著不少“那”文化的標記,即以“那”來命名的地名,如那基、那紹、那柏、那磨、那拐等村落。可見,西疇有著悠久的稻作農耕歷史和文化。“女子太陽節”活動的傳承地湯果村,當地居民從祖先開始就把村寨建在半山上,面對稻田,背靠大山,河流環繞,村前是稻田,村后是森林。他們的生產生活一直也以種植水稻為中心,還種植有多種水產蔬菜,河流和稻田里還有許多魚蝦,可謂典型的魚米之鄉。在遠古時期,這種深厚的現實農耕生活很容易產生對太陽的崇拜。
由此不難看出,數千年來一直在西疇湯果村傳承的“女子太陽節”正是壯族及其先民以農耕為主的生產生活方式及其悠久歷史的體現。
(三)它是壯族及其先民頑強堅韌民族精神的現代演繹和傳承
壯族及其先民在長期的稻作農耕生產生活中形成了頑強堅韌的民族精神,這在壯族神話傳說《媽勒訪天邊》《特康射太陽》《布伯》《莫一大王》《艾撤和艾蘇》等都有所反映,這些神話表現了壯族祖先探索自然,與自然、強權作斗爭,追求美好生活的不屈不撓精神。如《艾撤和艾蘇》神話中,為了尋找幸福的斯奧斯波,艾蘇歷經艱險,克服了怪獸餓虎等一個又一個障礙才最終達到了目的地。艾蘇找到樂土后又幾次往返尋找親人,表現了壯族祖先在遷徙過程中的苦難以及為達目的而頑強拼搏、絕不屈服的斗爭精神;又如流傳于桂中流域的《莫一大王》敘事文本說,莫一在與皇帝的斗爭中失敗后,被砍掉的頭還飛上天哈哈大笑,把皇帝的兵馬都嚇退了,死了還化為馬蜂飛到京城去鰲刺皇帝及其部屬,突出表現了壯族英雄祖先敗而不餒、鍥而不舍、百折不撓的堅韌戰斗精神。
這種堅韌不拔的民族精神在秦始皇用兵嶺南的過程中有深刻的體現,《淮南子·人間訓》載:“(秦始皇)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三年不卸甲馳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虜,相置桀駿以為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雎,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6]614以后秦始皇增派大量援兵,前后用了5年時間才最終平定嶺南地區,這比秦朝平定六國過程中任何一國所用的時間都要長,足見壯族先人的頑強。
西疇“女子太陽節”年復一年不斷地演繹和傳承著這種堅韌不拔的民族精神。這里流傳的有關尋找太陽和送太陽重返天空的古老傳說在活動過程中唱誦的《祭祀太陽古歌》中有完整的敘述,大致講述了太陽產生,郎星射太陽,乜星尋找太陽的艱難歷程以及把太陽送上天使光明重返人間,萬物得以再繁衍發展的過程。其中,找回太陽的過程尤為艱難,身懷六甲的乜星主動承擔了這個任務,因為她認為如果自己找不到,自己的孩子還可以按照大家的意圖繼續尋找下去。最終,乜星歷經艱難險阻,一路靠吃野果來充饑,并在途中生了一個女子,母女一塊經過12年時間才找回太陽,最后乜星與其他女性族人化作神鳥背著已經失去法力的太陽重返了天空,大地又迎來了光明。這種為了追求光明,不惜用幾代人的努力不懈追求來實現愿望,在困難面前無所畏懼的精神不正是壯族堅韌不拔民族精神的完美演繹和傳承嗎?
(四)它是壯族女性獨特地位的突出反映和現代延續
歷史上,壯族及其先民的女性地位一直較高,母系氏族時期自不必說,即使進入了男性在社會占支配主導地位的發展階段,直至近代甚至現代社會,壯族社會中的女性文化地位一直是那么顯赫,形成了具有民族個性的文化——女性文化。這個特征在姆六甲創世神話、花婆信仰、祭祀蛙婆的活動以及婚姻家庭中“依歌擇偶”、不落夫家、“入贅婚”等習俗中都得到了很好的體現。[10]在現實生活中,壯族女性也多能擔當重任,支撐起家庭的經濟和文化生活。總的來說,壯族婦女的地位高于當地漢族婦女。[11]136
壯族女性這種獨特的地位在傳承數千年的“女子太陽節”中得到了突出的體現。首先,活動的祭祀對象為“乜星”等四位太陽神鳥;參加者為年滿16歲的女性,男性除了幫助抬供品外,不能參加祭祀儀式,反映了其獨特的女性特征。其次,男性還需承擔這天家中所有的家務,并為參加祭祀活動的女性準備豐盛的晚餐,也不能參加女性的聚餐活動。可以說,在現代男性仍占主導地位的世界里,一直傳承的“女子太陽節”更像是一朵奇葩,綻放出絢爛的光彩。
二、西疇“女子太陽節”的文化意義
(一)有利于提高民族文化自信,增強民族凝聚力
文化自信,從本質來講是一種自覺的心理認同、堅定信念和正確的文化心態,是能夠理解并認同自身文化內涵與價值,并對這種文化的生命力和發展前途充滿信心。文化認知是文化自信的基礎,只有對本民族優秀的傳統歷史文化有清晰而深刻的認知才能產生一種文化的自覺,從而產生對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壯族及其先民創造了燦爛輝煌的文化,但是由于歷史上民族內部支系繁多,沒有建立起統一的民族文化體系,尚未實現民族文化的內部整合以及面對強大的漢文化和現代化的沖擊,一些人對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心有所減弱,這是一個客觀事實。要改變這種狀況,增強對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就需要對優秀的民族傳統文化進行保護、傳承,讓傳統文化得以充分展示,讓大家認知。
“女子太陽節”正是壯族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展演。通過年復一年的頌唱和展示,壯族先人找回太陽,送太陽重返天空,給大眾帶來光明的故事不斷被重復和強調,一種自豪感油然而生,對先人探索自然,追求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為了達到目標與自然堅持不懈斗爭的精神以及在這過程中秉承的與自然和諧的理念都有了充分而深刻的認識,從而增強了對民族文化的自信心。
文化自信是民族認同的根基,民族文化自信提高的同時就能激發大家維護和傳承民族文化的自覺,從而對民族文化產生認同,增強民族凝聚力。通過“女子太陽節”習俗活動,壯族優秀的傳統文化得以傳承,同時以一套完整的儀式,突出了其獨特的女性特征,凸顯了民族文化的特色,促進了人們對民族文化的認同,增強了民族凝聚力。據《春城晚報》記者茶志福調查,湯果村的壯族人都很熱愛自己的民族文化,從小孩到老人都會壯族傳統的歌舞。為了過好“女子太陽節”,在上海、浙江等外地做生意的壯家人都回來了。他認為,在傳統越來越受到現代化沖擊的今天,壯家人能如此認同,積極參與到民族文化的活動中來實屬不易,為了保護自己的傳統文化而人人“沖鋒陷陣”,反映了他們高度的文化自覺。[12]可見,傳承“女子太陽節”對提高民族文化自信,增強民族凝聚力有著重要的意義。
(二)為社會發展提供歷史人文資源,有利于構建和諧與穩定的社會
文化建設是我國構建和諧社會的內在要求,其中一部分重要的工作內容即是對民族傳統文化進行保護和傳承,并在此基礎上不斷創新,增強文化發展的活力。這就需要我們回到傳統的民族歷史文化當中,充分發掘和弘揚優秀的文化遺產,否則一切都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猶如空中樓閣,缺乏穩固的來源和基礎,是不可能長久的。保護和傳承“女子太陽節”可為構建和諧社會提供重要的歷史人文資源,充分挖掘其核心價值,對于當今構建和諧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弘揚民族精神,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具有巨大的借鑒作用。
首先,“女子太陽節”的傳承地湯果村無論在生態環境的選擇還是在祭祀過程中都閃耀著壯族及其先民一直信奉的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天人合一思想。湯果村在村寨的選址上一直遵循著壯族幾千年來的傳統生態觀念,即“以人為本,自然和諧”,村寨建在半山腰上,依山傍水,背靠大山,面對稻田,村前是稻田和河流,村后是森林,講究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湯果村在1956年曾遭受火災,民房全部被燒毀,重建的村寨仍遵循著這一傳統,恢復到被毀前的生態。此外,壯族人信奉“有林才有水,有水才有糧”的觀念,為了保護水資源,他們還以宗教的形式來規范和約束人們的行為。據湯果村的寨老講,壯族人為了保護古樹林木,把創世神“布洛陀”、始祖神“者弘”和太陽神封在村四周的古樹林木上,嚴禁砍伐,年逢祭日,全族舉行祭祀。[12]這種愛護森林,保護生態,與自然和諧相處的良好風尚,既古樸又科學,反映了壯族人天人合一的生態文化理念。
其次,“女子太陽節”一定程度上所體現出的“男女平等”思想內涵有利于家庭和睦,從而為和諧社會提供穩定而堅固的基石。“女子太陽節”是純粹的女人節,男性不僅被排除活動過程,更需承擔活動那天所有的家務,做好晚餐等服務工作。活動第二天,女人仍無需勞作,她們或在家款待賓朋,或結對唱歌,談情說愛。總之,節日的這兩天完全屬于女人,平日辛勞的她們只需享受著節日的快樂和男人們提供的美食等服務。這種形式雖與現代意義上的“男女平等”有一定的距離,但從現實社會中男女地位的差別以及活動過程中為了女人過好自己的節日而把平日由她們承擔的做飯等家務活讓男人承擔,她們只需享受節日快樂的出發點來觀察和思考,“女子太陽節”就更多有了“男女平等”的意蘊。這種“男女平等”的意蘊有利于家庭的健康、和睦,而家庭的和諧健康直接關系到社會的健康和穩定。此外,實現男女平等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保護和傳承“女子太陽節”對我們建設和諧社會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三)可為發展當地旅游提供文化基礎支撐,實現旅游的可持續發展
旅游與文化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改革開放初期,著名經濟學家于光遠就指出:“旅游不僅是一種經濟生活, 而且也是一種文化生活”,“旅游業不僅是一種經濟事業,也是一種文化事業;從旅游資源的角度看, 文化事業的發展也具有決定作用”。[13]可以說,文化是旅游發展的靈魂,是旅游業可持續發展的源泉,是旅游資源的魅力所在,是旅游主體的出發點與歸宿。旅游的各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體現著對文化的應用、旅游產品的品位,反映了策劃、規劃及開發者對文化的理解。只有把旅游與文化緊密結合起來,這樣的旅游產品才更具有生命力。
西疇縣位于云南省東南部,北回歸線橫貫整個縣境,地處“地球生物多樣性黃金十字帶”,氣候宜人,動植物多樣性明顯,這里有植物中的大熊貓“華蓋木”,是珍稀瀕危物種基因庫;這里有晚期智人“西疇人”遺址,是古人類的發源地之一。西疇具有豐富的自然旅游資源。然而,要想實現旅游業的大發展以及可持續發展,其支撐點還是靠文化,特別是有特色的民族文化。
“女子太陽節”就是一項值得深度挖掘的民俗文化,它有著深厚的歷史內涵,起源于母系氏族社會,至今已有數千年的傳承歷史;在世界范圍內的太陽崇拜文化中,其特殊的女性特征更具有唯一性,且其傳承完整、系統而嚴謹。僅憑其獨一無二的女性特征就能引起無窮的好奇心和無數關注的眼光,在發展旅游上大有文章可為。同時,“女子太陽節”的神話傳說表明這里是找回太陽的地方,是太陽鳥母的誕生地。因此,依托當地優美的自然環境,應當大力發掘和宣傳“女子太陽節”文化內涵,結合當地的歷史人文風情,打造適合現代人休閑旅游觀念,能滿足各層次人群消費需求的完整旅游系列產品和產業鏈條,實現旅游業的大發展和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英]愛德華·伯內特·泰勒.原始文化[M]. 連樹聲.譯.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2.
[2][英]麥克斯·繆勒.比較神話學[M]. 金澤.譯.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9.
[3][英]麥克斯·繆勒.宗教的起源與發展[M]. 金澤.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4]何星亮.中國自然神與自然崇拜[M].上海:三聯書店,1992.
[5]高福進.太陽崇拜與太陽神話:一種原始文化的世界性透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6](漢)劉安.淮南子[M].楊有禮.注說.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10.
[7]梁庭望.壯族的稻作文化和社會發展探索[J].文山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6(3):1- 5.
[8]覃乃昌.壯族稻作農業獨立起源論[J].農業考古,1998 (1):316- 321,311.
[9]覃乃昌.“那”文化圈論[J].廣西民族研究,1999(4):40- 47.
[10]邵志忠.傳統文化背景下的壯族女性研究[J].廣西民族研究,2002(4):56- 61.
[11]梁庭望.壯族風俗志[M].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7.
[12]茶志福.“女子太陽節”傳承千年的壯家風情[N].春城晚報,2014- 03- 19(A302).
[13]于光遠.旅游和文化[J].旅游,1981(2):2- 3.
(責任編輯婁自昌)
Historic Connotations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s of Women Sun Festival in Xichou
HUANG Jin-dong
(Library,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Women Sun Festival is an important Zhuang nationality folklore activity with thousands of years’inheritance in Tangguo village, Xisa town, Xichou county of Wenshan Zhuang and Miao Autonomous Prefecture and is in the national lis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presentative projects with its unique female features. It is related to the local physical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roots in Baiyue and their descendants’ long cultures with profound historic connotations, so it plays an important cultural role to inherit and protect Women Sun Festival.
Key words:sun worship; Women Sun Festival; historic connotations; cultural implications
作者簡介:黃金東,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古籍部副研究館員。
收稿日期:2015 - 03 - 28
中圖分類號:K892.318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 - 9200(2015)04 - 0009 - 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