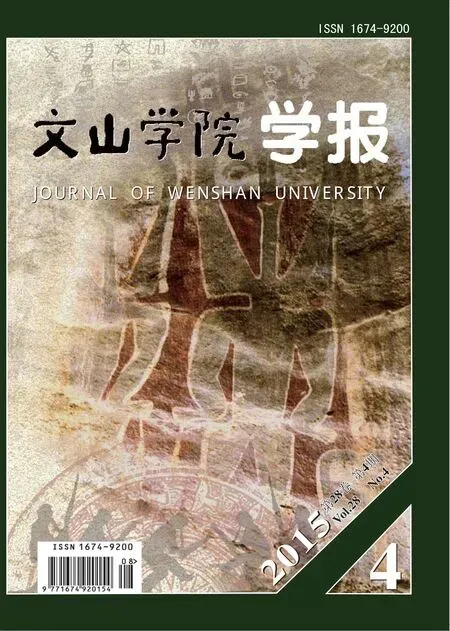女子太陽節與壯族創世史詩的傳承策略
林安寧
(廣西師范學院 文學院,廣西 南寧 530007)
女子太陽節與壯族創世史詩的傳承策略
林安寧
(廣西師范學院 文學院,廣西 南寧 530007)
摘要:西疇縣的女子太陽節中演唱的《祭太陽古歌》,是壯族史詩的活態傳承。口頭詩學理論對于研究壯族史詩起著重要的理論指導作用。《祭太陽古歌》的內容涉及壯族的太陽神話內容,是壯族創世史詩的活態展現,它的形式有獨特的程式特點。女子太陽節應承擔起壯族史詩活態傳承的更大責任,從而獲得更大范圍的關注。
關鍵詞:女子太陽節;《祭太陽古歌》;口頭詩學;活態傳承
西疇縣的女子太陽節是壯族富有特色的地方節日,也是壯族史詩演述的盛會。在祭祀儀式過程中歌唱的《祭太陽古歌》,活態地展示了壯族史詩的豐富內涵。儀式活動與歌唱習俗融為一體,共同演繹了壯族史詩優美詩篇,把壯族的太陽崇拜內容、壯族的優秀歌唱習俗及壯族燦爛的民族文化,生動地展示與傳承在節日里。對于文化越來越趨于同一性的今天,女子太陽節以其生動的史詩演述展示著文化獨特性,給人們帶來獨特的感受與深刻的思考。
一、口頭詩學對壯族史詩的意義
口頭詩學作為研究史詩的最新理論成果,它的影響力與作用已被目前我國史詩界所認可。“口頭程式理論是20世紀美國民俗學重要的理論流派之一,又稱‘帕里—洛德學說’(The Parry- Lord Theory of Oral Composition)。自這一學派的扛鼎之作即洛德(Albert B. Lord)的《故事的歌手》(The Singer of Tales)于1960年面世以來,其理論成果和工作方法已成功地應用到了多達150種語言傳統的學術闡釋中。”[1]國內一批學者把國外的口頭程式理論引進中國,對于推動中國史詩的研究范式轉變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代表性著作有《故事的歌手》[2]《荷馬諸問題》[3]《古代經典與口頭傳統》[4]等等。在論文成果方面,較有代表性的有《史詩的詩學:口頭程式理論研究》[5]《口頭程式理論》(Oral-Formulaic Theory)[1]和《關于口頭傳唱詩歌的研究——口頭詩學問題》[6]等。
壯族的史詩極為豐富,目前已為人知的代表作有《布洛陀經詩譯注》[7]《壯族經詩譯注》[8]和《壯族麼經布洛陀影印譯注》[9]等。對于壯族史詩的研究論文也很多,如針對《布洛陀經詩譯注》和《壯族麼經布洛陀影印譯注》的研究論文就不下幾十篇。其中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嶺南神話解讀》[10]《壯族社會民間信仰研究》[11]《布洛陀——百越僚人的始祖圖騰》[12]等十幾種,論文有《布洛陀文化的典型意義與獨特價值》[13]《古壯字結出的碩果——對〈壯族麼經布洛陀影印譯注〉的初步研究》[14]《口頭傳統田野研究基地的建設與科學管理——以廣西田陽壯族布洛陀文化與口頭敘事田野研究基地為例》[15]《壯族〈布洛陀經詩〉哲學意蘊初探》[16]《云南省馬關縣阿峨新寨祭布洛陀神樹調查》[17]和《壯族摩教文化探析》[18]等數十篇。
一些學者以史詩的理論對壯族史詩進行實踐與研究,取得了較大的成果。中國社科院重視壯族創世史詩的調查與研究,在田陽成立了壯族布洛陀文化與口頭敘事田野研究基地,對于促進“布洛陀口傳史詩”的保護與研究起到了較大作用。劉亞虎的《南方史詩論》[19]全方位考察了南方史詩,但對南方史詩的口頭詩學特征研究還有深入的余地。《神話與詩的“演述”——透視中國南方民族敘事藝術》[20]對南方史詩的“演述”闡述較為深入,但它不是研究南方史詩的專著。梁庭望等著的《布洛陀——百越僚人的人文始祖》[21]和農學冠的《嶺南神話解讀》[10]等專著雖對壯侗苗瑤民族史詩有較多論述,但它們較少涉及口頭詩學理論。在當前的研究形勢下,壯族的史詩研究中,對史詩的翻譯、整理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出現了一批較深入的研究成果,并對史詩的傳承做出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如田陽縣《布洛陀》口傳史詩被批準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但現實是,壯族的史詩演述已逐漸衰退。如《壯族麼經布洛陀影印譯注》中的史詩內容,民間的麼公已幾乎不能唱述,它只是作為手抄本被挖掘、保留下來。另一方面,對于民間還保存著的史詩演述傳統,還需要深入地挖掘①。
所幸的是,隨著壯族民族文化自覺意識的加強,壯族的史詩演述正不斷得到恢復與加強。隨著政府、學者和民眾的合力建設,壯族史詩的演述傳統正以新的面貌得到了傳承。田陽敢壯山的布洛陀口頭史詩的演述,近來已得到了很多學者的關注。而云南省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西疇縣的女子太陽節,《祭太陽古歌》的演述得到了恢復與發展,這對于壯族口頭詩學的研究,無疑提供了一個極好的機會。
二、《祭太陽古歌》是壯族創世史詩的活態傳承
(一)《祭太陽古歌》的太陽神話母題傳承
《祭太陽古歌》作為在女子太陽節上演唱的長篇敘事詩,其內容涉及到壯族的太陽神話內容,是壯族創世史詩的活態展現。《祭太陽古歌》歌唱的是壯族“生太陽”“射太陽”“找太陽”“請太陽”和“祭太陽”的過程。它的每一個情節都是對壯族史詩傳統內容的演繹。在“生太陽”中,古歌唱道:“全年十二個月/才有閑月/閑不過正月/要正月做節日/要二月做祭太陽的日子/哪座山高得觸到星星/天空有星星/到處有太陽/太陽十二個/太陽十二個/一個落下一個升起/一個旋轉一個升起/沒有個遮陰涼/老爺爺去種田/長輩過去耕地/一陣比一陣還熱/一陣比一陣還燙/累了沒有休息時候/累了沒有休息時間”②。古歌中雖沒有直接點明太陽是如何出現的,但它道出了在壯族的神話時空里,曾經有過12個太陽的經歷。太陽太多了,人間炎熱無比。這在壯族有名的史詩《壯族麼經布洛陀影印譯注》的有關史詩異文中,有著類似的敘述。如在《麼荷泰》中就這樣講述:“古時造有十二個太陽/一個落下又一個出來/一個旋轉一個來/一個拉腳一個出”。《祭太陽古歌》中的“射太陽”中唱誦:“老爺爺又商量/婦女又商議/商議射太陽/太陽成一個/太陽成獨個/出外面就害羞/太陽才生氣/賭氣不走村寨/所在地天就不亮/村寨天不亮/所在地沒有雨/天做吃不種/一陣陣做穿不成”。太陽太多了,人們就商量著把多余的11個太陽射下來,只留下一個不射。這樣的敘述,在壯族的口頭文學中都看得到。如《壯族文學發展史》[22]中就提到《特康射太陽》和《郎正射太陽》等韻文體史詩。《壯族麼經布洛陀影印譯注》中的史詩異文《巫兵棹能(naengh)啟科》唱述了阿正射太陽的故事:“阿正會滅火雷王/阿正會殺太陽/人去接阿正來/田地給阿正造好……晚上我制作響喳喳/制作弩三腳/要麻就來搓/拿來搓做繩子/拿來絞做條繩/削標竹做箭/破金竹做弓/射去天上嗖嗖/飛轉去射太陽/射第一次弓/三個它自己落下/六個它自己熄滅/還剩一個孤單/留下吃飯一會再說/留下吃早飯一會就完/王就跪拜連連/王就哀求連連/留下一個曬稻谷/留下一個暖大地”。其敘述內容與《祭太陽古歌》中所述大同小異,也是把多余的太陽射下來,只留下一個照耀人間。至于“找太陽”的內容,古歌中唱述:“老爺爺才想到/婦女才想著/有太陽才行/有太陽才好/相約尋找太陽/來回找了幾年/誰都找不著/老爺爺來商量/婦女又討論/給婦女靈去找/給婦女幫找/婦女去求情/婦女靈去幫找/婦女我們去找/婦女靈還帶孩子/婦女還帶小孩”。由于太陽躲起來了,天地一片漆黑,人們只好把太陽找出來,讓它繼續為人間帶來光明。熟悉壯族民間文學的人都知道,它與壯族的《媽勒訪天邊》的神話內容是大同小異的。著名作家韋其麟還以尋太陽的民間口頭資料創作出著名的詩歌《尋找太陽的母親》。“請太陽”與“祭太陽”的情節,在壯族的民間口頭傳統中,同樣很容易找到。
《祭太陽古歌》的情節內容,是壯族口頭傳統的活態傳承。因而,它把壯族豐富的太陽神話內容,輔以女子太陽節的民俗表演,把人們已熟知的內容,以獨特的活態形式展示,讓人們溫故知新。
(二)《祭太陽古歌》的口頭程式
《祭太陽古歌》篇幅不長,總共400多行。但即使是這幾百多行詩歌中,我們仍讀到很多多次出現的詞語或句式。其中,與壯族其他史詩一樣,數字“十二”很容易引起人們的關注。全詩中一共出現了5次“十二”,即“全年十二個月”,“太陽十二個”(兩次),“找太陽十二年”(兩次)。說全年是十二個月,是受中國農歷歷法的影響,壯族地區同樣使用農歷,這屬于壯族傳統文化的體現。假如說“十二個月”的“十二”屬于知識性的范疇的話,那么“太陽十二個”和“找太陽十二年”,性質就不一樣了。有學者已關注到壯族史詩中經常出現數字“十二”的現象,如《壯族麼經布洛陀影印譯注》的《麼兵布洛陀》中敘述“造十二個部族/下天十二姓/下方十二個部族/云下方十二官/村子十二個王”,這里一口氣出現了5個“十二”。對于壯族史詩中經常出現“十二”的數字,有的學者從數字本身的文化內涵與神秘性的視角出發,得出各種不同的解釋。誠然,這樣的解釋有其合理之處。但以口頭詩學的視角去看,這樣的解釋是不足的。因為口頭詩學理論把詩歌中反復出現的句法叫“口頭程式”,它在詩歌的創編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這些重復出現的單元是高度固定化了的。即使有些許變化,或者是在這些反復出現的短語單元前后附加上某些句法成分,其核心部分或是基本形態也可以輕易辨識出來。這些重復出現的單元,我們把它叫做‘程式’(Formula)”[23]136。
由此思路展開,我們在《祭太陽古歌》中還可以看到更多程式化的內容。如“老爺爺又商量/婦女又商議”“三婦女又商量/三婦女又商議”“三婦女才商量/四婦女才商議”“四婦女聰明/四婦女有智慧”等詩句形成了“老爺爺XXX/婦女XXX”,“XXX又(才)商量/XX又(才)商議”“三(四)婦女XXX/四婦女XX”等口頭程式。“一個落下一個升起/一個旋轉一個升起”“一陣比一陣還熱/一陣比一陣還燙”等形成了“一XXX一XXX/一XXX 一XXX”的句式。如果我們留意更多的壯族史詩,以《祭太陽古歌》與之對比,我們還能發現更多的程式,如詩歌開頭與結尾的程式,詩歌對天地修飾語的程式等等。結合《祭太陽古歌》的錄像資料,我們還發現其演唱過程中經常出現襯詞。這些襯詞作為歌唱的一部分,它對于詩歌的完成也有著不可缺失的意義。
當然,我們只有對更多歌手的演唱作反復的記錄,才有可能更深入地研究《祭太陽古歌》。在壯族的演述傳統里,每次的演唱都是一個全新演繹,不能就目前重點整理的對象作為一個標準的文本。③在口頭詩學理論視野下,史詩的文本不局限于某一個固定的文本作為權威的版本。正如朝戈金指出,“書面文學研究的出發點,往往是一個‘權威的精校本’。但是,若是帶著這樣的思維定勢著手口傳史詩的研究,則無疑會大失所望。首先,我們特別想強調的一點是,活形態的口傳史詩,并沒有一個所謂‘權威本’。”[23 ]72以壯族的創世史詩為例,盡管《布洛陀經詩譯注》《壯族經詩譯注》和《壯族麼經布洛陀影印譯注》等文本的整理出版,對于研究壯族創世史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但所有文本都是壯族史詩的一個演述版本。對于《祭太陽古歌》而言,同樣不可能就某一個文本就窮盡其演唱的文化內涵。
此外,壯族的民間歌唱傳統中的格律要求,如何影響著《祭太陽古歌》的創編,也是一個有待深入研究的內容。
三、女子太陽節對壯族創世史詩的活態傳承策略
(一)更為全面的調查與存檔
在全球而言,口傳文化正面臨著消失的危險。因而,非物質文化遺產搶救、保護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著。各民族對史詩的保護經驗,對于《祭太陽古歌》的傳承,以及更多壯族史詩的保護,有著極為深刻的啟發意義。
政府在保護口傳史詩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以赫哲族的伊瑪堪的保護為例,赫哲族的伊瑪堪于2011年11月23日被列入聯合國“急需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這個瀕臨消失的說唱說書形式,由于得到了政府的重視和赫哲族傳承人的努力,現在已培養出幾百個學員,使得這一說唱藝術得到發揚光大。
壯族的史詩保護也得到了社會各界,特別是政府的高度重視。田陽縣申請的“布洛陀”口傳史詩,被納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從而得到了有效的保護與傳承。壯族的史詩非常豐富,西疇縣的“女子太陽節”作為國家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逐漸被社會各界所認可,但還有很多的保護工作需要進一步的完善。其中包括對傳承人分布的調查,傳承人資料的完善,《祭太陽古歌》與民間麼教的關系的調查,西疇縣麼公的調查,西疇縣歌唱習俗的調查等等。除了全面的調查,保存大量的錄像、錄音、文字資料,可為學者的深入研究打下基礎,也可為政府的進一步決策提供可靠的依據。
(二)更為深入的史詩研究
西疇的女子太陽節中歌唱的《祭太陽古歌》,是壯族史詩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對《祭太陽古歌》的研究,還要在不同時期,對不同的傳承人演唱的過程作全面分析,才能更準確地把握其史詩演唱與壯族民俗和壯族歌唱傳統的關系。《祭太陽古歌》與其他壯族史詩之間存在著的千絲萬縷的關系需要進一步的梳理。《祭太陽古歌》與民間麼教經文的關系非常密切,因而,要研究好《祭太陽古歌》,需要對壯族的麼教傳統有較深刻的把握。此外,壯族的歌唱傳統與《祭太陽古歌》的關系,也需要得到更多學者的關注。
(三)傳承人和傳承環境的保護
女子太陽節作為壯族的重要文化活動,還應當承擔更多的責任。不僅在祭拜活動中歌唱《祭太陽古歌》,還可以在節日前后通過舉辦壯族史詩演唱比賽,壯族史詩傳承人培訓班等活動,促使更多的歌手參與到史詩的傳承當中,以此促進傳承環境的進一步改善。壯族的史詩傳承環境,與壯族的民間信仰有著天然的聯系。壯族史詩以創世史詩為主,創世史詩又被稱為神話史詩。神話內容與民間信仰互為一體,不可分割。要傳承壯族史詩,各界人士,特別是政府人員,應該尊重民間信仰的傳承人,特別是麼公在傳承史詩中的重要作用。只有重視民間麼公的文化傳承地位,才能全面地對麼公的歌唱文本進行記錄,才能客觀、準確地研究壯族史詩,也因此才能為壯族史詩的傳承與發揚作出更大的貢獻。若能如此,女子太陽節也必定能被更多人所關注。
總之,以女子太陽節為契機,以保護《祭太陽古歌》為突破口,傳承更多的活態史詩,這對于壯族史詩,甚至整個南方史詩文化而言都是一個極大的貢獻。
注釋:
① 這方面的工作,也有一些學者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如《壯族巫信仰研究與右江壯族巫辭譯注》(黃桂秋著,黃桂秋、覃建珍、韋漢成采錄、譯注.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2012)一書,即對壯族的巫辭演述過程作了較詳細的記錄,并對巫詞作了記錄、翻譯。
② 文中所引述《祭太陽古歌》內容均來自于西疇縣政府所提供的資料。由中央民族大學李錦芳老師及他的研究生記錄,翻譯。筆者根據資料的直譯內容作了意譯。
③ 在西疇縣政府與中央民族大學李錦芳和他學生的共同努力下,《木蘭谷》出版了《祭太陽古歌》(西疇縣文學藝術界聯合全主辦,2015年第1期,第60- 92頁)的8篇異文,這都是進一步研究的重要材料。
參考文獻:
[1]朝戈金,巴莫曲布嫫.“口頭程式理論”(Oral- Formulaic Theory)[J].民間文化論壇,2004(6):91- 93.
[2][美]阿爾伯特·貝茨·洛德.故事的歌手[M]. 尹虎彬.譯.北京:中華書局,2004.
[3][匈]格雷戈里·納吉.荷馬諸問題[M].巴莫曲布嫫.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
[4]尹虎彬.古代經典與口頭傳統[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5]尹虎彬.史詩的詩學:口頭程式理論研究[J].民族文學研究,1996(3):86- 94.
[6]朝戈金.關于口頭傳唱詩歌的研究——口頭詩學問題[J].文藝研究,2002(4):99- 101.
[7]張聲震.布洛陀經詩譯注[M].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1.
[8]何正廷.壯族經詩譯注[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
[9]張聲震.壯族麼經布洛陀影印譯注[M].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2004.
[10]農學冠.嶺南神話解讀[M].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2000.
[11]黃桂秋.壯族社會民間信仰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12]梁庭望,廖明君.布洛陀:百越僚人的始祖圖騰[M].北京:外文出版社,2005.
[13]劉亞虎.布洛陀文化的典型意義與獨特價值[J].廣西民族研究,2005(2):91- 96.
[14]梁庭望.古壯字結出的碩果——對《壯族麼經布洛陀影印譯注》的初步研究[J].廣西民族研究,2005(1):79- 87.
[15]李斯穎.口頭傳統田野研究基地的建設與科學管理——以廣西田陽壯族布洛陀文化與口頭敘事田野研究基地為例[J].社會科學管理與評論,2009(2):26- 34.
[16]徐贛麗.壯族《布洛陀經詩》哲學意蘊初探[J].廣西民族研究,1998(2):38- 43.
[17]王明富.云南省馬關縣阿峨新寨祭布洛陀神樹調查[J].文山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3(1):13- 15,18.
[18]何正廷.壯族摩教文化探析[J].文山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5(1):10- 16.
[19]劉亞虎.南方史詩論[M].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9.
[20]劉亞虎.神話與詩的“演述”——透視中國南方民族敘事藝術[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21]梁庭望,等.布洛陀——百越僚人的人文始祖[M].北京:外文出版社,2005.
[22]周作秋,黃紹清,歐陽若修,覃德清.壯族文學發展史[M].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7.
[23]朝戈金.口傳史詩詩學:冉皮勒《江格爾》程式句法研究[M].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0.
(責任編輯婁自昌)
主持人語:邊疆史地是一個涵蓋面較廣的領域。本期欄目的文章豐富多彩,體現了邊疆史地研究的多樣性。《試論云南各民族的人文精神》提出,愛國、寬厚、求實、企穩是云南各民族人文精神的集中體現,進而分析這一人文遺產的形成過程。《邊疆經略與交通變遷的互動》評述新書《中國西南邊疆古代交通格局變遷研究》,肯定該書采用長時段、整體史的方法,深入研究了邊疆經營與交通變遷的互動關系。《略論金代東北土地制度與農業發展》認為,金朝統治者根據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原則,在轄地實行不同的土地制度并取得成功。《南明與緬甸關系中的幾個問題(1649~1662年)》,考證南明是否在緬甸東部征稅、南明與緬甸東吁王朝是否存在宗藩關系、咒水之難是突發事件還是有預謀屠殺,對了解南明與緬甸的關系有參考價值。《從史料探究中國歷史時期孔雀的地理分布》,根據二十四史與其他史籍,認為古代孔雀廣泛分布在中國的西南部與東南部,以及越南、柬埔寨、印度、印尼等國,西域也有出產孔雀的記載。
主持人簡介:方鐵(1949- ),男,云南大學民族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2000年主持籌建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任中心主任兩屆。研究方向:中國西南邊疆史、民族史與邊疆歷史地理。
Women Sun Festival and Strategies for the Inheritance of Zhuang Nationality Epic
LIN An-n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Guangxi Normal College, Nanning 530007, China)
Abstract:Song Sacrifi ced to Sun sung in Women Sun Festival in Xichou county is a kind of live inheritance of Zhuang epic. The oral poetry theor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oretical guidance on Zhuang epic research. The content of Song Sacrifi ced to Sun is related to Zhuang’s Sun myths, and is live representation of Zhuang’s world creation epic featured with unique procedure characteristics. Women Sun Festival should bear more responsibilities in inheriting Zhuang epic and thus attracts more attention.
Key words:Women Sun Festival; Song Sacrifi ced to Sun; oral poetry; live inheritance
作者簡介:林安寧,廣西師范學院文學院講師,博士。
基金項目:廣西高校科學技術研究項目“壯族創世史詩活態研究”(KY2015LX214)。
收稿日期:2015 - 04 - 13
中圖分類號:K892.318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 - 9200(2015)04 - 0014 - 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