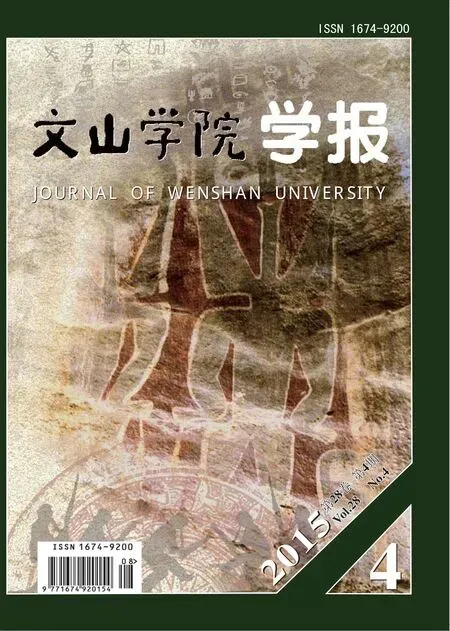探尋西南古老的神話王國——李子賢活形態(tài)神話研究述評
陳丹
(貴州師范學(xué)院 歷史與社會學(xué)院,貴州 貴陽 550018)
探尋西南古老的神話王國
——李子賢活形態(tài)神話研究述評
陳丹
(貴州師范學(xué)院 歷史與社會學(xué)院,貴州 貴陽 550018)
摘要:李子賢先生是自20世紀(jì)70年代末中國神話學(xué)復(fù)興以來涌現(xiàn)出的成就卓越的職業(yè)神話學(xué)家之一。他長期致力于西南少數(shù)民族活形態(tài)神話的研究,以其嚴(yán)謹(jǐn)?shù)膶W(xué)風(fēng)、務(wù)實的精神和深厚的學(xué)養(yǎng)為中國的神話體系的建構(gòu)作出了杰出的貢獻(xiàn)。其學(xué)術(shù)思想和理論成果值得我們認(rèn)真學(xué)習(xí)和總結(jié)。
關(guān)鍵詞:活形態(tài)神話;研究;述評
自20世紀(jì)三四十年代,人類學(xué)功能主義學(xué)派神話理論傳入我國后,活形態(tài)神話研究也隨中國民族學(xué)的拓展而得以迅速興起。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的30年中,由于意識形態(tài)的原因,中國的神話學(xué)研究成為階級斗爭的工具,神話研究被迫處于停滯狀態(tài)。改革開放以后,隨著神話學(xué)獨立學(xué)科地位的恢復(fù)和大規(guī)模民間文學(xué)普查工作的開展,中國活形態(tài)神話的研究也進(jìn)入了一個新的繁榮時期。以李子賢、張振犁、富育光、孟慧英、刑莉、楊利慧等為代表的中國新一代神話學(xué)者在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指導(dǎo)下,以銳意開拓的精神和求真務(wù)實的態(tài)度,在廣泛學(xué)習(xí)借鑒西方神話學(xué)理論和20世紀(jì)三四十年代中國學(xué)者研究成果的基礎(chǔ)上,對豐富的中國活形態(tài)神話資源進(jìn)行了深入、細(xì)致的研究,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活形態(tài)神話研究范式,豐富和發(fā)展了馬林諾夫斯基的活形態(tài)神話理論,把活形態(tài)神話的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李子賢先生是這個浪潮中重要的領(lǐng)軍人物。他長期致力于西南少數(shù)民族神話——尤其是活形態(tài)神話的研究,為中國神話體系的構(gòu)建作出了杰出貢獻(xiàn)。
一、李子賢先生活形態(tài)神話研究的主要內(nèi)容
李子賢先生自20世紀(jì)60年代初起,就開始致力于民族文學(xué)的研究。在長達(dá)半個世紀(jì)的辛勤探索中,他始終堅持田野考察,勤于思考。從20世紀(jì)70年代中后期起,他又開始與鐘敬文、袁珂、伊藤清司、君島久子等中外神話學(xué)家進(jìn)行廣泛的接觸和交流,這使他對中國神話的內(nèi)涵有了更深刻的理解。1979年8月,李子賢先生在西北民族大學(xué)學(xué)報上發(fā)表《活形態(tài)神話芻議》,標(biāo)志著他的研究從此進(jìn)入神話學(xué)領(lǐng)域。1987年8月,李子賢先生在《思想戰(zhàn)線》第六期上發(fā)表了《論佤族神話——兼論活形態(tài)神話的特征》一文,引起國內(nèi)外學(xué)術(shù)界的關(guān)注。次年,李先生在《思想戰(zhàn)線》第一期上發(fā)表了活形態(tài)神話研究的重要成果——《試論云南少數(shù)民族洪水神話》,贏得同行們的贊賞,奠定了他在新時期中國神話學(xué)研究中的地位[1]。此后,李先生成果不斷,很多思想和見解對中國神話學(xué)的發(fā)展都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
綜觀李先生活形態(tài)神話研究的學(xué)術(shù)實踐活動,除了對具體的神話進(jìn)行深入的研究以外,他還對活形態(tài)神話基礎(chǔ)理論研究及活形態(tài)神話的跨文化比較研究進(jìn)行了卓有建樹的嘗試和探索。這些極富成就的研究主要圍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
(一)對神話與文化生態(tài)環(huán)境相互關(guān)系的探索
將神話置于特定的文化生態(tài)環(huán)境中加以考察,重視對神話與文化生態(tài)環(huán)境的互動關(guān)系的思考與探索一直是李先生神話研究的一個重要方法,也是他自覺地學(xué)習(xí)和借鑒英國功能學(xué)派神話理論加以運用并最終實現(xiàn)了對該理論的豐富和發(fā)展的重要方面。早在1987年發(fā)表的《論佤族神話——兼論活形態(tài)神話的特征》一文就體現(xiàn)了這種思想萌芽。該文運用西方神話學(xué)理論,尤其是馬林諾夫斯基功能主義神話學(xué)理論對佤族諸多神話與獵頭習(xí)俗之間的關(guān)系進(jìn)行剖析,進(jìn)而對活形態(tài)神話的產(chǎn)生、保存、發(fā)展與社會經(jīng)濟(jì)、生產(chǎn)力發(fā)展?fàn)顩r、社會信仰、歷史文化的關(guān)系,活形態(tài)神話與民族節(jié)日、宗教儀式的緊密聯(lián)系以及神話形態(tài)與心理機(jī)制的關(guān)系等等問題進(jìn)行了探討。他不僅將神話置放在一定的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文化生態(tài)環(huán)境中來考察,而且突出了社會生產(chǎn)力在神話產(chǎn)生與發(fā)展中的基礎(chǔ)性作用。這種研究方法既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為指導(dǎo),又繼承了馬林諾夫斯基神話理論的合理成分,在活形態(tài)神話研究方面是一個了不起的突破。李子賢先生這一學(xué)術(shù)成就很快引起了國際同行的關(guān)注。為此,當(dāng)時的日本神話學(xué)研究權(quán)威刊物就設(shè)專節(jié)進(jìn)行了介紹。
近年來,隨著田野調(diào)查和研究的深入,李子賢先生對該問題又有了更為深刻的認(rèn)識。他認(rèn)為,要想準(zhǔn)確把握神話的本質(zhì)特征,就必須從整體上,動態(tài)地把握各種神話形態(tài)之間的聯(lián)系及其與文化生態(tài)系統(tǒng)的相互關(guān)系。“如果我們把神話視為一個處于變化狀態(tài)中的‘活體’,那么,神話賴以存活的文化生態(tài)系統(tǒng)就是‘母體’。‘活體’與‘母體’之間總是互相依存、互相制約,處于某種平衡、協(xié)調(diào)狀態(tài)。在很多情況下,當(dāng)‘母體’發(fā)生某種變化時,‘活體’總是及時地調(diào)整自己,改變自己,以適應(yīng)‘母體’的變化。一旦‘活體’賴以存活的‘母體’消失,‘活體’也就無安身立命之地了。然而,神話作為族群價值體系的表征,它又有維系乃至強(qiáng)化‘母體’存在的功能”[2]。他的這種認(rèn)識既吸收了馬林諾夫斯基關(guān)于神話在社會生活中起著維系和強(qiáng)化功能的觀點的合理成分,同時又比較客觀地反映了神話與文化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動態(tài)關(guān)系。為我們動態(tài)地分析和認(rèn)識神話的本質(zhì)特征和發(fā)展、流變規(guī)律提供了一個有力的借鑒。
(二)對神話存在形態(tài)的研究
神話形態(tài)的劃分是一個重要的學(xué)術(shù)問題。由于歷史的原因,泰勒把對神話的研究的焦點集中在文明社會中的“遺留物”和原始民族的心理狀態(tài)——“萬物有靈觀”去探尋神話的內(nèi)涵,而馬林諾夫斯基則由于對神話所作的田野考察僅限于單一的、無文字的、生產(chǎn)力十分低下的島民社會,因而都沒有對神話的形態(tài)進(jìn)行必要的劃分。李子賢先生從西南民族多元文化及各自發(fā)展?fàn)顟B(tài)的客觀實際情況出發(fā),堅持理論與實際相結(jié)合的原則,對數(shù)十年田野考察獲得的第一手材料進(jìn)行深入研究,實現(xiàn)了對神話形態(tài)認(rèn)識的突破。他認(rèn)為,由于自然環(huán)境的立體性、經(jīng)濟(jì)形態(tài)的多樣性、文化基因的豐富性、族群構(gòu)成的復(fù)雜性等因素,導(dǎo)致西南少數(shù)民族在社會發(fā)展階段上的參差不齊和文化的多元性,也致使西南少數(shù)民族神話的存在狀態(tài)呈現(xiàn)出錯綜復(fù)雜的特征。他們傳承的神話里不僅可以找到與克羅布里恩德島民社會中存在的類似的那種“原始的”活形態(tài)神話,而且還能找到已步入文明社會的有文字民族才可能具有的文獻(xiàn)神話,以及介于二者之間的口承神話。
李子賢教授進(jìn)一步分析論述了它們各自的特點,首次界定了活形態(tài)神話的基本概念并明確提出活形態(tài)神話是神話的典型形態(tài)的重要觀點。他指出,活形態(tài)神話是“與特定的社會組織、生產(chǎn)方式、宗教信仰、生活習(xí)俗等保持著緊密的有機(jī)聯(lián)系,并被人們視為‘圣經(jīng)’而具有神圣性、權(quán)威性的神話”。[3]83“如果將活形態(tài)神話視為神話的主體,那么其他各種存在形態(tài)的神話則是這一主體的變體。”[4]他從本體論的角度分析神話的基本結(jié)構(gòu),將神話的內(nèi)在結(jié)構(gòu)劃分為外殼、中質(zhì)和內(nèi)核三大系統(tǒng)。認(rèn)為“活形態(tài)神話從屬并獨特地表現(xiàn)著一定的文化這個大的系統(tǒng)。……上述各部分之間,存在著有機(jī)聯(lián)系,體現(xiàn)著這個大的文化系統(tǒng)的整體性、綜合性、動態(tài)性特征”[3]87。他將文獻(xiàn)神話與活形態(tài)神話的內(nèi)在結(jié)構(gòu)進(jìn)行比較研究,加深了我們對活形態(tài)神話內(nèi)在規(guī)律的認(rèn)識。這些認(rèn)識對于當(dāng)時的中國神話學(xué)界來講是十分了不起的突破。
近年來,李先生通過對各種生活形態(tài)的神話的考察,以及對各種文獻(xiàn)神話的辨析,對這個劃分標(biāo)準(zhǔn)進(jìn)行了反思和進(jìn)一步的補(bǔ)充、深化,將西南少數(shù)民族神話劃分為:“(1)與宗教祭儀緊密關(guān)聯(lián)、與信仰系統(tǒng)完全重合而在祭儀中展演的神話……(2)在喪葬儀式上由祭司吟誦的神話……(3)在傳統(tǒng)社會中,通過老人(歌手)講述(吟唱)出來,指導(dǎo)人們規(guī)范思想、行為模式的神話……”等9個存在形態(tài)[2]。這種劃分有助于我們從動態(tài)的眼光來認(rèn)識神話的本質(zhì),彌補(bǔ)了過去劃分標(biāo)準(zhǔn)的不足。他對神話9個生活形態(tài)的劃分的歸納牢固地植根于第一手材料,具有極強(qiáng)的說服力。從這個角度來看,在神話的形態(tài)劃分問題上,李子賢先生發(fā)展了馬林諾夫斯基的神話理論并實現(xiàn)了活形態(tài)神話理論的中國化,使得我們可以以更廣闊的視野、動態(tài)的眼光去審視神話,探究其發(fā)展演化的規(guī)律,揭示其內(nèi)部特征。此外,他還從神話結(jié)構(gòu)的歷時性變化和總體上的多向度發(fā)展演進(jìn)兩個維度對神話的動態(tài)結(jié)構(gòu)進(jìn)行了詳細(xì)考察和深入的分析,糾正了馬林諾夫斯基因過于注重對神話在現(xiàn)實中社會功能的考察,從而靜態(tài)地、客觀地、共時地觀察、研究神話,卻忽視其主觀性和動態(tài)性所帶來的形而上學(xué)的偏頗。
(三)活形態(tài)神話的跨文化比較研究
比較研究是神話學(xué)傳統(tǒng)的研究方法,也是探索神話文化內(nèi)涵和發(fā)展規(guī)律的有效手段。李先生將比較研究法運用于日本“記紀(jì)神話”與中國西南少數(shù)民族活形態(tài)神話的比較研究,去復(fù)原和發(fā)掘神話的原初形態(tài)。他在《固定了的神話與存活著的神話——日本“記紀(jì)神話”與中國云南少數(shù)民族神話之比較》一文中對中日神話進(jìn)行了比較。他認(rèn)為,中國西南與日本存在著許多共同的古文化要素及神話母題,西南少數(shù)民族至今仍存活著吟誦出來的神話史詩,與“記紀(jì)神話”有某些相似之處,二者不僅在內(nèi)容上有許多共同特點,而且都具有若干活形態(tài)神話的特征。“云南與日本曾經(jīng)有著相似的自然生態(tài)系統(tǒng)與文化生態(tài)系統(tǒng),因此,我們可以借助于云南少數(shù)民族的活形態(tài)神話還原日本‘記紀(jì)神話’寫定前后的原始面貌和存活形態(tài)”[4]。這種根據(jù)后進(jìn)地區(qū)活形態(tài)神話的文化生態(tài)環(huán)境與活形態(tài)神話的關(guān)系,通過對照兩個分屬不同民族但有著大致相同內(nèi)容的神話,來復(fù)原處于先進(jìn)文化發(fā)展階段的民族在遠(yuǎn)古時代社會面貌的基本特征及活形態(tài)神話在寫定前的基本形態(tài)的做法,是在新的社會歷史文化背景下對古典進(jìn)化論學(xué)派“以今證古”學(xué)術(shù)主張的一次有益嘗試。但李先生對研究材料的選取、運用和對結(jié)論的總結(jié)始終秉持了科學(xué)而謹(jǐn)慎的態(tài)度,堅持大膽設(shè)想小心求證的精神,在方法上具有很大的啟發(fā)意義,觀點獨到,結(jié)論令人信服。
(四)活形態(tài)神話研究的新型多維視角的開啟
神話是綜合性極強(qiáng)的古老文化事象。神話的這種本質(zhì)特征在西方很早就為人們所洞悉。數(shù)百年來,很多學(xué)者都曾對此問題進(jìn)行深入的探討。他們從神話學(xué)、社會學(xué)、民俗學(xué)、宗教學(xué)、考古學(xué)、歷史學(xué)等不同學(xué)科對神話進(jìn)行文化內(nèi)涵的詮釋與探討,取得了可喜成就。神話學(xué)進(jìn)入中國后,受到中國傳統(tǒng)文字學(xué)、音韻學(xué)、訓(xùn)詁學(xué)的影響,中國神話研究獲得了更多用于綜合研究的方法和手段。這些研究方法本身是具有科學(xué)性的,也是將來神話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研究方法。但是,長期以來,人們忽視了神話的存在狀態(tài)、動態(tài)結(jié)構(gòu)與文化生態(tài)環(huán)境的動態(tài)變化對神話流傳、變異的重要影響。因而神話學(xué)的研究一直缺乏一種將本體論、認(rèn)識論與方法論相結(jié)合,對神話多學(xué)科研究方法的綜合應(yīng)用進(jìn)行行之有效的整合的學(xué)術(shù)視角。長達(dá)半個世紀(jì)的辛勤探索使李先生對該問題有了深刻的認(rèn)識。他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chǔ)上,結(jié)合自己在田野中獲得的第一手資料進(jìn)行了細(xì)致、深入的研究與思考。他提出:要把握神話的特質(zhì),就必須從整體上,動態(tài)地對神話進(jìn)行考察。具體而言,就是要“關(guān)注神話的存在形態(tài)、動態(tài)結(jié)構(gòu)以及二者與文化生態(tài)系統(tǒng)的關(guān)系”[2]。他將活形態(tài)神話放在全部形態(tài)的整體背景下考察,既關(guān)注到了活形態(tài)神話與其他形態(tài)神話之間的聯(lián)系,也考慮到了其自身的特質(zhì)。尤其是對神話的存在形態(tài)也作了層次上的劃分,為因過去總是只從自身的研究領(lǐng)域出發(fā),固步自封地研究神話而一直被“神話何為”這一問題長期困擾的神話研究者們提供了一個可供借鑒的研究思路。此外,李先生通過對各種生活形態(tài)的神話的考察,以及對各種文獻(xiàn)(書面)神話的辨析,總結(jié)了神話的9種形態(tài),并分別從神話的載體與分類、神話的構(gòu)成要素、神話與文化生態(tài)的關(guān)系、神話發(fā)展的內(nèi)在規(guī)律與外在制約因素等角度對神話,尤其是活形態(tài)神話的特質(zhì)與發(fā)展變化規(guī)律進(jìn)行了認(rèn)真細(xì)致的分析,一定程度上彌補(bǔ)了馬林諾夫斯基因過分強(qiáng)調(diào)神話的社會功能而忽視了社會文化生態(tài)環(huán)境變遷對神話發(fā)展的影響而帶來的理論上的缺陷。
李先生在《存在形態(tài)、動態(tài)結(jié)構(gòu)與文化生態(tài)系統(tǒng)——神話研究的多維視角》[2]一文中總結(jié)了神話的6大要素特征,并在此基礎(chǔ)上進(jìn)一步提出了活形態(tài)神話的界定標(biāo)準(zhǔn),“活形態(tài)神話相對于其他存在形態(tài)的神話而言,則具備了神話的各種要素及最基本的特征,如果將活形態(tài)神話視為神話的主體,那么,其他各種形態(tài)則是這一主體的變體”[2]。這個界定標(biāo)準(zhǔn)的提出體現(xiàn)了李子賢教授對活形態(tài)神話本質(zhì)特征認(rèn)識的深入,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此外,文中突出了信仰體系和價值取向在神話黏和文化生態(tài)環(huán)境過程中的核心地位。這些觀點為我們在動態(tài)結(jié)構(gòu)中把握神話的精神實質(zhì)提供了一個有力的借鑒。在該文中李先生以田野調(diào)查獲得的第一手材料為依據(jù),運用了唯物辯證法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方法分析神話的發(fā)展運動規(guī)律及其內(nèi)外動因,尤其是神話的存在形態(tài)與文化生態(tài)的相互聯(lián)系。文章資料詳實、豐富且具有代表性。該文的面世標(biāo)志著李子賢先生的思想理論水平又發(fā)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是近年來神話學(xué)基礎(chǔ)理論研究領(lǐng)域難得的上乘之作。
二、李子賢先生活形態(tài)神話研究的重要特色
(一)始終堅持對神話典型形態(tài)的研究
李子賢長期從事西南少數(shù)民族神話的研究。他對研究對象本質(zhì)屬性的認(rèn)識是十分清楚的。他始終獨立思考,實事求是,堅持將“活形態(tài)神話”作為神話的典型形態(tài)來研究。早在20世紀(jì)80年代初,當(dāng)國內(nèi)外大多數(shù)學(xué)者還在“中國神話貧瘠論”的誤導(dǎo)下埋頭漢族文獻(xiàn)神話資料的梳理、校刊和考證的工作時,他就明確提出了這一重要的觀點。李先生獨到而清醒的認(rèn)識使他避免了其他非科學(xué)的神話研究思想對他的干擾,也讓他的研究始終保持著青春與活力。這種認(rèn)識是十分可貴的,在國內(nèi)是十分少見的。李先生的這一科學(xué)認(rèn)識已被30多年來中國神話學(xué)研究的曲折發(fā)展歷程所證實。由此,李子賢先生被學(xué)術(shù)界譽(yù)為“西南活形態(tài)神話研究第一人”。
(二)深耕本土,視野廣闊
在研究方法上李子賢先生具有廣闊的學(xué)術(shù)視野,他始終堅持并強(qiáng)調(diào)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思想,從宏觀上把握西南民族文化的起源與各個族系之間文化的交流、融匯,進(jìn)而把西南少數(shù)民族神話王國的探尋納入到中華民族文化史的總體格局中加以認(rèn)識。
基于對云南本土文化的熱愛及其在東亞、東南亞古文化體系中特殊地位的深刻認(rèn)識,使得李子賢的學(xué)術(shù)研究具有濃郁的地方特色。熟悉李先生學(xué)術(shù)著作或治學(xué)經(jīng)歷的人都能強(qiáng)烈地感受到他學(xué)術(shù)研究的這一重要特色。他常告誡學(xué)生:只有深耕本土,才能放眼世界。必須把認(rèn)識本土的文化作為一個支撐點,并在此基礎(chǔ)上不斷拓展自己的學(xué)術(shù)視野。李先生近年的很多高水平的重要著作和論文,如《探尋一個尚未崩潰的神話王國》(1991年)、《多元文化與民族文學(xué)》(主編,2001年)、《東亞文化格局中的云南文化》(1999年)、《被固定了的神話與存活著的神話——日本“記紀(jì)神話”與中國云南少數(shù)民族神話之比較》(2000年)、《沖繩神女組織探源——沖繩神女與云南少數(shù)民族祭司的比較》(2001年)、《存在形態(tài)、動態(tài)結(jié)構(gòu)與文化生態(tài)系統(tǒng)——神話研究的多維視點》(2006年)等等,都是來源于他長期立足本土文化的研究和對本土文化的珍愛、熟知、厚積薄發(fā)的結(jié)果。
(三)勤于田野調(diào)查,重視實踐
對于神話學(xué)研究來講,田野調(diào)查不僅是研究方法,更是方法論的問題。在研究過程中,基于西南少數(shù)民族神話的實際情況、活形態(tài)神話的本質(zhì)特征和運動規(guī)律的深刻認(rèn)識,他廣泛運用了田野調(diào)查方法。從1962年起至今,除因政治原因被剝奪了學(xué)術(shù)研究的機(jī)會外,在其余的時間里,即使在十分艱苦的歲月中,只要條件允許,李先生就始終不渝地堅持對民族文學(xué)進(jìn)行田野調(diào)查。李先生還曾經(jīng)多次到國外進(jìn)行田野考察:日本本島及沖繩地區(qū)、美國印地安保留地及中南半島都留下了他的足跡。直到現(xiàn)在,雖年過70,仍不辭辛勞地奔走于祖國西南的山山水水。這充分體現(xiàn)了李先生嚴(yán)謹(jǐn)、求實的科學(xué)態(tài)度和獻(xiàn)身科學(xué)的寶貴精神。李先生在田野調(diào)查上傾注了大量的心血,這在國內(nèi)同行中是極為罕見的。
(四)博采眾長、獨立思考又與時俱進(jìn)
李先生對神話的研究不僅學(xué)習(xí)、繼承了西方的神話學(xué)理論和方法,還繼承、吸收了“五·四”以來中國神話研究取得的研究成果。也學(xué)習(xí)、借鑒了日本、韓國、港臺及東南亞等地區(qū)同行們的治學(xué)經(jīng)驗,更自覺學(xué)習(xí)和掌握了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理論方法。在研究過程中,他從不附和他人的學(xué)術(shù)觀點,而是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xué)態(tài)度,明辨是非,汲取精華,棄其糟粕,走自己的路。這使得他的研究始終保持著旺盛的學(xué)術(shù)生命力。
李子賢先生神話研究不僅具有宏觀的學(xué)術(shù)視角,而且具有微觀的精細(xì)周密的思辨。既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dǎo)地位,又善于運用相關(guān)學(xué)科的理論、方法對神話進(jìn)行綜合研究。在他的研究過程中,不僅可以看到他對西方人類學(xué)各學(xué)派理論和研究方法的諳熟,也可以看到他對其他西方社會科學(xué)的深厚學(xué)養(yǎng):歷史學(xué)、社會學(xué)、考古學(xué)、生態(tài)學(xué)、文化學(xué)、宗教學(xué)、文學(xué)……只要有利于促進(jìn)神話研究發(fā)展的理論與方法,李先生總是以包容的胸襟,打破學(xué)科之間的藩籬加以學(xué)習(xí)和借鑒,這使得他的研究立論新穎,視角獨特,有較強(qiáng)的理論穿透力,體現(xiàn)了李先生廣闊的學(xué)術(shù)視野、巨大的理論勇氣和勇于探索的可貴精神。從大學(xué)時代起,李先生就在著名學(xué)者張文勛先生的耐心指導(dǎo)下系統(tǒng)閱讀民族文學(xué)的學(xué)術(shù)專著。后又在袁珂、鐘敬文先生的認(rèn)真指導(dǎo)和精心培養(yǎng)下主攻神話學(xué)。從1970年代中期起,李先生又開始了與日本、前蘇聯(lián)、韓國、港臺及東南亞等地區(qū)的神話學(xué)家們(如李福清等)進(jìn)行學(xué)術(shù)交流。20世紀(jì)80年代中后期負(fù)笈日本,到日本慶應(yīng)義塾大學(xué)投伊藤清司先生門下進(jìn)修,并與大林太良、御手洗圣、白鳥芳郎、君島久子、宮藤隆、西脅隆夫、小島櫻里等著名學(xué)者進(jìn)行頻繁的學(xué)術(shù)交流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廣闊的視野深化了李先生對神話研究的認(rèn)識,也使得他在文化觀上克服了本位主義的狹隘。此外,他還善于對具體問題作縝密而細(xì)致的思考。如上述對不同形態(tài)神話內(nèi)在結(jié)構(gòu)的比較、對神話9種生活形態(tài)的劃分等等,都充滿了精細(xì)、周密的思辨。
三、總結(jié)
李先生在長達(dá)60年余的學(xué)術(shù)實踐中融認(rèn)識、實踐和思辨三維為一體,身體力行,以戰(zhàn)士的精神和激情將畢生的精力毫無保留地全部投入到西南神話王國的探尋之中,為中國神話學(xué)體系的建構(gòu)作出了杰出貢獻(xiàn)。他敢于面對自己的不足,敢于揚棄與時代發(fā)展不和諧的東西,不斷超越自己、完善自己。因此,李先生的思想體系是一個充滿了生機(jī)和活力的開放的體系,是他為后輩學(xué)人留下的一宗巨大的精神財富,值得我們深入學(xué)習(xí)和不斷充實。
參考文獻(xiàn):
[1]劉錫城.新時期的民間文學(xué)(13)[EB/OL].[2007- 05- 30]. http://iel.cass.cn/news_show.asp?newsid=2890.
[2]李子賢.存在形態(tài)、動態(tài)結(jié)構(gòu)與文化生態(tài)系統(tǒng)——神話研究的多維視角[J].云南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哲學(xué)與社會科學(xué)版,2006(3):58- 66.
[3]李子賢.探尋一個尚未崩潰的神話王國[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
[4]李子賢.被固定了的神話與存活著的神話——日本“記紀(jì)神話”與中國云南少數(shù)民族神話之比較[J].云南民族學(xué)院學(xué)報:哲學(xué)與社會科學(xué)版,2000(1):74- 79.
(責(zé)任編輯婁自昌)
An Exploration of the Realm of Living Myths in Southwest China: The Review of Mr. Li Zi-xian’s Academic Thoughts
CHEN Dan
(School of History and Society, Guizhou Normal College, GuiYang 550018, China)
Abstract:Mr. Li Zi-xian is one of the most professional and accomplished mythologists emerging in the 70’s of the last century since the Chinese mythology revitalized. He has committed to the study of living myths of southwest minorities for a long time and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myth system with rigorous and realistic attitude in study and profound knowledge. It is worthwhile for us to study and summarize his academic thoughts and theory achievements.
Key words:living myth; study; review
作者簡介:陳 丹,貴州師范學(xué)院歷史與社會學(xué)院教師,博士。
收稿日期:2014 - 09 - 01
中圖分類號:I207.73
文獻(xiàn)標(biāo)志碼:A
文章編號:1674 - 9200(2015)04 - 0030 - 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