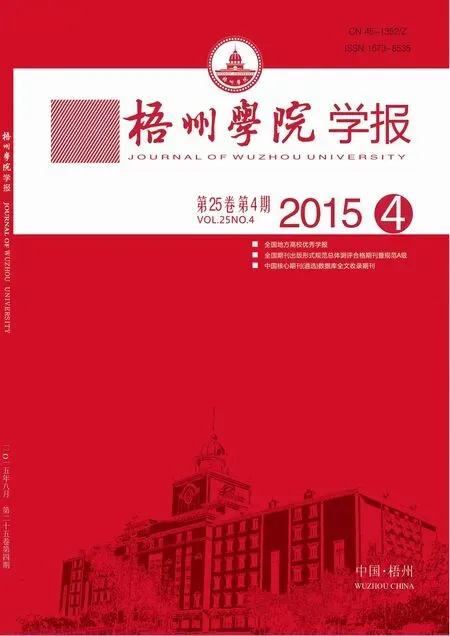張承志早期小說的男性敘事文本
——以《刻在心上的名字》為例
張芳
(遼東學(xué)院,遼寧丹東118000)
張承志早期小說的男性敘事文本
——以《刻在心上的名字》為例
張芳
(遼東學(xué)院,遼寧丹東118000)
《刻在心上的名字》是張承志的創(chuàng)作中關(guān)注度不高的作品。小說的主要人物圍繞父子、“養(yǎng)父子”兩代三位男性展開,作品以“成長”與“自省”為敘事主題,以“苦難”與“救贖”為敘事視角,以“矛盾”與“抗爭”為敘事內(nèi)容,以冷峻與溫情共存、敘事與思考共生的男性視角構(gòu)建了一篇典型的男性敘事文本,具有思想與文化意蘊,豐厚了作家“為人民”的創(chuàng)作內(nèi)涵。
張承志;早期小說,男性敘事
張承志早期小說的敘事空間有“一塊大陸”被他稱為“母親的草原”,敘事時間橫跨并延續(xù)著他的知青歲月,敘事母題直指異鄉(xiāng)的成長與感恩,敘事視角常常是以“我”為代言,將生活中那個年代的“我”和小說中的“我”相照應(yīng),在生活的真實和藝術(shù)的真實中時空交織,生發(fā)文學(xué)與文化意蘊。《刻在心上的名字》是張承志在1979年7月創(chuàng)作并于同年發(fā)表在《青海湖》上的一篇短篇小說。在張承志所有的創(chuàng)作中,這個作品的關(guān)注度并不高,也鮮見文學(xué)評論。小說的主要人物圍繞父子、“養(yǎng)父子”兩代三位男性展開,以“成長”與“自省”為敘事主題,以“苦難”與“救贖”為敘事視角,以“矛盾”與“抗爭”為敘事內(nèi)容,構(gòu)建了一篇典型的男性敘事文本。
一、“成長”與“自省”的敘事文本
關(guān)于“成長”為主題的小說,在中國是舶來
品,西方文學(xué)的“成長”母題由來已久,古希臘、德國、英國、美國等國家的學(xué)者都有自己的界定。但是關(guān)于“成長”具有普遍的文化象征意義是研究者對這類作品的共識。芮渝萍認為,“成長小說就是以敘述人物成長過程為主題的小說,就是講述人物成長經(jīng)歷的小說。它通過對一個人或幾個人成長經(jīng)歷的敘事,反映出人物的思想和心理從幼稚走向成熟的變化過程。因此,成長小說應(yīng)該限制在主人公從對成人世界的無知狀態(tài)進入知之狀態(tài)的敘事。”[1]新時期以來,知青文學(xué)以特有的精神面貌呈現(xiàn)在文壇,這些以知青生活為素材的作品,有描寫那段生活的苦難和艱辛,有對非常時期社會環(huán)境的描述,有緬懷青春歲月,有表達理想情懷。這些作品,都有一個共同的主題,就是“成長”。有身體的成長,心理的成熟,還有精神的豐富。
作為其中的一員,知青生活是張承志早期小說記錄的主要內(nèi)容,在這段艱苦浪漫的生活中,作家作為一個都市青年逃離到烏珠穆沁草原,從一個懵懂的熱血青年成長為一個地道的牧民、一個真正的騎手和一個信念堅定的男人。在這里,有自然條件的艱苦,生存環(huán)境的惡劣,草原生活的不適,還有那個特定年代的政治風(fēng)波。“我”在“成長”是張承志這段時間創(chuàng)作的主題。《刻在心上的名字》講的就是主人公小剛流著紅衛(wèi)兵的熱血投入到蒙古草原的廣闊天地中,本想大有作為卻在“錯誤”的斗爭中看到自己入住蒙古家庭的哥哥喪命,在追求理想的路上用哥哥的血使自己的名字有了“為人民”的內(nèi)涵。從這個意義上,《刻在心上的名字》就是小剛的“成長”敘事,這個心路歷程在經(jīng)歷重大事件后得以認識自我和人生,在一系列的情感動態(tài)變化中讓他的“成長”血肉豐滿又蘊含深遠。所以,作品中給我們展示的走向成熟不是表象的骨骼的強壯、生理的發(fā)育,而是心理的健全、道德的成長和精神的完善。
小說中小剛的“成長”是一個動態(tài)的發(fā)展過程,這個動態(tài)是伴隨著他在草原“政治風(fēng)波”的發(fā)生、發(fā)展和人物命運的變化而變化的,對紅衛(wèi)兵內(nèi)涵的理解是他“成長”的線索,對這個內(nèi)涵理解的深化成為他心理健全、道德成長和精神完善的內(nèi)在因素。帶著紅衛(wèi)兵的使命感和偉大的抱負到草原鍛煉自己,感情熾熱、愛憎分明是他的基本特征。但是由于哥哥被懷疑為內(nèi)人黨,在監(jiān)視、關(guān)押、審問的過程中他經(jīng)歷了一系列情感的變化,當哥哥用死祭奠了他的成長儀式,最終他也由于養(yǎng)父的引領(lǐng)完成了心理的自省、精神的成長與道德的救贖,也最終明白了紅衛(wèi)兵使命的真正內(nèi)涵,那就是永遠和人民站在一起,成為真正的“阿拉丁夫”。
小剛的“自省”明確體現(xiàn)在兩個人身上。對烏力記哥哥,小剛最初的情感是崇拜,因為他是草原上威風(fēng)凜凜的摔跤冠軍,小剛便央求要住到他的蒙古包里,一年多的共同生活讓他品嘗到草原異鄉(xiāng)人的溫暖和淳樸。烏力記剛被審查時,小剛堅信他的無辜,抱著很快過關(guān)的幻想,看到他的沉默使小剛與從前往事交織情感復(fù)雜,后來看見他牽掛馬群主動提醒時的懷疑,想到自己生病時烏力記哥哥冒著逃跑罪名舍命相救的無地自容,他想到最后心里充滿絕望自殺的悲憤。整個情感變化中小剛有著深深的愧疚與自省,后來他用在查干敖包山下打井來“償還”和“救贖”。小剛的“自省”還體現(xiàn)在永紅身上。當慘烈的斗爭結(jié)束時,小剛看到永紅輕松地與人談笑風(fēng)生時,開始反思自己的錯誤和對紅衛(wèi)兵精神的錯誤理解。“他承認自己的過失和錯誤,他比別人更不能寬恕自己”[2]35,就是在這種罕言寡語中審判自己的行為和靈魂。當桑吉阿爸用最簡單的道理“為迷惘的騎手指點了前進的路徑的時候”,小剛擁有了圣潔的名字,完成了“自省”和“救贖”。
二、“苦難”與“救贖”的敘事文本
苦難,是苦痛和災(zāi)難,同時還指遭受苦痛和災(zāi)難。這種對“苦難”內(nèi)涵的界定不僅僅包括生理上的疾病、物質(zhì)上的困境,還包括精神上的煎熬。它既是一種狀態(tài),也是一種經(jīng)歷和過程。佛家的“八
苦之說”可謂集人生苦痛之大成,以此觀照和感悟人生,人生就是一個苦痛的過程,人人都有苦難的歷程。在西方,“苦難”是基督教一個重要主題,身處“苦難”經(jīng)由信仰宗教而獲得靈魂的“救贖”,由此信仰宗教便成為消解“苦難”的途徑和方法。西方文學(xué),乃至雕刻、建筑、音樂、繪畫等諸多領(lǐng)域都對“苦難”與消解“苦難”這個無極限的命題,進行過多視角的闡釋。同時,如何面對“苦難”,并在“苦難”中得以消解和超越也是中國文學(xué)經(jīng)常探討的主題。
關(guān)于張承志小說苦難意識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他對有關(guān)穆斯林作品的研究上。黃土高原的“西海固”成為作者抒寫“苦難”的發(fā)生地,這個曾經(jīng)被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定義為“人類不能生存之地”在張承志的筆下卻成為一個文化象征。作家對這些貧瘠土地上存在哲合忍耶信仰的力量加以敘述,研究者也在作家的敘述中感受到這種生命的意志力。實際上,“苦難”是張承志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重要命題,也是張承志熱愛抒寫并涵蓋了他成長經(jīng)歷的主題。在張承志的草原小說中,也有關(guān)于苦難意識的描寫,與宗教信仰不同的是,成長中的苦難“我”時時在經(jīng)歷。
《刻在心上的名字》中具有苦難意識和豁達情懷的人的表象是桑吉阿爸,這個蒙古醫(yī)生在老年失子的苦難中原諒了小剛,并在小剛的錯誤斗爭中賦予紅衛(wèi)兵新的內(nèi)涵。桑吉阿爸是個見過世面的蒙古老人,雖然沉默寡言但對小剛的心思了如指掌,在小剛高燒時沒有絕情地離開放棄治愈一個生命,證明兒子被冤枉時老淚縱橫而沒有怨恨,當小剛痛苦地贖罪時,樸實老人的寬容和安慰充滿真情,“風(fēng)雪的春天總會有死去的羊羔子,可是羊群里的羊羔子還是越來越多……”[2]38這種樸實的豁達讓小剛無地自容,也讓他明白了簡單的道理:無論身份如何變化,首先要和人民站在一起,做人民的兒子。
小說中真正在苦難中得以救贖的是小剛。小剛的背后有兩個男人,一個是親如兄弟的草原哥哥,一個是親如父親的草原阿爸。作家以男性視角描述了三個男人的情感與苦難,有關(guān)于人生成長的冷峻思考,有關(guān)于異鄉(xiāng)親情的溫情描述,有面對問題的矛盾對抗,有人生苦痛的悲憫情懷……小剛的救贖就是通過這兩個男人,以自我救贖和他者救贖兩個途徑完成的。自我救贖在小說里表象上是通過在查干敖包山下打井的具體事件去體現(xiàn),實際上在整個事件的變化中的情感經(jīng)歷和內(nèi)心煎熬都是自我救贖的有機組成部分,是自我救贖的內(nèi)在有機體。他者救贖是通過烏力記哥哥的自殺和桑吉阿爸的寬恕共同完成的。應(yīng)該說,小說里“苦難”是成長的母體,是它的“溫床”與“良藥”,更是它清醒的催化劑。他者救贖是外在事件的推動與催促,自我救贖是內(nèi)在的驅(qū)動力與基礎(chǔ)。
一個知青帶著激情投入到火熱的斗爭中,這斗爭讓都市青年激情澎湃,也讓熱血青年失去了純真和友情,甚至失去了朝夕共處的親情,更悲涼的是,斗爭中有親如家人的兄弟的流血和犧牲。由于一場錯誤的斗爭,讓桑吉阿爸的兒子在屈辱中自殺,阿爸的豁達卻讓小剛理解到了靈魂的價值,他由此獲得了精神上的超越。這種世俗苦難的敘事讓作家歌頌沉靜、堅忍和勇敢的受難精神,也讓他在經(jīng)受苦難中看到了反諷和荒誕。如果烏力記哥哥果真是內(nèi)人黨,如果桑吉阿爸對他始終不原諒,小說的內(nèi)涵就遠沒有現(xiàn)在的沉重與蒼涼,這種諷刺和荒誕就失去了內(nèi)在的張力。所以,張承志筆下的“苦難”表面上具有文本敘事的悲劇性與抒情性,實際上更具有文化敘事中悲劇里的諷刺喜劇的濃重色彩。這種在“苦難”中的超越就不僅僅是停留在文本,也超越了文本,具有文化內(nèi)蘊。
三、“矛盾”與“抗爭”的敘事文本
在當代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死亡”是一個重要的敘事主題,不管是男性作家,如先鋒小說作家余華,魔幻現(xiàn)實主義作家莫言,還是女作家,如遲子建、畢淑敏等,他們的作品中都有關(guān)于“死亡”的敘述,也有眾多研究者分析他們筆下“死亡”的內(nèi)
涵。“死亡意境”作為某一人物的戲劇化人生的最后一筆或某一生命形式的末端,一般是情緒高峰,常常是具有倫理力量的性格的最后表現(xiàn),更能流露出死亡符號的價值觀與倫理觀,藝術(shù)家的道德尺度也借助人物的死亡得以顯現(xiàn)[3]。張承志的這篇小說也敘述“死亡”,這種生命儀式蘊含了作家的倫理觀與價值觀,并且作家的道德與人性在小說中得以體現(xiàn),具有深刻的文化內(nèi)涵。
小說中作為苦難的載體是白音塔拉大隊民兵排長烏力記。他是桑吉阿爸的兒子,烏日娜嫂子的丈夫,小剛的哥哥。他因為在1965年保衛(wèi)邊防的民兵演習(xí)中表現(xiàn)積極而被誤認為是內(nèi)人黨,在審查中因牧人的信念被踐踏后絕望自盡。這是個悲劇性人物,在健碩的身體、沉默的性格、堅韌的信念和命運的抗爭方面都表現(xiàn)出一系列的矛盾性,將草原的個人悲劇刻上了時代的烙印,這種死亡敘事對于塑造人物的決絕、窺探人性的苦難、加深靈魂的傷痛具有超現(xiàn)實的意義。其矛盾性的表現(xiàn)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名字寓意與生命相違的人生矛盾。蒙古族很重視給孩子取名,《蒙古黃金史》中有成吉思汗對次子察合臺最好飲宴的記載:“如果未出生,也為給你命名,如果沒有出母腹,也未看見光明。在父母創(chuàng)造,母親生產(chǎn)的日子恭敬地一起飲宴,這才是最好的宴會。”[4]所以按照傳統(tǒng)蒙古孩子的名字是長輩取的,“烏力記”是長壽的意思,因為家境貧窮長輩盼他長命。而這個名字的家族企盼寓意與28歲生命戛然而止的命運實在是不相稱,“人們并不一定能記住這個名字和這個名字的悲劇。”這似乎成了一個與生俱來的矛盾,這個矛盾本身就具有命運的諷刺意味。
二是沉默反抗與舍命相助的性格矛盾。小說中,烏力記的性格始終是矛盾的。沉默與開口的矛盾,逃跑與救命的矛盾是兩個重要矛盾的生成點和爆發(fā)點。烏力記被審查后,在相信群眾相信黨的“辯解”遭來十幾記耳光鮮血直流后便拒不講話,但又自覺維護草原呼吸而主動叮囑知青放馬的注意事項。這種身份的轉(zhuǎn)變沒有停止他牧民的職業(yè)本能。另一方面,小剛高燒時,烏力記冒著“叛逃邊境”的生命代價找來桑吉阿爸挽救小剛,這種身處逆境的冒死相救恰恰體現(xiàn)了他內(nèi)心深處的道德底線和人性的善良,這是人性與命運的抗爭,這個矛盾使人性站在了道德的高度。
三是身體勇武與精神無力抗爭的命運矛盾。在小剛的眼里,烏力記是個寬肩膀的騎手,“像天神一樣馳騁在馬群中”,“在牧民的歡呼聲里跳上摔跤場”,是個威風(fēng)凜凜的冠軍。這樣一個勇武有力的年輕人面對誤解在憨聲憨氣地分辨后滿含淚水,拒不講話。后來經(jīng)過幾個月的關(guān)押,用腰帶在屋里自盡。小剛壓抑憤怒,烏日娜帶著仇恨的目光粗暴地推開他,只有飽經(jīng)滄桑的桑吉阿爸聲音嘶啞,寬慰小剛。作家由衷地感嘆:“這個時代的草原就是這樣,沒有一個人能反抗命運,如果命運上蓋著一個公章。”[2]30與其說烏力記精神上懦弱,倒不如說他為自己牧人堅守的信念勇武地殉葬,那么,這就不是一個矛盾,而是具有崇高意義的悲劇英雄。
詩人蒙田說過:“誰教會人死亡,誰教會人生活。”是的,草原在季節(jié)中輪回,羊羔在風(fēng)雪的春天里越來越多,小剛在熱血青春里尋找到了圣潔的名字。只是,在張承志的創(chuàng)作道路上,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責任,堅持“為人民”的創(chuàng)作原則,用人民的生活豐滿創(chuàng)作內(nèi)涵。張承志,一直在尋找和堅持的路上……
[1]芮渝萍.美國成長小說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 2004:5.
[2]張承志.騎手為什么歌唱母親[M].上海:東方出版社,2014.
[3]顏翔林.死亡美學(xué)[M].上海:學(xué)林出版社,1998:40.
[4]馬哥孛羅.馬哥孛羅游記[M].張星烺,譯.上海:上海商務(wù)印書館,1937:172.
On the Narrating Version by M ale Persons in Zhang Chengzhi’s Early Novels——Based on A Name Engraved in the Heart
Zhang Fang
(Eastern Liaoning University,Dandong 118000,China)
A Name Engraved in the Heart is one of Liao Chengzhi’s novels which draws less attention from people.The plot of the novel develops among threemale persons:the father,the son and the step-father.In this novel,the writer takes“growing-up”and“self-examining”as the narrative theme,sufferings and redemption as the narrative perspective,conflict and struggle as the narrative content.Besides,hemixes coldness with tenderness and combines narration with conside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male person.Thus,he creates a typical narrating version bymale persons,which contains the expression of both thought and culture and enriches thewriter’s literary creation connotation of“writing for the people”.
Zhang Chengzhi;Early novels;Narration bymale persons
I206.7
A
1673-8535(2015)04-0056-04
張芳(1971-),女,滿族,遼寧省丹東市人,遼東學(xué)院副教授,碩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xué)。
(責任編輯:孔文靜)
2015-0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