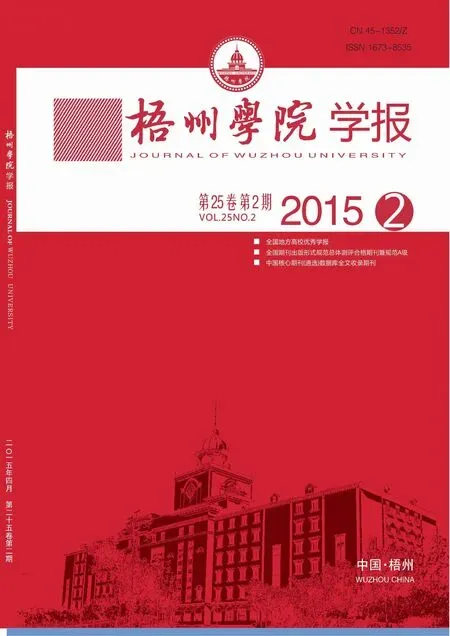從《黑暗的心》管窺康拉德后殖民書寫的矛盾性——一種霍米·巴巴視角
?
從《黑暗的心》管窺康拉德后殖民書寫的矛盾性
——一種霍米·巴巴視角
陳燕1,李昌銀2(1.2.云南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云南昆明650500)
[摘要]康拉德文化身份的混雜性和他的多元文化經歷共同造就了其作品后殖民書寫的矛盾性。以《黑暗的心》為例,該作品中人物形象的混雜性揭示了殖民主義的虛偽性,同時反映了康拉德對殖民主義的矛盾態度以及西方話語對東方“他者”既愛又恨的矛盾情感;《黑暗的心》所表征的殖民話語的含混性揭示了殖民地歷史的復雜性,殖民者和被殖民者既共謀又對抗的復雜關系消解了殖民權威;庫爾茲的人生悲劇映射出殖民主義與生俱來的矛盾;“模擬”本來是殖民統治的策略,但最后卻成為被殖民者反抗殖民壓迫的有力武器。
[關鍵詞]《黑暗的心》;霍米·巴巴;混雜;含混;模擬
一、引言
約瑟夫·康拉德是英國現代小說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牛津英國文學史》把他列為20世紀英國文學八大作家之一。康拉德身份的混雜性,他的多元文化經歷以及殖民地歷史的復雜性共同造就了他筆下充滿矛盾的文學世界。他的作品時而控訴殖民侵略的罪惡,時而又捍衛殖民統治,認為殖民主義代表歷史發展的方向,有助于推動殖民地的歷史發展。例如在《黑暗的心》中,康拉德無情地揭露了歐洲人所謂的“文明教化”的虛偽性,對西方霸權主義進行了有力的抨擊。然而,康拉德在對飽受苦難的有色人種給予深切同情的同時,又不時流露出種族歧視的傾向。評論界對康拉德作品的主題和話語的矛盾性和含混性褒貶不一,有評論者認為康拉德是種族主義者,但不是帝國主義者;另外一些評論者認為康拉德既不是種族主義者,也不是帝國主義者,而愛德華·薩義德在《文化與帝國主義》中指出:“康拉德既是反帝國主義者,又是帝國主義者。這并不矛盾。當他無所畏懼又悲觀地揭露那種自我肯定和自我欺騙的海外統治的腐敗時,他是進步的;而當他承認,非洲或南美洲本來可能有自己的歷史和文化,這個歷史和文化被帝國主義者粗暴踐踏,但最終被他們自身歷史和文化所打敗時,他是極為反動的。”[1]《黑暗的心》是康拉德的代表作,小說講述了受聘于一家比利時貿易公司的船長馬洛深入非洲腹地,營救重病纏身的貿易站代理人庫爾茨的故事。本文運用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論,通過分析《黑暗的心》管窺康拉德小說后殖民書寫的矛盾性。
二、人物形象的混雜性
在巴赫金那里,混雜性指的是多意語言的分裂性的變形力量,是在“單個詞語的界限內、詞語的范圍內兩種社會語言的混雜,兩種被時代、社會差別或者其他因素區分開的不同語言意識之間的混雜。”[2]霍米·巴巴借用巴赫金的混雜概念,認為混雜是“殖民權力生產力的標志,它表示所有存在于被歧視和壓迫中的必然變形和置換,是不同種族、族群、意識形態、文化和語言相互混合的過程。”[3]康拉德小說中的某些人物的身份具有混雜性特征,比如說《黑暗的心》中的庫爾茲,他的母親是半個英國人,父親是半個法國人,他是歐洲文明的產物;俄國人對他頂禮膜拜,公司經理卻把他當成傻瓜,在表兄眼里他是畫家、音樂家和作家,同行記者認為他是演說家和政治家;未婚妻崇拜他,始終認為他是個聰明、誠實和執著的人;馬洛先是把他當成“文明和光明的使者”,后來把他看作一個為了斂財不惜血腥鎮壓非洲黑人、被金錢和地位吞噬了靈魂的惡魔;他能力超群,被土著人奉為神明,他希望給非洲帶去光明卻又隨時準備鎮壓那些不合作或者大膽反抗的土著人。庫爾茲這個帝國主義精英的代表對非洲土著的奴役與殺戮使殖民主義所標榜的所謂“文明使命”的虛偽性昭然若揭。
康拉德作品中人物形象的矛盾性反映了康拉德的反殖民意識和無意中流露出來的殖民意識。在《黑暗的心》中,康拉德把那些殖民者稱作“傳播光明的使者”,從事著“高尚的事業”,同時認為他們“不顧一切而又缺乏膽略;貪得無厭而又膽小如鼠;殘忍暴虐而又毫無勇氣。”[4]康拉德對殖民地人民給予了深切的同情和憐憫,不時流露出對黑人生命活力的贊美。例如,他飽含深情地寫道:“……他們有骨頭,有肌肉,有一股狂野的活力和強烈的活動能量,同他們的海岸邊的浪頭一樣,自然而真實。”[4]然而在整部小說中,康拉德很少用“黑人”這個中性詞,而是從頭到尾把他們稱為“野人”“畜牲”“食人生番”“黑鬼”等,從康拉德對黑人的稱呼上可以能看出他對黑人的歧視。康拉德痛斥殖民者的殘忍與野蠻的殖民行徑,但他為歐洲征服和掠奪其他民族的行為找到了合理借口,他認為歐洲精英把文明的火種傳給其他所謂的“劣等”民族,使他們獲得進步和文明。康拉德這樣描寫非洲人的落后和愚昧:“隔一段時間,我還得去看一下那個野人司爐工。他是一個經過教育得到提高的標本……幾個月的訓練對這個真正不錯的家伙產生了效果。”[4]在白人眼里,黑人就像穿著人的衣服學人走路的狗一樣荒唐可笑,他們只有通過白人的教化才能變得有用和進步。正如巴巴所指出的那樣:“在殖民者眼里,被殖民者“既是野蠻人(食人生番),又是最恭敬和彬彬有禮的仆人(端茶送飯的人);既顯示出性欲,又天真得像個兒童;他是神秘的、原始的、心智單純的,同時又是老于世故的,是一個手段高超的騙子,縱橫捭闔的老手。”[5]康拉德對小說人物形象的刻畫反映了殖民話語對“他者”的既愛又恨的矛盾情感與態度。
康拉德作品中人物形象的混雜性和他對于殖民主義的矛盾態度與他的人生經歷有著密切的聯系。16歲以前的康拉德生活在沙俄統治下的波蘭,為了逃脫沙皇專制的統治,輾轉從波蘭來到法國馬賽,最后成為英國公民。21歲時康拉德加入英國商業船隊,足跡遍及歐洲、北美、南美、非洲、澳大利亞,童年時期遭受殖民壓迫的痛苦回憶,成年之后的多元文化經歷,尤其是目睹了殖民主義的惡劣行徑之后,康拉德不可能成為帝國話語的代言人。然而,在看到康拉德對帝國主義尖銳批判的同時,我們也應該意識到,接受過資本主義教育的康拉德對帝國主義心存幻想,他期望帝國精英能將科學與文明的火種傳播到殖民地,幫助加快殖民地社會的歷史發展進程。
三、殖民話語的含混性
英文單詞“ambivalence”通常意指對同一人、物、事的矛盾心理(如既愛又恨)、矛盾情緒或矛盾狀態。霍米·巴巴將“含混”的概念借用到后殖民理論中,用以描述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間既相互排斥又互相吸引的復雜狀態。巴巴認為東西方的權力關系不是截然對立的,而是含混的。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間不是一種單純的對立或者對抗關系,二者之間關系的混合模式超越了殖民權力的想象。庫爾茲憑借手中的武器成為土著居民崇拜的偶像,為了獲取更多的象牙,他以欺騙、奴役甚至殺戮的手段控制非洲土著,同時打著“教化”和“傳播文明”的旗號掩飾自己殖民行為的非正義性。但是,對殖民地情況缺乏全面了解的庫爾茲對土著居民并非一味地鎮壓,相反在一定程度上對土著采取迎合的態度,因為他知道這是征服殖民地的前提。例如,庫爾茲的土著情人對來自文明世界的庫爾茲充滿崇拜之情,對現代文明有向往之心,所以當俄國人親近庫爾茲時,她立刻產生了危機感,因為當照顧病重的庫爾茲的工作一旦被俄國人所取代,就意味著她不但會失去庫爾茲的愛,而且還會失去威信和財富。雖然從表面上看,庫爾茲似乎對殖民地擁有絕對的控制權,但由于殖民者需要土著的協助,因此土著經常利用這一弱點來對抗殖民者。庫爾茲的土著情人影響甚至操縱著庫爾茲,庫爾茲曾按她的意圖威脅俄國人交出象牙,并離開這個國家,否則就會殺了他,由此可見土著人對庫爾茲的控制力非同一般。我們從《黑暗的心》可以看出,被殖民者對現代文明有一種本能的向往與崇拜,但由于殖民者缺乏對殖民地的了解,被殖民者并不完全處于劣勢地位。由此可見被殖民者并非完全與殖民者對立,他們之間既排斥又吸引的矛盾關系揭示了殖民權威的脆弱性。
巴巴認為,殖民話語必定是含混的,帝國主義自身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其衰落。在巴巴看來,殖民主義表面上是霸權式的,但它本身帶有內在隱藏的缺陷。殖民使命需要白人的共同努力和配合,但在殖民地,白人們為了各自的利益互相敵視,相互爭奪對殖民地的控制權。在《黑暗的心》中,白人殖民者對同事的死無動于衷,白人之間的權力爭斗直接導致了庫爾茲的死亡。受到中心站站長青睞的磚匠一心想成為經理助理,但是庫爾茲的到來打亂了他的計劃,當他得知庫爾茲身患重病之后非但毫無同情之心,相反覺得十分快慰。公司經理擔心庫爾茲的出色表現會威脅到自己的地位,所以設置種種障礙來拖延營救庫爾茲的工作,因此當馬洛終于可以駕駛汽船去營救庫爾茲的時候,庫爾茲已不治身亡。庫爾茲的死亡顯示了帝國主義自身的內部矛盾,殖民者內部的斗爭不僅使庫爾茲成為殖民侵略的犧牲品,也是導致殖民統治在殖民地最終失敗的原因之一,因為殖民關系的矛盾性早已為自己的毀滅埋下了種子。
四、對殖民權威的消解與反抗
“模擬”指的是西方殖民者在殖民地采取的一種文化同化策略,即通過讓殖民地人民學習、模仿宗主國的語言、文化、法律制度,使殖民地人民認同宗主國的文化。“模擬”是殖民者施行的一種殖民控制形式,然而這種“模擬”策略有自身的矛盾之處——它企圖讓被殖民者與殖民者之間既相同又不完全相同。為了能讓自己所標榜的“文化教化”有其立論根基,殖民者鼓勵并引導被殖民者自我改進并逐漸接近西方文明,但同時要求土著與殖民者保持足夠的差異。殖民者“模擬”策略的矛盾性和要求保持“差異”的態度決定了殖民主義永遠不可能完全成功,而且這種似是而非的文化拷貝對殖民者而言是很具威脅性的。在《黑暗的心》中,敘述者馬洛發現并閱讀了英語文本《駕船術的幾點探討》。霍米·巴巴指出,“英語書”是殖民統治、殖民欲望和殖民制度的象征,但在《被視為奇跡的符號》一文中,巴巴指出,“那本英語書”不但不能預設歐洲統治的固定性,相反還為被殖民者提供了反抗帝國主義和殖民壓迫的形式與工具。傳播西方文化是殖民主義整體策略的一部分,殖民權力試圖通過傳播以英語為標志之一的西方文化來鞏固殖民權力。當馬洛所乘坐的船行駛至距離庫爾茲的貿易站8英里處,船上的白人忐忑不安,擔心自己被襲擊、被殺害,而黑人卻鎮定自若。一個黑人竟然模仿白人的英語說:“抓住他們。把他們交給我們。”馬洛問:“給你們,那你們怎么處置他們?”黑人說:“吃了他們!”[4]原本處在失語狀態的黑人模仿著白人的語言,說出要吃掉那些攻擊者的話,這樣的結果顯然與殖民者的“教化”意圖背道而馳。種種事實表明,黑人的殘暴并非出于天性,而是對白人的殘酷鎮壓做出的一種本能的反應。在小說中,馬洛的前任弗里斯·萊文被看作是“用兩條腿走路的動物中最和善、最文靜的”[4],但他居然為了兩只母雞殘忍鞭打村長,最后村長在盛怒之下將其刺死。殖民者企圖借助“模擬”策略培養有利于殖民統治的“他者”,但殖民權威其實是有限而脆弱的,康拉德筆下的黑人本來是殖民主義的“理想”目標,但他們通過“模擬”殖民者的文化嘲諷和反抗殖民權威,最終超越殖民權威的控制范圍。
五、結語
康拉德出生在過去的殖民地,雖然接受過西方教育,但他對故土有著揮之不去的情愫。作為一個受殖民侵略而背井離鄉的文化漂泊者,他始終無法獲得英國主流社會的認同。作為西方世界的“邊緣人”,康拉德將自己的創作視角更多地轉向第三世界國家。康拉德曲折復雜的人生經歷使他的作品呈現出后殖民書寫的矛盾性和含混性。應用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論來分析《黑暗的心》,我們可以看出,有著西方教育背景的康拉德認為殖民主義代表歷史發展的方向,能推動殖民地社會的發展,但殖民者的暴行讓他不能漠視殖民主義的罪惡;他的作品揭示了殖民主義的矛盾性、虛偽性和脆弱性,但他的種族偏見削弱了他對殖民主義的批判力度。康拉德成功地書寫了帝國殖民歷史的復雜性,他的文本既代表了帝國主義敘事話語,又通過混雜、含混和矛盾的話語顛覆了殖民主義權力話語的片面性和權威性,因此,正如格雷厄姆(KennethGraham)所言,康拉德的文本:“自始至終都似乎在挑戰唯一的意義詮釋。”[6]
參考文獻:
[1]愛德華·薩義德.文化與帝國主義[M].李琨,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11- 12.
[2]Bakhtin Mikhail.The dialogic imagination[M]//Trans by Caryl Emerson and Michael Holquist.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81:358.
[3]Homi K. Bhabha.“Signs takenfor wonders: Questions of ambivalenceandauthorityunderatreeoutsideDelhi, May1817”[M]//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4:112.
[4]康拉德.黑暗的心[M].黃雨石,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2.
[5]Bhabha,Homik.The Location of Culture[M].London: Rutledge, 1994:85.
[6]KennethGraham, ConradandModernism.[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LanguageEducation Press,2000:213.
李昌銀(1957-),男,云南鎮雄人,云南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后殖民文學批評與現代性。
(責任編輯:高堅)
On the Contradictoriness in Conrad’s Post-colonial Description Embodied His Heart of Darkness
——A Perspective of Homi K. Bhabha
Chen Yan1, Li Changyin2(1.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enming 650500, china)
Abstract:The heterogeneity Conrad’s cultural status and his multicultural experience jointly lead to the contradictoriness embodied in his post-colonial description in his works. Take as a case his Heart of Darkness, in which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characters of this literary work reveals the falsity of colonialism. Meanwhile, it also reflects Conrad’s contradictory attitude to colonialism and the contradictory emotion of the western words to the eastern word“others”. Besides, the vagueness of colonialist words represented in Heart of Darkness shows the complexity colonial history, in which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of collusion and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colonizing people and the colonized people dispels the colonial authority. Kurtz’s tragedy of life implies the natural contradiction of colonialism. "Simulation" is actually a ruling strategy of colonists, but it eventually becomes a strong weapon for the colonized people fight the colonizers.
Key words:Heart of Darkness; Homi K. Bhabha; heterogeneity; Vagueness; Simulation
[作者簡介]陳燕(1978-),女,云南普洱人,云南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英語文學。
基金項目:2013年度云南省哲學社會科學學科建設立項項目(XKJS201318)階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15- 02- 10
[文章編號]1673-8535(2015)02-0080-04
[文獻標識碼]A
[中圖分類號]I56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