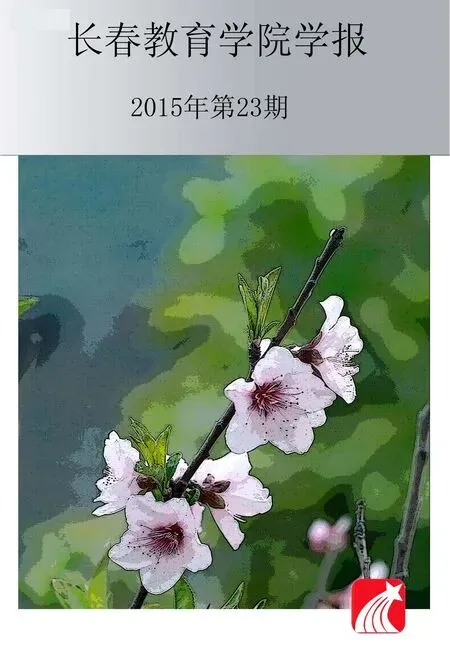曹丕以魏代漢之我見
韋運(yùn)韜
建安二十五年(220 年)曹操薨于洛陽,隨之而來的便是曹丕對王權(quán)的繼承和對皇權(quán)的“合法”擁有。此時(shí)三國割據(jù)勢力均衡,各自擁有一定的勢力范圍,富國強(qiáng)兵徐圖統(tǒng)一成為各國的軍政方略。隨后相繼有稱帝者出現(xiàn), 這為曹丕獲得皇權(quán)造就了天時(shí)與地利之勢。對于曹丕個(gè)人來說,需要完成其自身政治任務(wù)以外,還得繼承乃父曹操?zèng)]有完成的統(tǒng)一大業(yè)。政治訴求的實(shí)現(xiàn)需要把全國的行政、立法、司法乃至生死大權(quán)集于一身,并將權(quán)力牢牢地掌握在手中,而后才能有效地施政,安內(nèi)而后圖外。對于掌握皇權(quán),曹丕所選擇的手段至關(guān)重要,所謂“個(gè)人、群體或組織通過各種手段以獲取他人服從的能力,這些手段包括暴力、強(qiáng)制、說服以及繼承原有的權(quán)威和法統(tǒng)”。因受儒家政治哲學(xué)的影響,加之權(quán)力集中過程中所遇到的阻力并不大,所以效仿上古禪讓皇權(quán),以一種明顯的禮儀化的政治手段來達(dá)到“權(quán)威和法統(tǒng)”便成為最好的一種形式。
禪讓是“中國古代社會(huì)儒家以禮治國的理想與皇權(quán)專制政治的現(xiàn)實(shí)相結(jié)合的產(chǎn)物”,又符合中國儒家
郭沫若在《論曹植》中說道:“為什么一定要姓劉的才可以做皇帝呢?一般迂腐先生們先抱定一個(gè)忠君的公式,信手地依著自己的好惡而為是非,見曹操鷹揚(yáng),曹丕豹變,便斥為‘奸雄’,斥為‘篡賊’。”我們不妨換一種眼光來審視歷史, 通過對曹丕政治人生的梳理,探究其中的成因和歷史的必然。
曹丕的政治路途中,以魏代漢踐祚皇位的舉動(dòng)是其登上政治巔峰的轉(zhuǎn)折點(diǎn),其舉動(dòng)充滿著戲劇化的色彩,所謂的精心策劃和安排無非是想得到儒家正統(tǒng)觀念的認(rèn)可。其實(shí)曹丕以魏代漢踐祚皇位,應(yīng)該是歷史的必然。除去儒家觀念的左右,曹丕稱帝也可以說是實(shí)至名歸集權(quán)的體現(xiàn)。
漢家天下的政治局面早在董卓之亂后就已紊亂,曹操遷漢獻(xiàn)帝至許昌后,“挾天子以令諸侯”,政令皆出于曹氏。在皇權(quán)的擁有上來說,漢獻(xiàn)帝已經(jīng)成為一個(gè)傀儡。曹操雖然征戰(zhàn)四方,但以臣子的身份周旋在各個(gè)割據(jù)勢力之中。曹操與劉備和孫權(quán)的權(quán)力基礎(chǔ)有所不同,孫權(quán)獨(dú)占江東,憑借江河天險(xiǎn)固守江南一隅;而劉備憑借精心籌劃與政治聯(lián)盟經(jīng)營巴蜀之地;曹操以漢獻(xiàn)帝雄霸北方, 在政治上占有優(yōu)勢并更具合法性。赤壁之戰(zhàn)后三分天下基本形成,在軍事上三國彼此都無法吃掉對方,對于曹氏來說只要漢獻(xiàn)帝不倒,政治局面不至于全面崩盤,政治資本尚在。相反,如漢獻(xiàn)帝不復(fù)存在,則劉備以劉氏宗親的身份在政治上便可獨(dú)占鰲頭,也給了孫劉兩家共同討伐中原的借口,再加之普通民眾與眾多士人歸曹者乃因曹操政治上所具有的合法性資本——漢獻(xiàn)帝, 故而曹操要想稱帝,此時(shí)的天時(shí)地利與人和并不成熟。
曹操戎馬一生始終胸懷統(tǒng)一天下的心愿。他在四方征伐中逐步掌握大權(quán), 但爭奪權(quán)力的道路并不平坦。早在建安四年(199 年),“帝忌操專逼,乃密詔董政治哲學(xué)的基本要求,在曹丕看來可以大大地增加皇權(quán)的正統(tǒng)性。建安二十五年(220 年)曹丕繼承王位,對于曹氏權(quán)力體系中培植的臣子而言,老中青三代維護(hù)曹氏的臣僚集團(tuán)已經(jīng)形成,并且他們擁有一致的利益同向性。至此,曹丕具備了稱帝的人和之勢。不久曹丕改年號(hào)為延康元年,開始著手為受禪作輿論上的準(zhǔn)備。因?yàn)椤皞€(gè)人的價(jià)值目標(biāo)總是取決于社會(huì)所指向的價(jià)值理想,個(gè)人的價(jià)值取向總是取決于某種社會(huì)的價(jià)值導(dǎo)向,個(gè)人的價(jià)值認(rèn)同總是認(rèn)同某種社會(huì)的價(jià)值規(guī)范。因此,在社會(huì)的價(jià)值體系中,社會(huì)的價(jià)值理想、價(jià)值規(guī)范和價(jià)值導(dǎo)向總是處于主導(dǎo)和支配地位,總是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社會(huì)輿論導(dǎo)向和社會(huì)認(rèn)同便成為曹丕受禪的開始。
又因自漢代以來董仲舒的“天人感應(yīng)”學(xué)說將封建制度下君主的行為與天命聯(lián)系起來,以此來證明人事的好壞會(huì)招致天的福佑或懲罰,人要順天不能逆天,祥瑞的出現(xiàn)即代表行為順應(yīng)天命,而相反災(zāi)禍的降臨即代表行為逆天之命。儒家這一政治思想恰巧給予了曹丕天有所命、早有祥瑞所宣的輿論支點(diǎn)。據(jù)史載:“初,漢熹平五,黃龍現(xiàn)譙,光祿大夫橋玄問太史令單飏:‘此何祥也?’飏曰:‘其國后當(dāng)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亦當(dāng)復(fù)見。天事恒象,此其應(yīng)也。’內(nèi)黃殷登默而記之。”到了延康元年(220 年)三月,“黃龍復(fù)現(xiàn)譙。登聞之曰:‘單飏之言,其驗(yàn)茲乎?’”裴引《魏書》曰:“王召見登,謂之曰:‘昔成風(fēng)聞楚丘之繇而敬事季友,鄧晨信少公之言而自納光武。登以篤老,服膺占術(shù),記識(shí)天道,豈有是乎!’賜登谷三百斛,譴歸家”。隨后瑞祥頻繁而至示意于民,《三國志·魏書·文帝紀(jì)》載:延康元年“四月丁巳,饒安縣言白雉見”。裴注引《魏書》曰:“賜饒安田租,勃海郡百戶牛酒,大酺三日;太常以太牢祠宗廟”;“八月,石邑縣言鳳凰集”。相繼出現(xiàn)祥瑞無非是證明受禪仍具有天命性的依據(jù),為曹丕大膽而為、逐步擁有皇權(quán)奠定輿論的基礎(chǔ)。延康元年(220 年)十月,曹丕先后三次上《禪讓表》以示不受禪位之虛心,后作《受禪告天文》昭告天下,以天意所宣揚(yáng)其正統(tǒng)性,至此曹丕禪位之舉落下帷幕。在這個(gè)過程中不難發(fā)現(xiàn),自漢代董仲舒提出“天人感應(yīng)”和“君權(quán)神授”儒家學(xué)說以來,一直為王權(quán)的統(tǒng)治提供著理論基礎(chǔ),而對那些想擁有皇權(quán)的人來說,一旦違背了儒家政治哲學(xué)的理論基礎(chǔ),便成為所謂的亂臣賊子而被后人口誅筆伐。“在專制制度下,政權(quán)的轉(zhuǎn)移不可能通過民主的渠道實(shí)現(xiàn)。君主不僅獨(dú)占至高無上的權(quán)力和地位,而且沒有任何有效的制約機(jī)制和法定的任期限制,這就決定了皇權(quán)的更迭不可能一帆風(fēng)順。新勢力的變革和舊勢力的守舊,圍繞著權(quán)力展開殊死爭奪,其中或是血雨腥風(fēng),或是和平過渡,不管是誰置身于其中,都免不了受儒家道德標(biāo)準(zhǔn)衡量的評說。曹丕禪位以魏代漢踐祚皇位,因其舉動(dòng)有掩耳盜鈴之嫌,所以成為其詬病于后世、被指責(zé)為亂臣賊子、貼上篡逆標(biāo)志的原因之一。
然而用歷史發(fā)展的眼光去考察當(dāng)時(shí)的現(xiàn)實(shí)情況,就會(huì)明白其中有著發(fā)展的必然。從曹操開始,皇權(quán)實(shí)際已經(jīng)逐漸轉(zhuǎn)移了,曹操?zèng)]有稱帝是時(shí)機(jī)不成熟也不具備條件。曹丕繼承權(quán)力后所面對的三國鼎立的政治局面使權(quán)力擁有者發(fā)生了觀念及行為的變化,此時(shí)的曹丕需要集權(quán)于自身去完成政治任務(wù)。而對于社會(huì)的長久安定乃至國力的發(fā)展來看,也需要一個(gè)強(qiáng)有力的領(lǐng)導(dǎo)者去有效實(shí)踐施政方針。從所具備的天時(shí)、地利、人和發(fā)展來看,曹丕以魏代漢踐祚皇位勢在必行。
[1]郭沫若.歷史人物[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79.
[2](南朝宋)范曄.后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5.
[3]張作耀.曹操傳[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4]杜贊奇.文化、權(quán)力與國家[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
[5]楊永俊.禪讓政治研究[M].北京:學(xué)苑出版社,2005.
[6]孫正聿.簡明哲學(xué)通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7](晉)陳壽.三國志[M].北京:中華書局,1959.
[8]余華青.權(quán)術(shù)論[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