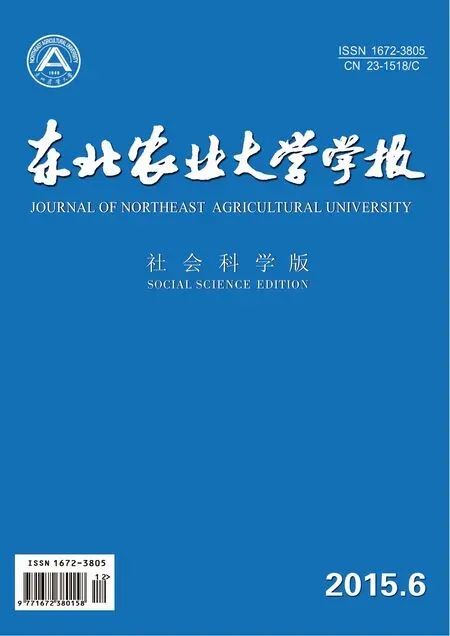張耒與蘇轍贈別詩中的禪性表達
楊威
(吉林大學,吉林長春 130012)
張耒與蘇轍贈別詩中的禪性表達
楊威
(吉林大學,吉林長春 130012)
張耒及冠前便與少公蘇轍有交誼,身居名流的蘇轍對籍籍無名的張耒十分器重,張耒從臨淮主簿,再到咸平縣丞,后進京入館,無論處在人生何種階段,蘇、張二人均保持密切的師友關系。二人之間的贈別詩中屢見慰問之語,細觀之,蘇、張常舉禪語相互寬慰。識禪、禮禪為“蜀門”偏愛,蘇、張贈別詩中禪性表達更為“蜀門”禪境平添一筆特色。
贈別詩;勞世;禪
張耒與蘇軾兄弟之間的交誼可從學術、文學、政治、單線聯(lián)系、宏觀交誼圈等多角度考查,學者已做出諸多努力。如楊勝寬在其文《改革與人生:蘇軾、張耒的共同話題——兼論黃州之貶對二人的影響》中強調:“蘇軾兄弟與蘇門弟子的結合,主要是文學意義上的,而非為政治目的而結盟。”[1]崔銘撰文《從少公之客到長公之徒——論張耒與二蘇的關系》,對張耒與少公蘇轍之間的交往時限及相關細節(jié)做有益的考證工作,同時強調二人“并不因日月的遷轉而疏遠,反因歲月的流逝而相知益深”[2]。此外,楊勝寬、馬斗成、孔凡禮等分別撰文探討蘇軾與張耒之間的交誼情況,雖著眼于大蘇與張耒之間關系,卻不約而同地強調少公在其中起到媒介作用,如馬斗成、馬納先生考:“從蘇轍、柳子文處,蘇軾對張耒的才識人品應已有耳聞,故有以上二賦之和,并由此奏響蘇軾與張耒友誼的序曲。”[3]
一、琴、酒與“山居”
蘇轍、張耒以才相引,又因地而聚。二人有著機緣的交匯點——陳州。
陳州可謂張耒的第二故鄉(xiāng),張耒少年時期即在陳州度過。熙寧九年(1076年),張耒父親亡故,在居喪期間,張耒“奔走于陳州、蘇州一帶,就食以繼活”[4]。紹圣年間(1094—1098年),張耒亦在陳州度過晚年。
熙寧三年(1070年),在張方平舉薦下,蘇轍被改辟為“陳州教授”:
二月戊午,觀文殿學士、新知河南府張方平知陳州,方平奏改辟轍為陳州教授。有《初到陳州詩》二首[5]。
此時蘇轍三十二歲,李宗易(張耒的外祖)辭官賦閑陳州,蘇轍不時前往李宗易寓所拜望,期間,十八九歲的張耒在陳州游學,結識長自己十五歲的蘇轍,《與黃魯直書》云:
仆年十八九時,居陳學,同舍生有自江南來者,藉藉能道魯直名[6]。
張耒青少年時光多在外祖父家度過,張耒有《初離陳寄孫戶曹兄弟》一詩:“三年流落寓于陳,一命青衫淮水濱。城北橋邊長送別,扁舟今自作行人。”[6]這首詩不僅透露張耒在陳州生活的大致時間,同時亦流露出其“出世”和“入世”之間的徘徊心態(tài)。蘇、張二人在陳州相識相交為其一生友誼打下堅實基礎。大概從此時到張耒任臨淮主簿期間,蘇轍將張耒推薦給蘇軾。《宋史》:“游學于陳,學官蘇轍愛之,因得從軾游。”[7]蘇轍的推薦使得張耒受到大蘇矚目,居官臨淮主簿第二年(1075年),張耒應大蘇之邀撰《超然臺賦》。大蘇之舉自有延譽張耒之意,從此角度看,張耒的才華已得蘇軾認可,這為日后張耒躋身“蘇門學士”做好前瞻。
蘇轍和張耒的友誼同樣體現(xiàn)在二人的詩文唱和中。張耒的早年文名與當時文壇翹楚蘇轍的獎掖有很大關系,《欒城集》中記載蘇轍與張耒詩酬數(shù)首,雖不很多,亦足可窺豹。其作略有:《次韻答張耒》《次韻王適送張耒赴壽安尉二首》《次韻張耒見寄》《次韻張耒學士病中二首》和《次韻張君病起二首》。在《欒城集》和《宛丘先生集》中多次記錄二人唱酬的詩作,其中兩首:
客行歲云暮,孤舟沖北風。出門何蕭條,驚沙吹走蓬。
北涉濉河水,南望宋王臺。落葉舞我前,鳴鳥一何哀。
重城何諠諠,車馬溢四郭。朱門列大第,高甍麗飛閣。
湯湯長河水,赴海無還期。蒼蒼柏與松,岡原常不移。
覽物若有嘆,誰者知我心。口吟新詩章,予撫白玉琴。
鳴琴感我情,一奏涕淚零。子期久已死,何人為我聽。
推琴置之去,酌我黃金罍。幽憂損華姿,流景良易頹[6]。
(張耒《泊南京登岸有作呈子由子中子敏逸民》)
客舟逝將西,日夜西北風。維舟罷行役,坐令鬢如蓬。
偶從二三子,步從百尺臺。云煙遍原隰,敞怳令人哀。
山中難久居,浮沉在城郭。欲學揚子云,避世天祿閣。
浮木寄流水,行止無所期。何須自為計,水當為我移。
外物不可必,惟此方寸心。心中有樂事,手付瑟與琴。
夜吟感秋詩,惜此芳物零。幽人亦多思,起座再三聽。
白駒在空林,瓶罄有恥罍。盡我一杯酒,愁思如云頹[5]。
(蘇轍《次韻答張耒》)
兩首詩的步韻韻腳分別是“風”“蓬”“臺”“哀”“郭”“閣”“期”“移”“心”“琴”“零”“聽”“罍”“頹”。次韻之詩雖然是文人之間相互酬答的一種文字游戲,但也真切反映出文人的文字功力。
張耒這首詩辭壯意豐,思想相對豐贍,上部分證道儒家的入世情懷。以儒業(yè)為本的文人士大夫常借“贈別”掘得一片美學天地,古來“贈別”之作卻難得突破“傷懷”的基調。張、蘇之間的離別同樣難脫窠臼。但細品其詩,卻也別有一番風味。其最得意的地方在該詩的后半部分,借“琴音”和“酒意”表露禪趣,藉禪抒懷,這在宋詩之中普通文人的詩贈交往中的確別具新意。一般而言,伯牙子期喻知音難覓不足為奇,但這段故事卻常被禪家引用,產(chǎn)生許多公案。如《天圣廣燈錄》中的兩段記載:
問:久負勿(無)弦琴,請師彈一曲。師云:“不是鐘子期,聵人徒側耳。”[8]
問:“伯牙未遇鐘子期時如何?”師云:“夜靜更深彈一曲。”進云:“遇后如何?”師云:“琴破弦斷一時休。”[8]
琴音禪趣是宋詩中常見的移情手法,禪語非深悟者難明,琴曲非知音者不知。張耒借禪語難悟如琴聲,實傳“我心誰懂”之真意,用心良苦,也足見蘇轍在他心中的知音形象。
在佛門音樂中,能夠感受內心的寧靜、安和。然而真正的禪門之音卻并不重在降服心中執(zhí)著的心魔,更重在對“心性”的啟悟。禪門忌諱“因聲得聲”,一旦墜入聲念便是執(zhí)著,倘放不下執(zhí)著便是未入門庭。真正的真如是妙得“弦外之音”。得其“理”而遺棄“表”正是禪家三昧。所以禪門啟悟常用“無弦琴”。鐘子期是凡世的知音又是佛門接悟的對象,以心對心,作不語之言,解弦外之音。若不解琴音,則不是接悟人,是琴旁聵人。
總體而言,張耒的詩在沉郁之中見諸性靈,孤獨和不舍間暗蘊真意。
蘇轍步韻其詩,以禪對禪,寬慰摯友。所謂“維舟罷行役,坐令鬢如蓬”,意即現(xiàn)在若掛舟不行,現(xiàn)狀未必改觀。“云煙遍原隰,敞怳令人哀”又暗喻朝堂之上“云煙”彌漫,勸慰朋友不該在此壓抑、肅殺的環(huán)境之下久居不移。無論故園和老友有幾多不舍,畢竟“山中難久居,浮沉在城郭”。
禪宗興起后,山居之風盛行,不僅一些高僧大德隱于山中,廟堂之上的文臣雅士也經(jīng)常為自己營造山居環(huán)境,進山過一段“身隱”時光。此處蘇轍借用“山居”便已動禪心。
宋代文人士大夫常懷“逃禪”之念,對“山居”的向往即是明證。據(jù)《全宋筆記》記載:
謝希深、歐陽永叔官洛陽時,同游嵩山。自潁陽歸,暮抵龍門香山。雪作,登石樓望都城,各有所懷……永叔取手板起立,曰:“以修論之,萊公之禍不在杯酒,在老不知退爾。”時沂公年已高,若為之動。諸公偉之[9]。
謝希深與歐陽修同游嵩山并無值得關注之處,然二人“各有所懷”卻頗值玩味。文中并未細言二人“所懷”的內容,然而從歐陽修后面“老不知進退”之論中,不難想見其登山觀望時的心理狀態(tài)。歐陽修憑山而招,所思正是在功成名就時歸山而居,進者儒,退者禪,能勘破人生進退,方是大智大慧。也正是這種人生智慧,才能沖破陳見,引得沂公“為之動”,諸公“偉之”。又,宋代和尚釋延壽亦作長達四千三百余言的超級長詩《山居詩》以體證“山居”的種種態(tài)度。限于篇幅,只截取其中一部分:
此事從來已絕疑。安然樂道合希夷。依山偶得還源旨。拂石閑題出格詩。
水待凍開成細溜。薪從霜后拾枯枝。因茲永斷攀緣意。誓與青松作老期。
古樹交盤簇徑深。闃無人到為難尋。只和算計千般事。誰解消停一點心。
凍鎖瀑聲中夜斷。云吞岳影半天沉。寒燈欲絕禪初起。透牖疏風觸短襟。
祗園閑適樂簞瓢。莫訝煙霞道路遙。龍穴定知潛碧海。鵬程終是望丹霄。
撥云巖下來泉脈。嚼草坡邊辨藥苗。門鎖薜蘿無客至。閹前時有白云朝[10]。
禪僧“山居”追求“物隱”是應有之義。“物隱”營造出的淡雅、清澈、超脫的外部環(huán)境即為內心深修而設。換言之,真正深修之人的心境需與外境同而無別,才是修行的根本境界。《古尊宿語錄》云:
上堂云:“道安巖下,朝朝鐘鼓聲喧,傘蓋山前,日日煙霞覆地。猿啼嶺上,魚躍淵中。山高則九夏花開,谷深則三冬積雪。知有者暢快于平生,不知有者空愛好山水。諸上座盡是知有者,不喚作山,不喚作水,且道喚作什么?開口即邈,擬議即差。”[11]
禪宗修“山居”品性,在于其內心的外推過程。“猿啼嶺上,魚躍淵中”似乎不難尋見,但“九夏花開”“三冬積雪”則在現(xiàn)實世界難得一見。而一旦禪修大悟,便正如“九夏花開”“谷深積雪”,其或豁達、或潛隱的修持狀態(tài)都在此“山居”之境中展現(xiàn)。真正得悟時眼中、心中已“無山水”,此境界只緣合自心,只有內心的正念才能契悟,任何言語議論都將謬之千里。“山居”真意正是身居山內而心悟山外。
蘇轍次韻張耒的詩中恰充溢著文人特有的“山居”情結。身心相悖正是儒禪焦灼的思想之辯。身在宦場,心向“山居”。因此“山中難久居”便成為必然,心之向往與身之羈絆構成不可調和的矛盾,進退維谷間,作者想到楊雄。事實上,天祿閣并非避難所在,楊雄斷腿于天祿閣下。蘇轍又設一喻,人生如寄身流水的浮木,行止不由自性,可他又不甘如此自怨自艾,“何須自為計,水當為我移”(“何”字疑為“可”字)一句別開精進之境。“怨”“樂”之意的轉衍全在自心,“自為”即藉“心”而為。身處逆境,“心”實有為,“水當為我移”便是“心意”作用的結果。“外物不可必,惟此方寸心”一語道出三昧:外境怎能成為索心縛性之網(wǎng)?區(qū)區(qū)“方寸心”正是破網(wǎng)解厄的真諦所在。此心此境,何苦之有?“琴”“酒”也從排憂澆愁之物變成“解憂取樂”之器,尾句“盡我一杯酒,愁思如云頹”正是這種心境下的結果。
二人在詩中皆談到飲酒,酒為消愁之物,常擾亂心性,所以禪門戒酒。但酒卻不避禪門。禪門中,酒戒為“遮戒”,而非“性戒”,可持亦可不持。禪林因酒得悟的例子也是不勝枚舉。由此可見,禪宗修持不在于靜、清與否,卻重在能否在淑與狂之間尋得禪悟真諦。
蘇轍的解勸不流于空浮,“理”事圓融,情神同傳,“心禪”兼?zhèn)洹M瑯淤泟e,二人接引之媒卻殊別他人。
二、“勞世”之嘆
元豐元年(1078年),張耒拜官壽安尉,有詩云:
其一、
西來秋興日蕭條,昨夜新霜緝缊袍。開遍菊花殘蕊盡,落余寒水舊痕高。
蕭蕭官樹皆黃葉,處處村旗有濁醪。老補一官西入洛,幸聞山水頗風騷。
其二、
落泊云隨宿雨開,西風似與早寒催。曉天雁起平沙去,霜岸風鳴敗葉來。
擾擾勞生移歲月,紛紛過眼旋塵埃。求田問舍真良策,功業(yè)應須與命偕[6]。
(張耒《赴官壽安泛汴二首》)
王適作詩送別,此時蘇轍亦步其韻贈別張耒:
其一、
綠發(fā)驚秋半欲黃,官居無處覓林塘。浮生已是塵勞侶,病眼猶便錦繡章。
羞見故人梁苑廢,夢尋歸路蜀山長。憐君顧我情依舊,竹性蕭疏未受霜[5]。
其二、
魏紅深淺配姚黃,洛水家家自作塘。游客賈生多感概,閑官白傅足篇章。
山分少室云煙老,宮廢連昌草木長。路出嵩高應少駐,孱顏新過一番霜[5]。
(蘇轍《次韻王適送張耒赴壽安尉二首》)
張耒任壽安縣尉時剛剛二十五歲,卻在詩中作“老補”之語。唐宋文人常皆故作老態(tài),此與特定時代及個人頻繁遷謫有關,其對儒業(yè)不諧之痛楚體會顯得更為超前。即將遠行,第一首張耒依然以“秋興”“新霜”“缊袍”“菊花”“殘蕊”“寒水”“黃葉”渲染離愁別緒,以“蕭”“盡”“寒”“黃”“濁”增重凄婉氛圍。作者滿腹牢騷,很不情愿,但尾聯(lián)一句“幸聞山水頗風騷”還是在心理上給自己些許慰藉。壽安地處洛水之濱,自然景觀和人文遺韻皆值得稱道,這或許也抵消了作者的慍懣,尾聯(lián)反而顯得豁達很多。
張耒的第二首依然以哀景起句。“云”“風”“雁”“葉”等意象極描飄零之境。“催”“去”“來”暗寓無奈與倉促。最為精彩之處還是后兩句。“勞生”“塵埃”皆佛語,可知張耒善借佛禪寬慰自己。僅僅二十五歲的張耒便已有勞世之嘆,在紛紛擾擾、忙忙碌碌的俗物中消耗生命,過眼之物皆如塵埃,也正是禪家對生命的理解。
“勞世”一語實早見于《莊子·大宗師》:“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12]莊子對人生的感悟為中國文化帶來至為深沉的思考,無論哲學、美學,抑或文學作品,“勞世”觀都在各個層面上被國人繼承和發(fā)揚。
《莊子》是道家思想的代表,其中的一些文化精神常與后漸中原的佛學思想不謀而合。這是佛教能夠迅速在精神信仰層面與國人產(chǎn)生契應的重要原因。因此,人們亦將《莊子》中的佛禪因子稱為“莊禪”。莊子的“勞世”之嘆又在后來的佛學經(jīng)典中演繹成“塵勞”,其精神內涵貫徹如一,如:
慧遠《無量壽經(jīng)義疏》卷上云:“五欲境界,有能塵坌,勞亂眾生,名曰塵勞。”
“五欲境界”即塵世,“勞亂眾生”即“塵勞”。張耒受宦游之苦,興“勞世”之嘆,正是禪門精神的真切反映。在蘇轍的次韻之作中亦見“浮生已是塵勞侶”之句,可見,“勞世”之嘆已在文苑產(chǎn)生廣泛共鳴。
“求田問舍真良策,功業(yè)應須與命偕”說的是當年許汜在國難當頭之時還在“求田問舍”,結果受到陳登奚落的典故。張耒對“擾擾勞生”不免產(chǎn)生自嘲之念:與其在毫無質量的生命顛簸之中消磨韶光,不如在有限的生命長度之內尋求“沉淪”。這明顯是一種自嘲,亦是禪家的打諢手法。
禪門慣用打諢實源于其對“人生如戲”“人生虛幻”的深刻認識。至宋代,勾欄瓦舍等娛樂場所的涌現(xiàn)及休閑意識的不斷高漲,將戲劇推向新的高度。而戲劇四門中又恰恰有“說經(jīng)”一門。“說經(jīng)”說的便是佛經(jīng)故事,在說的過程中難免將戲劇慣常的自嘲、打諢手法介入其中。佛門并不排斥這種新的表現(xiàn)形式,甚至藉此表現(xiàn)禪學旨微。宋代著名詩僧惠洪有《你能禪三鄉(xiāng)俊宿山》:
湘西春色無人要,萬頃鏡空飛白鳥。小閣披衣眼力衰,一聲欸乃酬清曉。芒鞋閑穿聚落來,此岸綠陰行不了。南臺老未忘鄉(xiāng)井,扺掌清談輒高笑。烹茶煮筍未當勤,放意賦詩語奇峭。此生何處不戲劇,萬事隨緣真道妙。何當借子西齋宿,共看湘月千峰表[13]。
人生緣起緣滅,亦實亦幻,總歸于幻。“打諢”“自嘲”能在看似嚴肅不茍的禪門流行,恰反證宋代文化亦俗亦雅的一面。
面對張耒的“牢騷”,蘇轍展示出長者之風,從始至終地寬慰摯友。蘇轍的兩首和詩基調并不沉重。此時雖已秋黃,但并非沒有可觀之景致,彼處尚有“洛水”“少室”“連昌”之景,而此處尚“無處覓林塘”,弦外之音已充滿寬慰之情。對張耒的“勞世”之念,蘇轍以禪境接引,“浮生”是佛家之常喻,此處蘇轍雖已肯定張耒的“勞世”說,但其真意在于“病眼猶便錦繡章”,處“勞世”而不“沉淪”。頸聯(lián)應分成兩個畫面:前句以蘇轍本人為視角,后句以張耒為敘事視角。“羞見故人梁苑廢”實則想要表達“梁苑廢而羞見故人”之意。“梁苑”即西漢梁孝王所建的“東苑”,是延攬人才之地,亦是才俊雅集之所,自他離去,雅集難行,自然有“梁苑”已廢之嘆。后句以張耒為視角,言其夢回故土需越一道道蜀山,其中不舍之情溢于筆端。尾聯(lián)讀來令人惻然,是蘇、張二人情誼的最真切寫照。蘇轍對張耒品性贊譽有加,以“竹”喻“品節(jié)”,恰當工穩(wěn)、意境高遠。
第二首詩蘇轍愈顯長者風度,不僅典工意新,而且意味深長,頗見功力。總而言之,少公此詩意在勸慰朋友:壽安地界既有各色旖旎風光,又有少室山、嵩山的壯景;既有賈太傅的感傷,又有王昌齡的吁嘆。自然風光和人文環(huán)境皆入上品,還有何求?
蘇轍是張耒的摯友、人生導師和德高望重的長者,張耒也是蘇轍最為欣賞的才子、后生和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朋友。二人相互以才、德砥礪,且在精神寄托和排解塵網(wǎng)的方式上亦趨一致,在二人的很多詩作當中有所體現(xiàn)。再舉二例。
相逢十年驚我老,雙鬢蕭蕭似秋草。壺將未洗兩腳泥,南轅已向淮陽道。
我家初無負郭田,茅廬半破蜀江邊。生計長隨五斗米,飄搖不定風中煙。
茹蔬飯糗不愿余,茫茫海內無安居。此身長似伏轅馬,何日還為縱壑魚。
憐君與我同一手,微官骯臟羞牛后。請看插版趨府門,何似曲肱眠甕牖。
中流千金買一壺,櫝中美玉不須沽。洛陽榷酒味如水,百錢一角空滿盂。
縣前女兒翠欲滴,吏稀人少無晨集。到官惟有懶相宜,臥看南山春雨濕[5]。
(蘇轍《次韻張耒見寄》)
這首詩作于元豐二年(1079年),此時蘇轍年屆四十,依然沉郁下僚,不得重用,且謫宦不已,先后歷宦筠州、汝州、袁州、雷州等地。和兄長一樣,蘇轍的謫旅坎坷不定,這一點與張耒極相似。熙寧六年至元豐八年(1073—1085年),張耒先后在安徽、河南等地做了十多年縣尉、縣丞一類地方官,并因秩滿改官不斷,往來京洛間,為政特別辛勞。“我迂趨世拙,十載困微官”(《悼逝》),“飄然羈孤,挈其妻孥,就食四方,莫知所歸”(《上蔡侍郎書》)所言即是這段經(jīng)歷。
可以說,蘇、張二人皆體驗過真實“勞世”的滋味。
蘇、張在經(jīng)歷上的相似完全可以用“憐君與我同一手,微官骯臟羞牛后”一句形容,二人惺惺相惜,常以禪、道的修持手法解慰“勞世”之苦:
宛丘之別今五年,汴上留連才一日。殘生飄泊客東南,憂患侵陵心若失。
先生神貌獨宛然,但覺巖巖瘦而實。有如霜露入秋山,掃除繁蔚峰巒出。
自言近讀養(yǎng)生書,頗學仙人餌芝術。披尋圖訣得茯苓,云是松間千歲物。
屑而為食可不饑,功成在久非倉卒。上侔金石免毒裂,下比草木為強崛。
涓涓漱納白玉津,鏈以真元納之骨。神仙自是人不知,豈為難求廢其術。
我聞公說心獨嗟,欲問太虛窮恍惚。奈何不使被金朱,乃俾枯槁思巖窟。
又觀世事不可常,倚伏誰能定于一。終身軒冕亦何賴,況有朝升而暮黜。
何如端坐養(yǎng)形骸,壽考康寧無夭屈。乃知豈即非良圖,卻笑兒曹嗜糠籺。
青衫弟子昔受經(jīng),賦分羈窮少倫匹。自知無命作公卿,頗亦有心窮老佛。
但思飽暖愿即已,妄意功名心實不。終期策杖從公游,更乞靈丸救衰疾[3]。
(張耒《再寄》)
此詩交流了道、禪的修持精微。道家重養(yǎng)生,煉丹服藥、吞津吐納是每日功課。太虛之境是世俗幻境的對應,是道、禪對真諦的求索。詩中潛涌著“形骸”“功名”“佛老”諸義。本詩從頭至尾盡是對“勞世”的回顧,結尾嘆息“儒業(yè)”未竟之余,坦露許身佛門之意,故“自知無命作公卿,頗亦有心窮佛老”為全詩的主題。結句反思人生真諦,“妄意功名心實不”是對“功名心”的批判,借此也點出“勞世”根由。這首詩誠可作為史料性文獻,折射出一個“四十不遇”、顛沛不已的儒者形象,字里行間不僅透出張耒和蘇轍相交之深,又能在言語間深刻感知二人交誼的紐帶——相似的經(jīng)歷和共同的精神寄托。
三、結語
蘇詩中有“中流千金買一壺”的醉世禪意,也有“臥看南山春雨濕”的閑禪啟悟;張詩中有“又思人世樂乃已”中隨緣自足的禪趣,也有“青衫弟子昔受經(jīng)”的“心隱”祁尚,更有“自知無命作公卿,頗亦有心窮老佛”的逃禪之意。在佛禪世界中,二人可以滌除“勞世”煩擾,在精神上尋得寸心的安定。蘇軾有言:“甚矣,君之似子由也”[14],如果說張耒為文作詩在遣詞、藝術祁尚、風格追求等方面與蘇轍高度一致,那么,蘇、張之間的禪性表達更是不可忽視的緊要一環(huán)。換句話說,內在精神的密切性更應成為考查二人交誼、詩文契密程度的重要標準。
贈別之言自古及今很難突破凄索的界囿,而張耒與蘇轍之間的贈別詩中卻潛涌著難得的禪慰之語,頓開“贈別”之別境,世俗慣有的憂慮與恐懼似在片字禪語中遁形消散,正如盧重玄疏解《列子》云:“仁者不憂,智者不懼,不受形也。”[15]蘇、張贈別詩中的禪性表達正契其指歸。
[1]楊勝寬.改革與人生:蘇軾、張耒的共同話題——兼論黃州之貶對二人的影響[J].黃岡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96(1).
[2]崔銘.從少公之客到長公之徒——論張耒與二蘇的關系[J].求是學刊,2002(3).
[3]馬斗成,馬納.蘇軾與張耒交誼考[J].泰安師專學報,2002(1).
[4]周義敢,周雷.張耒資料匯編[M].北京:中華書局,2007.
[5]蘇轍.欒城集[M].曾棗莊,馬德富,點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6]張耒.張耒集[M].李逸安,等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0.
[7]脫脫.宋史(卷四百四十四)[M].北京:中華書局,1977.
[8]佛光大藏經(jīng)編修委員會.天圣廣燈錄[M]//佛光大藏經(jīng)·禪藏(史傳部卷十九).高雄:佛光出版社,1994.
[9]朱易安,傅璇琮.全宋筆記[M].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
[10]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全宋詩[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1.
[11]賾蔵.古尊宿語錄[M].蕭萐父,呂有祥,蔡兆華,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6.
[12]郭慶藩.莊子集釋[M].王孝魚,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61.
[13]惠洪.石門文字禪[M]//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商務印書館, 1996.
[14]蘇軾.蘇軾文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6.
[15]列子[M].張湛,注.盧重玄,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I222
A
1672-3805(2015)06-0067-06
2015-10-12
楊威(1981-),男,吉林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方向為唐宋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