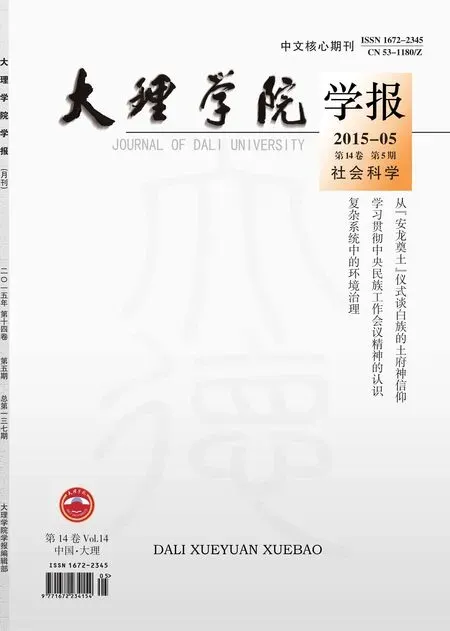學習貫徹中央民族工作會議精神的認識
周明甫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北京 100800)
一、關于中央民族工作會議的背景
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于2014 年9 月28 日召開。這次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會議。因為第一次是1992 年1 月14號開的。當時,我們請示是開一個全國民族工作會議,時任總理李鵬同志把全國民族工作會改為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以后,這個會議就這么定格了。就是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暨國務院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兩個會議合并起來。由于第一次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是1982 年開的,所以1992 年這一次等于是第一次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暨第二次民族團結表彰大會。2014年這一次是第四次。
每次會議它都有它的內容,有它的背景。第一次會議,我們實際上是從1991 年的1 月2 日開始準備的。這次會議主要解決一個國際上蘇聯解體,我們國家怎么面對這個情況的問題。第一次中央民族工作會議出臺了總書記、總理的講話。在第一次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之前,在1991年12月26日配合中央民族工作會議,國務院就出臺了關于貫徹民族區域自治法的若干意見。
第二次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是1999年開的,這次會議主要是考慮過去我們長期以來將民族問題界定為階級問題,把民族問題界定為民族和民族之間的關系問題。第一次中央民族工作會議非常明確提出來,我們要從過去的階級斗爭轉到發展上來,要把過去認為民族問題就是民族和民族的關系問題轉變到“一個發展,三個關系”的新的提法上。1999年主要配合國家整個發展戰略的調整,要突出西部發展戰略,也就是我們的西部大開發。所以,1999 年這次會議(的內容)主要就是江澤民總書記的講話,就是加快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問題。
第三次是2005年5月26日開的,這次會議主要就是到2005年的時候,面對我們前頭的一些事和國際上的一些事。所以,這次會議出臺的東西比較多,一個是中央領導的講話,也就是總書記的講話、總理的講話。還有當時作為國務院的委員司馬懿主任關于學習貫徹民族工作會議的一些意見。另外,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之后,中央出臺了2005 年的10號文件。10號文件是中央第一次出臺的黨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民族工作,加快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發展的決定。同時,國務院又出臺了關于實施民族區域自治法的若干規定,也就是出臺了一個行政法規。同時還出臺了三個規劃,即《扶持人口較少民族發展規劃》《興邊富民行動規劃》和《少數民族事業規劃》這三個國家級專項規劃。可見,2005年的會議的文件和內容都比較多。
第四次會議文件主要是幾個領導人的講話,還有就是進一步加強民族工作的25 條。這次會議有三個方面的背景情況。一個是國際上的背景情況。國際上,從蘇聯解體一直延續到東歐國家的解體,南斯拉夫的分裂,今天的烏克蘭問題。涉及到民主方面的東西,也就是北非和中東的顏色革命。還有就是“9·11 事件”以后暴力恐怖的問題引起全世界的關注,特別是高層,尤其是國家領導人,對我們的影響是不可忽略的。第二個方面就是從2008年西藏的“3·14事件”和新疆2009年的“7·5事件”,以及天安門的暴力恐怖事件,一直到昆明的火車站暴力恐怖事件,還有內蒙的“5·11 事件”,以及第二次中央民委中央新疆工作會議以后的“5·29暴力事件”等一系列的事件。還有就是國內我們的學界出現了一些不同的聲音。有的大家都知道的,名字報紙上都公開的。一個就是中央統戰部的原常務副部長朱維群同志關于民族領域的幾個問題的思考。還有就是馬戎先生的民族問題的去政治化。還有就是(胡鞍鋼)提出的第二代民族政策。這些東西對我們整個民族界,包括理論界,包括全社會,都引起了種種思考,種種議論。為面對這種新情況召開了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會議。它主要就是很明確地針對和國際關系的不同情況,中央斬釘截鐵地說,我們必須要堅持走中國特色的解決民族問題的道路。
二、關于中央提出必須要堅持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道路的原因
一個是中國的國情。中國的國情可以概括成5句話。也就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延綿五千年不斷的中華文明,我們是世界上的人口大國,我們的國土遼闊。第5 句話是,雖然我們現在的經濟總量是全球第2位,但是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所作的2013年全球人類發展報告當中,中國現在的人類發展指數在全世界排名第101位。中國五千年的歷史是不容改變的。五千年歷史中的輝煌和屈辱,悲歡離合是不容漠視的。孕育了五千年的文化基因是不容中斷的。所以特殊的中國國情就決定了我們只能走自己的路。我想這可能是第一層意思。
一個是我們中華民族,我們五千年都是一種單一制的國家體制。也就說,幾千年來中央王朝和地方王朝之間的關系是一種松散型的,也可能是一種緊密型的,也就是中央王朝和其他幾個王朝的合作比較好。大家都承認你是君,他是臣。你是主,我是副。或者再進一步說,我們是一體式的,中央王朝對地方政府的管轄是非常到位的。比方說解放后我們就是這種格局,但不管是解放前還是解放后,我們五千年單一制國家的歷史就決定了我們是這種體制。這種體制就是國家的架構、制度的安排、政策的設計,說明中國只能走自己的路。像中國這種情況全世界也是唯一的。
一個是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我們的治國理念,我們的價值取向,就決定了我們只能走自己的路。共產黨的價值取向,我理解就是六個字:平等,團結,繁榮。我想對團結兩個字多說幾句話。可能一般的同志一想起團結就想起民族和民族之間的關系。實際上,團結的涵義更深層。因為大家都知道,民族的產生,民族的發展,也必然有民族的滅亡。而團結不但是維護各民族之間團結和社會穩定的一種重要手段,也是我們的一種目標。同時也蘊含著促進各民族之間的交流、交往、交融,最終實現融合。是不是還有這么一層意思?但團結這個詞大家更容易接受。作為學者來說,可以想得更多一點。所以我想,我們這三個特性,也就是中國的國情,中國五千年單一制國家的歷史,中國執政黨的執政理念。這三條可能在全世界都是唯一的,所以,這三個唯一性就決定了中國只能走自己的道路,也只能在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中,走出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道路。
三、關于堅持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道路的路徑思考
第一,道路不是我們平常走的路。解決民族問題前面的路是什么?路在何方?從社會學的意義上講,我們說的道路只是說的過去的路,也就是說過去我們的路走在這兒了,證明我們走對了。但是,我們堅持這個路的理念,我們的價值取向,我們的選擇,實際上就決定了我們未來的路的走勢。所以這條路也就是正在進行時。所以堅持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道路,它必然蘊含著繼承和發展,鞏固和完善。也就是說只有發展才有堅持,沒有發展就不可能有堅持。所以,完善、發展、創新,就是我們未來的選擇。也就是說,要堅持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道路,就必須在現有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我想這是第一層意思。
第二,立足現代,面向未來。這條路怎么走呢?第一個問題就是對我們面臨的形勢和任務有一個總體的判斷和分析。我們可以分析出一百條,一千條,一萬條,條條都對。但我想來想去有一個最基礎性的問題,也就是中央現在成天強調的我們處于社會的轉型期。但這個轉型期現在論述的人不是太多。那轉型期是指的什么轉型呢?實際上就是指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我想,從人類學這個角度來解讀它的話,可能以2010 年為標準,我們已經基本結束了五千年的農耕文明,步入了工業文明的新的時代。這可能是轉型背后最深刻的東西。立足于現代,立足于我們最近一段時期,或者近十幾年來存在的很多問題,可以看到,可能是原先我們的理論,我們的理念,我們的制度,我們的政策,我們的工作方法已不適應這個轉型帶來的一系列問題。所以立足現代,面向未來,我們更應該是審時度勢,居安思危,未雨綢繆。
第三,必須面對現實的民族工作中面臨的一系列問題。今天我們都是學者。我想會議上說的這個對那個對,這個好那個好,都是正確的。我說的是立足現在,面向未來。我們已有的東西中我們還要完善的東西是什么,發展的東西是什么。我想破這個題可能是五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是我們的自治問題,或者叫自治制度問題。自治制度可能是四點。一個它是一項基本政治制度。倫理學,民族學所有涉及到民族問題的時候,從基本政治制度來談,來研究我們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有多少。一會兒我再說答案。第二個是自治問題。我們現在已經出臺了民族區域自治法,而且我們五個自治區,三十幾個自治州,一百二十幾個自治縣,除了新疆的五個自治州,六個自治縣以外,其他的都已出了自治條例。但我們的自治條例,包括我們的自治法所界定的內容基本上都是一般地方政府的一般問題,沒有突出的問題。也就說,既然是自治地方,首先一個問題,我們是中央和地方這個層面上。我們在地方這個層面,在地方層面當中的一種特殊類型。如果我們和一般類型都一樣,我們還自治什么。所以實際上我們應該自治什么,雖然有了法,有了條例,但實際上并沒有破解這個問題。這是自治當中的第二個問題。第三個問題,作為地方自治機關指的是地方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以及地方政府。這是法律規定的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尤其作為地方政府,要依法行政。而依法行政中,更多更具體的是具體法律所賦予它的行政權力。然而,除了憲法,母法,基本法,民族區域自治法外,所有的具體法律當中沒有一部法律說自治地方有什么權力。作為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必須依法行政,具體法律沒有賦予你這個權力,你從何行政呢?所以,怪我們的自治地方、自治政府沒有行使自治權力,或者行使不充分。第四個問題,我們的行政建制、行政區劃。大家知道,憲法規定我們是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下面是民族鄉。那么我們這一套行政建制是屬于省,自治區、地、州、縣、自治縣、自治旗,這是一套。另外一套是直轄市、地級市、縣級市。這是兩套政府。一套是城市政府,一套是區域政府,兩套政府系統的功能和配置是不一樣的。尤其是面臨兩個具體問題:一個是現在很多地方財政已經實行直管縣。尤其是我們自治州所屬的縣。如果自治州所屬的縣由省里直達以后,大家知道,我們所有的機構當中有一個財政,有一個民政,如果把財政這一塊由省直達縣以后,自治州還有什么啊?因為我們三十幾個自治州當中,只有新疆伊犁的哈薩克自治州是副省級單位,延邊自治州的州委書記是省委常委,剩下二十八個自治州,很多自治州所在地都是某一個縣的或是某一個市的某一個鎮。也就是說把縣這一塊切掉,它就成了個空的,自治州該怎么行使自治權呢?這種行政建制很難適應現代發展的情況。二是現在正在搞城鎮化。而且城鎮化這條路看來來勢越來越兇猛。作為我們這種區域政府,可以發揮一定的推動作用。但具體到自己就很難辦。我把這個事說簡單一點。比如說,黨中央國務院都在北京,那么北京市的每一寸土地的利用,劃撥的手續只有市長簽字才有用,總書記或總理簽字是沒有法律效力的。同樣,自治州的州長對所屬縣的土地利用這些具體的劃撥手續是沒有權的。所以在自治問題上,我就點出這四個事情。
我也想到底怎么辦好?我們現在那么多法律,我們要求所有的法律都給我說清楚,我這個自治縣可以自治什么?以這條思路去破解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同樣的,很多人從民族工作系統,中央也在努力在自治法下面去搞自治條例。我們都親身經歷了這個過程。二十多年了沒有搞成。我最終想明白了,在我們整個法律體系當中,母法、基本法、具體法律,下面是法規,然后到政府令,這套系統,下面的法必須服從上面的法。也就是說,你想要孫子必須先要兒子,如果沒有兒子不可能有孫子。所以,我想可能要在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一項基本政治制度這個角度去破解它。這項基本政治制度目前有些學者在探討的過程中認為,它實際上就是一種民主協商制度。我覺得可能是說得不夠。我想作為一項基本政治制度,從我們國家來說,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而民主協商也是一項基本政治制度。那么,我們作為一項基本政治制度,它需要什么法律來支撐它,需要什么制度配套來支撐它,它和根本政治制度,和其他基本政治制度到底是什么關系。尤其是廣西壯族自治區、寧夏回族自治區。你們注沒注意,內蒙古自治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西藏自治區,它沒帶民族的族字。所以這里頭也就隱含著很多的事情,需要我們去思考它。搞民族工作,堅持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道路這是個回避不了的問題。
第二個方面,是關系問題。大家都知道,我們有55個少數民族,但現在我覺得分類研究不夠。比如說我們55個少數民族當中,有一部分是在秦始皇統一全國之后,還在歷史上曾經長期建立過自己政權的民族,它和其他民族之間的關系,比如說我們還有三十多個跨境民族。當研究他們的民族關系的時候,肯定和其他民族也不一樣。比如說尤其在我們云南談這個問題,我們還有十幾個或者近二十來個民族,還有一大批,尤其我們南方民族一大批,就是兩千多年來,一直在中央王朝的統一統治下的民族的民族關系問題,肯定也和前幾類不一樣。比如我們集聚地區的民族關系問題和散居地區、和城市肯定不一樣。尤其是,當一個地域百分之百都是單一民族的時候,他們之間還有民族關系嗎?肯定沒有民族關系問題,只有自身發展問題。它只有和區域外的民族之間發生關系的時候才存在民族關系問題,所以民族關系問題中怎么分類法這是需要思考的。這樣研究出來的東西,研究出來的意見,研究出來的政策才有針對性,才有實效性。
民族關系中還有第二個問題,就是分層問題。我想一個就是我們到今天為止,不管是自覺還是不自覺,我們今天話語當中說的民族關系問題,基本上都是說的一個民族的整體和另一個民族的整體之間的關系。那對于我們這個大雜居、小聚居的國情,這樣來研究民族關系問題肯定是無法落地的。這是分層中的一個問題。第二個視角是局部地區部分群眾之間的關系問題。也就是說在民族學這個視角下,部分地區和局部地區的部分區域,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尤其是我們現在這種大交流、大交往的過程當中,少數民族現在一億多人口,已經有兩千多萬人口走出原來的居住地。在民族學的視角下,普通公民日常生活中的人與人的關系問題,可能又是一個研究民族關系問題的視角。第三個方面,是發展問題。發展問題從我們民族工作的角度講,一個是民族的發展。第一次中央民族工作會議就明確提出民族的發展。我們現在有一個誤區,認為現在單一民族區域研究會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煩。我也沒弄明白這個事。那是從民族制度的角度去研究單一民族問題,可能會帶來這一系列麻煩。但立足于現實,面向未來,我們已經法定了56 個民族,你不一個一個民族地去研究,怎么去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怎么去具體解決不讓一個民族掉隊的問題呢?而這就是少數民族發展進步的評價體系問題,一直到今天這個都沒出來。因為,這個事我已經弄了十年了。就在籌備第三次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搞少數民族“十一五”規劃的時候,就涉及到這個問題,但一直沒搞出來。因為有些資料沒法弄。我在來的頭一天有一個好消息。也就說“五普”的時候,在整個普查資料當中,民族的分卷出版了,兩本,加起來有這么厚,“六普”的資料,民族的資料也出來了,也是這么厚。也就是說,我們有十年之間的比較了。我們就可以用各民族的全國的數據,來和漢族,來和其他民族作一些比較和分析。這一套評價體系怎么建立還需要進一步去研究。然而,只要有了這套之后,你再具體研究自己民族區域的事情,你才好說話。比如回族是最典型的,全國哪兒都有,那么全國的回族整體發展,有一套指標體系可以量化的來說的時候,你對應著它說,寧夏的回族是什么,云南的回族是什么,你說的東西就有根有據了。還有一個就是民族地區的發展問題。民族地區發展問題大家都很關心,但是,從我們人類學、民族學這個角度,我們研究的發展和工作時候的發展,應該說視角是不一樣的。大家應該關注一下,尤其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們對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尤其是民族自治地方的政策取向應該好好研究一下。一切都讓市場去決定嗎?市場從來不愛我們少數民族的。真的是這樣的,我們的發展是這樣,我們的學生畢業就業也是這樣。但是一個國家,我們在研究這個問題的時候,沒有我們的價值取向嗎?在計劃經濟時代下,我們已有的優惠政策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應該更加優惠。但是這更加優惠如何來體現它呢?比如說,我們在計劃經濟時代,我們有財政優惠政策。比如說,1958年,在包頭建立鋼鐵廠的時候,我記得有三項政策:第一,鋼鐵產品當中,10%要留給包頭市;第二,在鋼鐵企業的利潤當中,要拿出10%留給包頭市;還有一個稅收。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們原先物質分配的這條邏輯就不起作用了,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主要手段一個是財政手段,一個是金融手段。這兩個手段中,應該怎么用能夠體現我們對民族地區的政策的價值取向。在我們就業問題當中,也是一大堆事。還有就是我們的人口流動也是一大堆事。在人口流動這個問題的研究當中,如果學者們感興趣的話,我建議你們應該用文化的視角來看。因為文化大家應該都很清楚了,這樣可以研究出人類學、民族學視角下的問題。還有一個是全國普遍的問題。在我們民族地區,一就是資源開發問題,還有資源開發中的土地問題。誰都可能知道,我們把農村的農民的土地征過來,給農民的是補償費。征過來之后,然后給開發商,搞的是交易。也就說,土地的價格是體現在交易當中的。再說白一點,從農民那里拿土地,一畝拿過來以后,可能是幾萬、十幾萬,能夠到一百萬、兩百萬的就太少太少了。但這一轉換成城市,政府拿了它來當招牌掛的時候,開發商來一平米弄不好就是十萬、二十萬、三十萬,如果一平米按三十萬來計算,一畝地是兩個億的價格。但是從農民那拿來是十萬、八萬。為什么對我們農民就不能用市場價來決定呢?我們不是說讓市場起決定作用嗎?如果我們開發商要用土地,我們這塊農民的地農民也去拍行不行呢?這可能是我們公有制國家剩下的一個最大的難題。然而在發展當中還有其他一些事情。
第四個方面,是文化問題。文化可能是四件事。一個就是我們傳統文化的表現形式,基本上都已經是景點化了;二是我們傳統文化的生態環境;三是我們傳統文化的民族認同和傳承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所以面對著傳統文化該上哪去,這是個必須思考的問題。第二,民族文化和主流文化和外來文化碰撞的時候,應該關注我們民族文化。第三,就是宗教文化。民間文化在宗教文化和民間文化發展中,它的流變是什么情況。也就是,宗教文化在發展過程當中。現在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宗教文化如果忽略它簡直是無知啊。那么在它的發展過程當中,宗教文化的發展,民間宗教文化的發展,和宗教信仰,民間信仰,這中間到底是什么東西?第四個問題,尤其是我們民族文化,民族傳統文化資源的產權和開發利用問題,都擺到我們面前了,現在產生的問題太多太多了。
第五個方面,是干部人才問題。搞民族工作,在民族地區,離開了民族干部隊伍肯定是不行的。這一塊是三支隊伍,一支隊伍是黨政干部,或者說公務員。現在需要關注的是什么,就是在現行一把手體制下,少數民族群眾占相當數量的地方,對一把手的配備是不是該考慮少數民族。第二個問題就是科技隊伍問題。培養科技隊伍問題當中,一個最主要的渠道就是我們的高等教育。如果在高等教育這個階段,能夠實現在校生的少數民族學生的比例和全國少數民族人口在全國人口的比例大體相當的話,我們這個問題就自然解決了。而現狀并不如此。少數民族在全國人口的比例是8.41%,但是在高等教育階段,我們最近十來年大體上是5%、6%,或者再多一點,沒有實現8%左右。在這個問題上,尤其是清華北大帶頭貫徹黨的民族政策。如果我們兩千多所,近三千所高校,都能夠實現總體上和少數民族在校生比例與少數民族在全國人口比例相當的話,科技人才的培養問題就差不多了。剩下的就是學校里頭怎樣去提升質量的問題了。第三個問題就是經營管理人才的問題。經營管理人才的問題如果我們三千所高校當中有兩千所左右都在著重于職業技術的培養,這個問題也簡單了。所以說,看得見方向,然而怎么具體去推動它,需要大家思考。所以我想對于堅持我們要走自己的路,在路徑選擇當中講了3個例子。
四、關于作為學者的責任和擔當
講學者的責任和擔當也是三層。學術、理論,是一個層面;法律、法規、政策措施,又是一個層面;實際工作又是一個層面。
這三個層面是個什么關系呢?就是一棵樹的關系。我們的實際工作就是枝和葉。大家希望枝繁葉茂,開花結果。但沒有干的支撐,行嗎?沒有根的供養,行嗎?所以,作為學者的責任和擔當,在座的各位學者,搞學術搞理論的,我們剛才說的這一堆事,你們必須把我們民族發展的規律、民族關系的規律,以及各個方面的規律、標準、范式要搞清楚。搞清楚了以后,這條路才好走。我說的是學術和理論,我沒有說學者。因為學者都是具體的人,當你處于這個社會的時候,你能不能按照理論上這種要求,堅持去做,要憑你們的學術倫理和學術道德。也就說,從學術角度講,就需要學者的職業道德。這是第一層意思。
第二層意思,你們的使命和責任是什么呢?尤其是人類學、民族學的學者都知道,我們回答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我是誰?”所以我們在說到整個歷史變遷當中,過去、現在和未來,你都要回答完過去我是誰,現在我是誰,未來我是誰。過去我怎么做的已經過去了,我現在該怎么做,未來該怎么做。這是第二層意思。
第三層意思,作為我們的學者要有擔當。我想這個擔當是什么呢?可能是兩層意思。一個就是你們必須在原有的理論基礎上,要有創新,要有引領。也就說我們原來的研究范式,經過了這些年,已經取得了很多很多成就,我們不說它,說的是我們現在面對著這么多事情,不該你們去引領,去解決它嗎?所以,不管從理念、理論,從視角、視野,從范式、模式、方式、方法,你們都要去研究。這里頭可能又是三個例子。一個就是現在中華民族也好,我們國家也好,已經進入了一種內源式的發展方式。也就說從鴉片戰爭到現代150 年,我們國家基本上走的是外源式的發展方式。簡單地說,就是這也好,那也好,都是從外國來的。然后,從國家層面領導人認可以后就推到下面了。外源式的意思就是從外到內,從上到下。內源式的發展方式簡單點說就是從下到上,從內到外。中華民族到了這個時候。第二個,我們五千年來或者是兩千年來,我們的研究范式基本上是我注六經。也就是說這是孔子說的,這是哪個說的,這是哪個外國人說的,現在要到了什么時候呢?到你說,你說完了以后,他一對,他和孔子說的一樣,他和總書記說的一樣,而這種轉變不需要擔當,不需要創新嗎?
還有第三層意思,我們多年來都是學這個,學那個的。說起來都是用中國的事實來驗證外國學者的觀點,我們不該轉變嗎?用中國的話語,在國際人類學中,創立中國的學派。所以每個單位,每個人都可能有自己具體的職責和任務,每個學者都有自己的專業和興趣。然而,堅持走中國特色的解決民族問題的道路是大家共同的責任。如果我們以堅持走中國特色的解決民族問題的道路去進一步做好自己正在做的研究,去實現自己的價值,可能是一種比較好的選擇。而且堅持走中國特色的解決民族問題的道路也是國家和社會對我們學者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