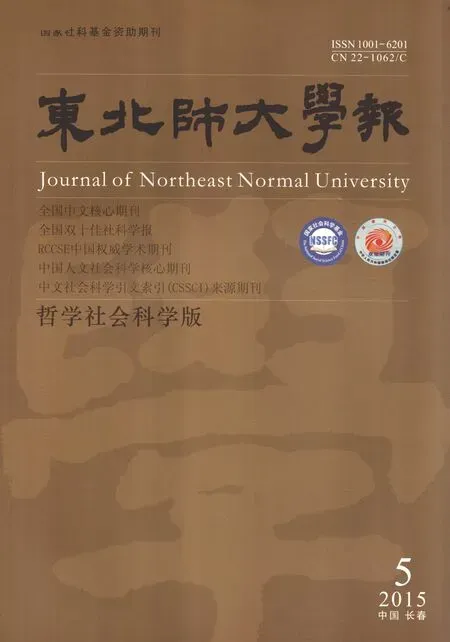黑格爾自由—權利辯證法視野下財產所有權概念的三層自由意境
羅朝慧
(中國政法大學 人文學院,北京102249)
關于黑格爾財產所有權概念,學界存在諸多爭論。有的認為它是為自由主義的權利理論辯護,主張所有權神圣不可侵犯甚至財產不平等思想;有的則認為它是對自由主義所有權觀念的批判,主張通過倫理國家實現和保護個人所有權;有的則持中庸觀點,認為它既包含了對自由主義的批判,又包含了對自由主義的辯護。然而,財產所有權或物權,到底在什么意義上是神圣不可侵犯,又在什么意義上是趨惡并值得批判的?財產所有權何以才能獲得正當的和客觀的普遍實現?如何調和或溝通財產所有權的神圣性與趨惡性?這些問題不僅屬于學理的,更是當代社會現實中為人們困惑并迫切求解的問題。實際上,黑格爾在其法哲學的自由—權利辯證法中,已經對財產所有權的三重自由意境作了清晰的闡釋和論證。在黑格爾那里,作為個人權利的生命、身體及財產所有權,乃是人類精神和道德自由之自然基礎與物質前提,包含著對個人獨立性與主體性的基本認同,具有不可任意侵犯和剝奪的神圣性。因為人的精神必須活在健康健全的有機生命體及其自然需要的滿足中,人的生命、身體及其私有財產的安全與保障,是個人獲得自我認同與尊重的外在感性表現形式,從而進一步尋求精神事業的創造和發展。
一、所有權概念的神圣性自由意境:個人自由意志或獨立人格的客觀表達
在黑格爾那里,財產所有權(property)概念,直接地源于個人的人格概念,即personality,根本地源于人自身精神的自由或理性本質。可以說,所有權概念是黑格爾假設的人類理性精神或自由本質自我認識和實現歷史過程中的最初階段,屬于人類對自身不同于世界其他人之獨特性的初步認識。“人從單純的內在生活,從純粹的思考,從規律與普遍性的世界,還不能得到安身之所,他還需要有感性的存在,要有情感情緒等等……人卻要從直接的生活中找到直接的滿足。”[1]125于是,自我意識的個人之相互區分,首先在于他的個人所有權,私有財產表達了他個人的特殊意志和目的。“私有財產是不可避免的第一步,即個體認識到自身最大愿望是理性自由的第一步。它是一個基本的世俗目的之首要的基礎性表達:外部現實的自由主人。共同擁有是對那種自由的危險性檢驗,因為個人將不被允許直接使用他們的財產作為他們特殊意志和目的的表達”[2]47-64通過財產的占有或私有財產,人類無差異、無規定的理性精神或自由本質第一次獲得了具體規定和客觀內容,同時自我也從無限性過渡到特殊性和有限性的自我認識,超越和克服了那種抽象的、潛在的無止境的自我訴求,亦即抽象的無限性自由。人在外在物或私有財產中認識和發現自身的人格與自由意志。所以,在黑格爾那里,財產權的合理性不在于需要的滿足,而是對個人純粹主觀性或純粹思維自我的代替和超越,人在他的財產或所有物中,才第一次作為一個人存在。
在黑格爾自由—權利辯證法的政治哲學中,個人所有權首先是人類對自身自由意志本質的一種客觀的自我認同,或者說是作為個人自由自我意識的物質基礎。個人(person)必須首先通過對自身生命、身體的絕對占有和保全來證明自己的存在,其次是保存其生命、身體必需的外部自然物或物質福利,表明個人作為自由意志主體存在的現實性和客觀性。“只有當自由獲得確定性存在和現實性時,當它外在化自身時,才是自由的。”[3]78“我”的精神與身體是直接同一的,“作為一個人,我同時擁有我的生命、身體以及其他事物,只有就此而言,我才擁有對它的意志或意愿。”[4]78所以,黑格爾認為必須首先承認并尊重個人作為自然有機體生命存在的原始既定事實,將其自然自由本性及其權利具體而客觀地表達為神圣不可侵犯與剝奪的個人所有權,包括對自身生命、身體以及必需的物質資料等私有財產的自然權利。“直到個人擁有其生命、身體及財物的所有權,他才能作為理性物存在。即使我的這種最初的自由現實性是一種存在于外在物中的現實性,因而是一種貧乏的現實性,但這正是抽象人格別無所有的直接存在。”[4]73
黑格爾的個人所有權概念,根本地源于人自身精神的自由意志本質,包含了對人之為人的主體尊嚴的尊重。“惟有人格才能給予對物的權利,所以人格本質上就是物權。這里所謂物是指其一般意義的,即一般對自由說來是外在的那些東西,甚至包括我的身體生命在內。這種物權就是人格本身的權利。”[5]48-49“所有權所以合乎理性不在于滿足需要,而在于揚棄人格的純粹主觀性。”[5]50在這個問題上,霍布斯和洛克將個人自由、生命和財產所有權的必然性歸于人自身利己的自然本性,并最終歸于上帝或神的理性法則,實際上仍然沒有真正根據人自身的精神或自由意志來解釋自由與權利、國家與法律的合理性本質。“洛克對私人財產所有權的辯護反映了一種唯物主義的觀點。相比之下,黑格爾將私人財產所有權看作是自由的內在本質,表現出一種唯心主義的觀點。對黑格爾來說,洛克的財產權觀點貶低了人類尊嚴,因為它把他們當作一種低于人類尊嚴所要求的存在,它按照生物的、動物的本性水平來看待他們,而沒有達到人類精神本性的水平。”[6]67“洛克對財產權的解釋建立在人類自然方面的本性之上,即他們擁有身體和生物的需要。黑格爾的解釋基于人類精神方面——他們擁有思想和意志。”[6]67在黑格爾看來,正是因為個人財產所有權源于他自身崇高的精神本質,所以必然要求獲得他人的尊重與承認,對其生命、身體及私有財產的尊重,就是對其人之為人的精神本質或人格尊嚴的尊重。“我對于一事物的權利不僅是占有,而且是作為一個人的占有,這就是所有權(property)。”[7]315“人為了作為一個思想的存在物,他必須給予自身一個外在的自由領域,因為個人作為自在自為的無限意志,他起初整個地來說還只是一種抽象的確定性,因此它必須首先為其抽象意志確立一個確定性的自由領域。”[4]73而且“就我是活著的而言,我的靈魂與我的身體是不可分離的,我的身體是自由的存在,我通過它感受到自由的存在。”[4]79
黑格爾認為私有財產作為個人權利之所以不可侵犯、剝奪或取消,不是因為它具有本體論的價值優先地位,而是因為它作為人類精神的自然生命,是精神得以存在和實現的自然基礎和首要前提,但它還不是精神本身追求的目的。人既作為精神和道德的自我意識主體,雖然首先要求其自然需要的滿足,但是又絕不可能在物的占有中得到滿足,而是不斷超越物的需求與滿足,尋求自身精神和道德的主觀需求與自由,從事精神的創造性認識與實踐活動,如科學研究、技術發明、藝術創造、文化教育、哲學、宗教等精神性事業。因此,作為人類自然需要滿足的私有財產和物質福利,只是人類精神自我實現、自我認同的一個過渡性環節或中介,不是人類自由的全部或最后的真理。“黑格爾對財產本質的解釋,只有在他作為整體的理性發展哲學中,才能得到充分理解。僅根據它自身來看財產的本質,是沒有真理性的。”[2]47-64黑格爾正是要將人類精神和道德從沉湎于物的占有、對抗與爭奪中拯救出來,使之能夠真正回復到內心精神或思想的自由追求與創造中,從物的自我認同轉向對人類精神或道德主體價值的自我認同,從人與人之間物或利益的沖突對抗,轉向精神或道德的根本統一。無論是個體與個體之間,還是個體與社會共同體之間,或者說個體與自身及外在世界的和解與同一,都只能發生在精神和道德的認識和實踐活動領域中,絕不可能發生在感性和自然的排他性物質利益與財富的占有活動領域中。
二、所有權作為單一環節的理想性自由意境:物質利益和財富的自由爭奪
黑格爾雖然強調個人所有權在根本上是源于并且最終是為了精神的自由發展與創造,從而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崇高地位,但是他從來不曾賦予個人所有權本身以自由真理的絕對地位,而是明確指出它自身作為單一孤立的自由實現環節,如果直接貫徹到底必然走向自由的反面,使自由成為偶然的、個別的和特殊的,人類精神和道德的自由將被物質利益和財富的斗爭所淹沒。在黑格爾看來,個人所有權只是將個人自由意志體現為物,以物為目的,人的自由意志因此容易陷于自身特殊的物質欲望與利益算計之中,并往往由此淹沒或者說遺忘了自身的道德本性。“真正的占有,從自由的觀點看,即所有權,作為自由的第一個存在,是一種為自身的基本目的。”[4]77所以所有物(property)作為個人自由意志之實現,具有特殊性和主觀任意性。“當我占有某物,偶然性和需要就發揮作用,我就進入了單一性領域”[3]66,即進入個人只為自身目的考慮和計算的單一自然意志的主觀性、任意性和特殊性。正是因為“這種占有的自由意志,其基本的外在化從一開始就包含了偶然性因素,經驗的單一性因素,以及僅僅需要的和任意性的因素”[3]65,所以“這種權利實現的過程就進入了偶然性領域,即一時的意念和需要的偶然性,因此是不平等的領域。”[3]66黑格爾認為不平等是財產所有權自身內在的必然性要素,它作為人的自然自由本性之實現或客觀存在,其外在實現必然造成財富占有的不平等。“關于占有的一切——它是這種不平等的基地——是屬于抽象的人的平等之外的。”[5]57財富占有的不平等體現的只是人們在自然上的差異與不平等之事實,正如“把自然物據為己有的一般權利所借以實現的占有取得,作為外部行動,是以體力、狡智、技能,總之我們借以用身體來把握某物的一切手段為條件的。按照自然物的差別,對這些物的獲得和占取具有無限多的意義,以及同樣無限的限制和偶然性。所以物的獲得和外部占有也具有無限的方式,并且多少是不確定的和不完全的。”[5]60
因此,個人所有權不僅內在地包含著不平等因素,而且包含著使人物化的傾向。個人所有權雖然作為自由意志的外在確定性領域,但是它一方面往往使人容易陷于外在物或財富的無止境追求、計算與享受中,同時另一方面使自身容易遭受外在的強制與暴力,即通過對物質生活資料的剝奪而強制個人的自由意志。“我的意志由于取得所有權而體現于外在物中,這就意味著我的意志在物內得到反映,正因為如此,它可以在物內被抓住而遭到強制。因而我的意志在物中可能無條件地受到暴力的支配或者被強迫做出某種犧牲、某種行為,以作為保持某種占有或肯定存在的條件。這就是對它實施強制。”[5]95因為我擁有某物——一個外在的東西,或甚至是我的身體,也是屬于我擁有的東西——這樣我的意志就有了外在性,它就能夠被以外在的方式對待。由此,他人外在的暴力行為是可能的,而且我表達于物中的意志也能這樣被抓住,因此我能夠被阻止使用屬于我的東西,被阻止實踐我的自由與權利,我的自由由此與我的所有權發生分離。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批判,與黑格爾不謀而合,認為資產階級正是通過剝奪工人、農民等無產階級的生產資料所有權,使其勞動與財產所有權發生分離,并進而剝奪其對宗教、文化和道德等精神領域活動的自由追求與創造的主體權利,實際上“也就把人的類生活變成維持人的肉體生存的手段”[8]274。這樣,貧困得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就永遠掙扎在滿足自然生存的勞動里,被當作會說話的工具、機器或物,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主張人類解放根本的和首先的必須是物質的或經濟上的解放。
在黑格爾看來,我不應該僅僅被當作物來看待和對待,更重要的是我作為一個擁有主觀自我意識的精神主體,必須得到應有的肯定與尊重,而不應根據我財富擁有的多少來決定我的道德地位與主體尊嚴。因此,人與人之間不應僅僅是表面平等的契約關系或法權關系,更深層和更根本的是人作為自在的道德主體,相互之間內在的責任和義務關系,即“互主體”關系。然而,“建基于財產權的社會,使得窮人感到受排斥、嘲笑,自我意識被逼到不再有任何權利的極限。……貧困導致缺乏他人的承認,剝奪了對窮人的尊重。窮人將他們自身看作自由的存在,但是他們的物質存在極大地否定了他們的自我尊重感,結果使他們感到自身處于內在和外在的分裂之中。”[9]379-405以個人所有權保護為絕對目的的法律和政治體制,可能會無視財產占有的不平等漫延到精神尊嚴或道德地位上的不平等。畢竟“權利理論討論的不是人(man),而是一個僅僅從人中抽象出來的東西:個人(person),這本質上是按照他的任意的自由意志從而他的權利能力來定義的。因此,對個人(person)來說,道德是不相關的,個人可以任意地做他有權利做的事情而不顧道德。確實的,不僅道德,而且整個人類相關的范圍——社會關系、人的情感,文化,福利以及個體發展,都從權利中被排除出去。”[10]315然而“在洛克和自由主義者們看來,最不能容忍的暴行乃是對私人所有權的侵犯”[11]202。黑格爾堅持“正義終極地在于人精神的自由意志本質”[3]101,個人所有權作為完全為自身目的的個人權利,將自身僅陷于外在物的無限需求和占有中,成為與道德不相關的東西。“反對把所有權絕對化,這個觀點是黑格爾整個思想的特征”,他甚至“把所有權的價值放得比生命的價值低”[11]201。
可以說,黑格爾關于作為個人權利的財產所有權觀點,與洛克等經典自由主義者甚至與以羅爾斯等人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者根本不同。從經典自由主義者洛克、斯密到羅爾斯、德沃金等新自由主義者,所主張的個人權利本位的平等,無論從市場經濟體制還是法律和司法體系方面如何修補完善,實際上堅持的只是抽象的平等權利概念。所謂市場經濟體系中的機會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實際上維護的不是個人現實而具體的自由與權利,相反只是對抽象個體及其抽象權利的抽象普遍性的維護。現實生活中人們財富占有的不平等,及在此基礎上導致的生存和發展的不平等、主體精神和道德尊嚴的不平等,市場和法律體系卻并不過問和干涉。美國學者沃特金斯(Watkins)指出“從古希臘、羅馬時代以降,法律下的自由就一直是西方政治生活最明顯的特色。西方強調政治的核心乃是法理而不是倫理。”[12]在契約式的法理國家中,“私人利益,包括自由、財產與生命的保護、維系和安全是自由主義全部的議程”[13]109。契約式法理國家中的個人,作為一種哲學上的抽象存在是絕對安全的,但是作為生活在現實世界或社會歷史實踐中的個人,卻處于極其危險的狀態中,雖然擁有獨立自主的個性自由,卻對實際的奴役、壓迫以及貧困毫無防范和反抗能力,他在抽象的或形式的法律自由系統中只是一個“自由的”、“無家可歸”的孤獨者。所以根據黑格爾的觀點看來,那種認為人只有作為個人或個體才是平等的觀點,是一種破壞性或毀滅性的狂熱主義,“黑格爾希望廢除那種被稱為‘占有性’個人主義的政治理論假設”[14]30-43。黑格爾認為,無論是人作為自然個體的抽象權利,還是作為道德主體的自治權利,它們作為自由的定義都還處于抽象概念的層次或屬于自由的理想階段,并且二者相互分離和排斥。如果將這種屬于抽象理智識見的權利或道德當作自由真理加以直接實踐、貫徹到底,必然會造成它們的對立面,即變成各個個人特殊性、主觀性和任意性的自由實踐,導致暴力與犯罪、邪惡與偽善,造成“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違法”,即強者、富人的特權和自由,而弱者、窮人的生命生存和道德尊嚴,則處于他人乃至整個社會的特殊性、主觀性、任意性和偶然性因素威脅之中。
三、所有權的客觀現實性自由意境:市民社會與倫理國家,亦即法、道德與民生福利的統一
所有權作為個人權利,是個人自由意志得以實現的外在確定性領域,它自身作為單一孤立的自由理想階段,內在地潛藏著財富占有的不平等、精神和道德尊嚴喪失等危險。但是,黑格爾仍然認為,它作為人類自由意志或精神事業發展的物質基礎,作為個人特殊性和主觀性自由的實現環節,必須不可壓制和取消。在黑格爾那里,市民社會便首先是個人所有權及主體(subject)自治權利得以充分實現的實踐場所。市民社會允許個人的特殊性和主觀性、自由選擇、任意行動,以及與自然相關的所有偶然性和幸福都得以充分施展和發揮,所有個人都平等地憑借自己自然和主觀方面的特殊能力、才干,自由自主地謀求幸福生活、占有社會財富,獲得個人成就、榮譽及社會承認。“市民社會的創造屬于現代世界,它第一次允許自由思想的各種確定性都獲得它們的權利。”[4]220每個人作為人都有平等地追求自己特殊需要及滿足的權利,但是每個人需要及滿足的內容、手段、方式和程度必然是不一樣的,所以在人的整體生存依賴于需要和享受增殖的整個社會經濟網絡體系中,“一個人既面對自身與他人同一的意識,同時又面對著一種不平等的意識。”[3]169因為市民社會中個人對普遍財富的分享及個體需要滿足的現實性,受到勞動技能以及勞動所需要的自然體質、教育及資本等條件的制約,這些偶然性因素產生了財富不平等的必然后果。所以黑格爾同時指出,僅僅參與到那個體系之中,這本身并不能保證一個人的需要是實際地得到滿足的,需要的經濟體系只是給個人在社會中提供自由及其需要滿足的可能性或機會。位于市民社會之下的經濟性事業中的自由并不是絕對的。市民社會中無論“看不見的手”即斯密的“市場機制”和康德的“道德自律”,還是另一支“看得見的手”即強制性司法體系,作為社會的主要調節機制,它們無法消除市民社會中的“自然狀態殘余”,即個人特殊性、主觀任意性所造成的一種市場之外和法律之外的偶然性或無故意侵害與危險。這就將原本屬于必然的和普遍的人格權利、道德自由,降低為偶然性的和不確定的。因此,黑格爾反對將各個人追求和實現自身特殊性和主觀性需要、占有私人財富的活動領域——市民社會,等同于法、道德和民生福利三者相統一的倫理性現代國家。“作為倫理總體的國家,它的生命原則在普遍的自由意志展示自身與必然性一致的程度上才是已被實現了的。只有在那種程度上,國家才是有機的整體。它的憲法或政府體制是一個民族的理性或者說是它的自由的組織原則。……因為意志是自在自為地自由的,它必須是與必然性一致的。自由必須是在必然性意義上的‘是’,而不是偶然性意義上的‘是’。”[3]227倫理國家就是將公民內在的理性和自由本質,即精神和道德的自由與平等,實現為公開地被大家知道和理解、并共同遵從的客觀普遍性東西——以憲法和法律為核心的倫理政治秩序,包括本民族的倫常禮俗、社會風尚等,使個人權利與道德不再根據個人自然需要、主觀愿望及特殊利益而任意地理解和行動。“一個人必須做些什么,應該盡些什么義務,才能成為有德的人,這在倫理性的共同體中是容易談出的:他只須做在他的環境中所已指出的、明確的和他所熟知的事就行了。正直是在法律上和倫理上對他要求的普遍物。”[5]168“自在自為的正義是什么,只能在正義的客觀形象中,即在國家作為倫理生命的結構中體現出來。”[7]306
黑格爾對待市民社會的態度,不像霍布斯和洛克的現代自然法政治哲學那樣,局限于“市民社會”領域,企圖從個人自我利益、個人所有權至上原則來分析公共領域。“霍布斯和洛克對于市民社會問題的解決是一種非解決的解決。經典自由主義者所提供的生命和財產安全是以犧牲人類尊嚴和自由為代價的。資本主義社會不過是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15]5而“黑格爾的市民社會解釋既包含著對于個人自由的承認,又包含著對于某種個人主義類型的自由的批判。”[15]250黑格爾認為市民社會是倫理性現代國家得以建立必需的物質基礎,個人特殊需要、主觀愿望的滿足以及私有財產的獲得,必須屬于作為“需要體系”的市民社會領域;然而倫理國家則屬于人們從中實現與自身精神和道德同一、獲得生活意義的普遍性領域,絕對不是個人從中謀求私人利益或占取私有財產的地方。作為倫理國家的政府,既不排斥和壓制個人的特殊需要與主觀自由,相反促進它們的實現,同時國家又不以個人的個別主觀性及特殊性利益作為自己的原則與目的。不過,為了使國家成為強大的和穩定的,個人需要發現他的特殊利益——他的人格、他的財產、他的物質福利——在國家中得到保證和安全。“國家是具體自由的現實;但具體自由在于,個人的單一性及其特殊利益不但獲得它們的完全發展,以及他們的權利獲得明白承認,而且一方面通過自身過渡到普遍物的利益,另一方面他們認識和希求普遍物,甚至承認普遍物作為他們自己實體性的精神,并把普遍物作為他們的最終目的而進行活動。”[5]260“特殊利益當然不能被拋棄,更別說壓制它;相反它們應該與普遍利益協調一致,以便他們自身及普遍性兩者都得到保持。”[4]285
黑格爾自由—權利辯證法視野中的個人所有權理論,如保羅·湯姆斯(Paul Thomas)所言:“與其說黑格爾關心人們生活經驗層次的個人動機,毋寧說他關心的是如何實現占有理智(reason)的理性(ration)重建”,“他希望廢除那種被稱為‘占有性個人主義政治理論’的假設”,因為“財富可能直接地滋生權力是黑格爾最大的擔憂之一”,“黑格爾權利哲學中設計的建筑性制度結構正是為了防止一種由財富及從中生長出來的權力滲透和同化的新的后封建制度”[14]30-43。黑格爾對市民社會的超越和揚棄,或者說個人所有權的普遍現實性,正在于他重建的倫理性現代國家,即真正以精神的和道德的普遍平等概念作為其制度設置與實踐安排的根本準則或價值理念,確立以憲法和法律為核心或至上原則的倫理政治秩序,實現法、道德和民生福利三者的內在統一,使所有公民在理性、客觀和普遍有效的制度基礎上被承認、被尊重和被對待為一個擁有普遍平等的獨立人格和主體尊嚴的人,保證每個人自由、自主地尋求和創造自身的幸福生活,使其擺脫自由市場中人們自然和道德方面自然狀態殘余的任意性與偶然性危險,將其物質權利和道德權利從市場經濟社會中偶然性意義的“是”,提升為必然性意義的“是”;制度性地尊重和保障每個公民個體平等的生命權、生存權、私有財產和主觀自由以及各種物質福利的權利,使人們在享有其自然和道德方面應有的尊嚴與財富的基礎上,回歸自身的精神和道德本質,實現真正的人的自由和解放。
[1] [德]黑格爾.美學:第1卷[M].朱光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125.
[2] Richard Teichgraeber.Hegel on Property and Poverty[J].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1977,38(1).
[3] Hegel.LecturesonNaturalRightandPoliticalScience,TheFirstPhilosophyofRight[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
[4] Hegel.ElementsofthePhilosophyofright[M].Allen W.Wood(ed.).劍橋政治思想史原著系列影印本.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
[5] [德]黑格爾.法哲學原理[M].范揚,張啟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
[6] Harry Brod.Hegel'sPhilosophyofPolitics:Idealism,IdentityandModernity[M].Boulder: Westview Press,1992.
[7] [德]黑格爾.精神哲學[M].楊祖陶,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8]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M]//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74.
[9] Costas Douzinas.Identity,Recognition,Rights or What can Hegel Teach Us about Human Rights?[J]Wily-Blackwell: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2002,29(3).
[10] Peter G.Stillman.Hegel'scriticalofliberaltheories ofrights[M]//HEGEL Critical Assessments VolumeⅣ:Hegel's philosophy of nature and philosophy of Spirit.Robert Stern(ed.).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3.
[11] [意]洛蘇爾多.黑格爾與現代人的自由[M].丁三東,譯.長春:吉林出版集團,2008.
[12] [美]弗雷德里克·沃特金斯.西方政治傳統——近代自由主義之發展[M].李豐斌,譯.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導論.
[13] [美]本杰明·巴伯.強勢民主[M].彭斌,潤洲,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109.
[14] Paul Thomas.Property's Properties:From Hegel to Locke[J].Representations,2003,84(1).
[15] Paul Franco.Hegel'sPhilosophyofFreedom[M].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