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duì)話(huà)與融合:對(duì)20世紀(jì)80年代中國(guó)現(xiàn)代主義與現(xiàn)實(shí)主義的考察
王衛(wèi)平,萬(wàn) 水
(遼寧師范大學(xué) 文學(xué)院,遼寧 大連116081)
我們現(xiàn)在言及現(xiàn)實(shí)主義早已突破了“社會(huì)主義現(xiàn)實(shí)主義”、“革命現(xiàn)實(shí)主義”的狹小局限,也不會(huì)再把現(xiàn)代主義看作是“頹廢”、“落后”的代名詞。我們對(duì)兼?zhèn)洮F(xiàn)實(shí)主義和現(xiàn)代主義特點(diǎn)的文學(xué)作品也早已習(xí)以為常,特別是當(dāng)莫言獲得了2012年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之后,我們對(duì)那種融合了多種風(fēng)格和手段的“魔幻現(xiàn)實(shí)主義”更是推崇備至。我們的這種文學(xué)觀念是什么時(shí)候開(kāi)始形成的?本文認(rèn)為它的源頭至少可以追溯到上個(gè)世紀(jì)80年代。
20世紀(jì)80年代的中國(guó)文壇可謂百花齊放、百家爭(zhēng)鳴,各種新老文學(xué)流派和各種關(guān)于文學(xué)的不同觀點(diǎn)幾乎在同一時(shí)間集中上演,場(chǎng)面可謂壯觀。其間各種流派基本可以劃歸為現(xiàn)實(shí)主義與現(xiàn)代主義兩大派別。這兩大流派的爭(zhēng)論與相互靠攏構(gòu)成了80年代中國(guó)文壇的基本樣態(tài)。以往的研究多關(guān)注二者的矛盾與斗爭(zhēng)的方面,本文試圖從二者相互融匯、借鑒的角度來(lái)考察,探究它們?nèi)诤系膶?shí)踐和原因。
一、20世紀(jì)80年代初期以前中國(guó)現(xiàn)代主義和現(xiàn)實(shí)主義的知識(shí)譜系
(一)在艱難中前行的現(xiàn)代主義
現(xiàn)代主義和現(xiàn)實(shí)主義的概念都屬于西方的舶來(lái)品,20世紀(jì)80年代西方現(xiàn)代主義的“中國(guó)之行”是一次故地重游,其第一次“中國(guó)之行”發(fā)生在20世紀(jì)二三十年代。當(dāng)時(shí)現(xiàn)代主義與現(xiàn)實(shí)主義結(jié)伴而來(lái),它們共同的對(duì)手是以文言文為主要形式的中國(guó)古典文學(xué),所以當(dāng)時(shí)作為同一陣營(yíng)的現(xiàn)代主義和現(xiàn)實(shí)主義的分歧和矛盾沒(méi)有凸顯出來(lái)。但是,很快“陳腐”的古典文學(xué)就被這股“新鮮”的異域藝術(shù)思潮沖垮,隨之而來(lái)的是,伴隨著對(duì)手的消失,現(xiàn)代主義和現(xiàn)實(shí)主義開(kāi)始分道揚(yáng)鑣。由于國(guó)內(nèi)外政治局勢(shì)的變化和中華民族的生存危機(jī),“革命”終于壓倒了“啟蒙”,而現(xiàn)實(shí)主義因?yàn)榉蠒r(shí)代發(fā)展的需要,而一躍成為30年代以后的主潮。現(xiàn)代主義則由于過(guò)于注重個(gè)人話(huà)語(yǔ)、個(gè)性解放甚至是個(gè)人主義,在此后的“半個(gè)世紀(jì)左右,對(duì)于文學(xué)說(shuō)來(lái),現(xiàn)代主義僅僅是一個(gè)含義不明的古怪概念。”[1]
1949年至1970年代后期,“現(xiàn)代主義”在中國(guó)大陸的命運(yùn)頗為奇特。這一時(shí)期的文學(xué)主潮排斥現(xiàn)代主義,一般讀者甚至不少當(dāng)代作家都不大清楚有這樣的思潮和作品存在。這一時(shí)期,為數(shù)極少的能夠公開(kāi)討論現(xiàn)代主義的例外是茅盾的《夜讀偶記》。但是這并不代表在這一時(shí)期的中國(guó)大陸“現(xiàn)代主義”真的絕跡了,現(xiàn)代主義的理論和作品在一種叫作“內(nèi)部讀物”的內(nèi)參性質(zhì)的讀本上生存著。這些內(nèi)參書(shū)主要可以分為三類(lèi):(1)60年代初刊印的被國(guó)際共產(chǎn)主義運(yùn)動(dòng)正統(tǒng)所批判的“叛徒”或“修正主義分子”,如密洛凡·德熱拉斯、特加·古納瓦達(dá)納等的作品;(2)60年代刊印的有關(guān)西方現(xiàn)代文學(xué)和哲學(xué)方面的書(shū)籍,如亞爾培·加繆、奧斯本、杰羅姆·大衛(wèi)·塞林格等的作品;(3)70年代初刊印的有關(guān)西方歷史政治方面的書(shū)籍,如費(fèi)正清等的著作[2]125-126。
西方現(xiàn)代主義文學(xué)作品的大量譯介主要是在20世紀(jì)60年代以后,據(jù)孫繩武回憶:“1960年,作家協(xié)會(huì)的領(lǐng)導(dǎo)召開(kāi)了兩三次外國(guó)文學(xué)情況交流會(huì)。……會(huì)議初期的中心議題是西方文學(xué)的新現(xiàn)象,因?yàn)楫?dāng)時(shí)文學(xué)界對(duì)蘇聯(lián)、東歐的了解較多,而同西方接觸較少。這幾次會(huì)議上談到了英、法、美的一些作品及傾向,例如反映這些國(guó)家中的青年人對(duì)社會(huì)頗為不滿(mǎn)的情緒,即所謂‘憤怒的一代’的代表性作品,并決定選幾種譯出,由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負(fù)責(zé)出版。”[3]這說(shuō)明當(dāng)時(shí)譯介的西方現(xiàn)代主義文學(xué)作品基本也是當(dāng)時(shí)正在西方產(chǎn)生廣泛影響的作品。也就是說(shuō),20世紀(jì)60年代西方的現(xiàn)代主義共時(shí)性地影響到了當(dāng)時(shí)的中國(guó)大陸,這也為日后20世紀(jì)80年代中國(guó)大陸出現(xiàn)創(chuàng)新或稱(chēng)叛逆的現(xiàn)代主義提供了思想資源。
(二)強(qiáng)大的現(xiàn)實(shí)主義傳統(tǒng)
20世紀(jì)80年代初,和第二次在中國(guó)大陸重新興起的現(xiàn)代主義思潮形成競(jìng)爭(zhēng)的是強(qiáng)大的現(xiàn)實(shí)主義傳統(tǒng)。在我國(guó),五四時(shí)期伴隨著強(qiáng)烈的西學(xué)東漸之風(fēng),批判現(xiàn)實(shí)主義和自然主義、浪漫主義等西方的各種藝術(shù)上的“主義”一起涌入我國(guó),其時(shí)的學(xué)者根本沒(méi)有時(shí)間來(lái)清理現(xiàn)實(shí)主義與自然主義的區(qū)別,一時(shí)間“客觀”、“寫(xiě)實(shí)”成為其時(shí)現(xiàn)實(shí)主義的特征;1933年2月出版的《藝術(shù)新聞》第2期刊登了林琪從日本《普洛文學(xué)》翻譯的《蘇俄文學(xué)的新口號(hào)》,在中國(guó)首次出現(xiàn)了“社會(huì)主義現(xiàn)實(shí)主義”這一口號(hào),同時(shí)30年代出現(xiàn)了關(guān)于現(xiàn)實(shí)主義的論爭(zhēng);40年代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huì)上的講話(huà)》一文提出“無(wú)產(chǎn)階級(jí)的現(xiàn)實(shí)主義”的說(shuō)法;1953年9月,周揚(yáng)在中國(guó)文學(xué)藝術(shù)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會(huì)上,正式宣布“社會(huì)主義現(xiàn)實(shí)主義”方法是我們文學(xué)藝術(shù)創(chuàng)作和批評(píng)的最高準(zhǔn)則;1958年,“革命現(xiàn)實(shí)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jié)合”的概念被提出;新時(shí)期初期,在第四次文代會(huì)前后,“社會(huì)主義現(xiàn)實(shí)主義”、“兩結(jié)合”、“革命現(xiàn)實(shí)主義”三種提法經(jīng)常同時(shí)登場(chǎng),其中以茅盾和周揚(yáng)的說(shuō)法最有代表性:在第四次文代會(huì)上茅盾強(qiáng)調(diào)“社會(huì)主義現(xiàn)實(shí)主義”和“兩結(jié)合”的一致性,而周揚(yáng)更多的是維護(hù)“兩結(jié)合”的最高指導(dǎo)地位。
20世紀(jì)80年代初期之前,我國(guó)的文學(xué)界和文學(xué)理論界關(guān)于現(xiàn)實(shí)主義的討論基本上集中在社會(huì)主義現(xiàn)實(shí)主義、“兩結(jié)合”、革命現(xiàn)實(shí)主義三個(gè)概念上,這三個(gè)概念雖然側(cè)重點(diǎn)不同,但是其共同的指向都是企圖確立一種“最好”的文藝創(chuàng)作方法來(lái)指導(dǎo)文學(xué)藝術(shù)的創(chuàng)作,都強(qiáng)調(diào)文學(xué)藝術(shù)對(duì)人的啟迪教育作用,都在一定程度忽視了文學(xué)藝術(shù)的獨(dú)立性,強(qiáng)調(diào)文學(xué)藝術(shù)為政治服務(wù)的一面。在某種意義上,現(xiàn)實(shí)主義已經(jīng)不再僅僅是一種文學(xué)創(chuàng)作方法,它“反映了文學(xué)的總體性制度對(duì)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具體要求、文學(xué)的社會(huì)功能和作家的使命。”[4]
在20世紀(jì)80年代初以前,我國(guó)的文學(xué)理論界雖然有著各種不同名號(hào)的現(xiàn)實(shí)主義之間的爭(zhēng)論,但是基本上沒(méi)有跳出現(xiàn)實(shí)主義的框架,現(xiàn)實(shí)主義以外的流派是沒(méi)有資格參與論爭(zhēng)的。隨著新時(shí)期的到來(lái),在相較以往開(kāi)放的文化政策下,現(xiàn)代主義作為一個(gè)潮流與現(xiàn)實(shí)主義展開(kāi)了真正地交流。
二、20世紀(jì)80年代現(xiàn)代主義與現(xiàn)實(shí)主義的融合
(一)現(xiàn)代主義向現(xiàn)實(shí)主義靠攏
賀桂梅根據(jù)袁可嘉等選編的《外國(guó)現(xiàn)代派作品選》(四冊(cè),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1985年)和何望賢選編的《西方現(xiàn)代派文學(xué)問(wèn)題爭(zhēng)論集》(上下冊(cè),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4年)概括總結(jié)出“現(xiàn)代主義”這一概念在20世紀(jì)80年代的兩層含義:“現(xiàn)代主義”與“現(xiàn)代派”、“先鋒派”在當(dāng)時(shí)是可以互換的概念,它既可以指西方(主要是歐洲和美國(guó))的一個(gè)歷史階段或文學(xué)史階段(歷史階段為從“一戰(zhàn)”直到20世紀(jì)六七十年代,文學(xué)史階段為從現(xiàn)實(shí)主義和浪漫主義的衰落到經(jīng)由自然主義和唯美主義演變而來(lái)的現(xiàn)代主義文學(xué)階段),又可以表示一個(gè)除現(xiàn)實(shí)主義之外的西方20世紀(jì)(加上19世紀(jì)中期的唯美主義)各種藝術(shù)流派的總體概念,這里涵蓋了“二戰(zhàn)”前產(chǎn)生的象征主義、表現(xiàn)主義、未來(lái)主義、超現(xiàn)實(shí)主義、意識(shí)流文學(xué),以及“二戰(zhàn)”后產(chǎn)生的以存在主義哲學(xué)為基礎(chǔ)的各種藝術(shù)流派,如存在主義文學(xué)、荒誕派戲劇、“黑色幽默”、“垮掉的一代”等[2]139。
1980年代中國(guó)文學(xué)的現(xiàn)代主義實(shí)踐包括如下幾個(gè)方面:第一,大量有關(guān)研究雜志的創(chuàng)辦和專(zhuān)門(mén)出版機(jī)構(gòu)的成立。其中雜志包括:《外國(guó)文藝》、《外國(guó)文學(xué)》、《當(dāng)代外國(guó)文學(xué)》、《譯林》、《譯海》、《外國(guó)小說(shuō)》、《蘇聯(lián)文學(xué)》、《俄蘇文學(xué)》、《日本文學(xué)》、《外國(guó)文學(xué)研究》、《外國(guó)文學(xué)報(bào)道》、《外國(guó)文學(xué)動(dòng)態(tài)》、《外國(guó)文學(xué)研究集刊》等;出版機(jī)構(gòu)包括:從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分離出來(lái)的外國(guó)文學(xué)出版社、上海譯文出版社、中國(guó)對(duì)外翻譯出版公司等。第二,文化界多次圍繞“現(xiàn)代派”的爭(zhēng)論。這其中包括在《外國(guó)文學(xué)研究》雜志上進(jìn)行的“關(guān)于西方現(xiàn)代派文學(xué)的討論”專(zhuān)欄討論、包括徐敬亞事件在內(nèi)的有關(guān)“三個(gè)崛起”的討論,以及關(guān)于“薩特?zé)帷焙痛嬖谥髁x的討論。
這一時(shí)期圍繞著現(xiàn)代主義的討論,形成的主流立場(chǎng)認(rèn)為:由于50—70年代對(duì)西方現(xiàn)代主義的嚴(yán)密封鎖,而這一時(shí)期又要有限度的接納它,所以最好能夠使其平滑過(guò)渡,從而將其納入新時(shí)期的話(huà)語(yǔ)體系之中。用內(nèi)容與形式的“兩分法”,剝離西方現(xiàn)代主義的意識(shí)形態(tài)內(nèi)容,取其新奇、先進(jìn)的表現(xiàn)手法,是其有效的手段。特別是在文學(xué)界和文學(xué)理論界,主張?jiān)趫?jiān)持現(xiàn)實(shí)主義的主體地位的前提下引進(jìn)西方現(xiàn)代主義作為“補(bǔ)充”的觀點(diǎn),也屬于這樣一種立場(chǎng)。
20世紀(jì)80年代的中國(guó)文學(xué)現(xiàn)代主義實(shí)踐最終結(jié)果不是越來(lái)越否定現(xiàn)實(shí)主義,而是漸漸地融匯了現(xiàn)實(shí)主義。
現(xiàn)代主義的宣揚(yáng)者為了能夠盡快把現(xiàn)代主義“合法化”,大都采用了現(xiàn)代主義“現(xiàn)實(shí)主義化”的策略。規(guī)避掉現(xiàn)代主義的“唯心主義”色彩,使之盡量向以唯物主義反映論為哲學(xué)基礎(chǔ)的現(xiàn)實(shí)主義靠攏是現(xiàn)代主義的宣揚(yáng)者首先要做的工作,所以就出現(xiàn)了“現(xiàn)代主義和現(xiàn)實(shí)主義構(gòu)不成一對(duì)矛盾”的說(shuō)法,因?yàn)椤罢嬲袃r(jià)值的‘現(xiàn)代主義’作品也是‘反映’現(xiàn)實(shí)的,其中往往也有廣義的現(xiàn)實(shí)主義,也有廣義的浪漫主義。”[5]袁可嘉認(rèn)為:“大多數(shù)現(xiàn)代派作家雖說(shuō)以象征手法為主,目的還是在反映現(xiàn)實(shí)生活,只是側(cè)重從內(nèi)心世界來(lái)寫(xiě)。”[6]47同時(shí)也出現(xiàn)了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諸如心理現(xiàn)實(shí)主義、文化現(xiàn)實(shí)主義、象征現(xiàn)實(shí)主義、生命現(xiàn)實(shí)主義等,它們的出現(xiàn)在很大程度上把現(xiàn)代主義的意識(shí)流等一系列特有的手法納入到了現(xiàn)實(shí)主義的范疇。一個(gè)典型的例子是李陀在1986年的一次名為“現(xiàn)實(shí)主義及其發(fā)展”的討論會(huì)上對(duì)當(dāng)時(shí)現(xiàn)代主義的發(fā)展?fàn)顩r和趨勢(shì)的表述,他認(rèn)為“現(xiàn)實(shí)主義在國(guó)外已分裂出魔幻現(xiàn)實(shí)主義、心理現(xiàn)實(shí)主義、結(jié)構(gòu)現(xiàn)實(shí)主義等多種形態(tài),中國(guó)也正在面臨著這個(gè)問(wèn)題。”葉立文在《“無(wú)邊的現(xiàn)實(shí)主義”——論新時(shí)期初西方現(xiàn)代主義文學(xué)的傳播策略》一文中,把這種現(xiàn)象看作是在80年代現(xiàn)代主義為了能夠順利傳播而采取的有意的“誤讀”策略[7]。
現(xiàn)代主義的宣揚(yáng)者其次要做的工作是:給予現(xiàn)代主義作品中所表現(xiàn)的荒誕、悲觀、虛無(wú)等思想內(nèi)容以合理地解釋。西方典型的現(xiàn)代主義文學(xué)作品中所表現(xiàn)出來(lái)的如上思想內(nèi)容一般都是某種西方現(xiàn)代哲學(xué)思想的反映,如薩特的存在主義哲學(xué)之于其存在主義文學(xué)作品的關(guān)系就是典型的例子。但是在80年代的中國(guó),學(xué)者們多習(xí)慣于用馬克思主義的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理論來(lái)解釋其所表現(xiàn)的思想內(nèi)容的合理性。如袁可嘉稱(chēng):“現(xiàn)代派(又稱(chēng)先鋒派或現(xiàn)代主義)文學(xué)總的傾向是反映分崩離析的現(xiàn)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huì)里個(gè)人與社會(huì)、個(gè)人與他人、個(gè)人和物質(zhì)、自然和個(gè)人與自我之間的畸形關(guān)系,以及由此產(chǎn)生的精神創(chuàng)傷、變態(tài)心理、悲觀絕望情緒和虛無(wú)主義思想。”這樣,現(xiàn)代主義文學(xué)作品中所表現(xiàn)的荒誕、悲觀、虛無(wú)等思想內(nèi)容就成了資本主義制度本身所固有的荒誕、悲觀、虛無(wú)的表現(xiàn),以及對(duì)其的批判[6]46-48。
現(xiàn)代主義的宣揚(yáng)者第三要做的工作是:把一系列的經(jīng)典現(xiàn)代主義作家現(xiàn)實(shí)主義化,卡夫卡和普魯斯特就是兩個(gè)典型的例子。李士勛、舒昌善的《表現(xiàn)主義》一文為證明卡夫卡的現(xiàn)實(shí)主義性,還引用盧卡契對(duì)卡夫卡現(xiàn)實(shí)主義的定性來(lái)為自己找論據(jù)。把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比肩于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并將其稱(chēng)為對(duì)資產(chǎn)階級(jí)上流社會(huì)腐朽沒(méi)落的反映,也是當(dāng)時(shí)的論者的習(xí)慣性表述。
以上的所謂“現(xiàn)代主義的宣揚(yáng)者”基本上都屬于比較溫和的一派,他們?cè)诮庾x現(xiàn)代主義的時(shí)候大都采用了唯物主義反映論的視角,而且把現(xiàn)代主義看作是現(xiàn)實(shí)主義的新發(fā)展。在今天看來(lái),這樣一種顯然的“誤讀”并沒(méi)有阻礙現(xiàn)代主義思潮在我國(guó)的傳播,相反,更加促進(jìn)和加速了對(duì)現(xiàn)代主義的接受。其實(shí),在把現(xiàn)代主義現(xiàn)實(shí)主義化的過(guò)程中,論者們明顯混淆了作為一種文學(xué)精神的現(xiàn)實(shí)主義和作為一種藝術(shù)創(chuàng)作方法的現(xiàn)實(shí)主義的區(qū)別。“作為文學(xué)精神的現(xiàn)實(shí)主義,強(qiáng)調(diào)的是作家直面現(xiàn)實(shí)的精神,并非現(xiàn)實(shí)主義創(chuàng)作方法所獨(dú)有,浪漫主義、現(xiàn)代主義等方法均需有這種精神。”[8]
也許這正應(yīng)了法國(guó)人阿蘭·羅伯格里耶的那句話(huà):“所有的作家都希望成為現(xiàn)實(shí)主義者,從來(lái)沒(méi)有一個(gè)作家自詡為抽象主義者、幻術(shù)師、虛幻主義者、幻想迷、臆造者……”“歷史上的情況歷來(lái)如此,每一個(gè)新的流派都是打著現(xiàn)實(shí)主義的旗號(hào)來(lái)攻擊它以前的流派:現(xiàn)實(shí)主義是浪漫派反對(duì)古典派的口號(hào),繼而又成為自然主義者反對(duì)浪漫派的號(hào)角,甚至超現(xiàn)實(shí)主義者也自稱(chēng)他們只關(guān)心現(xiàn)實(shí)世界。在作家的陣營(yíng)里,現(xiàn)實(shí)主義就像笛卡爾的‘理性’一樣天生優(yōu)越。”[9]
(二)現(xiàn)實(shí)主義向現(xiàn)代主義敞開(kāi)
從五四時(shí)期現(xiàn)實(shí)主義的概念傳入我國(guó)開(kāi)始,現(xiàn)實(shí)主義在絕大多數(shù)時(shí)間里都被冠以一系列的非文學(xué)性限定語(yǔ),諸如“社會(huì)主義現(xiàn)實(shí)主義”、“革命現(xiàn)實(shí)主義”等等,以致現(xiàn)實(shí)主義被弄得面目全非,聲名狼藉。新時(shí)期開(kāi)始以后,現(xiàn)實(shí)主義亟待恢復(fù)名譽(yù),一系列關(guān)涉現(xiàn)實(shí)主義的討論隨之展開(kāi)。其中有兩個(gè)問(wèn)題的討論顯示了向現(xiàn)代主義開(kāi)放的趨勢(shì)。
第一個(gè)問(wèn)題:關(guān)于“寫(xiě)真實(shí)”的討論。“寫(xiě)真實(shí)”一向是現(xiàn)實(shí)主義者對(duì)文學(xué)的一項(xiàng)基本要求,但是“什么是真實(shí)”這個(gè)問(wèn)題卻不是不言自明的。所以關(guān)于“寫(xiě)真實(shí)”討論的實(shí)質(zhì)內(nèi)容便是討論什么是藝術(shù)真實(shí),藝術(shù)真實(shí)與生活真實(shí)的關(guān)系,以及追求藝術(shù)真實(shí)是否就是文學(xué)藝術(shù)的本質(zhì)特征。其間產(chǎn)生了一些十分有見(jiàn)地的觀點(diǎn),比如王蒙發(fā)表在1980年8月27日《人民日?qǐng)?bào)》上的《是一個(gè)扯不清的問(wèn)題嗎?》一文認(rèn)為:“對(duì)于主觀世界,真誠(chéng)的東西就是真實(shí)的。”“自然主義、現(xiàn)實(shí)主義、古典主義、印象派、象征派、超現(xiàn)實(shí)主義……各有各的對(duì)于真實(shí)性的理解,各有各的反映生活的路子。從廣義上說(shuō),我們是堅(jiān)持文學(xué)要反映生活的現(xiàn)實(shí)主義精神的,但是我們絕不能望文生義地、輕率地否定其他流派和風(fēng)格。”[10]雖說(shuō)該文對(duì)文學(xué)藝術(shù)的本質(zhì)的認(rèn)識(shí)還基本囿于反映論,但是其對(duì)主觀世界以及各種非現(xiàn)實(shí)主義流派的肯定,顯示了其對(duì)文學(xué)藝術(shù)本質(zhì)的寬容理解。
第二個(gè)問(wèn)題:關(guān)于“文學(xué)藝術(shù)是社會(huì)生活的反映”命題的討論。
魯樞元的《文學(xué),美的領(lǐng)域——兼論文學(xué)藝術(shù)家的“感情積累”》一文是較早地對(duì)“文學(xué)是社會(huì)生活的反映”這一命題提出質(zhì)疑的文章。該文認(rèn)為應(yīng)該把文學(xué)看作“是一種物質(zhì)世界和文學(xué)家藝術(shù)心靈(如資稟、氣質(zhì)、人格、性情、思想、才學(xué)等)的有機(jī)結(jié)合體,而且,在這一精神產(chǎn)品的生產(chǎn)過(guò)程中起主導(dǎo)作用的,還應(yīng)該是文學(xué)家的創(chuàng)作實(shí)踐活動(dòng)。”[11]周來(lái)祥也批評(píng)了把藝術(shù)歸結(jié)為一種認(rèn)識(shí)活動(dòng)的觀點(diǎn),并認(rèn)為藝術(shù)應(yīng)該是介于認(rèn)識(shí)、情感、意志之間的一種獨(dú)立存在的形態(tài)[12]。程麻則認(rèn)為文藝活動(dòng)不僅僅是認(rèn)識(shí)活動(dòng),更表現(xiàn)了作者的價(jià)值判斷,所以?xún)H憑反映論難說(shuō)清文藝問(wèn)題[13]。上述文章都不同程度地突破了從反映論和認(rèn)識(shí)論角度解釋文藝現(xiàn)象,更多地強(qiáng)調(diào)文藝的體驗(yàn)性、價(jià)值性、生存性等特點(diǎn)。
對(duì)上述兩個(gè)問(wèn)題的討論,大大拓展了現(xiàn)實(shí)主義的范疇,使得心理現(xiàn)實(shí)、情感真實(shí)等主觀要素合理、合法地進(jìn)入到現(xiàn)實(shí)主義的范疇,同時(shí)對(duì)藝術(shù)本質(zhì)的理解也不再局限于反映論和認(rèn)識(shí)論的范疇,這都為在不否定現(xiàn)實(shí)主義的前提下肯定和融合現(xiàn)代主義做出了必要的準(zhǔn)備。
到了80年代末期,學(xué)界出現(xiàn)了一種鼓吹“新現(xiàn)實(shí)主義”的觀點(diǎn)。該觀點(diǎn)通過(guò)對(duì)“社會(huì)主義現(xiàn)實(shí)主義”徹底地批判和否定,提出了自己對(duì)現(xiàn)實(shí)主義的認(rèn)識(shí),認(rèn)為人道主義的批判精神應(yīng)該是現(xiàn)實(shí)主義的基本原則,當(dāng)前我國(guó)文壇應(yīng)該倡導(dǎo)的是一種“新現(xiàn)實(shí)主義”,它不是“社會(huì)主義現(xiàn)實(shí)主義”的繼續(xù),而是19世紀(jì)現(xiàn)實(shí)主義和五四現(xiàn)實(shí)主義的繼承。而且“新現(xiàn)實(shí)主義”吸收和融合了現(xiàn)代主義因素,最重要的是它“吸收了現(xiàn)代主義的精神——對(duì)個(gè)體價(jià)值的肯定和對(duì)精神自由的追求。”[14]
三、結(jié) 語(yǔ)
現(xiàn)實(shí)主義與現(xiàn)代主義兩大思潮在其發(fā)源地是有著嚴(yán)格的區(qū)分的。作為一種文學(xué)思潮,從時(shí)間上看,現(xiàn)實(shí)主義始于對(duì)浪漫主義的反撥,終于現(xiàn)代主義的興起;從哲學(xué)基礎(chǔ)上看,現(xiàn)實(shí)主義以唯物主義為基礎(chǔ),而現(xiàn)代主義以各種西方現(xiàn)代主義哲學(xué)為基礎(chǔ)。作為一種創(chuàng)作方法,現(xiàn)實(shí)主義強(qiáng)調(diào)“模仿”與“再現(xiàn)”,強(qiáng)調(diào)真實(shí)性和整體感,強(qiáng)調(diào)理性精神和批判精神,而現(xiàn)代主義強(qiáng)調(diào)運(yùn)用變形、象征、意識(shí)流等手法表現(xiàn)作者內(nèi)心的真實(shí)。那么它們?yōu)槭裁茨軌蛟?0年代的中國(guó)文壇呈現(xiàn)出相互融合之勢(shì)呢?原因有二:第一,中國(guó)的現(xiàn)實(shí)主義在被引進(jìn)之時(shí)就沒(méi)有足夠重視在它的發(fā)源地所強(qiáng)調(diào)的“模仿”、“再現(xiàn)”兩大核心[15],而過(guò)多強(qiáng)調(diào)的是對(duì)生活的介入精神和態(tài)度,這就為日后在現(xiàn)實(shí)主義范圍內(nèi)接受現(xiàn)代主義奠定了基礎(chǔ)。第二,中國(guó)的現(xiàn)代主義本身就包括現(xiàn)實(shí)主義和浪漫主義。王富仁認(rèn)為“中國(guó)現(xiàn)代主義文學(xué)”是一個(gè)獨(dú)立的概念,它是與“中國(guó)古典主義文學(xué)”相對(duì)的概念,它理應(yīng)包括“受西方現(xiàn)代主義影響的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作品,也包括受西方浪漫主義和現(xiàn)實(shí)主義文學(xué)影響的文學(xué)作品。”[16]
20世紀(jì)90年代中期,我國(guó)文壇上興起了一場(chǎng)關(guān)于現(xiàn)實(shí)主義的大討論,討論的核心議題是“現(xiàn)實(shí)主義重構(gòu)”問(wèn)題,即現(xiàn)實(shí)主義在新的時(shí)代需要下,根據(jù)新的現(xiàn)實(shí)發(fā)展的問(wèn)題。討論中,現(xiàn)實(shí)主義需要向現(xiàn)代主義開(kāi)放成為一部分學(xué)者的共識(shí)。但是經(jīng)過(guò)我們的考察,此種觀點(diǎn)并不是90年代才開(kāi)始形成的,在80年代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兩種文學(xué)觀念相互靠攏的趨勢(shì)。關(guān)于文學(xué)的觀念不是一成不變的,現(xiàn)代主義和現(xiàn)實(shí)主義的文學(xué)觀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文學(xué)觀念的多元化是文學(xué)的本質(zhì)性需要,一元化的文學(xué)觀只能扼殺文學(xué)本身的多樣性,歷史已經(jīng)證明其不足取,但是問(wèn)題的另一個(gè)方面是,我們同樣要注意在分類(lèi)學(xué)意義上對(duì)諸種文學(xué)觀念進(jìn)行區(qū)分,否則一旦概念失去了邊際,就等于取消了概念的自足性,加羅蒂的“無(wú)邊的現(xiàn)實(shí)主義”和馬爾科夫的社會(huì)主義現(xiàn)實(shí)主義的“開(kāi)放體系”就是前車(chē)之鑒。
[1] 南帆.現(xiàn)代主義、現(xiàn)代性與個(gè)人主義[J].南方文壇,2009(4):6.
[2] 賀桂梅.“新啟蒙”知識(shí)檔案[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0.
[3] 孫繩武.關(guān)于“內(nèi)部書(shū)”:雜憶與隨感[A].張立憲.讀庫(kù)0703[C].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82.
[4] 陳曉明.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主潮[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9:313.
[5] 卞之琳.現(xiàn)代主義和現(xiàn)實(shí)主義構(gòu)不成一對(duì)矛盾[J].讀書(shū),1983(5):45.
[6] 袁可嘉.歐美現(xiàn)代派文學(xué)概述[J].百科知識(shí),1980(1).
[7] 葉立文.“誤讀”的方法:新時(shí)期初西方現(xiàn)代主義文學(xué)的傳播與接受[M].北京: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2009:139.
[8] 崔志遠(yuǎn).重整現(xiàn)實(shí)主義的理論武庫(kù)[J].文藝爭(zhēng)鳴,2010(2):115.
[9] 阿蘭·羅伯—格里耶.從現(xiàn)實(shí)主義到現(xiàn)實(shí)[A].柳鳴九.20世紀(jì)現(xiàn)實(shí)主義[C].北京: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1992:320.
[10] 王蒙.是一個(gè)扯不清的問(wèn)題嗎?[A].郭友亮,孫波.王蒙文集:第6卷[C].北京:華藝出版社,1993:58-59.
[11] 魯樞元.文學(xué),美的領(lǐng)域——兼論文學(xué)藝術(shù)家的“感情積累”[J].上海文學(xué),1981(6):43-44.
[12] 周來(lái)祥.審美情感與藝術(shù)本質(zhì)[J].文史哲,1981(3):29.
[13] 程麻.僅憑反映論難說(shuō)透文藝問(wèn)題[J].當(dāng)代文藝思潮,1986(5):76.
[14] 楊春時(shí).“社會(huì)主義現(xiàn)實(shí)主義”批判[J].文藝評(píng)論,1989(2):16.
[15] 張傳敏.中國(guó)左翼現(xiàn)實(shí)主義觀念之發(fā)生[J].文學(xué)評(píng)論,2008(1):30.
[16] 王富仁.中國(guó)現(xiàn)代主義文學(xué)論:上[J].天津社會(huì)科學(xué),1996(4):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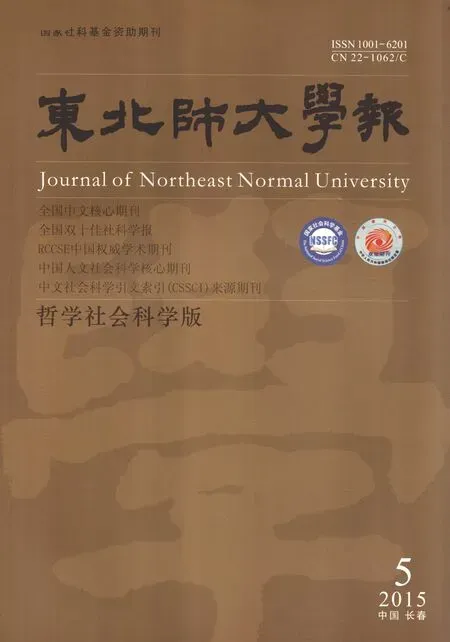 東北師大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5年5期
東北師大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5年5期
- 東北師大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的其它文章
- 高校繼續(xù)教育課程設(shè)置問(wèn)題探究
- 高校英語(yǔ)教師專(zhuān)業(yè)發(fā)展的改革與創(chuàng)新研究
- 研究型大學(xué)科研質(zhì)量標(biāo)準(zhǔn)構(gòu)建問(wèn)題宏論
- 大學(xué)生科學(xué)精神與技術(shù)責(zé)任理念的培育——雅斯貝爾斯科學(xué)技術(shù)教育思想研究
- 孔子學(xué)院“有限市場(chǎng)化”發(fā)展戰(zhàn)略模型與要素分析
- 學(xué)術(shù)本身成為目的才會(huì)有真學(xué)術(shù)——與前輩學(xué)術(shù)經(jīng)典重逢時(shí)的治學(xué)反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