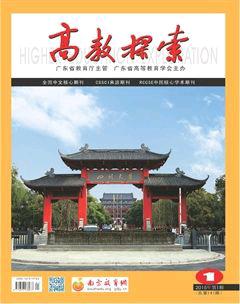美國城市化崛起時期城市學校的課程設置
李朝陽
摘要:在美國城市化進程中,為應對城市化的教育需求,使學生適應未來的職業和社會角色,城市學校課程設置手工訓練、職業教育和公民教育,課程呈現分化。城市化時期課程設置轉向分化,這是一種官僚戰略,它是對學校體制面臨的一系列外部需求和壓力的回應,以此應對城市多元人口的教育需求。這為我國新型城鎮化進程中課程設置提供借鑒。
關鍵詞:城市化;城市學校;課程;分化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城市化崛起時期,多元文化背景下如何滿足不同人群的教育需求是一個突出問題。隨著大批非英語國家的移民涌入,美國城市學校承受著教育窮人和移民的壓力,城市學校只有通過改變課程來適應城市化的需求。到19世紀90年代,針對不同學生群體的專門化課程出現。城市學校設置多樣性的課程:觀念形態探索的手工訓練,勞動市場與學校銜接的職業教育,追求公民身份的公民教育。
一、手工訓練:一種觀念形態的探索
(一)手工訓練的倡導者
卡爾文·伍德沃德(Calvin Woodward)是美國手工訓練倡導人之一。伍德沃德認為手工訓練是智力和道德教育的需要,也是一種恢復人工勞動價值和尊嚴的方法。他投入大量時間研究如何使年輕人為工業化的需求做好充分的準備。為達到這一目的,他提出課程應重視以工業為導向的技能教育,提倡在傳統課程中增加手工訓練,他認為手工訓練將會幫助學生從小認識到“知”與“行”的聯系,這一舉措可使教育符合現代社會的要求。 [1]
于是伍德沃德通過制造木材與工具,引入手工訓練制度,指導學生如何使用工具,其教學價值在于使學生心手協調。伍德沃德的研究也促使他更深入地改革課程,設置豐富的手工訓練課程(包括商店活動、數學和科學),他也主張為學生提供良好的英語通識課程。伍德沃德確信經過手工訓練課程的培訓,學生會在所有的學科與領域取得成功。手工訓練試圖平衡工業進步和社會穩定,它向學生傳授社會價值和道德價值。1880年開辦的圣路易斯手工訓練學校的座右銘表達了伍德沃德的目標——有教養的頭腦與靈巧的手。
(二)手工訓練中哲學與政治的斗爭
在對待手工訓練的態度上,伍德沃德與威廉·哈里斯(William Harris)產生分歧。哈里斯反對公立學校引入手工訓練,他認為公立學校課程的學習性質應歸結為文明生活的五大分支,即靈魂的五個窗口:數學、地理、文學、語法和歷史。數學與地理學致力于人類征服和理解自然。文學談論文學藝術作品,語法談論語言的研究和使用,歷史談論的是對國家機構多方位的理解。而伍德沃德提出數學、文學、科學、繪畫和手工訓練以代替哈里斯的五個窗口。[2]學校須隨著社會的轉變而改變是伍德沃德的教育信仰。他認為:“需要知道更多具體的,少些抽象的;更多初級知識,少些中級知識;更多個人經驗,少些記憶;更多的生活、活動、興趣和實施,少些被動;更多的成長,少些吸收。”[3]這種轉變可通過手工訓練實現。
二者爭論的焦點是對未來工人而言,什么樣的技能是最重要的。哈里斯不接受伍德沃德宣稱的手工訓練的益處。哈里斯認為傳統課程為智力發展提供一種極好的手段。他認為對于無法達到規定課程標準的學生來說,手工訓練才有用,這是一種傳統偏見,正是這種偏見使得哈里斯反對手工訓練。雖然存在這種偏見,但美國一些城市陸續效仿圣路易斯手工訓練學校。伍德沃德學校成為一個重要的有影響力的教學法典范,它允諾培訓工業社會所需要的熟練工人。到1891年全國教育協會成立工業教育和手工訓練部。
總之,伍德沃德堅持課程設置的實用性,關注城市青少年人口的需求,開展一場強有力的、不可逆轉的運動,擴大了課程領域,增加了正規教育的責任。課程以制圖、藝術教育或機械技能訓練形式被引入到許多學校。但手工訓練融入公立學校并非順利,反對手工訓練的人士指出,公立學校不能專門來為企業培養工人。還有的教育家認為,手工訓練培養的技能與工業所需的技能沒有關系。雖然有諸多反對的聲音,但手工訓練對另一種運動——職業教育起到重要作用。
二、職業教育:勞動市場與學校的銜接
(一)職業教育主義的政治性
19世紀70年代以來歐洲工業教育已在美國教育論爭中日益突出。職業教育面臨的問題不僅是政治性的,也涉及適用性問題,即什么樣的訓練最有價值。“公共教育制度必須擴大和使其組織多樣化,以致于為職業教育帶來廣泛的真正的供應。”[4]許多人關心城市生活,他們期望通過改革課程和教學法達到再生社會價值的目的。關鍵不是人們掌握什么技能,而是他們如何利用技能,以及技能對道德決策和道德行為的重要性。
而職業教育超越了上述問題。由于職業教育對工業化擁有堅定的信念,即使技術進步和社會穩定有沖突,職業教育也淡化了這種沖突。事實上,職業教育并不是尋找過去的傳統價值觀,而是贊美與工業最密切相關的部分。但更重要的是,工業教育拒絕把共性作為公立學校教育的基礎。過去的教育要把兒童培養成有相似學習經歷的人,但現在的教育考慮到差異,教育針對不同兒童而設計,是一種專業化的學習,兒童的專業化學習是高效工業生產的需要。在職業教育的影響下,分化型學習和分離的學校計劃成為民主教育制度的思想基礎。這種思想將很快迫使重新定義教育機會均等。[5]
(二)職業教育主義與教育機會均等
職業教育制度化要求對學生進行分類、區分課程,知識要求適用性。職業教育者確信城市化的美國需要熟練工人,他們要求學校立足于不同學生的特征,進行專業化和不同類型的教育。城市建立工業學校,吸引潛在的學校輟學者。雇主將用更高工資雇傭職業上受過訓練的人。在這個過程中教育工作者促進了職業指導運動。
1.職業指導
職業培訓針對14~16歲的年輕人,但后來證明這是不適當的,于是職業教育者針對小學進行職業指導,職業指導強調分類。職業工作者期望通過傳授工業行業的基本知識,提高工人階級的孩子的水平,職業工作者也主張兒童在離開學校之前,應接觸經濟知識。學生一旦進入學校,學校教育的優勢就變得很明顯,即使學生不再繼續求學,也應接觸工作技能。學校為兒童進入職業學校開設的課程有縫紉、烹飪、家務管理和個人衛生,這些課程與現有的手工訓練類似。女生經過學習后深入了解喜歡的工作,獲得一些具體有用的學科知識,她們完成學業后找到高標準的工作,過上高品味的生活。她們如期或比期望更高地精通學術科目,獲得更高的義務感、責任感、正義感、誠實工作感、勤勞和節儉習慣,使她們具有更好的工作態度和更有條理的工作習慣。
職業指導在社區學院體現的尤為明顯,社區學院對學生的學術能力和工作技能都提供指導。例如,北卡羅來納州都柏林市的布萊登社區學院提供兩類課程,一類是為學生就業做準備的職業培訓課程,一類是為學生繼續深造準備的課程。其也為學生提供各種類型的職業指導,學院進行職業指導的目的是讓學生更充分地了解自己獲得的技能適合什么樣的工作。學院圖書館為學生提供詳細的職業信息手冊、情況介紹表以及工業目錄。學生服務中心為學生提供團體或個人職業信息咨詢服務。
布萊登社區學院為學生提供的職業培訓專業有:會計學、農業綜合經營技術、副學士學位護理、人力資源管理、木工工藝、計算機技術、化妝藝術、刑事司法技術、早期兒童教育、電氣技術、美學技術、酒店管理、嬰幼兒護理、翻譯技能、護理助理、助理理療、實用護理技術、學齡兒童教育、焊接技術等。
以會計學專業與農業綜合經營技術專業為例。會計學專業的目的是為學生進入會計行業做準備,教授學生會計學基本知識和技能,培養學生用“商業語言”分析財務業務。學生要學習會計基本知識與理論,并進行實踐,同時還要學習商業法、金融學、管理學和經濟學等課程。學生通過學業交流、計算機應用、金融案例分析、批判性思維訓練和職業道德教育獲得會計學的其他相關技能。該專業畢業生應達到會計職業準入標準,能勝任會計師事務所、小型公司、連鎖企業、銀行、醫院、學校、政府機構等的會計工作。
農業綜合經營技術專業是為農業行業中的農業綜合經營培養人才。該專業為學生提供與農業行業相關的商業理念和基本規則等知識。學生需學習農業產業組織與管理規則,并學會在農業生產中運用這些規則。學生還需了解農業的經濟學知識、政府政策和農業產業項目等。本專業畢業生適合在農業設備銷售、飼料經營、農產品供給、農場經營和農產品營銷公司等農業綜合經營的部門工作。[6]
2.職業教育主義運動
1911年喬治·斯特雷耶(George Strayer)基于對318個城市的研究得出結論:公立學校13~15歲的學生,有一半輟學。他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建立一個適應個別差異的課程,把打算上大學和計劃或需要找工作的人分開。要想真正的民主,學校需為每個學生提供最適合其未來工作的訓練。斯特雷耶的觀點是一種有代表性的意見,它推崇放棄一個共同的課程,把年輕人分流到不同軌道上。斯特雷耶預測大量學生將會學習專門化的職業課程,基于這種假設,他認為如果課程更加強調實用性,就會有更多兒童上學。因此,如果說服家長和兒童相信接受的學校教育越多,學校教育的價值就越大,向他們充分展示教育價值,窮苦家庭可能愿意做出必要的犧牲以延長子女的教育。[7]
1920年保羅·道格拉斯(Paul Douglas)把許多孩子的經歷描述為:從工作到工作,從工業到工業的漂流,孩子過早接觸社會和工業的罪惡,這些罪惡不利于他們的成長。當孩子步入成年后,他會發現自己收入極低,社會地位脆弱,又由于更年輕的非技術工人不斷涌入勞動力的隊伍之中,他可能成為非熟練工人階級中的失業人員。道格拉斯指出:孩子除了青春,他沒有什么可出賣的;他出賣了自己的青春,但卻一無所獲。[8]
這些研究所表達的對青少年的高度關注來自于一種評定——城市經濟已經步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因此未受學校教育的青少年已成為社會責任。只有青少年找到有酬的工作,即使非技術性工作也可被看作是未來發展的需要或有價值的前奏。在20世紀之前,服務行業對技能的要求很低,許多勞動崗位也不要求工作人員具有成年人的能力,而這些崗位又很缺少人手。但在世紀之交,隨著收銀機、氣動導管、折紙機和電話的引入,必然導致從事這些工作的勞動力過剩。前進的技術不僅帶來就業的不穩定或大批失業的青少年,同時也要求學校為青少年提供適應現代工業體系的指導。
在20世紀最初十年,教育工作者、商人和有組織的勞工組成全國工業教育促進會,他們迫切要求將職業課程列入公立學校課程。在國家層面,1917年國會通過《史密斯-休斯法》,該法案的出臺開啟了聯邦基金首次贊助職業培訓的先河,這奠定了聯邦資助中等與高等職業教育的基礎。于是,《史密斯-休斯法》就與1862年的第一《莫雷爾法案》、1887年的《哈齊法案》以及1890年第二《莫雷爾法案》一道共同構建了美國高等職業教育的立法體系。
走向職業教育主義運動最明顯的表現是,全國教育協會的兩個有影響力研究的轉變——十人委員會報告和《中等教育的基本原則》。十人委員會主要研究了中學課程和大學的銜接,委員也更廣泛地界定中學功能,認為全面改組中等教育是當務之急,要重新調整課程以適應城市化所創建的新社會秩序。這就促使了綜合中學的誕生,它包括適應個別差異的課程,這是對十人委員會報告中哈里斯模式的直接否定。
由于更為復雜的經濟秩序的發展,社會發生的根本改變是“用工廠生產制代替家庭包工制;機器代替手工勞動;工序的高度專業化與之相應的勞動精細化”[9],使得特殊的職業培訓成為一個公共責任。由于認識到這一點,到1918年,經過多次的調查研究和分析,委員會認為除了通常的大學課程之外,還準備設立農業、商業、文書、工業、美術和家政學課程。
3.職業信息局
職業信息局是波士頓教育體制中一個重要力量,它利用和波士頓慈善及教育機構的密切關系,與學校委員會建立工作協議,為城市公立學校提供一個專任的職業顧問。職業信息局工作者和職業指導委員會合作,向挑選出來的教師和校長提供培訓課程,與家長、教師舉行公開會議,在大多數小學舉辦職業指導講座,創辦職業圖書館。職業能力評定作為進入波士頓商業和實用工藝中學的條件。
在邁耶·布盧姆菲爾德(Meyer Bloomfield)領導下,職業信息局成為美國職業教育和就業機會信息的中心。職業指導強調職業信息和安置,主要關注如何培訓孩子,使其能更好地適應工作。布盧姆菲爾德認為專業化使每一個選擇更為重要,他希望給個人提供更多信息,用知識作為改革機構的杠桿,尤其對城市貧民窟的居民。貧民窟的家長被迫從事繁重工作,通常不能有效地指導孩子,他們只能把子女送到過度擁擠的學校。布盧姆菲爾德指出這些孩子因缺乏機會,再加上他們周圍的社會混亂而情緒低落。為了扭轉這種狀況,布盧姆菲爾德呼吁每個孩子“開始到社會上做事”的計劃。[10]
布盧姆菲爾德希望喚醒社區責任,使公眾逐步認識到保護年輕人的必要性,例如了解童工法、就業證書、健康和工廠審查、職業教育以及職業介紹所許可證的發放要求。布盧姆菲爾德主張擴大學校在社會改進中的作用。他認為在一個民主社會,不能把工作與學校硬性分開,它們必須共同承擔責任,以使未來一代取得更好的成績。作為一個具有社會目的的教育機構,學校應著手調查工業和揭露那些損害青少年的環境。[11]
綜上,職業教育有助于使直接服務成為公共教育的主要目標。工業教育運動通過學校吸引窮人、移民和輟學者,也試圖使學校民主化。因此職業主義闡述了教育民主的新定義。有區別的學校教育和學生分類取代了共同的學習環境。教育機會均等意味著起始于不同水平的個人將在不同層次結束他們的學校生涯,學生的教育質量是由教育起點和教育終點所構成的整體效率所決定的。[12]職業教育也是擴大生源的主要措施。它創建了一種新型課程。到20世紀20年代末職業教育成為美國公立學校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但對于職業教育的價值,在黑人高等教育領域曾展開過一場辯論,著名的黑人領袖華盛頓(Booker Washington)認為教育是黑人提升自身地位和爭奪權利的基石,職業教育是黑人得以謀生的基礎。在教學實踐上,華盛頓為黑人廣泛設立技術學校,進一步開展職業教育。而另一位黑人民權領導者杜波依斯(W. DuBois)則反對華盛頓用職業教育來爭取黑人地位的言論,杜波依斯指出一味地追求職業教育禁錮了黑人提高自身的職業和社會地位,認為應該為黑人提供多樣的高等教育,而非單一的職業教育。
三、公民教育:公民身份的追求
不同兒童坐在同一間教室里,向他們提供識字和道德的基本知識,這將保證民主社會運行所必需的同質性和凝聚力。幫助兒童逐步適應特定社會的經濟和政治制度,并成為社會成員,這是城市學校的共同目標。為達到這一目標,城市學校通過公民教育,在思想意識層面對移民進行教育。
但在19世紀的最后幾十年,對社會環境的畏懼在教育辯論中占重要地位。公眾的不忠實、勞動騷動、炫耀性消費、貧民窟生活等成為技術和社會變革的產品。在少數族裔聚居的城區,他們的價值觀和行為模式與主流文化觀念明顯不符,這威脅了價值觀和行為模式的同質性,而這種同質是公共教育存在的理由。學校教師再也不能依賴外界環境灌輸道德,也不能寄希望于在州的層面上宣傳文明。他們開始修改公民身份的定義,從識字和廣泛道德價值觀的信念走向明確引導行為與愛國主義。在搜索團結的象征過程中,他們把國家假日和旗幟作為教育的基礎。這些道德價值觀念在馬薩諸塞州的公共夜校得以發展。
(一)夜校體制的正規化
馬薩諸塞州通過立法使夜校授課合法化,并規定地方學校委員會為夜校提供資金,夜校運動得到加強。夜校計劃采用小學日校的課程作為教學基礎。在1870年《工業繪圖法》頒布之后,許多大城市開設繪畫學校,吸引半熟練的工人、辦事員和白領工人。夜校法規強制規定:未成年人只有參加夜校學習,才能被雇主雇用。法規要求任何商業或機械機構不能雇用14歲以下又不會讀寫簡單英語句子的兒童。同時法規要求所有14~21歲的文盲需參加日間或夜間班級,雇主不能向沒有入學證書的個人提供工作,否則會遭到50-100美元的罰款。[13]夜校體制的合法化提供一個明確的社會功能——向不說英語的人傳授讀寫能力。夜校通過該法擺脫了靠意志辦學的模式,變成強制性機構,立法增加了學生的規模和異質性。這迫使人們重新定義夜校,有利于鑄造公民教育的新內涵。
夜校委員會與監督者分析計劃的進展和缺陷,他們用表格記錄按時出勤的學生,然后發給本地雇主。這使得夜校課程正規化,并明晰所討論的主題和目標。1890年之后,教授移民如何生活也促使了夜校的正規化,夜校為不說英語者制定了美國生活手冊。夜校開始成為個體獲得權利的機構,并使個人學會如何成為公民。夜校不再把自身功能僅看作傳授讀寫能力和道德價值,而是越來越多地承擔向新移民解釋美國社會環境的任務,向他們提供具體的行為指示,通過情感投入改善他們的環境。夜校讀本增加個人衛生與保健知識,并向移民解釋政府運作方式及各政府機構間的關系,介紹移民入美國國籍所需的程序和入籍文件。1907年波士頓成立特殊委員會,為夜校設計一個公民初級讀本,詳細介紹了市政府的運作程序,這是移民到達美國后最先接觸的機構。委員會要求夜校教員每周為移民介紹城市衛生、國家假日與歌曲、當前事件及公共場所的行為規范。
(二)晚間社會中心
晚間社會中心運動是教育公民的另一種方法。晚間社會中心是利用社區觀念將個人納入公民和諧的一個方式。它認為生活在人口稠密的異質城市,鄰里關系不和睦會阻礙群體合作與社區的發展。團結、友愛、公民參與是晚間社會中心的期望。城市學校學區通過廣泛利用現有設施,學校更緊密聯系社區,使公民身份呈現新涵義。晚間社會中心將發展社區利益、睦鄰友好的精神和城市民主作為主要目標。
(三)美國歷史與傳記
學校作為社區活動的中心,美國歷史的學習受到高度重視。這是一種灌輸民族自豪感和鞏固群體忠誠的方式。學習歷史的首要目標是讓學生了解國家過去的狀況,認識到前幾代的奮斗和英雄精神,最終逐步感受到來之不易的神圣和平、今日的繁榮與舒適、自身對其延續的責任。[14]出于對移民涌入的關注,1857年州立法機構要求公立學校必修課增加美國歷史。19世紀末隨著移民的增加和社會的分化,學校課程再次重視歷史教學,以保證移民的忠誠。學校督學指出,公立學校的職能之一是使移民子女成為忠誠的美國公民,教授美國歷史無疑是實現此目的的最有效方法。學校歷史課本增加戰爭編年史和總統行政當局對社會生活的討論。一些教科書引入腳注、補充閱讀書目和建議研究的話題。例如,紐約城市大學開設了美國研究課程,該門課程的主要任務是通過傳統課程的學習,幫助學生了解美國文化和歷史。美國研究觸及英語、歷史、哲學、社會學等領域。這些課程體系涉及美國歷史文化、美國思想史、美國民族學和民族志、大眾文化社會史。[15]
與美國歷史教學相關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傳記的教學。傳記是“勇氣、愛國主義、忠誠信任、堅持不懈、自我否定、人道”的一個實物教學。[16]傳記對孩子來說是一個明確的聲明:他們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成功的機會在于自己的行動,社會與這些行為決定休戚相關。教育者越來越關注明確的行為教學,公民學納入公立學校課程就是明顯的體現。
(四)公民學
19世紀末公民政府課程開始論述正規機構和政治理論。1875年喬治·馬丁(George Martin)的教科書《公民政府》探討政府形式與職能、公民身份的職責和性質。他追溯了殖民地時期美國政府起源及部門運行與憲法作用。[17]后來馬丁對美國社會的看法發生改變。他提出對公民身份的特殊訓練不再是一種奢侈品,卻是一種必要。馬丁強調小學階段需盡早認識到公共利益的重要性,讓學生了解個體對集體的從屬關系和遵守法律的重要性。兒童在離開學校之前,需知曉公民身份的義務和權利,保護本身的自由不受外國、政府及鄰居的威脅。他強調美國人的政治教育應多于工業教育。1895年馬丁再次呼吁新一輪的愛國公民身份的教育。[18]這提升了公民學在課程中的地位。例如,紐約城市大學布魯克林學院就開設了公民、權力和政治這樣一門課程。該門課程通過研究美國社會的權力、政府機構和社會組織,讓學生重點了解美國政府和公民的互動關系。[19]
四、結論與啟示
美國城市化崛起時期城市學校的課程設置不僅體現在分化,還體現在多樣性上。多樣性一詞描述了該時期處于變化中的城市社會組織。社會中角色的不同與日益擴大的勞動分工、勞動市場和職業專業化相關。信奉效率的管理進步主義認為,學校基于個人天生的興趣和能力,分配給他們不同的社會角色,有助于使專業化和分化過程更加順利。這不同于前幾代教育工作者強調的主題——共性和伙伴關系。隨著管理進步主義者突出強調專業化和區別,20世紀初美國課程設置注意到多樣化和靈活性的需要。[20]課程“分化以顧及不同階級學生的需求”[21]。這樣的學習計劃是為了讓青年人為不同目的做準備,使學校成為學生開始奔向各自不同命運的地方。
而目前在我國新型城鎮化進程中,課程設置如何滿足多樣人群的需求是一個重要的課題。學校和社會的互動是影響課程發展的因素,學校課程應切合城市化社會的問題和需求。我們要根據所能發現的學生的能力和傾向,為他們分配不同類型的差異性課程,既要顧及到升學也要考慮就業。課程需基于不同個體的特點、學生能力來設置,最終要讓學生獲得適合自身資歷的工作,這也是實現教育機會均等的一種方式。當每個人都有機會接受適合于其才智的教育和從事適合于其資質的工作時,民主的理想才能得到最充分實現。
參考文獻:
[1][3][9]Selwyn Troen. The Public and the Schools: Shaping the St. Louis System, 1838-1920[M].Mo.: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75:168-170, 170, 181.
[2]Calvin Woodward. Manual Training in Education[M].New York: Scribner and Welford, 1890:41-46.
[4]Massachusetts Board of Education. Annual Report[R].1914-1915:41-42.
[5][12][13][14][16]Marvin Lazerson. Origins of the Urban School: Public Education in Massachusetts,1870-1915[M].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178, 200, 214,232-233,234.
[6]Bladen Community College. Bladen Community College General Catalog[EB/OL]. http://www.bladencc.edu/pdf/college_catalog.pdf,2014-11-02.
[7]George Strayer. Age and Grade Census of School and Colleges[M].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1:139-140.
[8]Paul Douglas. American Apprenticeship and Industrial Education[M].New York: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21:85.
[10]Meyer Bloomfield. Readings in Vocational Guidance[M].Boston: Ginn and Company, 1915:12-20.
[11]Meyer Bloomfield. Youth, School, and Vocation[M].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15:24-25.
[15]Bulletin.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EB/OL]. http://www.gc.cuny.edu/CUNY_GC/media/CUNY-Graduate-Center/PDF/Publications/Bulletin/Archives/GC_Bulletin_2014-15.pdf,2014-11-02.
[17]George Martin. A Text Book on Civil Gover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M]. New York: A.S. Barnes and Company, 1875: 219-224.
[18]George Martin. New Standards of Patriotic Citizenship[J].Journal of Proceedings and Addresses, 1895:134-139.
[19]CUNY-Brooklyn College. People, Power and Politics[EB/OL].http://www.brooklyn.cuny.edu/courses/ShowCourse.do?dsc=CC&crs_num=%20%2023,2014-11-02.
[20]康德爾. 教育的新時代[M]. 王承緒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92.
[21]David Tyack. The One Best System: A History of American Urban Education[M].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191.
(責任編輯陳志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