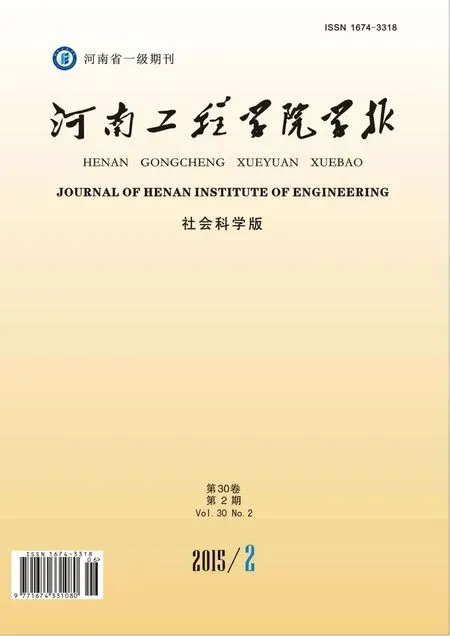論消費文化范式下張愛玲文本的電視劇改編
楊 曙
(常州工學院教育與人文學院,江蘇常州213022)
在消費社會環境下,很多名家小說被改編為電視劇。社會學家布爾迪厄曾經這樣說道:“藝術品價值的生產者不是藝術家,而是作為信仰的空間的生產場,信仰的空間通過生產對藝術家創造能力的信仰,來生產作為偶像的藝術品的價值。”[1]張愛玲的小說是文學經典,在消費文化時代,很自然被導演們直接拿來并改寫,在改寫以后,也就產生了一定的文藝場,本文關注的就是這個文藝場。
一、張愛玲文本的原初商業語境
當代中國已經進入十分明顯的消費主義時代,并帶有很強的消費主義文化特征,消費主義文化在當代中國已經具備了話語權。消費本身的目的不是為了吃穿,而是刺激與制造欲望,并不斷滿足欲望。不管是基本的生活物質還是文化產品都會被這種消費氣息所感染,傳播媒介會大肆利用這種氣息并制造強大的欲望。早在20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華洋雜處的上海就因為其開放,娛樂、金錢、欲望等現代消費主題一開始就綁定在電影中,不管是純文學還是純音樂純繪畫,都或多或少沾染到大眾文化的消費氣息。就實際的文化場來看,大眾文化與商業的密不可分也為不少當時的海派商業文人提供了創作的契機和作品原初的本質,當他們成為一種大眾文化的合謀者時,他們能完全利用大眾媒介的攻勢,與充滿現代性的上海十里洋場大眾文化融合,使得原本高高在上的雅文學出現雅俗交匯的狀態。“淪陷區的作家大部分必須以稿費和版稅為生,讀者的反應對于他們而言即是生計的來源,米珠薪桂是任怎樣超然的人也不可能超脫的現實。”[2]通俗文學從來都面向大眾,沒有受眾也就沒有文學的欣賞,文學是否有受眾也就成為作家文學成就的重要標尺。舊上海印刷業的發達,也使文學具備了較強的商業屬性,張愛玲的文本從一誕生就進入強大的流通領域,也成為她個人謀生的工具。
1943年和1944年是張愛玲文學創作最重要的兩年,自從她在周瘦娟主編的《紫羅蘭》上發表《沉香屑第一爐香》后,又連續在《萬象》《天地》《古今》等雜志上發表了大量作品。在這兩年里,張愛玲不僅發表作品的速度加快,而且密度很高,其主要作品充斥著男女婚姻,主要人物存在的價值也是為了情欲。表現情欲的作品往往流于世俗,不管是何種性別與國籍都樂于賞鑒。
值得注意的是,張愛玲的這種批量生產不僅表現在她總量的批量生產,連同她自身的作品也存在著復制性,她的一些作品存在著驚人的相似,如《十八春》和《半生緣》、《金鎖記》和《怨女》、《小兒女》和《哀樂中年》,這些作品主題都是差不多的;《有女同車》和《等》都是在表現女人念叨的總是男人,女人所議論的也是男人;《道路以目》和《色·戒》都是表現封鎖中的情感;《私語》和《童言無忌》中的自傳回憶又出現在《茉莉香片》和《十八春》中。這種文學復制性帶有很強的消費意識形態性,這是張愛玲消費意識寫作的明顯表征,因其感受到某種敘事模式帶來的神奇商業魅力,才會將這種模式繼續使用。在她的筆下,商業與文化已經成為一個交互體,讓商業文化成為生產領域的重要調料。大眾文化學者費斯克認為,不少大眾文本的意義并不是天生就有,而是在與大眾的交互作用中產生的,大眾文化的文本就是“大眾文化產品同大眾日常生活需要以及大眾日常經驗的相關性”[3]。文學文本的消費性被二度移植到電視文本,而且把張愛玲原先訴說的家長里短表現得更加凡俗化,十里洋場的光怪陸離與燈紅酒綠得到更加普泛化的表現。“大規模的傳播意味著內容被非語境化(decontexualized),在這一過程中,內容失去了本雅明所說的‘靈韻’(aura)。”[4]
二、當代電視傳媒與原初文本的合謀和消解
20世紀90年代以后,在市場經濟高速發展的背景之下,張愛玲的文本消費更加深入大眾文化領域。在這種情形下,由于大眾文化水準的參差不齊,在傳媒的炒作下,文學消費開始走向欲望化,大眾傳媒將自身的關注熱點集中在張愛玲的文學作品方面。雖然當今的受眾和20世紀40年代的受眾存在很大的區別,但他們都熱衷消費的本質是一樣的。不管是文學文本還是影視文本,都體現了“大眾文化產品同大眾日常生活需要以及大眾日常經驗的相關性”[3]。
與傳統文字相比,影視手段往往比較直觀,且具感染力和震撼力,因此,在消費社會極具生產能力。這種生產能力與張愛玲文本本身具備的原始消費屬性產生了合謀。大眾傳媒在內容傳播方面,較之傳統的文字更能表現人的欲望。正如南帆所言:“影像撤去了文字形成的屏障;影像的空間邏輯令人感到,欲望的對象與自己同在。這極大地誘導了自居心理的發生:人們將自己想象為欲望周圍的一個角色,甚至朦朧地構想自己與欲望對象的種種生動情節。”[5]從受眾角度而言,影視改編給大眾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愉悅,人們不用讀書便可進行觀看。現實生活中的人們,為了娛樂需要,必然想獲得自身的快感。從大眾傳媒角度而言,傳媒機構往往有巨大的經濟壓力,傳媒被逼迫著在“生產—消費”模式下進行運轉,使用富于商業性的文本進行影視作品改編往往也有著更高的收視率。
但是,由于市場經濟的飛速發展,20世紀90年代至今和20世紀40年代畢竟有著較大的文化消費差異。在一定意義上,電視文本在挑剔的受眾和高壓力的收視率下,會削弱原著的思想深度,更多體現出一種趣味性,表現為一種直觀快感。正如安德烈·勒文孫所言:“在電影里,人們從形象中獲得思想,在文學中,人們從思想中獲得形象。”[6]電視中審美會出現與原著的背離,從觀眾的角度去把握電視細節,電視中往往會出現一種“匱乏與拯救”[6],也就是說,電視作品中會表現一種現實生活中人們所匱乏的品質,轉而由影像中的人物來完成這種品質,包括對愛情的忠貞、對理想的追求、對友情的負責,人們在電視中所追求的人物形象往往是至善至美的,這種完美形象完全是人們日常審美中的追求,因為人們日常缺乏,所以他們會在電視中尋求表現,以此來完成一定意義上的人生救贖。
原初張愛玲筆下的人物并不是人們日常審美中的完人,她平日寫作就是打破傳奇,解構完人。她的筆下從來沒有英雄,全是世俗男女,帶有種種人性的缺陷,這些人物鉤心斗角、自私、膽怯,這些有著瑣屑缺點的小人物,才是時代的真正代表人物。王佳芝、許小寒、曹七巧、范柳原、白流蘇、葛薇龍……這些一個又一個樹立在經典文學之林的人物形象并不是高大全,而是個個充滿著人性的缺點,張愛玲一定要揭開每個小人物的面紗,直接從本質上揪出那真實的卑微和缺陷。
原著中的《傾城之戀》實際上講述了一個自私女人白流蘇和一個自私男人范柳原的結合。白流蘇雖然外貌很好,但是本人十分工于心計,她在娘家敗落和積蓄被哥嫂盤剝的情況下,就只想著依靠嫁人改變自己的命運,她找范柳原就是覺得范柳原既能給她帶來收入又能給她帶來面子。正如文中白流蘇所言:“我又沒念過兩年書,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我能做什么事?”[7]239在這樣賭博式的婚姻支配下,她自然和范柳原就沒有什么感情。“如果她是純粹為范柳原的風儀與魅力所征服,那又是一說了,可是內中還摻雜著家庭的壓力——最痛苦的成分”。[7]2552009年上演的電視劇《傾城之戀》中,白流蘇卻一掃那種小資產階級女性的弱點,端莊大方,善良聰慧,對范柳原情深意切,對哥嫂忍讓妥協,在戰爭中頑強、勇敢、有愛心,簡直就是一個高大全的人物,找不到任何人性缺點。小說中的寶絡,是白流蘇的妹妹,是個隨波逐流式的人物,在哥嫂的離間下,她認為白流蘇奪她所愛,與白流蘇直接斷掉姐妹情誼。在電視劇中,寶絡是非常有主見的女子,她總是支持白流蘇,和白流蘇感情非同一般,戰爭爆發后,寶絡完全接受革命的洗禮,成為一個堅強的女子。雖然這樣的改動更加符合觀眾的期望,但是原先文本的文學張力缺失了很多,文本的主題被顛覆掉,而且文學的審美價值被削弱了很多,這種人物刻畫手法是不符合現代文學的人物塑造原則的。
電視劇對文學文本的二度創造是不善表現人物豐富的心理活動的,但經典名作都善于表現人物細致的心理活動,將人物的心理活動描寫得十分仔細。電視劇不可能表現出人的心理活動,心理描寫必須依靠人物的言語及行動表現出來,如果表現不好,則會被原先文本中的心理描寫局限住。張愛玲的開山名作《金鎖記》,其成功之處就在于塑造了曹七巧這個人物形象,她原本是個有姿色的普通女孩,健康又潑辣,她以自己的愛情為代價和一個殘廢的少爺結婚,幾十年后,她擁有了豐厚的家產,此時她心理卻壓抑到極點并引起心理變態,她折磨自己的兒媳,和自己兒子曖昧,破壞自己女兒的婚姻,完全成了一個感情畸形的怪胎。這些心理變化過程在小說中表現得細致入微。《金鎖記》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地位極高的原因之一即為該小說把中國心理分析小說推向極致,人物的變態心理被十分細致地鏤刻出來,一系列毒辣的心理活動讓讀者產生了驚心動魄的感覺,這些是電視劇無法表達的。電視劇是極其通俗化的,2002年由穆德遠導演的電視劇《金鎖記》中,曹七巧變成了一個溫情脈脈的人,最后帶著一顆釋懷的心離世。電視劇中人物性格的藝術感染力顯然大不如小說,悲劇性被降低了很多,電視劇完全是站在一種極為通俗化的角度來進行制作的,適合大眾的口味,但是削弱了原著的心理描寫所帶來的藝術滲透力。
三、電視消費語境中的經典削弱
存在于張愛玲作品電視劇改編的大眾文化,令受眾感到興奮的是改編中的符號,這種符號的存在,導致經典意義的改變。電視劇在不斷地生產各種符號,受眾的快感體驗也在不斷更新。當電視劇對經典進行再造,受眾和張愛玲經典作品也就構成了不斷消費的關系。媒介不斷對張愛玲經典作品進行改造,大眾文化符號在生產領域是一種文化消費的形態,具有很強的潛力。文化學家威廉斯曾經這樣寫道:“新的技術具有經濟關系,其實際作用因而帶有極端復雜的社會性。技術的改變必然使資本的總額與集中程度大為增加,從報紙和電視的經營可以最清楚地看到,這種增加的曲線至今仍然在上升。”[8]威廉斯一語道出包括電視劇在內的大眾文化的生產模式,為了大眾的消費而去進行大眾的生產,甚至將經典意義削弱,這種經典意義削弱實際包括以下兩個方面的含義:
第一,電視劇的觀看行為長久以來被認為帶有強烈的消費化特點。在這樣的日常活動中,人們的思維習慣和行為準則逐漸養成,并去重塑人們的日常行為和價值取向,經典美學發生了革命性的質變,成為日常生活審美。經典的美學變革也暗示了美學所包含的人生態度的一場轉換,依靠消費對日常人生狀態的呼喚而成為人類日常存在的一種新式坐標。曾經一度有知識分子幻想能把所有的精英文化對普通大眾進行開放和啟發,但這種烏托邦式的幻想和大眾文化的喧囂形成了一定的反差,知識分子原先主張的一種貴族式的理想已經變得非常荒誕,因為審美日常化已經成為當今美學的重要主題,類似張愛玲的文本只有經過當代重塑才能實現受眾消費,眾多經典的美學定義和理論范疇都做出相應的變化,經典的張愛玲文本也就失去了原先的價值,而改編進入到每個人自身的存在領域當中,以此希望提高當代人對美學的日常應用與經典意義的提升。毋庸置疑的是,人們日常生活和美學的密切關系已經成為當代美學革命的一場重要前戲,經典美學改變了曾經從某種自然美或藝術美出發去確認美本質的抽象思辨,轉而以自我的認同來關注生命的意義和生活的隨意。改編的美學變革也暗示了美學所包含的人生態度的一場轉換,依靠大眾對日常人生狀態的呼喚而成為經典存在的一種新式坐標。
第二,在對張愛玲小說的電視劇改編中,大眾的夢已經成為文化經典削弱活動中必不可少的支點,呈現出大眾消費的審美快感。費斯克曾經反復強調大眾在自身的文化消費過程中所獲得的一種快感,他認為:“快感、切身相關性與賦予權力的行為為其共同的母體,就在大眾文化的核心。”[9]8真正的大眾文化應該世俗性極強,大眾消費時能獲得一種快感。盡管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等文化學者把大眾文化看得一文不值,但是對張愛玲作品的電視劇改編而獲取的蓬勃收視率畢竟是不爭的事實。藝術家在面對職業化時必須依靠買辦與藝術中介力量來進入市場領域,使大眾獲得收視快感。對張愛玲經典文學的電視劇改編成為一種時代風尚,經典文本發生動搖之際,正是觀看生理欲望與功利思想追逐的頂峰之時。傳統文學中所具備的個性獨特、意味悠長、意境高深變成了欲望的無盡釋放和快感的無盡追逐,崇高莊嚴的大悲劇式模式被消解,油滑的喜劇被捧上高高的藝術臺階,傳統的典雅藝術是少數美學家的象牙塔專利,形而下的經典文化改編和身體感官享受已經成為大眾文化的必然選擇。“把快感在文化中的作用加以理論化,此類嘗試可謂屢見不鮮。這些嘗試雖然相去甚遠,但其共享的期望,是將快感分成兩個寬泛的范疇,一個他們彈冠相慶,另一個他們痛加譴責。”[9]60費斯克所理解的快感和庸俗式的享樂并非截然不同,而是有著一定曖昧關系,崇高快感的存在有時是為了映襯低俗的享樂。“我也愿意承認快感的多義性,并能夠采取相互抵觸的形式;但我更愿意集中探討那些抵抗著霸權式快感的大眾式的快感,并就此來凸顯在這二分法中通常被視為聲名狼藉的那一項。”[9]60費斯克所認定的快感可以分成兩組:有時這種快感是圍繞身體而造成了一種冒犯;有時這種快感表達了一種社會認同度,實際則是對于傳統經典霸權的符號化抵制,這就構成了一種反權威的力量,是一種合理的快感。而這種觀點恰好和法蘭克福學派認為的大眾文化只是低俗淺薄的觀點相左。
對張愛玲小說的電視劇改編本身即是世俗與審美的結合,當受眾觀賞后,他們所看到的景象是建立在自身快感體驗基礎上的,表現出自身情感與世俗審美的強烈統一,在日常生活審美化的當下,消費文化借助受眾日常情感的潛移默化,實現了經典審美的日常價值。
[1] 〔法〕布爾迪厄.藝術的法則:文學場的生成和結構[M].劉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276.
[2] 范智紅.世變緣常 四十年代小說論[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48.
[3] 金民卿.大眾文化論當代中國大眾文化分析[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2:18.
[4] 〔美〕戴安娜·克蘭.文化生產:媒體與都市藝術[M].趙國新,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1:25.
[5] 南帆.雙重視域——當代電子文化分析[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69.
[6] 〔美〕愛德華·茂萊.電影化的想象——作家和電影[M].邵牧君,譯.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89:114.
[7] 張愛玲.張愛玲文集(第四卷)[M].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2.
[8] 〔英〕雷蒙得·威廉斯.文化與社會[M].吳松江,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389.
[9] 〔美〕約翰·菲斯克.理解大眾文化[M].王曉鈺,宋偉杰,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