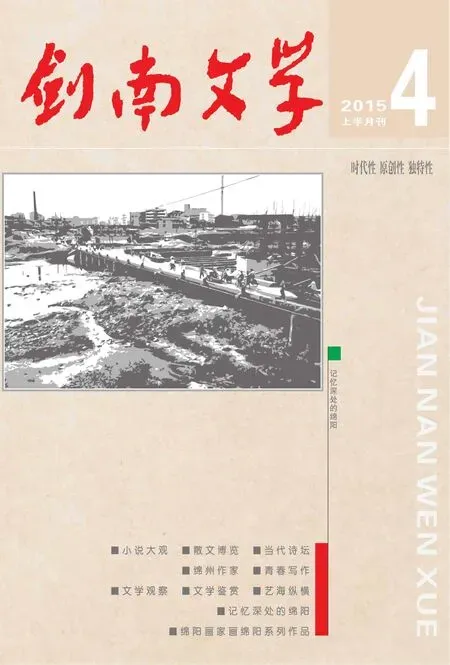科舉制度對中韓古代文學(xué)交流的促進(jìn)作用研究
■肖 俊
科舉制度自產(chǎn)生與就與古代文學(xué)有著不可分割的關(guān)系。科舉制度在古代中韓歷史上都長期存在,對中韓兩國古代漢文學(xué)的創(chuàng)作與發(fā)展有很大的影響,促進(jìn)了兩國古代歷史上的文學(xué)交流。論文將從科舉制度對中韓古代書籍交流、對兩國古代文人之間的文學(xué)交流、以及對兩國古代詩文風(fēng)氣轉(zhuǎn)變的三個方面闡述科舉制度對中韓兩國古代文學(xué)交流的促進(jìn)作用。
中韓古代兩國交往密切,文學(xué)交流就是其中重要的一個方面。中古代韓文學(xué)交流的重要的一個推動因素,是兩個國家之間的政治關(guān)系,在復(fù)雜的政治因素當(dāng)中,同在兩國古代社會文化發(fā)展過程中起重要作用的科舉制度不可忽視。科舉制度推動了兩國古代歷史上文學(xué)交流的發(fā)展,促進(jìn)了古代兩國文人之間的交流,從而促進(jìn)了整個韓國古代漢文學(xué)的創(chuàng)作與發(fā)展。
一、科舉制度對中韓古代文學(xué)書籍交流的促進(jìn)作用
從科舉制度誕生之日起,科舉考試的科目就沒離開儒家經(jīng)典文學(xué)的理論基礎(chǔ),以及詩賦策論的外在表現(xiàn)形式。因此在同樣實(shí)行科舉制度的韓國古代歷史上,儒家經(jīng)典是理論依據(jù),科舉考試的賦詩、作文之道,中國文學(xué)大家就是借鑒。這樣就在一定程度上規(guī)定了韓國古代自上而下的共同的閱讀導(dǎo)向。因此,在中韓古代的典籍交流也就特別重視儒家經(jīng)典以及重要的文學(xué)選集,文學(xué)大家的別集。而廣義的中國文學(xué)也包括了儒家的經(jīng)典著作,從這一方面看,科舉制度對于中韓古代文學(xué)書籍交流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
1.1 科舉制度對漢文典籍東傳的促進(jìn)作用
筆者統(tǒng)計朝鮮書目叢刊可以發(fā)現(xiàn)眾多中國的書籍如先秦文獻(xiàn):“五經(jīng)”、諸子文;文學(xué)選集:《文選》、《文苑英華》、《冊府元龜》、《古文真寶》、《唐宋八家文選》、《八家詩選》、《唐百家詩》等等;個人別集:《陶靖節(jié)集》、《李太白(文)集》、《杜工部集》、《白香山集》、《韓文公文鈔》、《歐陽文忠公文集》、《東坡集》、《半山集》等等。這些文學(xué)文獻(xiàn)資料在韓國古代的書目中比比皆是,而這些文學(xué)文獻(xiàn)書籍的傳入與在韓國古代文人心中產(chǎn)生的影響是離不開科舉制度的實(shí)行的。
在朝鮮半島科舉制度萌芽的統(tǒng)一新羅時期,規(guī)定必讀書書目有《春秋左傳》、《文選》、《論語》等及其他儒家經(jīng)典。
“新羅元圣王四年,始定讀書出身科:讀春秋左氏傳若《禮記》、《文選》,而能通其義兼明《論語》、《孝經(jīng)》者,為上;讀《曲禮》、《論語》、《孝經(jīng)》者,為中;讀《曲禮》、《孝經(jīng)》者,為下;讀若博通五經(jīng)三史、諸子百家者,超擢用之。前此,但以射選人,至是改之。”
在統(tǒng)一新羅時期,《論語》、《文選》、諸子百家等極具文學(xué)性的書籍已經(jīng)傳入朝鮮半島,并且在選賢上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科舉制度初創(chuàng)期的高麗朝考試科目為制述科,明經(jīng)科。制述科類于中國進(jìn)士科,試“詩賦頌及時務(wù)策”,明經(jīng)科主考中國儒家經(jīng)典。
“光宗九年五月,雙冀獻(xiàn)議,始設(shè)科舉。試以詩、賦、頌及時務(wù)策,取進(jìn)士。兼取明經(jīng)、醫(yī)、卜等業(yè)。十一年,只試詩、賦、頌。十五年,復(fù)試詩、賦、頌及時務(wù)策。”
在科舉制度初創(chuàng)時的高麗朝,明經(jīng)科主考四書五經(jīng),制述科考詩賦策等,其中又獨(dú)以制述科為主,在整個高麗朝時期,明經(jīng)科及第的人數(shù)遠(yuǎn)遠(yuǎn)少于制述科及第者,這就決定了高麗朝時期的文人主要走詩賦頌策創(chuàng)作的制述科,因此在高麗朝時期中國各個大家的文章文集也就受到了極大的重視。在崔滋的《補(bǔ)閑集序》中認(rèn)為:“漢文唐詩,于斯為盛”說明了高麗朝文人在科舉制度之下的主要詩文風(fēng)氣。又引述了俞升旦的話語:“凡為國朝制作,引用古事,于文則六經(jīng)三史,詩則《文選》、李、杜、韓、柳,此外諸家文集,不宜據(jù)引為用。”俞升旦的這句話說明了高麗朝科舉及日常作文都必須遵照的文集規(guī)范有 《文選》、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等的文章,這在側(cè)面也說明了,在高麗朝時期,兩國的文學(xué)書籍的交流已經(jīng)有了重大的突破。除此之外,諸如白居易的詩文也在此一時期傳入半島并產(chǎn)生重要影響,崔滋《補(bǔ)閑集》卷中:
“杜枚自負(fù)文章俊逸,譏樂天之詩龍雜淺陋。 當(dāng)時貍德若視日者,皆從而作誘,伴然同辭。故至于今詩人,雖不及知古人所謂白俗之意者,擾曰‘長慶雜說,何足看也’笑錢。”從這段話中不難看出高麗朝時期的文人們對白居易詩文的欣賞與借用。
在高麗中晚期的科舉制度當(dāng)中蘇軾、黃庭堅、歐陽修、韓愈、柳宗元的詩文大行于世,受到了眾多學(xué)子們的追捧,他們的文集也得到了廣泛的流傳。李奎報在《全州牧新雕東坡文跋尾》說道:
夫文集之行乎世,亦各一時所尚而已。然今古以來,未若東坡之盛行,尤為人所嗜者也。
以及他的《答全履之論詩文書》中談到:
“且世之學(xué)者,初習(xí)場屋科學(xué)之文,不暇事風(fēng)月,及得科等,然后方學(xué)為詩,則又嗜讀東坡詩,故每歲榜出之后,人人以為今年又三十東坡出矣。”
從李奎報的兩段話當(dāng)中,我們不難看出在高麗朝后期,隨著兩國科舉制度的不斷推行,蘇軾的詩文毋庸置疑的成為高麗朝文人爭相模仿的對象。蘇軾的詩文也就成了高麗朝科舉制度選人的評判標(biāo)準(zhǔn)之一。這一點(diǎn)在徐居正的《東人詩話》中可以得到印證:
“高麗文士專尚東坡,每及第榜出,則人曰:‘三十三東坡出矣。’”
再如崔滋的補(bǔ)閑集中所說:
“李學(xué)士眉叟曰,吾杜門讀蘇黃兩集,然后語道冉韻鏘然,得作詩三昧。”
他們的這些話都說明了,在科舉制度下,考生們?yōu)榱四軌蛟诳婆e考試中拔得頭籌,他們就必須學(xué)會用蘇黃之文,這也就推動了蘇黃等文集在高麗朝時期的流傳及接受。在高麗朝初期尚《文選》,《文選》等大行于世,在高麗中晚期由于科舉詩文風(fēng)氣尚古文,因此韓柳蘇黃等古文大家的文集開始得到傳播。這些都說明了在科舉考試的帶動下,兩國的文學(xué)書籍的交流也在不斷發(fā)生變化,文學(xué)書籍的流入為高麗朝的文人文學(xué)創(chuàng)作提供了典范,促進(jìn)了高麗朝時期漢文學(xué)的發(fā)展。
而在科舉制度完備及衰落時期的朝鮮朝時期,三年一試,分初中終三場,初場試經(jīng)義主考朱熹注四書五經(jīng),中場試論,詔,表等,終場試經(jīng)史時務(wù)論等。在科舉制度影響下的文學(xué)書籍交流逐漸被牢不可催的以性理學(xué),經(jīng)義考試為主的書籍所替代,而文學(xué)書籍的交流也逐漸是在國家支持下或者個人努力下進(jìn)行的,文學(xué)書籍的交流與科舉制度考試的內(nèi)容有了明顯的脫節(jié)。在李朝實(shí)錄當(dāng)中所描寫的關(guān)于明清賜予的書籍也多是性理學(xué)著作。李朝實(shí)錄中的中國史料(一)“又賜王六經(jīng)、四書、通鑒、漢書”,除此之外《大學(xué)衍義》、《性理大全》等也是賜予王庭的重要書籍。文學(xué)書籍只是在私下購買。
科舉制度下,因?yàn)榭荚嚳颇康奶厥庑枰约爱?dāng)時詩文風(fēng)氣的需求使得中國古代優(yōu)秀的文學(xué)典籍得以源源不斷的傳入朝鮮半島,并引起了眾多文人的的重視。先期的先秦典籍及《文選》、初中期的唐詩漢文、中晚期的《古文真寶》等古文大家的集子,都是在這種條件下得以在韓國古代的文人當(dāng)中快速的傳播,正是科舉制度的絕對權(quán)威促使了中國的漢文典籍在韓國古代歷史上文人中間得以快速傳播。
1.2 科舉制度對韓國古代對漢文典籍保存及回流的影響
科舉制度的實(shí)行推動了經(jīng)學(xué),性理學(xué)書籍在韓國的流傳與接受,試詩賦策等又推動了文學(xué)選集在韓國的接受,科舉詩文風(fēng)氣在一定程度上促進(jìn)了各個中國大家在韓國的接受與發(fā)展。因此科舉制度促進(jìn)了中國典籍的東傳,同時科舉制度也為韓國留存中國眾多的漢文典籍,其中不乏善本珍本。最典型的漢文典籍回流當(dāng)屬發(fā)生在宋哲宗元祐五年的下旨要求高麗王朝進(jìn)獻(xiàn)重要的漢文典籍,在索求的書目當(dāng)中,文學(xué)書籍也占有相當(dāng)大一部分,如“······《元白唱和詩》一卷、公孫羅《文選》、《揚(yáng)雄集》五卷、《班固集》十四卷、孔這《文范》一百卷、《類文》三百七十卷、《文館詞林》一千卷、《古今詩苑》、《司馬相如集》二卷、”。宋代的求書127 種,4980 余卷。其中文學(xué)書籍有十余種2000 卷左右。宋朝要求“雖卷第不足者,亦須傳寫附來”。這些書籍都是高麗朝時期保存的較完善的冊子,這些書籍的保存于科舉制度實(shí)施下的文人們重視中國典籍是分不開的,如果文人想在科舉中及第就必須經(jīng)史子集樣樣精通,因此各種書籍的保存成了上至王庭下至普通文人所必須重視的事情。這也就為漢文文學(xué)典籍能夠回流起到了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
在科舉制度的影響下,中韓兩國的文學(xué)書籍,或者是具有《文學(xué)》性質(zhì)的書籍都得以快速的流傳與接受,中國古代優(yōu)秀的文學(xué)書籍東傳為韓國古代漢文學(xué)的創(chuàng)作與發(fā)展提供了范本與導(dǎo)向,同時韓國古代對漢文文學(xué)典籍的保存又為典籍回流創(chuàng)造了條件。科舉制度促進(jìn)者兩國古代歷史上的文學(xué)書籍的交流。文學(xué)書籍的交流離不開創(chuàng)作文人的支持,因此,在科舉制度下兩國文學(xué)交流的另一個方面也不得不談及兩國文人之間的文學(xué)交流。
二、科舉制度對中韓古代文人交流的促進(jìn)作用
文學(xué)詩歌唱和是兩國文人的主要的文學(xué)交流形式。文學(xué)唱和是文人之間的重要的文學(xué)交流方式,是具有個人色彩的文學(xué)交流形式。中韓古代文人的相互酬唱是重要的文學(xué)交流,兩國文人之間筆談,次韻,這一方面顯現(xiàn)出了韓國古代文人的漢文造詣,另一方面也加深了兩國文士之間的情感。
文士之間的文學(xué)酬唱需要有幾個基礎(chǔ)性的條件,這在中韓古代文士的文學(xué)唱和中也是必須的。其一,酬唱的雙方必須要有相同的語言文字運(yùn)用及行文習(xí)慣。韓國古代通行漢字的書寫習(xí)慣,運(yùn)用漢字作文被看作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特別是在科舉制度實(shí)行以后,無論是在統(tǒng)一新羅時期 “讀書三品科”中對《論語》等儒家經(jīng)典的要求和對《文選》的重視,還是在高麗朝時期科考試中對“詩賦頌策”的重視。大量的中下階層為了能夠在科舉中及第,他們就必須學(xué)會使用漢語,學(xué)會漢文詩賦頌策等的創(chuàng)作。這樣就為兩國文士交流奠定了基礎(chǔ)的條件即共同的語言文字,共同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體裁。兩國文士都喜歡賦詩言志,因此這又為兩國文士的交流提供了唱和形式的借鑒。這些語言文字及行文習(xí)慣是架構(gòu)在科舉制度對中國文人要求的框架之下,科舉制度影響文人的創(chuàng)作,同樣也會影響到兩國文士之間的文學(xué)唱和交流。

其二,酬唱必須要有共同的理論思想基礎(chǔ)。中韓兩國古代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與儒家思想理論是密不可分的。兩國共同推行的科舉制度,在兩國的科舉史上考試科目有不同的變化,唐代尚《文選》,宋代尚古文,明清主性理學(xué),但是考試科目中一直沒有發(fā)生變化的是對儒家經(jīng)典的重視,統(tǒng)一新羅的“讀書三品科”、高麗朝的明經(jīng)科、朝鮮朝的文武科必考復(fù)試項(xiàng)目都為四書五經(jīng)。兩國都奉儒家經(jīng)典為必讀書目,這使得兩國文人之間的酬唱的理論基礎(chǔ)是架構(gòu)在儒家思想之上。儒家經(jīng)典的闡釋,儒家思想的發(fā)展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兩國文士的交流。科舉制度的使用,加大了儒家思想在文人思想中的影響。兩國文人都是在這種架構(gòu)下進(jìn)行學(xué)習(xí)和閱讀的,因此兩國的文人就有了共同的閱讀視野,共同的心理期待。兩國的文人交流有共同的立足點(diǎn),理論思想的支撐。這也推動了兩國文士間的文學(xué)唱和。
兩國的文學(xué)唱和主要表現(xiàn)在詩辭唱和、次韻上。這些詩歌唱和主要表現(xiàn)在兩國出使的文人唱和之上,最為讓人矚目的當(dāng)屬《皇華集》,一部部《皇華集》中所記述的都是兩國重要的文人之間的文學(xué)唱和之作。如《丙午皇華集》中的朱之蕃與柳根,中韓兩國的的狀元之間的文學(xué)唱和就極具典型性。朱之蕃山雨樓詩:
層樓規(guī)面是南山,朝暮生云出更還。
大溥甘霖蘇垅畝,旋添清此瀉滄灣。
浪浪夜枕孤燈炯,渺渺關(guān)途去馬間。
愛客轉(zhuǎn)嫌歸計促,雨余峰頂待躋攀。
柳根和山雨樓詩:
佳氣浮空不覓山,山形如往又如還。
平臨闤阓長安陌,俯瞰煙霞漢水灣。
雨后謾看千態(tài)變,蹲前能得幾時間。
流膏澤物皆夭賜,欲謝夭扉不可攀。
朱之蕃尚唐詩,他曾主編過《中唐十二家詩》、《晚唐十二家詩》、《唐科試詩》等,他的詩作中往往有唐音,因此在文學(xué)唱和的過程中也明顯的有尊唐的蹤跡。
再如倪謙與朝鮮文人的唱和:倪謙謁《成均館宣圣廟似同行諸君子》
曉向成均謁廟堂,杏壇弘敞碧山陽。
教典懷箕子,萬世儒宗仰素王。
濟(jì)濟(jì)衣冠忻在坐,青青衿佩喜成行。
文風(fēng)豈特覃東海,圣化于今遍八荒。
鄭麟趾讀悅謙此詩,當(dāng)即和詩《奉次高韻》:
謂圣還從入講堂,周旋笑語似春陽。
風(fēng)云氣概凌霄漢,黼傲文章佐帝王。
杜老詩情已得妙,蘭亭筆法更分行。
陪游此日真天幸,漸愧吾材拙且荒。
倪謙的詩歌贊頌了朝鮮隊(duì)箕子,以及儒家傳統(tǒng)的傳承,緬懷同學(xué)儒家文化,鄭詩則稱贊倪謙,同時也表現(xiàn)出了自身對漢儒文化,特別是遠(yuǎn)道而來的倪謙的漢文化功底的由衷的贊嘆,兩人的詩歌唱和是在共同的文學(xué)體裁,共同的思想基礎(chǔ)之上進(jìn)行的,兩人的唱和詩沒有因?yàn)槊褡宓赜虿煌懈糸u。
在《皇華集》中這樣的唱和詩非常多的。分其門類有詩,文等等。詩分四五六七以及雜言詩,文章類則有賦、小文、游記等。這些中國古代盛行的文體,在科舉制度的推動下,使得每一個韓國古代文人都耳熟能詳。他們與中國古代文人的唱和既表現(xiàn)在相同的文體意識,同時也表現(xiàn)出了相同的思想理論如在文章中,賦的創(chuàng)作與唱和又是極其重要的,在眾多的唱和作品當(dāng)中主要以吊古為主,如對箕子廟的描寫。兩國同質(zhì)的文化理論,同樣的思想架構(gòu)都在這些詩賦的創(chuàng)作中表現(xiàn)出來。
三、科舉制度對中韓古代詩文風(fēng)氣演變的促進(jìn)作用
科舉制度從誕生以來就與古代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與發(fā)展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它既推動了唐朝詩歌的發(fā)展,也成就了宋代古文的地位,同時在科舉末期也為俗文學(xué)的發(fā)展提供了堅實(shí)的創(chuàng)作基礎(chǔ)。這種影響不僅在中國古代有重要地位,在韓國古代的科舉史上也是不得不提的。科舉制度推動了兩國古代詩文風(fēng)氣的轉(zhuǎn)變,推動了兩國在文學(xué)交流上的共同的創(chuàng)作理論,創(chuàng)作依據(jù)。
對于科舉詩文風(fēng)氣對社會文學(xué)風(fēng)氣影響來說,中國的科舉制度與詩文風(fēng)氣的轉(zhuǎn)變可以大致分為三個階段:隋唐宋初的重詩賦,偏愛六朝及以前詩文,促進(jìn)了唐詩的發(fā)展繁榮;宋重古文,求文以載道,奠定了宋代古文的地位;元明清思想禁錮時期,但科舉制度卻在一定程度上促進(jìn)了小說文學(xué)的發(fā)展。而韓國古代的科舉詩文風(fēng)氣也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統(tǒng)一新羅后期,高麗中前期重《文選》詩文風(fēng)氣偏六朝及以前;高麗后期朝鮮朝前期,重古文,文以載道;朝鮮朝中晚期重朱子學(xué)說,思想禁錮。兩國古代的這些詩文風(fēng)氣的轉(zhuǎn)變都與科場詩賦創(chuàng)作的要求有直接的關(guān)系。
在統(tǒng)一新羅至高麗朝初中前期,科場,文人的創(chuàng)作多重視《文選》,科舉科目與盛唐無異,統(tǒng)一新羅時期三品中的上品是如此規(guī)定的:
“新羅元圣王四年,始定讀書出身科:讀春秋左氏傳若《禮記》、《文選》,而能通其義兼明《論語》、《孝經(jīng)》者,為上。”
在《高麗史》中記載:“三國以前,未有科舉之法,高麗太祖,首建學(xué)校,而科舉取士未遑焉。光宗用雙冀言,以科舉選士,自此文風(fēng)始興。大抵其法,頗用唐制。”
徐居正《東人詩話》卷下指出:高麗光、顯以后,文士輩出,詞賦四六,穠纖富麗,非后人所及。
這三段話都說明了在科舉制度在韓國古代的萌芽及初創(chuàng)期都效法唐朝,行唐風(fēng),詩文風(fēng)氣也大受隋唐的影響,喜四六詞賦,文辭駢儷,因此在共同的科舉詩文風(fēng)氣的導(dǎo)向下,中韓兩國在科舉先期的文學(xué)發(fā)展都表現(xiàn)出了對以《文選》為代表的六朝及以前詩文風(fēng)氣的重視,兩國的文人交往書籍交流也架構(gòu)在這一風(fēng)氣之上,科舉制度為新羅高麗前期帶來了新的詩文風(fēng)氣,促進(jìn)了其漢文學(xué)的創(chuàng)作與發(fā)展。
中國的詩文風(fēng)氣從宋朝開始和隋唐時期的華麗詩文風(fēng)氣有明顯的差別,在宋朝中后期的詩文壇中,隨著科舉考試科目以及作文規(guī)范的推動,尚古文的風(fēng)氣占據(jù)了主導(dǎo)地位,高麗中晚期也表現(xiàn)出了同樣的趨勢。對 《文選》以及對唐詩的效法使得高麗詩文越來越走向駢儷化,詩文風(fēng)氣的改變已經(jīng)到了不得不進(jìn)行的地步。李穡曾批評道:“唐風(fēng)崇律賦,流弊盛東方。音韻皆平側(cè),文章局短長”李穡對這種唐風(fēng)的批評是對詩文風(fēng)氣轉(zhuǎn)變的一種警示。因此高麗中期以后,被推崇為韓國漢詩文創(chuàng)作典范由《文選》的地位一落千丈,詩文風(fēng)氣也為之一變,由原來的華麗駢儷轉(zhuǎn)變?yōu)橹氐赖墓盼娘L(fēng)潮。從高麗武臣執(zhí)政時期后正式推動的文學(xué)轉(zhuǎn)折即從貴族文學(xué)轉(zhuǎn)變?yōu)樾屡d士大夫文學(xué)的過程中,韓愈柳宗元等唐宋八大家的詩文成為值得學(xué)習(xí)的典范。高麗文人林椿說:“幾千年出韓愈,振文章于已衰。”在高麗史金黃元列傳中有如此記述:“少登第,力學(xué)為古文,號海東第一。”崔滋《補(bǔ)閑集》(下卷)“文順會曰“囊余初見歐陽公集,愛其富,再見得佳處,至于三拱手嘆服。”徐居正《東人詩話》“高麗文士專尚東坡,每及第榜出,則人曰:‘三十三東坡出矣。’”進(jìn)入朝鮮朝之后,因統(tǒng)治者重道學(xué)而排斥詞章之學(xué),重翰藻的文選遂為有尚理尚古傾向的 《古文真寶》《文章正宗》等選本所代替。
此一段時間科舉考試詩文規(guī)范,由國家規(guī)定以及推動,韓愈、歐陽修、蘇軾等古文大家的文章文集得以在眾多的讀書人中快速的流傳,科舉的詩文風(fēng)氣也帶動了社會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風(fēng)氣,從而推動了高麗和朝鮮朝初期社會詩文風(fēng)氣的轉(zhuǎn)變。
在中韓古代科舉制度的歷史上對文學(xué)創(chuàng)作風(fēng)氣的影響上主要表現(xiàn)上述方面,當(dāng)科舉制度進(jìn)入禁錮文人思想,代圣人立言的階段,科舉制度對文學(xué)的創(chuàng)作的影響就沒有先期那么明顯,這也影響了朝鮮朝時期中韓兩國的文學(xué)及詩文風(fēng)氣轉(zhuǎn)變的交流。因此不做贅述。在科舉制度的影響下兩國文人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活動有著共同的禁區(qū),但同時兩者又有共同的創(chuàng)作素材和創(chuàng)作傾向。科舉制度對兩國文學(xué)的創(chuàng)作的影響是不可替代的。中韓兩國的文學(xué)交流與科舉制度的關(guān)系是密不可分的,科舉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加強(qiáng)了兩國的文學(xué)交流,科舉制度規(guī)定了共同的閱讀教材,使兩國文人雅士有了共同的閱讀導(dǎo)向,促進(jìn)了兩國文學(xué)書籍的交流與運(yùn)用。科舉制度要求貫徹儒家經(jīng)典思想,這使得兩國文人有了共同理論思想基礎(chǔ),推動了兩國文人在文學(xué)上的交流,在共同的儒家理想框架下的交流與唱和。科舉制度對詩文風(fēng)氣轉(zhuǎn)變的推動作用,在兩國的詩文創(chuàng)作中也有明顯的作用。總之科舉制度對中韓兩國的文學(xué)交流有著重要的促進(jìn)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