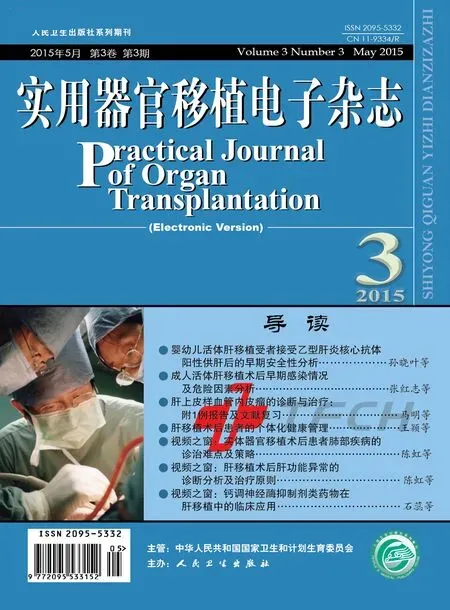肝移植術后排斥反應機制與免疫耐受
趙靜雯,唐纓(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超聲科,天津 300192)
1963年,Starzl醫生報道了第一例肝移植手術[1],此后肝移植被醫學界公認為是治療終末期肝病的有效手段。肝臟是人體最大的免疫特惠器官,原因可能與它的結構有關:肝臟具有門脈和動脈雙重血液供應系統;肝竇內皮細胞間隙大,有助于耐受宿主的免疫系統攻擊;肝臟中的Kupffer 細胞還可以吞噬抗原抗體復合物,因此肝臟具有一定程度的天然免疫耐受性[2]。但是即便如此,免疫排斥仍然是肝移植的主要并發癥,根據移植排斥反應發生的時間、強度、病理學特點及機制,可分為超急性排斥反應(hyperacute rejection)、急性排斥反應(acute rejection,AR)和慢性排斥反應(chronic rejection,CR)[3],對于移植肝的功能有著很大的影響。近年來關于器官移植術后排斥反應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這些進展與臨床應用之間尚有距離,了解移植術后的免疫排斥以及免疫耐受的機制對于研發新方法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1 肝移植排斥反應的效應機制
同種異體肝移植排斥反應的本質是一種針對異型移植抗原,即主要組織相容性復合體(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MHC)的特異性免疫應答,T細胞介導的細胞免疫應答發揮關鍵作用[4],尤其是在急性排斥反應中。初始T細胞的完全活化有賴于雙信號和細胞因子的作用,第一信號來自T細胞上的受體(T cell receptor, TCR)與MHC的特異結合,有以下3種情況[5]:① 直接識別:指TCR直接與供者抗原提呈細胞(antigen presenting cell,APC)表面的抗原肽-供者MHC分子復合物結合并產生免疫應答,這是早期AR中最常見的機制。② 半直接識別:指受者APC通過接觸供者APC或者與供者APC分泌的包裹著MHC分子的微囊泡融合的方式,將抗原肽-供者MHC分子復合物提呈給受者T細胞;間接識別是指供者移植物的細胞在經過受者APC的攝取、加工和提呈后,以抗原肽-受者MHC分子復合物的形式提呈給受者T細胞,在中晚期AR和CR反應中起重要作用。TCR特異性識別結合在MHC分子糟中的抗原肽后,在協同刺激分子的作用下,分化為具有不同功能的效應細胞,部分細胞分化成為記憶細胞[6]。
1.1 細胞免疫應答效應:初始CD4+T細胞表面受體經過特異性識別抗原肽后,激活CD4+T細胞的增殖和分化,在白細胞介素-12(IL-12)的誘導下分化為CD4+Th1輔助T細胞,Th1細胞在急性排斥反應中是主要的效應細胞,它通過產生γ-干擾素(INF-γ)等細胞因子激活巨噬細胞和中性粒細胞,導致炎性細胞浸潤和遲發型超敏反應性炎癥,造成移植肝的組織損傷[7]。除了效應T細胞的免疫作用之外,記憶T細胞(memory T cell,Tm)介導的二次免疫應答,也是造成組織損傷的一個重要因素,記憶T細胞是指對特異性抗原有記憶能力、壽命較長的T淋巴細胞,再次接受抗原刺激時可迅速活化,它對免疫抑制劑不敏感,是免疫耐受治療中的一個屏障[8]。此外,細胞毒性T細胞(cytotoxic T cell,CTL)通過釋放穿孔素以及Fas途徑殺傷組織細胞,在移植肝的損傷機制中也發揮重要作用[9]。
1.2 體液免疫應答效應:CD4+T細胞在局部微環境中所存在的不同種類細胞因子的調控下可定向分化為不同的T細胞,例如在白細胞介素-4(IL-4)細胞因子的誘導下,可分化為CD4+Th2輔助T細胞[10],Th2細胞向胞外分泌IL-4和IL-5等細胞因子,輔助B細胞的增殖與分化,促進B細胞分化為漿細胞,進一步分泌特異性抗體,通過損傷血管內皮細胞、介導血小板聚集、溶解細胞和釋放促炎性介質等機制參與排斥反應的發生[11],但一般情況下不起重要作用。
1.3 固有免疫應答效應:在以上特異性免疫排斥反應發生之前,移植肝在受者體內首先引發固有免疫應答,其誘發的因素有很多,主要是手術所致的機械性損傷以及移植肝的缺血/再灌注過程中的組織細胞損傷,這些都會引發受者的非特異性免疫應答[12]。在這些外力損傷的激活下,巨噬細胞和自然殺傷細胞(natural killer,NK)發生一系列應激反應,繼發“瀑布式”炎性反應,導致移植肝組織細胞發生炎癥、損傷和死亡[13]。
2 肝移植排斥反應的特點
超急性排異反應指移植術后24小時之內發生的排異,是由抗體-補體介導的體液性免疫反應,大多見于ABO相容性肝移植或反復輸血的個體,組織學表現為移植肝血管內皮損傷,肝竇中可見中性粒細胞浸潤,纖維蛋白沉淀和血小板聚集,形成血栓,使器官發生不可逆性缺血、變性和壞死[14]。
急性排斥反應是最常見的一類排斥反應,一般出現在術后2周左右。主要臨床表現有發熱、煩躁、局部壓痛、膽汁稀薄、血清總膽紅素、轉氨酶和IL-2受體升高等,但是這些表現并不是排斥反應所特有的,因此,病理檢查結果是診斷排斥反應的“金標準”[15]。急性排斥反應在組織學上最具特征性的病理改變有3個,即匯管區細胞浸潤、內皮炎和膽管損傷,又稱為“三聯征”:① 匯管區炎性細胞浸潤,以大量淋巴細胞浸潤為主,以及不等量中性粒細胞與嗜酸粒細胞浸潤;② 門靜脈和(或)中央靜脈內皮細胞下的淋巴細胞浸潤;③ 膽管損傷,炎細胞侵入膽管上皮內,使膽管上皮細胞變性、凋亡。其中,內皮炎是最重要的診斷特征,嚴重的排異反應可累及肝細胞及肝小葉出現局灶壞死,甚至中央靜脈周圍肝細胞壞死[16]。臨床上急性排異反應的明確診斷是依據1997年頒布的Banff分級評分標準,按照以上“三聯征”計分的總和將急性排異反應分為輕、中、重度[17]。
慢性排斥反應多繼發于急性排斥反應的反復發作,發生于移植術后數周、數月甚至數年,其組織病理學特點[18]:① 肝內小膽管明顯減少或消失;② 中央靜脈周圍肝細胞膽汁淤滯、氣球樣變性、脫失及壞死。③ 匯管區纖維化,同時浸潤的炎細胞逐漸減少;④ 排異性動脈病變,動脈內皮受到免疫損傷,脂質沉積于內皮下,使動脈管腔狹窄或閉塞。慢性排斥反應對免疫抑制療法不敏感,是影響移植肝長期存活的主要原因[19]。
3 肝移植術后免疫抑制治療及免疫耐受機制
臨床上對于肝移植術后免疫抑制治療方案的基本原則是在術后早期聯合用藥,依據藥物作用方式和毒性的不同,使每種藥物達到最低的有效濃度。目前,免疫抑制藥物有以下幾類[20]:① 神經鈣蛋白抑制劑,代表藥物有環孢素A和他克莫司(FK506)。其作用原理是通過阻斷鈣調磷酸酶使IL-2基因不能正常轉錄翻譯而發揮免疫抑制作用,IL-2作為T細胞自分泌生長因子,其轉錄對于T細胞的活化是必需的,通過減少IL-2的生成,可以有效預防免疫排斥的發生。② 抗代謝藥物,代表藥物有嗎替麥考酚酯和硫唑嘌呤。作用原理是通過抑制DNA的合成,從而抑制B細胞和T細胞的增殖。③ 全身性免疫抑制劑,主要指皮質激素如地塞米松,是非特異性的抗炎藥物,由于其廣泛的不良反應,一般作為維持用藥而不長期使用[21]。④ TOR抑制劑雷帕霉素,它通過阻斷信號傳導通路抑制T淋巴細胞增殖,與FK506相比,優勢在于可以阻斷鈣依賴性以及非鈣依賴性的信號傳導通路,且對于腎臟的毒性更低[22]。⑤ 抗淋巴細胞抗體,包括單克隆抗體及多克隆抗體,這種生物性抑制劑可以特異性靶向免疫相關淋巴細胞,從而減少了對非免疫系統的損害,在輔助誘導免疫耐受和免疫抑制方面具有廣闊的前景[23]。
除了免疫抑制藥物的治療作用外,機體自身還會表現出一定的免疫耐受,研究其中的機制及影響因素對于研發出靶作用更強、副作用更小的免疫抑制劑有著重要的意義[24]。調節性T細胞(regulatory T cells,Tregs)是CD4+T細胞在轉化生長因子-β(TGF-β)等細胞因子的誘導下分化成的一種T細胞,具有免疫無能性及免疫抑制性。Treg通過分泌細胞因子或者細胞接觸兩種方式發揮免疫調節作用,抑制自身反應性T細胞應答,在維持免疫耐受中發揮重要作用。這種T細胞表面除了表達CD4+CD25+外還有核轉錄因子Foxp3,它的組成性表達是Treg不受活化狀態影響的標志性分子,也是發揮功能的前提條件[25-26]。Demirkiran 等[27]研究表明,在肝移植術后發生急性排斥反應的患者體內循環的CD4+CD25+Treg的數量較未發生排斥的患者低,表明提高受者Treg的數量有利于移植肝的生存,He等[28]的研究結果也支持了這一論點。因此,Treg細胞有可能成為診斷或發現肝移植術后急性排斥反應發生的有效指標。
CD4+T細胞除了可分化為Th1、Th2以及Treg細胞之外,它還可在IL-6及IL-1β的誘導下分化為Th17細胞。有研究表明[29],Th1和Th17細胞與免疫排斥有關,而Th2細胞與免疫耐受有關,Th1/Th2向Th2漂移可以誘導肝移植后的免疫耐受。但Zhang等[30]人在小鼠上的研究結果顯示,Th1/Th2向Th2偏移與免疫耐受并無關系。近年來的研究逐漸將關注點移向Th17/Treg,免疫排斥還是免疫耐受取決于Th17和Treg的平衡[31-32]。Th17細胞在TGF-β等因子的存在下促使初始T細胞活化,在機體內起到免疫促進的作用,而Treg是抑制免疫細胞毒作用的關鍵,它們之間的關系密切而復雜[33]。Treg可以促使CD4+T細胞向Th17細胞分化,也可以在IL-2和IL-1β的誘導下以自我轉化的方式形成Th17細胞,而Th17在某些情況下受Treg的調控[34]。初始T細胞的定向分化取決于T細胞激活的微環境,這就提示我們可以通過抑制IL-6、TNF-α、TGF-β以及INF-γ這些細胞因子來實現移植肝的免疫耐受。
盡管免疫抑制劑的使用延長了移植受者的生存時間,但是這些藥物均具有一定的毒副作用,因此,誘導受者產生針對移植肝的免疫耐受是徹底克服移植排斥反應的理想策略,并已成為移植免疫學研究領域最富挑戰性的課題之一。目前尚在實驗研究中的免疫耐受方案有阻斷T細胞識別抗原后活化所需的共刺激信號,誘導T細胞失能、過繼輸注Treg細胞、定向調控輔助T細胞亞群的分化以及造血干細胞移植等[35-39]。
經過多年的發展,肝移植術后免疫排斥反應的研究機制越來越清楚,藥物選擇越來越廣泛,誘導免疫耐受的研究也越來越豐富,但實際應用于臨床上的有效方法還很少。如何在理論的基礎上開展有益于患者的臨床研究仍然是今后工作的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