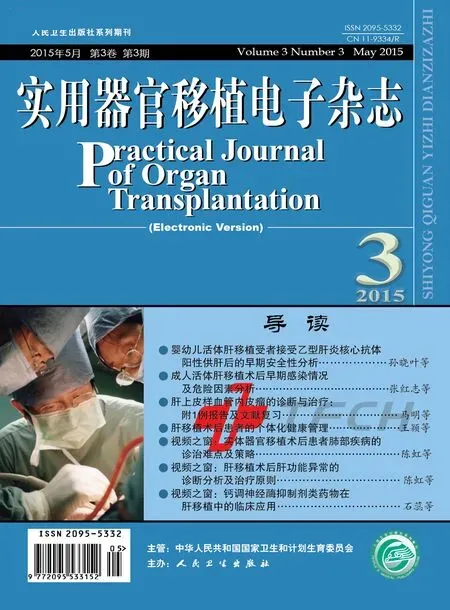成人活體肝移植術后早期感染情況及危險因素分析
張紅志,陳凡,高偉,馬楠,王凱,徐彥貴(.天津中醫藥大學研究生院,天津 009;.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藥劑科,天津 009;.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器官移植中心,天津 009)
感染是肝移植術后繼排斥反應之后的第二大并發癥,亦是引起移植物功能不全、功能喪失及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1-2]。肝移植術后早期大劑量糖皮質激素和鈣調磷酸酶抑制劑(CNI)等免疫抑制劑的使用,雖然預防了排異反應的發生,卻增加了肝移植受體發生感染的危險[3]。了解肝移植術后早期感染發生的相關危險因素,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對改善患者預后及提高生存率有重要意義。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收集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2008年4月至2014年1月出院的所有行肝移植術的資料,將其中術后30天內感染患者歸為試驗組,未感染者為對照組。
感染診斷標準:遵循美國疾病控制中心關于院內感染的診斷定義[4];其余以檢查報告單為準。
1.2 方法
1.2.1 高危因素的確定:查閱相關文獻,匯總所有可能的危險因素[5-7],將危險因素歸納為術前因素、術中因素、術后因素。通過記錄患者基本情況、存在高危因素情況、感染情況(出現感染的時間、細菌培養結果、藥敏結果、感染部位)等,建立紙質數據調查表,錄入Excel 2010,將高危因素作為自變量X(有記為1,無記為0),是否感染作為因變量Y(感染記為1,未感染記為0)。
1.2.2 統計學方法:應用SPSS 19.0軟件進行統計學處理,其中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高危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歸分析,以優勢比(OR)和95%可信區間(95%CI)表示。根據單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將P<0.05的因素納入Logistic回歸方程,再進行多因素分析,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 果
2.1 患者基本情況:本研究共納入患者143例,其中男性115例,占80.41%,女性28例,占19.59%。試驗組27例,平均(45.11±9.08)歲;對照組116例,平均(45.76±8.22)歲。兩組患者年齡、性別、終末期肝病模型評分(MELD)、移植物受體體重比(GRWR)等基本情況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均P>0.05)。
2.2 感染部位和病原菌:肺部感染18例,其中肺炎克雷伯菌4例,葡萄球菌和(或)念珠菌9例,銅綠假單胞菌2例,鮑曼不動桿菌1例,嗜麥芽菌1例;膽道感染5例,其中念珠菌1例,大腸埃希菌1例;葡萄球菌2例,糞腸球菌1例;腹腔感染4例,其中糞腸球菌2例,耐甲氧西林金黃色葡萄球菌(MRSA)和銅綠假單胞菌1例,大腸埃希菌1例;自發腹膜炎1例。感染發生平均時間:肺部感染9.33天,膽道感染11天,腹腔感染7.5天。
2.3 高危因素統計結果(表1):在所納入的高危因素中,手術過程中大量失血、術后重癥監護病房(ICU)留置時間過長及術后腸外營養時間過長是本院器官移植中心成人活體肝移植術后30天內發生感染的獨立危險因素。
3 討 論
移植術后感染是肝移植患者最常見的嚴重并發癥,由于術后早期應用免疫抑制劑尤其是大劑量糖皮質激素預防排斥反應,使得患者易發感染[3]。自從Thomas Starzl博士于1963年在美國實施了世界上第一例人體原位肝移植手術,實體器官移植至今已有50余年之久。我國臨床肝移植也于20世紀80年代興起。進入90年代,包括我國在內的全球臨床肝移植進入成熟階段,這得益于新型免疫抑制劑、器官保存液及新型的肝移植手術方式的涌現[8]。但是,術后感染,尤其是術后30天是感染的高發期,在這個時期盡量降低感染的發生可以大大提高手術成功率。
本研究發現,感染部位以肺部感染最為常見,常見病原菌為葡萄球菌,這與Hara T等[9]最新報道相同。此外,我們的研究同樣出現了真菌感染病例,這與真菌感染多發于術后1個月內的文獻報道吻合[10]。多因素回歸分析結果顯示,術中大量失血、術后ICU留置時間過長是術后30天內發生感染的獨立危險因素,與既往文獻報道基本一致。但腸外營養時間過長是本次調查新發現的獨立危險因素,單純腸外營養導致腸壁通透性異常、腸道菌群失調、細菌移位,這些因素造成腸源性感染率增加,進而損害機體的免疫功能。此外,術后ICU留置時間的OR值為1.702,提示該因素可能不是重要影響因素,可能與我們本次研究納入的樣本量較小相關,這有待于進一步擴大樣本量研究。

表1 各種危險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統計結果表
結合本次回顧性病例研究發現,為降低臨床活體肝移植術后早期感染的發生率,應盡量減少術中失血量,縮短術后ICU留置時間和術后腸外營養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