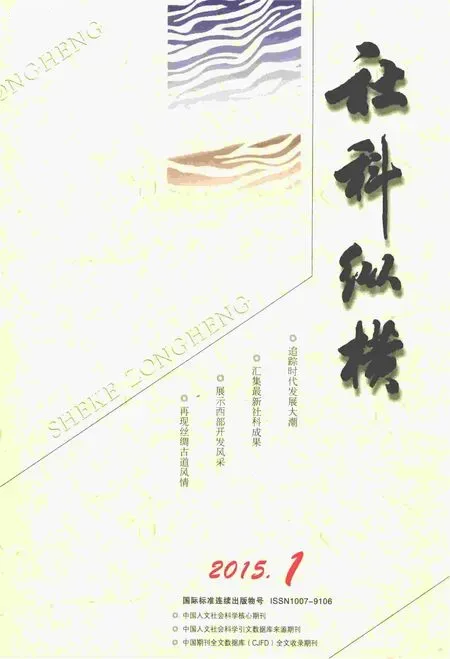論基層公務員行政行為選擇的政治生態邏輯
羊許益
(保山學院政治學院 云南 保山 678000)
一、政治生態:概念的闡述
(一)政治生態理論與政治生態環境
政治生態理論是用生態學的觀點和方法研究社會政治現象及環境關系的一種理論和方法。政治生態學借助生態學的方法,從政治與其環境的相互關系中研究政治現象的產生與發展以及探求某種政治現象之所以具有某種特性的環境原因。[1]此外,政治生態理論還試圖對政治如何才能實現生態化發展進行探討,尋求政治的生態化道路,以實現生態化的政治理論思想。政治生態理論的目的在于揭示政治發展的生態學路徑也承擔著為現實社會政治實踐提供理論參考和導引的學術責任。從研究對象上看,政治生態理論與一般政治學無異,仍以政治現象及其規律為研究旨歸。不同的地方在于政治生態理論把政治體系放到社會環境乃至自然環境這一更為廣闊的背景下,予以整體性、系統性考察,也即借鑒生態學的觀點和方法,研究政治體系與社會環境的實然性互動關系,以及這種互動關系,生態化發展的應然狀態。
政治生態環境是相對自然生態、經濟秩序而言的一種社會政治狀態,是一個地方政治生活現狀以及政治發展環境的反映,是黨風、政風、社會風氣的綜合體現。政治生態環境由政策環境、法治環境、輿論環境和廉政環境等構成,直接體現在干部的精神狀態和工作作風上。[2]
(二)政治生態的兩個基點
1.支配公務員行政行為過程的政治文化
1956年,美國政治學家阿爾蒙德提出了“政治文化”的概念。60年代,政治文化成為西方尤其是美國政治學者研究的重要對象之一。一般認為,政治文化屬于政治社會的精神范疇,是指一個社會關于政治體系和政治問題的態度、信念、情感和價值的總體取向。政治文化支配著公務員的行政行為,在任何社會中都“不只是漫無目標的聚合,而是代表著共同適合和相互加強的內在模式,在任何具體的共同體中都存在著一種有限的、不同的政治文化,它賦予政治過程以意義、預見性和形式,每個人必須根據其自己的歷史關系學習關于其人民和共同體之政治的知識與感情,并且并入其自己的個性之中”[3]。事實上,我國歷史積淀下來的諸如集權政治、無限政府、官僚政治、人情政治等傳統政治文化,至今仍在很大程度上支配著我國行政人員的行政行為過程。
2.影響公務員具體行政行為選擇的行政倫理
行政倫理即行政道德,是以“責權利”的統一為基礎、以協調個人、組織和社會的關系為核心目標的行政行為準則和基本規范。行政倫理是行政管理過程中的角色倫理,即行政人員在具體行政行為選擇中所應具有的價值取向和行為規范,主要涉及行政主體實施具體行政行為的正當性與合理性,亦即領導、決策、指揮、執行、協調和控制等行政活動的合法性問題。作為行政主體的基層公務員在履行行政職責過程中必然會面臨行政行為的倫理選擇,公務員的行政行為選擇往往與其責任心、榮譽感、道德修養和道德作風等相關聯;由于行政倫理價值觀念的不同,即使所處的境遇完全一樣,不同的公務員可能作出不同甚至相反的選擇。
二、政治生態環境:基層公務員行政行為選擇的邏輯起點
(一)市場環境下行政行為的向度
市場化進程對政治生態的影響主要表現為兩組沖突:一是市場化與政府自我擴張的沖突。二是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的沖突。
政府行為應堅持公共性的價值取向,并以公共性作為其根本屬性。正如洛克所指出的:“都只是為了公共福利”(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政府論》第4頁),這是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基礎。所以,政府作為公共利益的代理人,其效用目標應該是也只能是公共效用的最大化。但毋庸諱言,政府自利性是一個無法否認的事實存在,在市場化進程中,政府自利性更為凸顯,行政主體也與市場主體一樣以實現個人效用的最大化作為行政行為選擇的根本原則。市場經濟的一般特征決定了市場具有無限擴張的特性,而政府作為權力的擁有者又具有自我擴張的傾向。如果政府的權力過大,就可能將擴展權力尋租空間作為自身追求;政府與市場的博弈必然導致政治生態環境的惡化。
在市場化進程中的政府環境里,基層公務員不斷在政治人與經濟人、社會人的角色中轉換,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的嚴格區分也變得困難。在國家權力賦予的保證下,在合法范圍內,政府與市場發生交換,既保證能從社會獲取維持自身所需的資源,又向社會提供社會所需的公共資源。在這個過程中,基層公務員是帶有政治烙印的政府細胞,承擔著履行職業職責的義務。同時,基層公務員作為一個社會人,以個人身份同樣在市場經濟中以一個普通“經濟人”的身份出現,與市場進行著不斷的交換。基于“經濟人”的假設,獨立的個人有其自己的利益,公共利益就根本不存在。公共選擇學派對行政官僚的分析認為,官僚不是圣人,是有私心的個人利益追求者,他們像普通人一樣有權力欲和金錢欲,且由于個人私利的不同,一個中心單一的官僚權力機構不可能總為全民的利益著想。[4]基層公務員作為官僚機構的一部分,他們也有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傾向,我們當然不能否認其正當合法的利益追求;但基層公務員畢竟是公共權力的擁有者,如果不加約束,他們在運用國家權力實施行政行為時就可能會選擇“權力的商品化”,通過“搭便車”謀取個人私利就無法避免;為了追求效益的最大化,他們往往成為“權力攀登者”,在其價值結構中,首先考慮的是權力、收入、和聲望。[5]
(二)制度環境下行政倫理的向度
制度環境對于政治生態的影響不言而喻,制度文明本身就是政治生態環境良性發展的重要內容。亞里士多德曾在《政治學》中說到“要理解政體(或政治制度),我們就必須研究政府(城邦)的本質”,“政體之所以存在各種不同的類型,其原因就在于每一個城邦具有不同部分和不同要素,例如平民大眾和貴要階層的差別。所謂政體就是對不同官職的安排;在城邦的不同部分之間有多少種官職安排就有多少種政體。”[6]探討政治體制對制度環境的影響離不開對民主問題的思考,從政治生態學的理論來看,依據人類當代政治實踐活動規則取向,民主規則已成為政治制度的共同選擇。民主是什么?民主就是國家與社會關系的合民意性選擇,以及對這種選擇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與任何替代性方案相比,民主實質上能夠在更大程度上提供一個和平有序的制度環境,基于此,多數公民能夠促使政府去做他們最希望政府去做的事情,并避免去做他們最不希望政府去做的事情。毋庸諱言,這只是一種應然;由于政治體制的影響,民主在當下中國政治生態中尚未成為基本價值。
民主缺失的制度環境不可避免地導致自由裁量權的濫用。自由裁量權存在,既是對行政人員理智和良知的肯定,更是對其行政能力與行政倫理的挑戰。自由裁量權對行政倫理的挑戰。在公共行政實踐中,行政人員的自由裁量權的廣泛存在并不斷擴展,這對行政人員的行政倫理提出了很高要求。在傳統的公共行政中,公共行政人員只需要中立地、嚴格地適用法律、執行政策,也就不可能存在自由裁量權。但由于現代公共行政所面臨事務的多元性、復雜性,一般的、概括性的法律和制度不可能完備地規定出行政活動的每一個方面,也不可能準確地預見到公共行政領城的可能變化。因此實際上公共行政活動中是存在自由裁量的彈性空間的。這就使行政自由裁量權的存在具有了某種正當性。但是,自由裁量權能否得到正確行使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行政人員的個人行政責任和道德,在民主缺失、監督缺位的制度環境下,自由裁量權往往淪為權力尋租的有效工具。
三、凈化政治生態:基層公務員行政行為選擇困境的破解
(一)正確的群眾觀、權力觀:凈化政治生態內部環境
1.樹立正確的群眾觀,將群眾作為我們工作價值的最高裁決者
群眾觀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核心。毛澤東遵循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明確指出:“我們共產黨人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標志,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系。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7]江澤民進一步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我們工作價值的最高裁決者。”[8]因此,基層公務員應樹立正確的群眾觀,將群眾而不是領導作為自己工作價值的最高裁決者,將著力解決民生問題、維護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作為行政行為選擇的基本準則。
2.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將人民滿意作為行使權力的根本標準
馬克思主義認為,公共權力在本質上來源于人民,只不過人民又以一定的方式把這種屬于人民的權力授給了政府,再由政府使用人民授予的公共權力來解決公共問題,而政府工作人員則不過是公共權力的具體行使者。而現實中,很多公務員認為權力是上級給的,想問題、辦事情不怕群眾不滿意,只怕領導不注意,逢迎拍馬、唯上是從;或者認為權力來源于個人努力、個人奮斗,把“有權不用、過期作廢”奉為信條,濫用權力甚至以權謀私。這些思想和行為同馬克思主義權力觀是背道而馳的。如果奉行這樣的權力觀,不可能不出問題、不犯錯誤。福柯認為,在現代社會中,權力并不是掌握在某一個人、某一集團或某一階級中,它不是占有的對象。誠然,任何權力被個人或組織掌握后,都會通過權力的運作謀取特定的利益;但國家的一切權力來源于人民,基層公務員要“把人民群眾滿意作為行使權力的根本標準”[9],要通過權力的運作為人民群眾而不是自己謀取特定利益,真正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
(二)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凈化政治生態外部環境
1.處理好市場與政府的關系,明確政府權力的邊界
政治權力總是試圖跨入經濟領域,經濟領域也試圖腐蝕政治體系。這對當前的政府行為方式提出了嚴峻的考驗,在當前的政治生態環境背景下,科學的政府行為方式,必須構建于新型的政府行為理念和行為方式之中。具體而言,要把主體中心主義轉化為客體中心主義、把權力中心主義轉化為服務中心主義、把個人利益中心主義轉化為公共利益中心主義,政府應承擔為市場和企業提供服務和信息、協調社會秩序的角色,不是單向度的考慮政府行為效率,而是把效率的提升放在行政成本投入降低的雙向度的思考之中,要由以往的直接控制、直接經營轉變為以間接調控為主的管理模式。尤其是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市場各元素的多元化,大大加大了政府政策的試錯成本,明確政府權力的邊界,加快由政府管理向政府治理的轉變勢在必行。
2.科學設定行政自由裁量權的運行邊界
要防止行政自由裁量權的濫用,避免行政人員根據個人好惡進行選擇性執法,就要根據“行政合理性”和“行政合法性”兩個基本原則明確行使自由裁量權的法定標準和范圍,科學設定行政自由裁量權的運行邊界。根據亞里斯多德的觀點,法律的精神、法律的原則就是行政自由裁量權合理運行的邊界,即行政人員自由裁量權必須控制在法律精神和原則的范圍內,在此范圍內才可以酌情自由地處理行政事務。自由裁量權的出發點和歸宿是為了維護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實現社會公平正義。行政自由裁量權僅僅是對既存法律的救濟,行政人員行使自由裁量權僅僅是為了彌補法律規定與現實實踐之間的“縫隙”。基于此,一方面,我國應對現有的行政法律、法規進行相應的清理、修訂,把過量的彈性條款的模糊概念具體化、明確化,涉及公民權利義務的領域應盡量減小裁量的自由度,對裁量度較大的規范應根據相關的情節等劃定不同的檔次,對適用條件上的彈性規定應做進一步細化,在確實需要留有較大自由裁量空間的地方也要制定明確的條款,使行政主體在實施行政行為時依據立法的精神而為。另一方面,我國要進一步完善對行政自由裁量權的司法控制制度,對逾越或濫用自由裁量權的行為進行司法審查。
[1]劉京希.政治生態論——政治發展的生態學考察[M].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7:8.
[2]盧西安·派伊,西尼·維伯編.政治文化有政治發展[M].美國新澤西州: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65:7.
[3]丁忠甫,鄭林.反腐倡廉,構建和諧政治生態環境[J].云南行政學院學報,2010(4).
[4]藍志勇.行政官僚與現代社會[M].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3:28.
[5]安東尼·唐斯著.行政官僚制內幕[M].郭小聰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89.
[6]亞里士多德著.政治學[M].高文書譯.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209.
[7]毛澤東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31,1094.
[8]江澤民.論黨的建設[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181.
[9]習近平.領導干部要樹立正確的世界觀權力觀事業觀[J].中國黨政干部論壇,2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