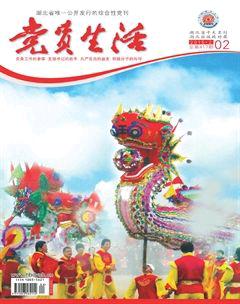文化“李向陽”
肖華良 孫苗 薛繼偉 張燕萍
電影《平原游擊隊》里,有位曾經家喻戶曉的抗日英雄李向陽。如今在咸寧,文化“李向陽”也是遠近聞名。他,就是市委黨校常務副校長李城外。
文化“李向陽”,是省委書記李鴻忠對他的親切稱呼。因為,20年來,李城外的業余時間,幾乎全花在對向陽湖的研究和宣傳上。
向陽湖位于咸寧市郊,是斧頭湖的一個湖汊。1969年圍湖造田后,向陽湖變身為一個典型的江南魚米鄉。
真正讓向陽湖載入史冊的,還是隨后在這兒開辦的“五七”干校。1969年至1974年,文化部及其下屬單位6000多人陸續被下放到此勞動改造。其中有文化部領導干部,但更多的是作家、書畫家、文博專家和電影工作者等,如冰心、沈從文、臧克家、蕭乾、張光年、周巍峙、馮雪峰、郭小川、馮牧、王世襄、周汝昌……
1994年,擔任咸寧地委領導秘書的李城外,在瀏覽地方志時,偶然了解到這段歷史,內心深處波瀾驟起。他覺得,這批文化大家能和向陽湖聯系在一起,就是咸寧的幸運和驕傲。“文化大革命”要否定,可“五七”干校畢竟是一段抹不掉的印痕,不能讓它湮滅在歷史的煙波中。李城外的心底,頓時升騰起一份神圣的使命感,他要在向陽湖中打撈歷史的記憶!從此,李城外的人生有了新的航向。
1995年春,李城外利用進京出差的空隙,登門拜訪了詩翁臧克家。當時臧老已90高齡,為身體健康著想,家人婉拒了很多采訪。聽說李城外來自咸寧,才破例應允。采訪前,李城外做足了功課,臧老的《憶向陽》等詩歌他倒背如流。采訪進行了一下午,兩人相談甚歡。
此后3年,李城外陸續采訪了200多位文化人。有時一天之內要跑五六個地方,甚至凌晨兩三點,他還懷揣錄音機,身背照相機,奔走在京城的大街小巷。
最奇特的一次經歷莫過于采訪畫家顧樸。顧老天生不能說話,采訪時,各人面前放一摞紙,你在紙上問,我在紙上答。整整3個小時,房間里一片寂靜。
其實,向陽湖的6年,是很多人內心深處不愿回首的痛楚。每遇這種情形,李城外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原國家新聞出版署署長宋木文便是其中之一。1996年5月李城外求訪時,宋老不情愿寫稿,他覺得“怎么寫都很難寫出有積極意義的東西”。13年后,當李城外再次邀請他參加向陽湖文化人聯誼會時,宋老不再推辭。他說:“李城外10多年來的堅持令人敬佩,他的執著精神使我逐漸轉變了態度”。2010年,宋老特地為李城外的叢書撰寫了總序。
鑒于這批人大多年事已高,李城外形容自己的采訪是“與時間賽跑”。至今,他已親身采訪四五百位文化名人,整理了數百萬字的文稿,留下大量珍貴的錄音錄像資料和照片。為了宣傳向陽湖文化,李城外在國內多家媒體開設專欄,發表人物專訪100多篇。著名學者任繼愈先生認為:“后來人如寫文化大革命史的‘儒林傳’,這是一批極珍貴的第一手資料,此種野史的真實性或為正史所不及。”
2000年春,38歲的李城外走上了正縣職領導崗位。不過,他所去的地方是咸寧市政協。有人為他的“仕途”惋惜,他卻不以為然。他說:“我熱愛文史工作,只要有利于向陽湖的研究,我都愿意去。”之后,他又相繼擔任了市新聞出版局局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直到現在任職于市委黨校。
對于李城外的“不務正業”,有些同事不太理解,有冷嘲熱諷的,也有好心規勸的。1999年冬,李城外與一位市委領導坦率交流了思想。市領導認為,“這是一段辛酸的歷史,不值得過于張揚。從政治經濟角度看,對咸寧正面的作用不大。比如遼寧并不宣傳干校,江西并不宣傳共大。”不過,他十分欣賞李城外的文筆和敬業精神,對他的研究“既不肯定,也不否定”。
李城外的妻子是市中心醫院一名新生兒科專家,對于丈夫的選擇,她倒是始終如一地支持。20年間,家里的大小事務多半是她操持。遇到丈夫忙的時候,她還會搭一把手,發動兒子一起粘信封、貼郵票,把剛發表的作品復印后寄給北京的文化名人。
1996年11月,廣東一家報紙刊發了南京青年博士王彬彬《還有什么不能賣》的文章,指責李城外“拿文化人的苦難作賣點”。李城外連寫了《還有膚淺不能賣》《還有粗野不能賣》《還有偏激不能賣》3篇評論予以反駁。隨著《羊城晚報》《收獲》《文學報》《文學自由談》等多家媒體的介入,這場轟動全國文化界的“向陽湖風波”被寫進了新華社《內參》。
論戰平息后,李城外反倒吸引了更多人的目光。1997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李城外編著的《向陽情結》和《向陽湖文化人采風》。這是我國第一部綜合反映“五七”干校生活的回憶錄和散文集。2010年12月,《人民畫報》辟出30個頁碼,隆重推出“重返向陽湖”專題。同年,“向陽湖文化叢書”出版。這套叢書共7本,300余萬字,其中《話說向陽湖》獲“冰心散文獎”,并被翻譯成日文發行海外。近年來,不少日本、德國、美國的學者專程到咸寧實地考察,請教有關文革和“五七”干校研究的問題。
李城外幾乎成了向陽湖的“度娘”,方圓幾十公里沒有他不知曉的:馮雪峰在哪兒放過鴨子,王世襄在哪兒捕過魚,沈從文在哪兒看過果園,司徒慧敏在哪兒挑過糞,他都一清二楚;紅旗橋從什么角度拍好看,五七橋是哪些人修建的,誰和誰住過同一間房子,他都爛熟于心。每當有外地人來,他必實地導游。
李城外透露,省向陽湖文化研究會就設在咸寧市委黨校,參與者與日俱增,現有博士3名,碩士10余名。電大畢業的他,任武漢大學兼職教授和省委黨校碩士生導師,空余時間常應邀到全國各地講學。
采訪期間,李城外邀請記者參觀他的“五七干校資料收藏館”。100多個書柜、5萬冊藏書,構成了他的私人館藏“向陽軒”。如此之大的規模,若非親眼所見,實在不敢相信。信步其中,有一個房間尤為特別,里面擺放著主人多年來四處收集的文化名人資料和實物,如蕭乾的部分手稿和二戰時在西歐戰場上當記者用過的皮箱。李城外自豪地說:“國內現有上千所‘五七’干校,各省有代表性的我基本上都去過了。‘五七’干校史料,沒有哪個單位比我收藏得更全了。有人說,文革發生在中國研究在國外,但‘五七’干校的研究在湖北,在咸寧。”
2011年10月底,省委書記李鴻忠來到向陽湖,仔細察看了過去的珍貴史料、照片和實物展示,對李城外的研究成果贊賞有加,連聲稱他是“文化李向陽”。李鴻忠說,這么多文化名人在特定的歷史時期集中在一個地方,在全國乃至全世界都很少見。向陽湖文化是咸寧獨一無二、不可多得的歷史文化遺產。要按照“文史農旅”相結合的思路,繼續搞好保護和開發工作。
經過多方努力,呼吁開發向陽湖的提案和議案進入全國“兩會”。2013年5月,“向陽湖文化名人舊址”終于被國務院列入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站在干校舊址,李城外感慨萬分:“這是全國第一個被列為國保的‘五七’干校,也是共和國最年輕的文物保護單位啊!”
向陽湖文化名人舊址核心區,坐落在一片地勢開闊的高地上,24棟紅磚砌成的平房,全是北方樣式,仿故宮建筑。這里的一磚一瓦,都是當年“五七”戰士們親手燒制的,房頂的每片紅瓦上,還印有“五七干校磚瓦廠”字樣。據咸安區委組織部部長黃建平介紹,這幾年,按照李鴻忠書記的指示,市區政府已制訂了整體保護與開發的規劃,原先住在舊址里的村民已全部搬出,通往市區的道路業已動工,一座占地2000平方米的博物館也呼之欲出……
向陽湖,一群文化人的集體記憶,一代知識分子的精神家園。不久的將來,它會散發出更加獨特的魅力,吸引無數的后來者去追懷和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