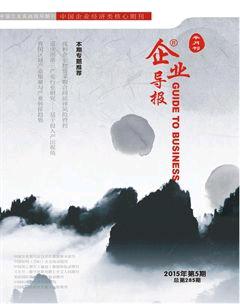簡(jiǎn)論廢名的“趣味”觀及其文體表現(xiàn)
何三三
摘 要:趣味主義作為前期京派文人的生存方略,不僅體現(xiàn)在其文學(xué)觀念,更影響到其文學(xué)創(chuàng)作實(shí)踐。周作人是趣味主義的倡導(dǎo)者與先行者,而廢名則是其趣味主義宗旨的積極響應(yīng)者,他以其獨(dú)特的文風(fēng)實(shí)踐著這一文學(xué)理念,并從中外文學(xué)里“涵養(yǎng)他的趣味”,具化為其“簡(jiǎn)潔生辣”的文體風(fēng)格。
關(guān)鍵詞:趣味主義;廢名;前期京派文人
一
以個(gè)性主義為核心的趣味主義作為前期京派群體文化生存方略,一定程度上構(gòu)成了這一文化群體幾乎全部文學(xué)觀念及其創(chuàng)作實(shí)踐所追求的藝術(shù)宗旨。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史上,真正把趣味主義作為一種審美意向和藝術(shù)理念加以提倡并徹底貫串于生活實(shí)踐和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的人,周作人要算是第一個(gè)。事實(shí)上,“作為群體心態(tài)和具有相似性的文學(xué)認(rèn)知,周作人常用‘趣味二字概括他(或他所屬的群體)對(duì)文學(xué)本質(zhì)的理解。”然而,“對(duì)于批評(píng)家來(lái)說(shuō),這顯然已不是傳統(tǒng)文學(xué)認(rèn)知范疇中的所謂‘趣味,而是一種具有現(xiàn)代否定性文化認(rèn)知特征的‘趣味主義”,因此,“在現(xiàn)代文學(xué)(文化)史上不可避免地要被視為一種具有消極價(jià)值取向的自由主義文學(xué)(文化)形態(tài)”。
周作人以這種個(gè)人主義而趣味主義的創(chuàng)作旨趣和審美心態(tài)影響了整個(gè)《駱駝草》時(shí)期的前期京派文人群。《駱駝草》是前期京派的一塊主要陣地,也是前期京派文學(xué)走向成熟時(shí)期的產(chǎn)物。在談到周作人的“趣味”性及其影響力時(shí),沈從文曾有過(guò)這樣的論述:“在路旁小小池沼負(fù)手閑行,對(duì)螢火出神,為小孩子哭鬧感到生命悅樂(lè)與糾紛,那種紳士有閑心情,完全為他人所無(wú)已企及。”就廢名而言,沈從文認(rèn)為,“用平靜的心,感受一切大千世界的動(dòng)靜,從為平常眼睛所疏忽處看出動(dòng)靜的美,用略見(jiàn)矜持的情感去接近這一切,在中國(guó)新興文學(xué)十年來(lái),作者所表現(xiàn)的僧侶模樣領(lǐng)會(huì)世情的人格,無(wú)一個(gè)人有與周先生面目相似處”。“五四”以來(lái),周作人“以清淡樸訥文字,原始的單純,素描的美,支配了一時(shí)代一些人的文學(xué)趣味,直到現(xiàn)在還有不可動(dòng)搖的勢(shì)力”,并且“儼然成一特殊風(fēng)格”。
二
在《駱駝草》同仁中,廢名無(wú)疑是趣味主義這一藝術(shù)宗旨的積極響應(yīng)者。對(duì)此,沈從文當(dāng)年做過(guò)這樣中肯的論述:“馮文炳君作品,所顯現(xiàn)的趣味,是周先生的趣味”,“對(duì)周先生的嗜好,有所影響,成為馮文炳君的作品成立的原素”,而“用同樣的眼,同樣的心,周先生在一切纖細(xì)處生出驚訝的愛(ài),馮文炳君也是在那愛(ài)悅情形下,卻用自己一枝筆,把這境界纖細(xì)的畫出,成為創(chuàng)作了”。廢名自己也曾經(jīng)說(shuō)過(guò):“我自己的園地,是周作人先生,我自己的園地,是周作人先生的定來(lái)”。他承認(rèn)“文藝作品總要寫得interesting”,這里的“interesting”即周作人所說(shuō)的文章的“趣味”性。
廢名文章的趣味性體現(xiàn)于為文姿態(tài)的隱逸性以及獨(dú)具一格的語(yǔ)體模式。廢名的這類文章多為具有田園風(fēng)味的詩(shī)化小說(shuō),“多寫鄉(xiāng)村兒女翁媼之事,于沖淡樸訥中追求生活情趣,并不努力發(fā)掘題材的社會(huì)意義”,以表現(xiàn)“朦朧的情趣”???為滿足,不注重作品深刻的思想功效,拋開(kāi)主體社會(huì)功利性和時(shí)代主題下文藝的趨同性選擇,堅(jiān)持自我個(gè)性與生命力的凸顯。這種“趣味”在同時(shí)代的某些作家看來(lái),雖然“將使中國(guó)散文發(fā)展到較新情形中”,卻漸漸遠(yuǎn)離了“樸素的美”,而同時(shí)所謂地方性,這樣一來(lái)也就完全失去,“代替作者過(guò)去優(yōu)美文體顯示新型的只是畸形的姿態(tài)一事了”???。廢名自身并非沒(méi)有意識(shí)到同時(shí)代格調(diào)不大相稱的“趣味”文體生存的尷尬困境,他說(shuō)過(guò)這樣一段話,“近來(lái)有一二友人說(shuō),我的文章很容易知道是我的,意思是,方面不廣。我承認(rèn),但并不想改,因?yàn)閯e的東西我也能夠?qū)懀珜懙臅r(shí)候自己就沒(méi)有興趣,獨(dú)有這一類興趣非常大。”???廢名始終堅(jiān)持自己獨(dú)立的精神人格,不愿趨時(shí)附勢(shì),正體現(xiàn)了前期京派文人旗幟鮮明的自我立場(chǎng),合乎其“趣味主義”的精神內(nèi)核。周作人極為肯定這一點(diǎn),他非常認(rèn)真而誠(chéng)懇地評(píng)價(jià)道:“廢名沿著一條路前進(jìn),發(fā)展他平淡樸訥的作風(fēng),這是很可喜的”,雖然寂寞一點(diǎn),卻實(shí)在是“最確實(shí)的走法”,應(yīng)當(dāng)繼續(xù)這條道路,走到“比此刻的更是獨(dú)殊他自己的藝術(shù)之道上去”。
三
“簡(jiǎn)潔生辣”的文體風(fēng)格是廢名小說(shuō)趣味性在藝術(shù)實(shí)踐中的具體顯現(xiàn)。周作人在《中國(guó)新文學(xué)的源流》中明確指出:“胡適之、冰心和徐志摩的作品,很像公安派的,清新透明而味道不甚濃厚。好像一個(gè)水晶球樣,雖是晶瑩好看,但仔細(xì)的看多時(shí)就覺(jué)得沒(méi)有多少意思了。和竟陵派相似的是俞平伯和廢名兩人”,竟陵派以“奇僻”之風(fēng)矯公安派流麗之弊,廢俞文風(fēng)在現(xiàn)代中國(guó)文壇的崛起亦有相近的意義,“同樣用白話寫文章,他們所寫出來(lái)的,卻另是一樣,不像透明的水晶球;要看懂須費(fèi)些功夫才行”。這恰符合周作人在《<燕知草>跋》中所主張的,文章除須有“簡(jiǎn)單味”,還應(yīng)添上“澀味”一層才耐讀的趣味理論。“簡(jiǎn)潔生辣”的文體風(fēng)格主要體現(xiàn)于廢名文章的表現(xiàn)手法。廢名說(shuō)自己的文章“分明地受了中國(guó)詩(shī)詞的影響”,寫小說(shuō)“同唐人寫絕句一樣,絕句二十個(gè)字,或二十八個(gè)字,成功一首詩(shī),我的一篇小說(shuō),篇幅當(dāng)然長(zhǎng)得多,實(shí)是用寫絕句的方法寫的,不肯浪費(fèi)語(yǔ)言”,講求語(yǔ)言的簡(jiǎn)省,用極精練的文字傳達(dá)出創(chuàng)作主體的內(nèi)在思想才情,故而在廢名看來(lái),“運(yùn)用語(yǔ)言不是輕易的勞動(dòng),我當(dāng)時(shí)付的勞動(dòng)實(shí)在是頑強(qiáng)”。語(yǔ)言的簡(jiǎn)省并不意味著創(chuàng)作主體精神世界的空洞或淺薄,作者“雖因?yàn)榱呦淖郑瑫r(shí)時(shí)感到簡(jiǎn)單,也仍然見(jiàn)出作品的珠玉完全的”。這種文字的簡(jiǎn)約還反映在廢名文章里“有句與句間最長(zhǎng)的空白”,作者“用心思索每一句子的完美,而每一完美的句子便各自成為一個(gè)世界”。這種耐人尋思的“空白”并不是一種“刪削”或一種“經(jīng)濟(jì)”,而往往“是句與句間缺乏一道明顯的‘橋的結(jié)果”,是作者某種思想觀念的結(jié)晶。這樣的例句在《橋》和《莫須有先生傳》中屢見(jiàn)不鮮。如《橋》中“路上”一章,寫琴子和細(xì)竹上花紅山采摘映山紅,有一段這樣的話:“細(xì)竹喜歡做日記,這個(gè),她們自己的事情,卻決不會(huì)入她們的記錄呵。女人愛(ài)照鏡,這就表示她們何所見(jiàn)?一路之上尚非是一個(gè)妝臺(tái)之前。”作者在敘述過(guò)程中,思維從途中景色跳到細(xì)竹的日記,忽而又聯(lián)想到女人的照鏡妝臺(tái)。又如《莫須有先生傳》中“月亮已經(jīng)上來(lái)了”一節(jié),起首之言頗富哲理禪意:“山中方一日,世上幾千年?然而怎么的,吾們這個(gè)地球并沒(méi)有走動(dòng),靜悄悄的?”這里是從佛禪世界與目下所在時(shí)空的流動(dòng)與變幻著眼引發(fā)出的感悟;接著寫莫須有先生于月明之夜閑坐四棵槐樹下,很感著夜的寂寥,“立于一個(gè)人的想象里”,浮思聯(lián)翩:“我不如高山仰止望鬼見(jiàn)愁,你看,我正其瞻視,雖然望之亦不見(jiàn)什么,實(shí)有個(gè)高山惡林在,那兒深處便是一個(gè)樵夫之家住著個(gè)小白廟,白馬之白,白雪之白,夫鬼見(jiàn)愁者,西山之最高峰也,唉,誰(shuí)知道我的抱負(fù),日下花前五岳起方寸……”,這簡(jiǎn)直就是意識(shí)流的寫法,緊接下文,卻又是峰回路轉(zhuǎn),柳暗花明又一村。作者的每句話,都像是“布在溪面上的一個(gè)個(gè)跳石”,在每個(gè)跳石之間,又沒(méi)有“用木版架設(shè)的橋梁”,流水自從石間潺潺淌過(guò)。作者獨(dú)特的藝術(shù)思維從一個(gè)聯(lián)想跳到另一個(gè)聯(lián)想,從一種感覺(jué)跳到另一種感覺(jué),這種詩(shī)式的跳躍法,能夠減少作家情感表達(dá)的障礙,易于收到凝練、含蓄、耐人尋味的藝術(shù)效果。
廢名還從中外文學(xué)里“涵養(yǎng)他的趣味”。廢名說(shuō)自己早期寫短篇小說(shuō),就是“受了外國(guó)的影響”,像西方的莎士比亞,塞萬(wàn)提斯,哈代,中國(guó)的李義山,溫庭筠等,都是構(gòu)成他作品的重要養(yǎng)分,特別是中國(guó)古代溫李一派。廢名傾心于溫庭筠綺麗精工的花間詞,在他的詞里,“無(wú)論一句里的一個(gè)字,一篇里一兩句,都不是上下文相生的,都是一個(gè)幻想,上天下地,東跳西跳”,但又能夠?qū)懙梦膹淖猪槪白詈侠K墨不過(guò)”,當(dāng)推為花間之首。溫詞不用典故,因?yàn)椤霸谒慕夥诺脑?shī)里用不著典故,他可以橫豎亂寫,可以馳騁想象”,廢名自己的文章中就多有這樣的表現(xiàn)。這類文章“不沾不滯,不凝于物,不為自己所表現(xiàn)‘事或表現(xiàn)工具‘字所拘束限制”,提供給作者一個(gè)更為廣闊的藝術(shù)想象和情感表現(xiàn)空間。晚唐時(shí)期另一位大家李商隱,廢名以為“在中國(guó)文學(xué)史上,只有庾信可以同他相提并論”,這個(gè)人的詩(shī),“真是比什么人的詩(shī)還應(yīng)該令我們愛(ài)惜”;李商隱有著六朝的文采,在他的文采之中,卻“又深藏了中國(guó)詩(shī)人所缺乏的詩(shī)人的理想”;他的詩(shī)好比一盤散沙,卻又粒粒都是“珍寶”。溫詞不喜用典故,李詩(shī)則是“藉典故馳騁他的幻想”,溫李都是在詩(shī)詞中自由表現(xiàn)個(gè)人的“感覺(jué)”和“理想”,二人均以不同力度滲入了這一時(shí)期廢名的小說(shuō)創(chuàng)作,構(gòu)成作者為文所追求的趣味之旨。
參考文獻(xiàn):
[1] 周仁政.京派文學(xué)與現(xiàn)代文化[M].湖南長(zhǎng)沙:湖南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2:112。.
[2] 沈從文.論馮文炳[A].陳振國(guó).馮文炳研究資料[C].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91:198。
[3] 沈從文.論馮文炳[A].陳振國(guó).馮文炳研究資料[C].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91:199。
[4] 廢名.《竹林的故事》序[A].陳振國(guó).馮文炳研究資料[C].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91:99。
[5] 廢名.說(shuō)夢(mèng)[A].馮文炳研究資料[C].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91:105。
[6] 唐弢.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史(一)(節(jié)錄)[M]. 陳振國(guó).馮文炳研究資料.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91: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