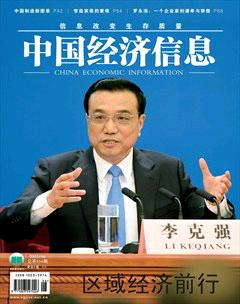降息之后……
易玨


2月28日,央行宣布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下調0.25個百分點至5.35%;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下調0.25個百分點至2.5%,同時結合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將金融機構存款利率浮動區間的上限由存款基準利率的1.2倍調整為1.3倍,千呼萬喚的降息姍姍來遲。不過,時隔2014年11月的非對稱降息僅僅3月。三個月間,兩次降息,一次降準,市場預期中國的貨幣政策正在走向寬松。
降息跟著降準
降低存款準備金率之后必然要降息,成為央行貨幣政策調控的規律之一。廈門大學宏觀經濟研究中心副教授盧盛榮在接受《中國經濟信息》記者采訪時表示,一般來說貨幣供給增加以后,反應資金的價格應該下降,但事實上,中國降準之后,社會融資成本并沒下降,如果不跟著采取降息的措施,降準就是無效的。
而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在于我國國際貿易格局的轉變。“我們過去增加投放貨幣的主要渠道是外匯占款,但2014年由于我國的國際貿易格局發生了很大變化,外匯占款增速降低,去年一整年,僅增加1340億美元。因此,通過降準來解決融資成本問題很難。”盧盛榮認為,也正是這個原因,公開市場操作、再貼息、再貸款成為過去一年中國的主要貨幣政策調控工具。
這一次降息的新特點就在于,11月22日,央行為了保護商業銀行的利益,并無意收窄商業銀行的息差,采取非對稱方式下調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和存款基準利率。
2月28日的對稱性降息側面說明了此前的非對稱性降息效果不佳。“這次將存款利息上線提高到1.3倍,收窄了銀行的息差,擠占了銀行的利潤。”盧盛榮說,表面看來,存款利率提高提升到1.3倍使得銀行融資成本上升,但這種提升是有必要的,上升有利于居民儲戶提高財產性收入。同時,貸款利率下降,相應地逐漸將拉低企業社會融資成本,貸款利率下降也能刺激消費,僅從個人住房貸款來看,減少利息可以釋放出部分消費空間。
此外,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2015年1-2月,全國發電量為8561億千瓦時,同比增長1.9%。,2015年2月CPI同比增長1.4%,我國的通縮風險在加大。“名義利率上升,主要對付通脹,名義利率不下降,導致實際利率上升,不利于經濟復蘇;此外,整個世界有20多個國家加入了降息潮。降息可能帶來人民幣貶值,不利于人民幣國際化,人民幣兌美元在貶值,但對日元、歐元、盧布等都在升值,人民幣的有效匯率在升值,在目前的國際貿易形勢下,不利于出口。”
降息對拉動出口、投資、消費需求都有效果。在盧盛榮看來,2015年,僅僅這一次降息對穩增長是不夠的,下一步還將繼續既降準又降息。“因為貨幣政策的傳導時滯,必須要提前,預調才能使經濟波動更小,更平穩,在這方面,就要求央行的貨幣政策具有前瞻性,對政策進行預調微調。”
金融改革也需同步
這樣的貨幣政策調控節奏也有別于其他國家。就中國而言,在貨幣政策調控空間打開之后,往往需要進行連續動作才能發生作用,也就是常說的貨幣政策梗阻問題。盧盛榮認為,這個問題的本質在于數量與價格的傳導不暢,而正是金融體制的不完善才帶來梗阻問題。
盧盛榮指出,目前中國金融體系主要載體是國有大中型商業銀行。它們存在明顯的信貸偏向,即偏好大型企業、國有企業。對于銀行來說,這些企業沒有信貸資料的收集成本,易于辨識風險,而民企、中小企業卻很難辨別。這一方面是由于小企業的信用、財務等各方面數據不完善、一方面則是銀行不愿意深入調研,付出成本。
“對發展前景好、有技術含量、在管理上不斷完善的中小企業應該更加關注。”這方面國有銀行執行得并不好,以至于需要政府用行政上的定向貨幣政策去解決中小企業融資問題,但從實際效果來看很有限。
盧盛榮指出,要完善金融體系,就需要大力發展民營銀行。中國的社會資金不少,有100多萬億元的M2,只是存在結構性錯配問題。“現在很多城市都有城商行,表面看來是市場化的股份制銀行,深究股權結構,發現地方財政占比51%,原則上還是國有絕對性控股,他們也都往國企貸款。”盧盛榮認為,民營銀行作為市場化主體,有動力去服務更多的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
此外,國家鼓勵大眾創業、大眾創新,這不是一句口號,在國外創業創新都有配套的資金跟進,根據不同的風險偏好,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
“財稅體制改革固然重要,但金融體系也需要同步改革。”盧盛榮說。
對于時下互聯網金融,盧盛榮表示,互聯網金融今年是拐點,P2P在監管沒跟上的情況下,遇上經濟形勢下滑,風險就會被放大。在目前情況下,傳統金融的運轉依然好于互聯網金融。互聯網金融是金融發展的趨勢,但應當謹慎推進。
存準制度需調整
值得注意的是,我國的存款準備金率大型金融機構為20%,中小金融機構為16.5%,是全世界最高比例。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存款準備金率設在5%,有些是3%,有的發達國家1%-2%,甚至0%。
存款準備金制度的初衷是防止銀行出現擠兌風險而留存部分備用金。但今年年底存款保險制度推出以后,存款準備金率設置得那么高就沒有意義了,存款保險制度覆蓋了準備金制度的初衷。
“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控效果的確很直接,但對經濟造成的波動大,容易造成負面影響。我國的調控需要從數量型工具轉向價格型工具,比如利率。”盧盛榮說,這次存款基準利率上浮幅度調到1.3倍也是為利率市場化作準備,這與匯率市場化逐步放開的節奏類似從萬分之三,到萬分之五,再到百分之一,擴大到百分之二。
香港金融管理局前總裁任志剛也公開表示,存款準備金制度對銀行體系的運行效率有著不可忽視的負面影響。中國內地的存款準備金率目前已達20%左右,而央行付出的存款準備金利率只有1.62%,這意味著商業銀行都被迫持有一筆回報率非常低的巨額資產。存款準備金制度退出后,釋放放于央行20余萬億元的存款準備金,將使流動性更加充裕,可更有效地資源配置。endprint